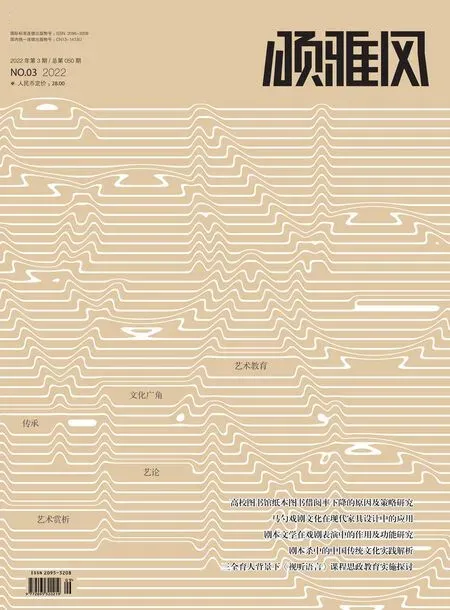全濁聲母上聲字的演變分析
◎任杰
一、全濁聲母上聲字的演變類型
據史料分析與當代學者研究表明,全濁聲母上聲字在歷史發展中為適應語音變化與社會交際不斷演變并融合發展。在演變的過程中,大量全濁聲母上聲字由于其聲調的特殊性導致它逐步趨向去聲;但依然有少量全濁上聲字依舊保持上聲,并沒有歸入去聲。這些保留下來的原全濁上聲字并非是偶然,而是有一定的內在原因。本文以研究“濁上變去”為主,輔之“濁音清化”加以說明“濁上變去”與“濁上不變”這兩類主要的演變類型。
二、“濁上變去”產生的原因
(一)中古上去聲的聲調
悉曇家安然在《悉曇藏》中對上聲的聲調有所記錄:“我日本國元傳二音……上聲直昂,有輕無重;去聲稍引,無輕無重;……上中重音與去不分。金則聲勢低昂與表不殊,始重終輕,呼之為異。”其中的“元傳二音”指的是流傳于日本的兩種漢字讀音系統,一種是表信公所傳的“漢音”,另一種則是朝鮮學者金禮信所傳的“吳音”。下面我們將以這兩種語音系統為主要研究對象對中古上去聲的調值做一個分析。
1.上聲的聲調
表信公的漢音中對上聲的描述為 “上聲直昂”指的就是上聲為“直昂”調,直為平,昂為高,直昂作為聲調的形容詞時指的就是高平調,也就是說上聲是高平調。
但金禮信所傳的“吳音”中對上聲的表述是:“始重終輕,呼之有異。”也就是說金禮信認為上聲是有一個升調的過程,這與表信公所認為的上聲是一個持續高昂高平調是有所差別的,那么,上聲究竟是否有升調這一過程呢?
曾在唐朝長安留學的日本空海法師在公元804年所著的《文鏡秘府論》中對上聲有這樣的記載:“上聲厲而舉。”唐代的《元和韻譜》中關于上聲的記載與其高度一致,所以空海法師的記載應該是比較可信的。“上聲厲而舉。”其中厲為高揚,舉為上托,厲而舉應該是一個上升為高調的過程,這與金禮信的意思一致。但升調與高平調的差異還是很明顯的,表信公與金禮信所記載的上聲聲調按照道理來說應該是不會相混的,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高平調與升調相混的情況呢?我們不妨做出一個大膽的猜測:上聲的聲調是高平調與升調的結合體。
這個猜測也在敦煌出土的藏漢對音佛經中得到了證實。在藏漢對譯中漢語上聲字往往會用兩個元音對譯,也就是說一個上聲應該是由兩個聲調組成的,并且這兩個聲調應該是高低不同并且遵循由低到高的順序,這也就解釋了金禮信所傳“吳音”與《文鏡秘府論》以及《元和韻譜》中對于上聲的升調記載。與此同時,為滿足表信公的“直昂”,我們可以推測出這兩個高低不同的聲調應該是兩個平調。換言之,上聲是由兩個高低不同的平調由低到高組成的一個組合型聲調,這樣既符合前者的“高平調論”,也符合后者的“升調論”。
2.去聲的聲調
《悉曇藏》中對于去聲的記載為:“去聲稍引。”引為延長之意,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出去聲其實是一個長調,這一點與現代漢語中去聲為短調是相沖突的,但是在《文鏡秘府論》中對去聲的記載:“去聲清而遠。”同樣也可以說明去聲并非是短調,而確確實實是一個長調。并且根據我們的音理學常識可知,如果中古去聲也同現代漢語的去聲一樣是個降調,而它同時又是一個長調,那么這兩者之間就是自相矛盾的,降調無法滿足我們對音節延長的要求,只有升調或平調才能有“清而遠”的長調效果。根據日本真言宗里的“四座講式”與“祭文”的佛教歌曲中去聲唱上升調的記載,我們可以推測出去聲是一個長調的升調,這與我們現代漢語中對去聲的定義是截然相反的。
(二)全濁聲母上聲字與去聲字聲調接近的原因
1.清聲母音節的發音方式
根據音理學知識我們可以得知,我們在發清聲母音節的時候聲門處于松弛狀態,同時聲帶舒張;在除阻完成的同時舌位移至適當的元音發音位置時,聲門才閉合、緊張,此時聲帶振動,發出可聽見的聲音。在整個過程中語音易保持一定的強度與較高的振動頻率。
2.濁聲母音節的發音方式
與清聲母音節發音方式不同的是,發濁音時發音器官各部位都很緊張,并且清音是在除阻完成時舌位移動后聲門才閉合;而發濁音時,在成阻階段聲門就已經閉合,聲帶就已經振動了;等到了除阻階段,舌位才移到適當位置發出可聽見的聲音,此時聲帶振動已經逐漸減弱了,并且難以維持均衡音勢和較高的振動頻率,這就導致了聲音變低。
3.全濁聲母上聲字脫離上聲
上述已經提及由于濁聲母特有的發音方式導致其聲音一開始就處于一個低沉的狀態,也就導致了它無法跟清上聲一樣為高調的狀態;與此同時全濁上聲又保留了它作為上聲的本質特點,即盡量無限趨向于高調,又因為其平調的特質,所以這個過程是緩慢上升的,因此也就導致了發全濁上聲時有類似于升調的行為,這就與同為上升調的去聲非常接近。也就導致了全濁聲母上聲字逐步脫離了上聲而無限接近于去聲,即我們所說的“濁上變去”。
三、“濁上不變”出現的原因
(一)“濁音清化”的出現
根據上述對清濁音發音方式的表述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清音長而強,濁音短而弱。因此清音往往更加響亮,易于被對方聽見。為了滿足社會交際的需要,人們會潛意識地偏向于清音的發音方式,即在潛移默化中刻意地加強氣流量與氣流速度,因此濁音會逐漸向清音過渡。語音自身的屬性與社會交際的需要促使濁音清化現象的產生。
(二)“濁音清化”與“濁上變去”發生的時間
1.“濁音清化”的始末時間
“濁音清化”與“濁上變去”的始末時間節點眾說紛紜。就“濁音清化”的時間而言,多數學者認為其開始于唐朝中晚期,如《悉曇藏》中表信公將漢音分為輕重兩類,此間的輕重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清濁,它對上聲的表述是“有輕無重”,這里我們可以理解為上聲有清無濁,也就是說,在安然著《悉曇藏》的年代已經發生了濁音清化,以此推出唐朝中晚期已經出現濁音清化的現象;但周長楫在《濁音清化溯源及相關問題》中認為早在秦漢或是更早的時期就已經發生了“濁音清化”。各家論述都依附于一定的史料依據,關于“濁音清化”的起始時間目前來說仍值得商榷。
根據李新魁先生提出的關于濁音清化“以平聲始,以去聲終”的推斷,我們可以判斷出濁音清化的結束時間應該是去聲的濁音完全消失之后,這個時間點應該是元末北宋初期。
2.“濁上變去”的始末時間
安然在唐晚期所著的《悉曇藏》中提道:“上中重聲與去不分。”其中“重”即為“濁”,由此可看出唐晚期已經出現了“濁上變去”現象,由于暫時找不到早于唐晚期之前的關于“濁上變去”的證明材料,筆者暫時將“濁上變去”起始時間定為唐晚期。
賈善翔在為《南華真經》中給全濁上聲字注音時,將《廣韻》中的全濁上聲字與全濁去聲字看成了同音字,由此可以推斷出北宋時期“濁上變去”的現象已經發生,這進一步佐證了“濁上變去”起碼開始于唐晚期。根據周德清在《中原音韻》中對有關“濁上變去”的記錄能看出“濁上變去”在元代已經結束。
(三)“濁音清化”與“濁上變去”發展的先后順序
根據上述材料論證,我們已經能夠對“濁音清化”與“濁上變去”的始末時間有一個大致的判斷,下面筆者將根據始末范圍的劃分來闡述“濁上不變”的原因。現今學者對“濁音清化”與“濁上變去”產生的先后順序依然持懷疑與不確定的態度,僅根據目前能參考的史料與前輩學者的研究筆者并不能給出確切的先后順序,因此,筆者將根據現有的判斷做出以下兩種假設情況。
1.假設一——“濁音清化”比“濁上變去”出現的時間早
持這一觀點的學者以周長楫為代表,根據他的推測,我們暫且將“濁音清化”出現的時間定為秦漢前的某一時間點,假設此時間點為A,所以“濁音清化”的發展時期即為A——元末;同時,“濁上變去”的發展時期即為唐晚期——元代。因為元末與元初時間相隔不遠,為方便推理,可姑且將元初與元末模糊為元,因此,“濁音清化”的發展時期為A——元(A為秦漢前的某一時間節點);“濁上變去”的發展時間為唐晚期——元。(以上所有出現的時間點或朝代通通按照數學上的時間點,不看做可延長的歷史時期)下面筆者將根據上述幾個重要的時間點進行分類討論。
(1)A——唐晚期
濁音清化的發展情況:假設全濁聲母上聲字在變化前共有X個,在這一時間段中變為清音的有Y個,因此全濁聲母上聲字在唐晚期后的剩余量為X-Y個。同時,這一時期不發生“濁上變去”。(上述未知數代表的都不是明確的全濁聲母上聲字的個數,僅僅只是作為一種數學手段進行的模糊化數字處理,下面出現的未知數也與之同理。)
(2)唐晚期——元
濁音清化的發展情況:由上述可知全濁聲母上聲字到唐晚期這一節點剩余X-Y個,假設這一時期變為清聲母的有Z個,則理論上元后全濁聲母上聲字為X-Y-Z個。

濁上變去的發展情況:假設這一時期全濁聲母上聲字變為去聲字的數量為K,除去上述變為清聲母的上聲字,在理論上可以認為“濁上不變”的數量為X-Y-Z-K個。
2.假設二——“濁音清化”比“濁上變去”出現的時間晚
持這一觀點的以夏俐萍、李琴等學者為代表。根據他們的推測,可將“濁音清化”出現的時間定于晚于唐晚期的某一時間節點(這里的唐晚期非真正意義上的歷史時期,僅僅代表“濁上變去”出現的唐晚期中某一特定時間節點),筆者將這一時間節點設為B。因此,“濁音清化”的發展時期則為B——元;“濁上變去”的發展時期依然為唐晚期——元。下面依舊進行分類討論。
(1)唐晚期——B
濁上變去的發展情況:假設全濁聲母上聲字在唐晚期前為X,在唐晚期——B這一時間段變為去聲字的數量為Y,則B后全濁聲母上聲字的剩余量為X-Y。這一時期未出現濁音清化。
(2)B——元
濁音清化的變化情況:由上述分析可知,B后全濁聲母上聲字為X-Y,假設這一時期全濁聲母上聲字變為清聲母的數量為Z,則全濁聲母上聲字剩余量為X-Y-Z。
濁上變去的變化情況:假設這一時期全濁聲母上聲字變為去聲字的數量為K,除去上述“濁音清化”的數量,在理論上可認為“濁上不變”的數量為X-YZ-K個。
(3)對比分析
將上述兩個假設情況的結論進行對比分析可發現盡管未知數代表的時間段有所差異,但最終所得出的“濁上不變”的情況是一致的,即都剩下X-Y-Z-K個,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濁音清化”與“濁上變去”出現的先后順序對“濁上不變”情況的影響并不大。根據上述的兩個假設分析,我們可發現全濁上聲字X在沒有濁音清化的干擾下演變的最終結果應該是X-Y-Z,這個結果與理論上的推算結果即X-Y-Z-K的差異就在與它多減去了一個K量。這個K值即變為清聲母的上聲字,因此“濁上不變”現象的出現其實是全濁聲母上聲字在演變的過程中受到了濁音清化的影響。王士元的詞匯擴散理論即“全濁聲母是濁上變去的前提條件。”也側面證實了這一點,換言之,若全濁聲母上聲字失去了全濁的前提,即濁音清化,那么濁上變去就不能發生,也就導致了濁上不變現象的出現。
(四)“濁音清化”導致“濁上不變”的音理學原因
根據上述所提及的音理學知識,我們可以知道由于全濁聲母自身的音理屬性,濁音低沉無法發出高調,且無法維持均衡音勢,因此全濁上聲字無法發出與其他上聲字一樣的高平調,這樣就會導致它轉變為去聲。但是當全濁聲母轉為清聲母后,原本無法發出高平調的全濁聲母上聲字就能轉變為可發生高平調的清聲母上聲字了,所以目前仍保留上聲的現清聲母上聲字有一部分就是由古全濁聲母上聲字轉化而來的,他們保留了上聲的本質屬性,也就是相對于“濁上變去”的“濁上不變”。
四、結語
綜上所述,全濁聲母上聲字的演變過程是復雜且漫長的。本文從“濁上變去”發生的原因以及其受“濁音清化”的影響使得部分被清化的全濁聲母上聲字未演變為去聲,而是保留了其上聲的聲調的史實完整地說明了全濁聲母上聲字發展演變的全過程以及演變的內外在原因。對于全濁聲母上聲字演變機制的探討對我國語音學中語流音變的進一步研究分析有非常顯著的作用,為現代語音的形成與發展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