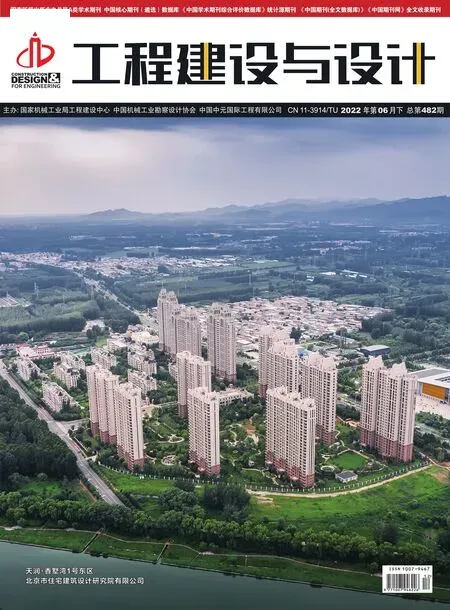浦江流韻,蘭臺新曲
——從上海檔案館新館論當代檔案館設計
黨育
(上海都市建筑設計有限公司,上海 200071)
1 引言
檔案館是集中保管國家和社會重要檔案的基地,是記錄社會發展和存儲歷史文化記憶的重要場所。我國漢朝將國家重要檔案藏于蘭臺閣,并由御史中丞掌之,故檔案館又稱“蘭臺”。
檔案館面向社會開放,提供信息資源服務,其作為涉密單位一直給人以一定的神秘感。如今,我國已經邁入以5G、物聯網和數字媒體為導向的全新時代,在當前社會主義建設新階段,作為當代城市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組成,符合時代要求的高標準檔案館,對提升城市形象和公共服務水準,以及科學合理利用檔案資源具有重要意義。
筆者有幸作為主創建筑師參與了上海市檔案館新館國際設計競賽,雖終獲第二名,但能以一定深度參與檔案館題材的創作,仍不失為一次難能可貴的機會,也加深了對新時期檔案館規劃設計的理解。
2 項目概況
上海市檔案館新館定位為上海浦東新區的檔案中心,兼具檔案安全保管基地、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檔案利用服務中心、政府信息公開查閱中心、電子文件備份中心的“五位一體”功能的現代化公共檔案館。其作為重要文化設施,應與上海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城市建設相適應,并具有上海特色,時代特征,充分滿足不斷進步的社會公共文化服務發展需求。
新館位于上海浦東花木地區,緊貼內環線,距離陸家嘴和花木城市副中心均在2 km 以內,交通便利,區位優勢明顯,服務投射力強。
3 設計理念
3.1 指導思想
美國建筑師F·L·賴特①弗蘭克·勞埃德·賴特〔美〕(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建筑師,著名建筑學派“田園學派”(Prairie School)的代表人物,工藝美術運動(The Arts&Crafts Movement)美國派主要代表人物,美國藝術文學院成員。指出:“有機建筑是自然的建筑。特定自然環境形成特定的、自然的建筑,建筑是環境的一部分,同時使環境增色。”即建筑是有生命個體,和自然萬物一樣會發展進化,并對周邊環境做出反饋。先適應環境,然后自然生長,體現出建筑與環境共生的設計價值觀。
秉承有機建筑體系,作為城市文化綜合體,檔案館應注重建筑與周邊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城市環境和人文環境)的互動,處理好建筑與環境的關系,本著“生于斯、長于斯”的自然主義情懷,可持續發展理念,打造契合環境,融入城市的文化地標[1]。
3.2 設計立意
為建立完整的建筑敘事,將新館稱作“浦江新蘭臺”(見圖1),充分顯示出其地域和建筑特點。

圖1 項目鳥瞰圖
由于新館是信息的寶庫,設計團隊建立“城市記憶容器”這一設計模型,希望利用混凝土、鋼材、玻璃構建檔案館的厚重底蘊,塑造有特色、有內涵的建筑空間。具備城市氣質,飽含時代精神,代表城市文化發展水準的檔案館建筑。
檔案存儲和查閱服務是檔案館的立館之本。隨著時代的發展,如何通過設計與時俱進是設計的最重要關切。筆者及其團隊認為:新館最重要的特征是其“開放性”,以開放姿態為大眾服務;而“場所精神”是建筑與環境對話的介質,是實現人與建筑互動的基礎;此外,“海派文化”作為核心設計要素,是建筑的文脈所在;而“綠色設計”作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符合當代建筑設計要求。
4 總體規劃
本項目規劃原則為“規劃應適應其環境”——開放的城市邊界,模糊的建筑界面,簡潔的規劃布局,高效的場地組織,便捷的交通流線以及遵循生態設計原則的景觀規劃[2]。
4.1 場地設計
地塊北鄰龍匯路(見圖1)設人行主廣場;西接培花路設車行口;東鄰白楊路設消防應急口;南鄰檔案館路設人行次廣場。其中,人行主入口面北,正對主題廣場,滿足建筑形象展示和訪客集散的要求;次入口朝南,通過景觀棧橋跨越下沉庭院與主入口相連,形成南北貫通的城市開放界面。
項目建設量較大,而基地略顯局促。為迎合檔案館運作特點,滿足眾多服務及業務用房設置要求,同時保持功能區間的緊密聯系,嘗試以“絕對開放,相對封閉”的理念規劃場地,以“垂直功能支撐體”的理念塑造建筑。
首先,沿建筑主體周邊設置階梯狀下沉景觀庭院,以組織服務于檔案館內部的垂直動線,通過目的地區分,回避內外人流交叉,形成“相對的封閉”;其次,規劃貫穿南北的景觀通廊,橫跨下沉庭院,聯通南北城市景觀帶,引入城市人流和風景,形成“絕對的開放”。同時,以南北景觀通廊這一天然分期建設界限,自北向南布置一、二期建筑,構建一個空間均衡,形態穩定、邏輯清晰的檔案館綜合體[3]。
4.2 豎向組織
本案力求擺脫傳統檔案館以庫房為核心的集中式布局,借鑒路易斯·康②路易斯·康〔美〕(LouisI.Kahn,1901—1974)1924 年畢業于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1947 年個人開業。20 世紀50 年代起,執教于賓州大學和耶魯大學的建筑學碩士研究班。1974 年卒于從達卡返回美國的途中。縱觀整個現代建筑發展演變的歷程,路易斯·康是一位關鍵人物,他以極為出色的建筑理論與實踐對后現代主義的出現提供了重要的啟迪思想,并且對現代建筑的推進與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都起到了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的“服務—被服務”空間理論,以及“垂直功能支撐體”的相關觀點,將主要功能分區模塊化、立體化,同時借助建筑內部巨型桁架豎向支撐體系,將模塊根據需求復合疊加,并留有擴展的余地,既滿足當下要求,又可展望未來。
新館首層架空,作為集散廣場,留給城市,完全開放。公共服務用房設于北區主樓3~5 層,建筑主體四角豎向結構支撐體內設有豎向交通核,通過扶梯或直梯可直達各個公共區域。報告廳及公共休息區等服務配套設置在地下1 層,借助下沉庭院實現天然采光通風,并引入景觀綠化。
南區塔樓設有檔案中央庫區以及各類業務用房,配有專用電梯供工作人員和內部物流使用。外部貨運車輛亦可直接進入檔案接收區,通過電梯將貨物運送至各個部門或直接入庫。此外,主樓和庫房通過空中連廊南北相連,便于南北區域互動管理[4]。
5 建筑設計
5.1 設計理念
客觀、準確、完整的檔案記錄源于社會發展的積淀,讓人們能夠探尋過去,展望未來。在設計過程中,嘗試以“記憶的容器,歷史的重器,文脈的蓄器,文化的播器”定義新館,賦予其內涵、性格和意境,力求建筑功能與形態的有機結合,體現功能性和藝術性的有機統一。
檔案館主體建筑借鑒國寶文物“后母戊鼎”的形態比例(見圖2),寓意“藏歷于鼎”,以契合其“國之重器”的定位。一期建筑主體9 層,四足(交通核及結構支撐體)落地,下部架空留出城市廣場,以“鼎立”之態向上發展,體態雄渾。新館建筑內部空間層次豐富,除架空層和下沉庭院,還設有挑高的采光生態中庭,中庭上方懸置象征“蘭臺”的藝術裝置——“物華天寶”,象征檔案館“歷史書記員”的神圣職責。整組建筑中軸對稱,體量雄渾,簡潔大氣,莊重典雅,細節飽滿,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

圖2 項目街角透視效果圖
5.2 設計主題
本案希望凸顯以下4 個主題。
5.2.1 “城市地標,文化重器”——新館設計與符號象征主義
歷史檔案歷來被稱為“國器”,檔案文化建立在“器”的基礎之上,其本身也是一個文化容器,
器的概念,源于中國傳統文化對于空間的理解,如《道德經》中“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所述,一種建立在古樸哲學基礎上的對于空間的理解。抽象的“器”字便成為設計的原點,設計者以“器”為基本形態的象征和隱喻,塑造建筑作為“容器”的形態,體現“器”的存在感和文化寓意。
建筑外墻作為沿街展示面,設有仿“古書竹簡”造型的干掛水泥纖維板(UHPC)板排列組成的鏤空表皮(見圖2),后襯LOW-E 玻璃和金屬百葉所組成的雙層呼吸式幕墻,在建筑體量“鼎”的加持下,形成虛實相間,細節豐富的界面。既有“史載長卷,千古流傳”的寓意,又能起到遮陽、通風、蓄熱的生態效應。
而中庭空間的核心藝術裝置“蘭臺”,作為多媒體檔案放映廳,同時作為“物華天寶”的容器主題藝術裝置,從傳統裝置“宮燈”上汲取靈感,通過構建半透的金屬編織物的婆娑垂幕表皮,輔以周邊U 形玻璃幕墻帶來透光不透視的朦朧,烘托出“蘭臺”的輕盈懸浮,給人以視覺上的震撼。
5.2.2 “扎根海派文化,傳承浦江文脈”——新館設計與地域建筑文化傳承
空間是建筑的精神,文化是設計的魂魄。
歷史賦予新館記錄和傳播現代海派文化的職責,推動老城鄉與新城鎮的文脈交融。“海納百川,兼容并蓄”是海派文化的精神內核,并一直在尋求融合和發展。海派建筑根源江浙地區傳統合院,同時又具備西方建筑符號,可謂中西合璧。設計團隊向海派傳統民居重要典型——石庫門常見的“天井院落”空間致敬,打造采光中庭(見圖3),以增強室內空間層次,中庭周邊外墻還鑲嵌雕刻肌理源自后母戊鼎的紋樣,同時在中庭回廊結合休息空間設有主題雕塑。結合“蘭臺”這一中庭核心藝術裝置,加強了建筑文脈的敘事表達,充分展現出中庭這一極具凝聚力的建筑空間。

圖3 項目剖面及綠色建筑技術體系示意
5.2.3 “絕對開放,相對管控”——檔案館“開放”環境的營造
設計團隊力求將過去檔案館的封閉式管理引向開放模式——設計中館設有大量專題展廳和教室,以舉辦主題展覽,推廣檔案文化;在滿足基本服務配套的基礎上,配置文獻查詢中心,學術研討室和公共文獻中心,以“開放”的姿態豐富服務功能,為大眾提供集閱卷研究、展覽教育、信息共享于一體的服務,與民眾積極互動。同時,以檔案的保密程度作為功能分區和交通組織的設計依據,進而確保檔案保密體系的完整,實現“絕對開放,相對管控”[5]。
5.2.4 “智能低碳,綠色先鋒”——檔案館建筑的可持續發展
綠色設計是當代建筑設計的重要內容和特征。在新館設計中,積極推進以被動技術為主,主動技術為輔的綠色建筑設計策略(見圖3),整合了熱壓自然通風,天然采光,AI 電控遮陽,多層幕墻,薄膜光伏發電,中水處理,雨水綜合利用綜合節能措施。同時,基于智能化管理的全自動存取檔案系統的運用,可以節約能源、人力、時間成本,提高了建筑運營效益,實現高效低碳運營模式。
6 總結與啟發
“浦江流韻,蘭臺新曲”是對新時期檔案館設計的一次淺顯探索,代表了當代檔案館建筑“開放化、多元化、人性化、可持續”的發展方向。作為“歷史文化檔案保管者、管理者和傳播者”,新時期檔案館設計需要全新的定位和理念,在滿足基本設計要求前提下,需注重歷史文脈在設計敘事中的價值、建筑與環境的融合、文化符號與設計細節的共鳴;注重持續發展和綠色設計策略的運用;注重檔案館作為公共文化資源與民眾積極互動,滿足大眾通過檔案服務,直面往昔與當下,探尋歷史與記憶,實現當代“蘭臺”的真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