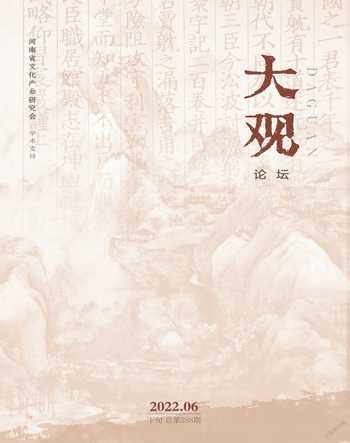福寶高腔山歌音樂藝術特征分析
馮穎
摘 要:福寶高腔山歌是在巴蜀文化、夜郎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中形成的一種獨具原始特色的音樂藝術。這種藝術形式節(jié)奏鮮明、曲牌多樣、內容豐富、唱腔高亢、富有感染力,集中體現了當地音樂文化的歷史特征和藝術特色。基于此,從福寶高腔山歌的發(fā)展歷史入手,結合山歌內容分析其旋律節(jié)奏、歌詞和襯詞、演唱方式和技巧等方面的藝術特征,希望推動其進一步發(fā)展。
關鍵詞:福寶;高腔山歌;音樂風格;藝術特征
注:本文系2020年度內江師范學院校級科研項目“福寶高腔山歌口述實錄與研究”(2020YB04)研究成果。
福寶位于四川省合江縣東南,地處川南黔北渝西結合部,北連合江縣城,東鄰重慶江津,西南接貴州習水,原始森林的自然風光、夜郎古道留下的歷史遺跡讓這里的自然和人文融為一體。福寶高腔山歌是在福寶產生、流傳并在川南黔北渝西地區(qū)廣泛傳播的一種古老而獨特的原生態(tài)山歌。在漫長的發(fā)展歷史中,福寶依托獨特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并受巴蜀文化、夜郎文化與中原文化的影響,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山地文化,進而孕育出了充滿原始性的高腔山歌。福寶高腔山歌在傳播過程中展現了自然與人文的融合,兼具山之聲、水之音、物之韻、人之靈,因此,在音樂藝術方面極具研究價值。本文將對福寶高腔山歌從發(fā)展概況、文化精神、審美價值等方面進行系統(tǒng)的研究,進一步結合福寶高腔山歌的現實情況,呼吁社會各界對其進行更多的關注,弘揚地區(qū)音樂文化。同時,探索根據社會習俗與生活環(huán)境相適應而共生共演的動態(tài)歷史過程,以及對高腔山歌未來發(fā)展的建議等,探尋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新出路,為后續(xù)研究積累大量資料。
一、福寶高腔山歌概述
福寶地處原始森林,山高谷深,人煙稀少,山地居民之間的語言交流需要穿過重重的自然障礙,而這種獨特的交流方式就成為高腔山歌產生的源頭。當然,高腔山歌作為一種音樂藝術,其在形成與發(fā)展的過程中必然少不了人文情感的參與,例如從福寶高村東漢崖墓群中“農耕圖”巖畫中可以看到當地先民在農耕、漁獵、伐木等勞動的過程中已經開始唱山歌,而這種類似勞動號子的音樂形式,自然也表達了先民在勞動中的復雜情感,如對自然的敬畏,對辛苦勞動的感嘆,對美好生活的寄托。正是在這樣豐富的情感中,福寶高腔山歌逐漸發(fā)育,并形成了一種獨具原始特色的音樂形式。
通過歷史溯源,福寶高腔山歌的起源大約在漢代。隨著唐宋時期的發(fā)展,蜀地、黔地與中原的交流不斷增多,高腔山歌也與中原音樂出現了融合,并開始從福寶地區(qū)傳出去。例如山地居民通過唱高腔山歌,表達對山水的熱愛、對愛人的渴慕、對神明的敬畏等,這種極具穿透力的聲音在山谷中回響,與自然中的聲音融為一體,奏響了和諧的樂章;再如馬幫往來各地,行人為緩解旅途寂寞會用家鄉(xiāng)的高腔山歌自娛自樂,而山歌唱到哪里,便在哪里停留,這也讓山歌走出了福寶,向川南、黔北、渝西等地傳播。
在漫長的發(fā)展歷史中,福寶高腔山歌留下了豐富的遺產,例如《谷王腔》《幺姑腔》《嗩吶腔》《斑鳩腔》等,這些原汁原味的作品豐富了當地的音樂文化,展現了當地人的精神面貌。然而,隨著現代社會的發(fā)展,福寶的原始生活狀態(tài)逐漸被打破,高腔山歌的傳承和發(fā)展也走向了沒落,許多珍貴的作品遺失,能夠演唱高腔山歌的人也逐漸減少。面對這種情況,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時代背景下,加強對福寶高腔山歌的研究成為一種必然。
在福寶高腔山歌口述實錄方面,筆者通過文化館和當地有關部門的幾經詢問幫助,已找到福寶高腔山歌的傳承人鄧敬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筆者只能通過網絡聯(lián)系傳承人。從言語交流中,筆者能感覺到鄧敬祿是個非常和藹可親的老人,他對我們的問題也都很有耐心,并且熱情地為我們邊唱歌邊講解。
鄧敬祿說:“福寶的特色就是高腔山歌,山歌都是原生態(tài)的,教學也都是耳聽心記,口口相傳,所以沒有譜子。當地高腔山歌我已經是第三代了,第一代是叔公,第二代是大哥,第三代是我。當年每當我讀書回來就參加他們的勞動,在田間邊插秧邊跟他們學唱山歌,傍晚休息時在院子里繼續(xù)跟著唱,他們唱,我來學。后來參加了合江縣的鄉(xiāng)鎮(zhèn)比賽取得了第一名,但是當繼續(xù)參加瀘州市里的比賽彩排時負責人說我的歌詞短了,所以就臨時加了一些,真正比賽時說歌詞又長了點,所以取得了第二名。”
隨后,鄧敬祿先唱了歌名為《谷王腔》的山歌,介紹說這是農村種莊稼時演唱的腔調。然后又為我們唱了《斑鳩腔》,并且告訴我們歌曲中多次出現的“嗚嗚”,是指斑鳩飛行中拍著翅膀由近及遠的聲音。
二、福寶高腔山歌音樂藝術特征
通過田野調查和翻閱資料等方法,筆者發(fā)現了福寶高腔山歌的一些音樂藝術特征。
(一)福寶高腔山歌的旋律與節(jié)奏特征
旋律和節(jié)奏是音樂作品塑造聽覺形象的核心要素。福寶高腔山歌產生于原始的自然環(huán)境,其中包含著山地居民對自然聲音的模仿,同時受到巴蜀、黔北等地文化的影響,其在旋律上也更加柔和,偏向于抒情。因此,整個山歌的曲調旋律優(yōu)美、節(jié)奏舒緩,流暢自然且富有意境。這些特點在具體的曲牌中可以得到直觀的驗證。其中《谷王腔》在演唱中通常采取一領眾和的方式,前面兩句是角調式,后面兩樂句轉到了徵調上,這種一呼百應的節(jié)奏方式,能夠讓旋律從舒緩到高亢,急轉直上的同時保持旋律優(yōu)美,并且十分具有感染力。《拜腔》通常在賽歌開場中演唱,以表示對手之間的相互尊重和禮讓。這一曲牌主要是徵調式,音域在五度內,旋律通常選擇四二拍,音程是上、下行五度,這讓整個音樂呈現出反復吟唱的特點,內容自然舒緩,表現出了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幺姑腔》是一首情歌,歌曲借花喻人,展現青年男女之間纏綿悱惻的愛情。樂曲中包含徵調式,在起始之后,領腔和幫腔在唱完襯詞調后轉為商調式,并且融合了倚音、下滑音,形成假音效果;音域在八度內,旋律連貫優(yōu)美,音程有純一度、大二度、小三度、大三度,其中男聲十分具有感染力,且具有戲劇性變化,能夠展現出男女情感的濃烈。這種感情在表達過程中必然是舒緩的,而通過譜例的分析,我們也可以看到有的樂段采取商調式四二拍,在音程上有純一度、大二度、大三度、小三度,最大的是十度、十一度,音域在十五度內,演唱難度較大,可以說是循序漸進,情感和聲音的配合十分密切。《斑鳩腔》《老鴰腔》則是人們在觀察、欣賞斑鳩、老鴰的過程中所獲得的靈感,并且形成的曲牌,這是福寶高腔山歌原始特征的重要體現。其中《斑鳩腔》是羽調式,優(yōu)美平穩(wěn)的四一拍中加入了斑鳩翅膀扇動的聲音,整個旋律十分舒緩;《老鴰腔》則是徵調式,其旋律節(jié)奏的特征與《斑鳩腔》類似。《打鑼腔》是人們模擬打鑼的聲音創(chuàng)作的曲牌,曲牌的內容主要表現春來花開的熱鬧景象。曲牌為徵調式,風格歡快喜慶,節(jié)奏富于變化,旋律跳動大,音程有純一度、大二度、小三度、純四度、純八度,節(jié)奏十分密集,展現出敲鑼打鼓的熱鬧氛圍。
福寶高腔山歌中的曲牌還有很多,這些曲牌在節(jié)奏旋律上各有特色,從某種程度上展現出了山歌舒緩的節(jié)奏和優(yōu)美的旋律,而這樣的音樂特征也正是人們喜歡高腔山歌的原因。
(二)福寶高腔山歌的歌詞和襯詞特征
古語云“歌以詠志”,歌曲是人表達情感的一種獨特藝術,歌詞則是訴說情感的方式。福寶高腔山歌的歌詞是在青山綠水間形成的,它表現了質樸的山地居民對自然的敬畏和熱愛,也描繪了一代代山地居民在自然的滋養(yǎng)下形成的豐富感情。通過對現有福寶高腔山歌歌詞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有訴說愛情的、有感嘆勞動的、有慶賀節(jié)日的,每一類歌詞展現的藝術特征豐富多樣,各有區(qū)別。例如《薅秧紅》是一首描寫男女之間相互關愛的歌曲,歌詞唱道“太陽出來辣焦焦,我和情妹把秧薅,太陽照在妹身上,情哥看到好心焦”。歌詞中的語言十分直白——對燥熱天氣的描寫直白,對男主看到女主辛苦勞作時焦躁心情的描寫也很直白。直白的語言展現了男女之間真摯的情感,同時也營造出一種歡樂、溫馨的音樂氛圍。再例如《高高山上一頭牛》是借助對牛的描寫來抒發(fā)對勞動人民辛苦勞作的感嘆,歌詞唱道“高高山上一頭牛,口含青草眼淚流,問你牛兒哭什么,犁頭耙兒在后頭”。整個歌詞配上曲調一唱、一嘆,展現了山地居民像牛一樣辛苦勞作的模樣,讓音樂充滿了生活氣息,很容易引發(fā)人們的共鳴,因此非常適合在勞動中歌唱。《五月十五大端陽》則是描寫端午節(jié)熱鬧氣氛的歌曲,歌詞唱道“五月十五大端陽,人人都來劃白龍船,人人都說紅船劃得好,劃攏江邊把場搶”。歌詞將描寫視角對準了熱鬧的龍舟競渡,通過觀眾的歡呼喝彩來表達節(jié)日期間的歡快喜悅,寄托人們對生活的美好期待。
福寶高腔山歌除了有豐富的歌詞外,還有古樸生動的襯詞。所謂襯詞,就是穿插在歌曲中的一些襯托性詞語,如語氣詞、形聲詞、諧音詞等等。在高腔山歌中,襯詞多是虛詞,并且根據曲牌的不同而變化,例如《拜腔》中的“啰哦”,《幺姑腔》中的“喲嗬依喲喂”“耶嘿喲”,《老鴰腔》的“哎喲”“哎嘿哎喲喂”等,這些襯詞發(fā)音古樸,甚至有些是獨立成段,有著極強的表現力,也突出了福寶高腔山歌原始的特色。
(三)福寶高腔山歌的演唱特征
第一,山歌采用一領眾和的形式進行演唱。一領眾和就是在領唱的帶領下,其他人進行唱和。領唱者會唱抽腔、提腔,體現“一枝獨秀”的效果,凸顯山歌的情感基調和節(jié)奏旋律。而唱和則會運用幫腔、和腔進行輔助,共同完成演唱。這種演唱形式目前在福寶地區(qū)的山歌比賽中依然傳承,演唱時歌聲穿透力強,極具感染力。
第二,演唱的場地靈活。福寶高腔山歌是勞動人民創(chuàng)造的,因此,它的演唱地點自然也以勞動場所為主,例如田間地頭、院壩等等,當然,還有各種節(jié)慶廟會上。靈活的地點讓歌唱與勞動人民更加貼近,同時也讓歌聲在勞動人民中世代傳承。
第三,具有典型的禮儀禮俗。隨著歷史的發(fā)展,福寶高腔山歌的演唱逐漸形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形式和禮俗,筆者調研發(fā)現,無論是在什么樣的場合演唱福寶高腔山歌,人們都會遵循其固定的歌俗、歌禮、歌規(guī),或許只有這樣,才可以深切地表達表演者對福寶高腔山歌演唱的熱忱,展現人與人之間的禮敬。
福寶高腔山歌作為一種獨特的音樂形式,在演唱中也體現了一定的技巧性。例如對于跨度較大的歌曲,在演唱中,要準確控制聲音的連接與中斷,將聲音與情感相融合,用聲音的連與斷來表現情感的收與放,同時融入假聲的變化,用上揚和下抑的方式適應音域跨度,呈現較好的藝術效果。再如為凸顯高腔特色,演唱者,尤其是男生可以用假聲演唱,并融合不同的潤腔手法,在力度、音色等細節(jié)上進行調整,展現出高亢而不刺耳的效果。
三、結語
本文從傳統(tǒng)音樂文化的視角,利用訪談法、調查法、文本分析法,結合民族學、音樂學、中國民族音樂史等,進行多學科、多維度的研究。通過前期的資料準備及筆錄、錄音、錄像等方法,實地采風、考察,收集、整理有關福寶高腔山歌的相關資料及具有歷史意義的觀點,目的是在現代傳媒的快捷及新樂種的通俗化的影響下,對福寶高腔山歌從發(fā)展概況、文化精神、審美價值等方面進行系統(tǒng)的研究,從而進一步推動福寶高腔山歌的發(fā)展。如今,農村呈現出空心化的態(tài)勢,基于鄉(xiāng)土文化的福寶山歌出現了傳承危機,此外,在東西方交流不斷深入的情況下,西方文化在青少年中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因此我們要以學校、社會公益組織、企業(yè)等主體為代表推廣和傳承山歌。總之,福寶高腔山歌作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福寶乃至川南黔北渝西地區(qū)文化發(fā)展的產物,這種原生態(tài)的歌唱藝術既融合了自然的因素,也受到了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的影響,呈現出的獨有的音樂藝術特色,是當地人精神文化的體現,也是社會變遷的記錄。在新時代下,只有加強對福寶高腔山歌音樂藝術特征的研究,才能夠讓更多人了解山歌的歷史、藝術特色,從而推動非遺的傳承,為當地文化的發(fā)展找到合適的載體,促進當地文化的發(fā)展和繁榮。
參考文獻:
[1]成容.四川福寶高腔山歌《涼風繞兒天要晴》的音樂形態(tài)探究[J].藝術評鑒,2017(19):19-20.
[2]田紅.合江民歌小調音樂藝術特征探究[J].四川戲劇,2015(12):117-119,122.
[3]謝云秀,周娜.合江民歌“福寶高腔山歌”音樂藝術特征[J].音樂探索,2015(2):87-94.
[4]肖成英.合江民歌藝術特征研究[J].四川戲劇,2013(4):136-137,141.
作者單位:
內江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