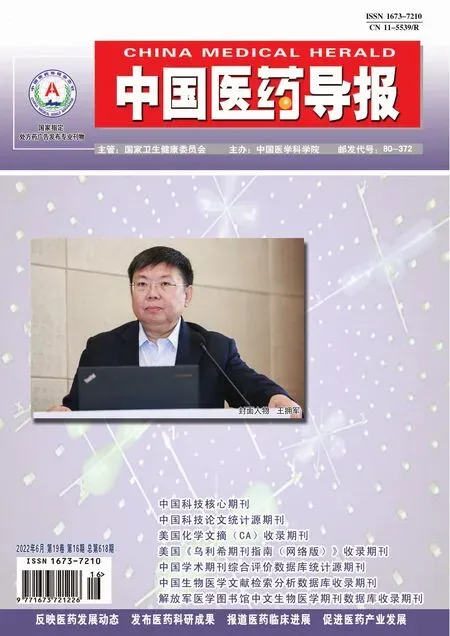3D 打印模型輔助CBL 與PBL 教學模式在脊柱畸形教學查房中的應用效果
趙 雄 張 豐 王新力 孟 冰
1.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骨科,陜西西安 710032;2.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病理科,陜西西安 710032
脊柱畸形是常見的脊柱疾病之一,是指脊柱在冠 狀面、矢狀面及軸位偏離正常位置,臨床上主要表現為側、后、前凸及旋轉等多種復雜畸形,所涉及的解剖結構極為復雜[1]。目前脊柱畸形包括的種類有先天性脊柱畸形、特發性脊柱側彎、脊柱后凸畸形、成人脊柱退變側彎等。本科學生在臨床實習之前,雖然已經掌握了脊柱解剖知識,但對于這種脊柱三維畸形,理解還是比較困難的。如何才能提高學生對脊柱畸形的認識和理解是臨床教學中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目前,臨床教學過程中常用的教學方法包括基于問題的教學(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其是 以學生為中心,由教師提出臨床問題,學生通過小組討論等方式學習。與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方式比較,這種教學方式有一定優勢[2-3]。基于病案的教學(case based learning,CBL)是在教學過程中引入新鮮案例,通過案例講解,穿插相關知識和技能,使學生掌握相關知識與技能[4-5]。隨著數字化技術的迅速發展,3D 打印技術制備骨科模型在骨科領域得以廣泛應用[6-7],可以直觀地顯示復雜脊柱畸形的解剖形態,還可以為確定手術方案提供一定參考。本研究將3D 打印脊柱模型與CBL、PBL 兩種教學方法結合,以期為臨床教學提供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擇2020 年8 月至2021 年4 月在空軍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以下簡稱“我院”)實習的60 名學生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空軍軍醫大學2016 級臨床醫學專業5 年制本科實習學生(大學第五年);②完成了所有醫學基礎與臨床相關課程;③各科成績超過及格線;④自愿參加。排除標準:①英語六級考試成績低于分數線。應用隨機數字表法將其分為觀察組與對照組,每組30 名。觀察組采用3D 打印模型輔助CBL 與PBL 教學模式,對照組采用CBL 與PBL 教學模式。兩組采用的教學患者相同,授課時間相同,由教學經驗豐富的同一位教師授課。兩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
1.2 3D 打印脊柱模型制作
獲取用于教學的患者的脊柱薄層CT 數據資料,由我院骨科3D 數字打印技術中心相關人員完成數據處理,在計算機的精確控制下通過材料堆積,打印出與患者脊柱同等尺寸的3D 模型。見圖1。

圖1 脊柱畸形患者3D 打印模型
1.3 教學方法
對照組采用PBL 與CBL 教學模式,具體方法是帶教老師提前準備典型患者,根據該患者提出相應的問題,包括“脊柱畸形的分類?”“如何對脊柱畸形患者查體?”“脊柱畸形治療原則以及手術方式有哪些?”。提前3 d 將該患者的一般資料及提出的問題發給學生,學生可以通過查閱文獻、書籍、詢問病史等途徑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教學查房時,教師指定實習小組里的一名學生進行問診、查體、閱讀影像學資料并進行匯報,教師必要時進行指導及操作演示。之后,組織學生分組針對該患者展開充分討論,分析患者影像學資料,明確診斷,制訂手術方案。最后,老師對教學查房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予以糾正,對該患者進一步分析與總結,通過教學讓學生建立正確的臨床思維方式。觀察組則在對照組的基礎上增加3D 打印骨骼模型,學生通過仔細觀察3D 模型,思考畸形特點,根據該3D 模型分析討論手術入路選擇、具體置釘矯形操作方法及術中術后需要注意事項等,帶教老師予以點評,并利用模型向學生講解畸形的特點及具體手術過程。
1.4 教學效果評價
由帶教老師對兩組學生進行出科考試,其中臨床專業考試的主要內容是脊柱畸形理論知識與臨床技能(總分均為100 分),記錄兩組考試成績。按照不記名問卷調查方式對兩組學習興趣、理解能力、內容掌握、滿意度進行評價,每項總分5 分。評分標準:不滿意1 分,不太滿意2 分,一般滿意3 分,比較滿意4 分,非常滿意5 分,學生根據學習過程中的實際情況進行評分[8-9]。問卷的Cronbach’s α=0.64。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9.0 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比較采用t 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數表示,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考試成績比較
觀察組理論知識、臨床技能成績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見表2。
表2 兩組考試成績比較(分,)

表2 兩組考試成績比較(分,)
2.2 兩組主觀效果評價比較
觀察組學習興趣、理解能力、內容掌握、滿意度評分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5)。見表3。
表3 兩組主觀效果評價比較(分,)

表3 兩組主觀效果評價比較(分,)
3 討論
PBL 是一種基于問題的教學方法,這種方法是教師根據教學內容提前向學生提出問題,學生通過查閱圖書、文獻資料等尋找答案,這一過程可以鍛煉學生查找資料尋找答案的能力及獨立思考問題能力[10]。之后,教師與學生共同探討分析,來解答學生的疑惑,完成授課過程。PBL 教學能夠幫助學生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逐步掌握知識及技能。截至目前,全世界超過200 個醫學院已部分或完全實施了PBL 教學[11]。大量的研究表明,PBL 教學法可提高學生的信息管理能力和決斷能力,有助于提高臨床診斷技能和醫學生綜合能力[12-13]。但PBL 教學也存在某些不足,如果學生對某個疾病缺乏不夠的了解,就很難組織他們主動積極地討論[14]。脊柱畸形是一種3D 的形態學改變,這就需要具有3D 空間想象力,這也是當前眾多本科學生所面臨的困難。教師純理論授課的話,學生可能對3D空間改變理解不夠,學習積極性下降。
CBL 教學是由哈佛大學Langdell 教授創立的,這是一種以臨床實際患者為基礎的小組討論式教學方法,在老師的指導下討論案例[15]。在這個過程中,學生應用所學到的知識來分析問題,并找到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通常情況下,臨床經典患者往往被用作教學模板。通過對患者的理解,激活學生的基礎知識,讓學生參與到臨床疾病的推理過程中,從而掌握如何詳細問病史、全面查體、規范制訂治療方案及如何進行鑒別診斷,為將來成為合格的臨床醫師打下基礎[16]。這一方法可以引導學生通過案例進行分析和思考,避免傳統的灌輸與填鴨式教學,提高學生的臨床綜合分析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是CBL 教學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即一次只能討論一個案例,解釋最重要的知識點,對學生的基礎知識的掌握要求較高。
有研究表明,將PBL 與CBL 兩種教育模式相結合,可以相互取長補短,達到很好的教學效果[17-21]。其具有以下優勢:①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有助于學生在實踐中成長,加深對理論知識的理解,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有利于臨床思維能力的培養;②有助于教師和學生之間的溝通,以問答的形式探索問題,拓展臨床思維的深度和廣度;③將主題討論與病案分析相結合,形成以問題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使學生從被動學習向主動學習轉變,逐步加深對疾病發病機制、臨床表現和手術方案的認識和理解,進而提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22-23]。通過改變教學形式,提高了學生的團隊合作意識和團結協作能力。然而,脊柱結構相對復雜,大多數學生對脊柱畸形的認識仍然是基于正常的脊柱解剖學。在這種聯合教學的模式下,仍然不能突破理論形式教學的瓶頸,學生不能直觀體驗脊柱畸形的真實特征,使教學效果不理想。
3D 打印技術是一種快速成型技術,其通過逐層打印計算機模型生成的3D 數據信息,快速準確地打印出模型實體[24-28]。多項研究表明[29-32],采用3D 打印模型作為輔助教學工具,可以有效地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促進其掌握基礎理論知識。研究結果表明,將3D 打印技術與CBL 教學模式相結合,可以向學生直觀地呈現脊柱畸形的特點。與傳統影像資料比較,3D打印模型不僅提高了學生對疾病本身的認識,而且加深了學生對脊柱解剖結構的認識,提高了其在臨床中閱讀和分析影像資料的能力[33]。3D 骨骼模型還可以為學生演示手術過程和提供真實的手術場景,使學生更真實地了解骨科手術的細節,掌握相關知識點[34]。
在本研究中,3D 打印技術與PBL、CBL 教學融合在一起,將脊柱畸形患者的脊柱3D 打印模型直接展現在學生面前,學生們通過對3D 打印模型的觀察,將抽象變具體,降低了對知識點的理解難度,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提高臨床實踐能力,使學生能更好地理解脊柱畸形的解剖特點、畸形進展機制及手術矯形方案,進而提升臨床診治思維,該教學方法值得推廣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