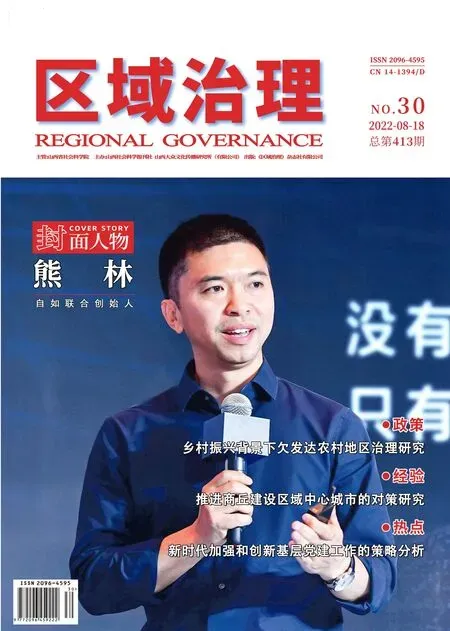塞罕壩生態模式的效用及其推廣研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學 竇晗
一、引言
塞罕壩人工林場的建造和維護,有利于改善當地及周邊的生態環境,尤其為減輕京津冀地區沙塵暴、霧霾等天氣現象的發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人工造林是我國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手段,對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及碳排放總量的控制有著重要意義。在“雙碳”計劃的背景下,探究塞罕壩的效用并模擬塞罕壩生態模式的推廣,對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
二、區域生態環境指標體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環境保護標準》規定,某區域生態環境影響的預測和評價應從水環境、大氣環境、土壤環境、聲環境、生態環境等方面著手[1]。塞罕壩的聲環境在其修復前后無明顯變化,且均處于達標水平。因此,文章使用大氣環境、水土環境、生物物種環境作為評估塞罕壩生態環境的主要指標(二級指標)。這3個指標允許進一步細化,擴展至10個具體指標(三級指標):溫度、露點溫度、空氣質量指數AQI、氧氣含量、二氧化碳含量、涵養水量、土壤酸堿度、森林覆蓋率、林木蓄積、區域物種多樣性。
選取1952年至2021年塞罕壩的相關數據[2-5],進行正向化和標準化處理后,通過熵權法確定10個三級指標的權重,通過客觀賦值法確定3個二級指標的權重。其中,部分數據難以精確至塞罕壩區域,以圍場縣數據代替。
最終,將各指標按權重綜合為塞罕壩生態環境指數Z1。該指標值越大,表示塞罕壩的生態環境越優良,反之越惡劣。塞罕壩修復前后,其生態環境指數Z1隨時間的變化關系如圖1所示。
三、塞罕壩對京津冀地區抗沙塵暴的影響
京津冀地區的抗沙塵暴能力可通過沙塵暴天氣發生的次數直觀反映,也可通過城市綠化覆蓋率、粉塵排放量、降水情況等間接反映。因此,定義從現實能力和潛在能力兩個角度探究京津冀的抗沙塵暴能力。
(一)沙塵暴指數
1.現實能力
沙塵暴天氣依據強度由高到低依次為沙塵暴、揚沙和浮塵[6],將三者發生的次數按權重綜合為風沙指數:

其中,S為風沙指數,即結合了強度因素的沙塵暴天氣發生的綜合次數,S值越大,表示京津冀的風沙天氣狀況越嚴重,即抗沙塵暴能力相對越弱。S1、S2、S3依次為沙塵暴、揚沙、浮塵天氣發生的次數。w1:w2:w3=3:2:1,依次為3種強度沙塵暴天氣現象的權重值。
2.潛在能力
考慮京津冀地區汽車逐年增多、干旱少雨、常見大規模基建施工等的地域特點,以及其為環境保護實施的城市綠化措施,該地區的粉塵排放量越低、降水量越大、城市綠化率越高,表示其抗沙塵暴能力相對越強。
對上述4項指標:風沙指數、粉塵排放量、降水量、城市綠化率進行正向化和標準化處理后,使用熵權法計算權重,按權重綜合為京津冀抗沙塵暴指數。選取1952年至2021年京津冀地區的相關數據[4-5]進行計算,得到逐年的抗沙塵暴指數如圖1所示。

圖1 塞罕壩生態環境指數與京津冀地區沙塵暴指數隨時間的變化曲線圖
(二)塞罕壩與京津冀沙塵暴間的關系
計算塞罕壩的三級生態指數分別與京津冀抗沙塵暴指數之間的皮爾遜相關系數,如表1所示。可知,二氧化碳含量和森林覆蓋率與抗沙塵暴指數間的相關系數大于0.95,同時,超過三分之二的生態指標與抗沙塵暴指數之間的相關系數大于0.8。綜合而言,塞罕壩的生態環境狀況與京津冀地區的抗沙塵暴能力之間的相關性很強,塞罕壩人工林場對京津冀沙塵暴天氣狀況的改善具有重要影響。分析其中的緣由,塞罕壩的建立調節了其周邊區域的氣象狀態,直接影響了碳循環和水循環,進而對降水格局做出了調整,使得京津冀的降水量增大,風沙天氣狀況得以改善。同時,北京以北直線距離不足200公里的內蒙古渾善達克沙地是京津冀地區沙塵暴的重要來源地之一,若無阻擋,來自西伯利亞的北風將攜沙塵大舉南下[7]。而塞罕壩位于北京與渾善達克沙地之間,其中茂密高聳的森林筑起了一道綠色屏障,風沙得以有效攔截。

表1 塞罕壩生態指標與京津冀地區沙塵暴指數之間的相關系數
四、我國部分省市自治區生態區建設
(一)生態環境指數
近年來,我國的生態工作更加注重于對森林覆蓋率、PM2.5、人均水資源占有量的監測。與塞罕壩生態環境指數的求解類似,使用上述3個指標的數據[5][8]計算2021年我國部分省市自治區的生態環境指數Z2。
A:香港的地方小、人工成本高、廠房租金高,對于想要擴大規模的企業來說,可謂進退兩難。改革開放為眾多香港企業提供的最大助力是,發展空間。在內地,地租便宜,人工成本也相對較低。如果不來內地,我們不可能發展如此快。相輔相成,我們這些首批進入東莞的香港企業,帶來了先進的管理理念、技術,這也為內地印刷業培養了很多人才。大家一起默默耕耘,為行業發展貢獻了一份力量。
(二)生態異常省份
中國整體的生態環境狀況較穩定,以此為標準狀態,偏離程度大者意味著生態處于異常狀態,設定生態異常臨界值如下:

其中,EIab為生態異常臨界值,μ(Z2)2021為2021年我國部分省份生態環境指數均值,σ(Z2)2021為2021年我國生態環境指數的一倍標準差。若某省2021年的生態環境指數小于臨界值,即認為該省份生態狀況異常,需要考慮建造生態區。
(三)具體建造計劃
生態狀況呈現異常的省份,可以認為其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已有的措施效果較弱。為其建立生態區后,生態區發揮的作用可作為今后該省生態發展的主要影響因素。因此做出假設,先忽略其他因素的影響,只考慮生態區的引入對該省份生態環境指數變化的影響。
使用2021年及之前的塞罕壩生態環境指數Z1與時間t進行logistics回歸擬合,得到二者的函數關系f(Z1,t),并用此函數關系預測未來10年塞罕壩的生態環境指數。
對于不同的省份,它們的經濟、工業、人類活動對生態區的制約不同,生態區的作用可發揮的程度不同。同時,不同省份現有的生態環境狀況基礎也不同。若要達到相同的生態環境目標,可以作出如下推導:

其中,Y為某省某年(建造生態區后)的生態環境指數,Y0為該省于2021年(未建造生態區時)的生態環境指數,N為需要建造同塞罕壩生態模式與規模相同的生態區的個數,y’為一個生態區對該省生態環境指數的變化帶來的作用,Z1滿足關系f(Z1,t)。系數b的值由省份的經濟、工業發展等因素決定,表征生態區的作用可發揮的程度大小,例如,某省份經濟發展越強,生態區受到的制約越大,則b越小,表明建造生態區可帶來的生態環境改善效果越弱。
根據引入塞罕壩生態模式并建造生態區的最初目的,可作出計劃:在理想情況下,自2021年起,以9年為限,生態異常省份的生態環境指數達到2021年我國生態環境指數均值μ(Z2)2021。據此計劃,總計至少需要建造35個生態區。
五、對碳達峰的影響
(一)引入生態區的影響
根據“雙碳”計劃,中國預計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且實現的時間越早,越有利于未來實現碳中和目標[9]。
可以認為,2030年實現碳達峰的同時,我國整體生態環境指數也達到一個局部極值。在進行預測工作時,選用2030年生態環境指數達到極值代替碳排放量達到峰值作為前提基準,再變動碳排放量峰值年份,保證經濟受到的影響在相較之下更小,加速生態環境發展時各方因素的平衡受到的破壞也更小。
為了探究生態區的建造為碳排放量帶來的影響,假設除建造生態區的省份外,其他省份的生態環境狀況始終保持在2021年的水平。
我國整體生態環境指數隨時間的變化受到生態區帶來的影響,因此有:

其中,Yall為某年(建造生態區后)我國整體的生態環境指數,Yall0為2021年的我國生態環境指數初值,Zall’為2021年考慮建造的所有生態區共同對我國生態環境指數的變化帶來的影響,b1,b2,...,bn和 N1,N2,...,Nn分別依次對應生態異常的省份。
同樣的,碳排放量隨時間的變化也受到生態區建造帶來的影響:

其中,Wall為某年(建造生態區后)我國整體的碳排放量,Wall0為2021年的我國碳排放量初值,k表示理想貢獻Zall’在碳排放量方面的實際效用權重。
(二)碳達峰年份的變化
假設無論是否建設生態區,生態環境指數Zall均在2030年達到峰值,此假定已在前文作出解釋。利用式(4)計算生態區建設后2030年的生態環境指數值,再通過關系f(Zall,C)計算該值對應的碳排放量值,則可通過式(5)計算得到此時的碳排放量峰值對應的年份。建造生態區后,相比未建造生態區時,我國的碳排放量達到峰值的年份提前了2.5年,該峰值也有所降低。
六、結論與討論
環境保護是21世紀的主題,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適地人工造林、劃分自然保護區、南水北調等工程,是我國在實現生態可持續發展進程中探索出的一條條成功之路。這些措施帶來的效果有目共睹,且其具備的生態改善潛力是巨大的。如何從已有成效的生態環境改善措施中總結經驗、發掘模式,并進一步推廣至其他區域,是我國現階段生態環境發展工作的重要內容。
文章通過探究歷年來塞罕壩生態指數與京津冀地區抗沙塵暴指數之間的關系,說明塞罕壩對京津冀沙塵暴天氣狀況的改善具有重要作用。同時,界定區域生態異常的標準,計算生態異常省份需要建造的生態區規模,據此,為這些省份提供了生態環境治理力度的參考。進一步模擬建造生態區后我國碳排放量的變化,探究塞罕壩生態模式在部分省市自治區的推廣對我國“碳達峰”計劃的推動作用。
人工造林等生態改善措施的意義已遠遠超出環境保護的意義。文章中考慮了經濟、工業狀況對生態區功能的制約作用,以及“碳達峰”年份提前對中國經濟帶來的影響,則對于經濟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可以有進一步的思考:經濟發達地區往往因為在工業發展、建設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環境消耗”,面臨著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問題;經濟欠發達地區則面臨著可依托當地良好的生態環境資源實現超越式經濟發展的機遇[11]。
今后,隨著生態環境治理工作的逐步完善,治理方案將更加全面并具有針對性。生態區的建設和維護為經濟和生態的共同發展提供了一個可操作的模式,若能因地制宜地規劃生態區建造方案,我國的生態環境有望得到更有效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