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
——基于政黨的類型學分析
臧秀玲
歷經百年奮斗歷程,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建黨建國、興黨興國、強黨強國的時代壯舉。百年來的理論與實踐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使命型政黨,超越了西方政治學者對政黨類型的分類,形成了自身的特質與優勢。這是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的關鍵所在。
西方政黨政治的類型學分析和現實困境
世界政黨政治實踐的長期性與多樣性決定了政黨分類標準的差異性和動態性。總體來說,當前西方學術界關于政黨分類的方法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方法基于政黨自身的組織結構特征對其進行分類,包括政黨組織的形式、代表和整合功能、集中和結盟水平、區域滲透和擴散能力等。如美國政治學家理查德·卡茨和愛爾蘭政治學家彼得·梅爾將政黨組織形式分為四種:精英型政黨、群眾型政黨、全方位型政黨和卡特爾型政黨;德國政治社會學家西格蒙德·紐曼則根據政黨的代表整合程度將政黨劃分為個體代表型政黨、社會整合型政黨和全部整合型政黨。第二種方法是通過分析政黨特征凝練出政黨類型的“屬概念”,即政黨門類,并將政黨類型歸于這些門類當中,包括政黨的內外部起源、族群支持情況等。如法國學者莫瑞斯·迪韋爾熱將政黨分為內生黨和外生黨,美國學者理查德·岡瑟和拉里·戴蒙德則根據族群支持情況將政黨分為純粹族群型政黨和族群議會型政黨。第三種方法則是根據政黨具有的社會學特征進行分類,包括階級、宗教、民族、意識形態等。如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通過世界觀和宗教對政黨進行分類的方法流傳甚廣。這三種政黨分類方法或從政黨結構出發,或向上歸納“屬概念”特征,或向下總結社會學表現,圍繞的中心是政黨組織本身的結構與性質。
在政黨政治嬗變與轉型過程中,西方政黨呈現出歷史性和連續性特征。原始民主體系下僅有少數有產成年男性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受此影響,19 世紀中葉以前的政黨政治運行實踐局限于少數特權階層,政黨以精英為核心、結構松散,鮮見議會外政黨,這一時期占主導的政黨類型為精英型政黨。19 世紀末20 世紀初,隨著民眾對政黨權力壟斷的排斥,一些具有明確組織結構特征和鮮明意識形態特點的議會外群眾型政黨應運而生。到20 世紀中葉,在群眾型政黨完成政治整合之后,政黨組織逐漸向專業化方向發展,為了緩和社會矛盾、吸引更多選民,這些政黨的意識形態逐漸淡化,政黨間的聯合頻率逐漸增多,全方位型政黨由此產生。20 世紀末,政黨政治愈加成熟,西方主要政黨為了占據公共職位,限制新興政黨的挑戰和威脅,加強對國家權力和社會資源的壟斷,卡特爾型政黨出現。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和新聞傳播的進步,掌握較多私人資源的社會企業家們利用市場策略和塑造領袖形象參與競爭性選舉活動,對傳統的政黨政治格局產生嚴重沖擊,并由此產生新型的商業公司型政黨。
西方語境中政黨類型的劃分和政黨政治的演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階段性特征,但始終難以解決西方政黨政治的危機。一是治理危機。西方政黨體制固化,利益集團地位難以撼動,社會問題無法得到有效解決。西方發達國家的政黨已難以提出符合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的政策主張,失去了提供不同政策選擇的政黨政治功能,如英國和美國,但是在政治上這些國家還是不得不訴諸低效的兩黨制和利益集團的勢力角逐來解決矛盾,難以提出并實施有效的政策措施。二是認同危機。西方政黨將競爭性選舉簡化為民主范式,將人民的整體權力拆分為三權分立,違背了人民至上的信條,失去了民意基礎。西方政黨政治通過選票將維護人民利益的民主選舉包裝為政治秀場,真人秀演員、喜劇演員、節目主持人等都可以參與競選甚至成為總統,普通民眾對政黨政治和選舉政治的認同度普遍較低。三是信任危機。不斷失敗的政黨轉型和持續衰敗的治理體制使得民眾對傳統政黨力量失去信心,政黨政治碎片化趨向顯著。為了迎合選民意愿和短期利益,民粹主義和極端主義政黨發展勢頭迅猛,他們利用媒體博取選民眼球、搶占話語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西方選舉的“政治狂歡”。

中國共產黨對政黨類型學的超越
在世界政黨類型學的分類譜系中,相較于西方政黨所呈現出的疲憊衰敗跡象,中國共產黨歷經百年風雨依舊展現出強大的生機活力。作為一種新的政黨類型,使命型政黨不僅存在于中國語境下,而且遵循著政黨政治轉型與發展的一般規律,是對中國共產黨的重新定位和性質解讀,蘊含著“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的答案。中國共產黨堅守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主導著中國政黨政治的運行邏輯和發展方向,實現了對西方政黨政治話語的超越,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超越政黨的數量概念,強調政黨之間的團結。當前,在競爭型政黨體系下,大多數西方國家采取兩黨制或多黨制,并普遍認為采取一黨制的國家是不穩定的、無法長久維系政權的“特例”或“異端”。同時,西方學術界提到“政黨”一詞時,也多是使用該詞的復數形式。“政黨”在西方話語體系中的這一表現,一方面是因為西方國家的政黨在起源上就具有對立、分歧和斗爭的傳統。例如,英國的政黨在初始階段便分別圍繞強化國會還是國王權力、自由主義還是保守主義而展開斗爭,雖然彼時的紛爭早已不復存在,但是這種兩黨對立之勢卻延續至今。另一方面,西方國家不相信政黨能夠自我約束,也不相信長期執政的單一政黨能夠根據現實變化調整施政方針,認為必須存在多個政黨,以權力分化實現黨際監督,以政黨競爭激勵政黨變革。然而,這也為黨爭不斷、“否決政治”、利益集團拉扯、政策短視等問題埋下了隱患。作為使命型政黨,中國共產黨不照搬西方政黨競爭與輪替形式,采取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新型政黨制度,不拘泥于政黨的數量,而是注重政黨所代表的人民群體的范圍。在歷史使命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共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勇向前。
第二,超越政黨間利益對抗,強調政黨協商合作。無論是以維護特權階層利益為核心的精英型、卡特爾型政黨,還是反映部分民眾意愿的群眾型政黨,西方語境中的政黨都是從利益角度出發,以“利益至上”的觀念與其他政黨展開“零和博弈”。這樣的政黨類型學也具有壟斷與反壟斷的發展特征,政黨治理下的國家和社會內部具有不可避免的對抗性本質。中國共產黨作為使命型政黨展現出全然不同的特質。中國共產黨不僅有科學嚴密的組織體系和集中統一的領導體系使各個政黨之間形成合力,更有矢志不渝的使命意識體系統領各黨派的參政追求。對于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來說,在政黨利益之上還有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使命擔當,正是這樣的政黨使命造就了各黨派的目標取向、價值方向和根本精神追求,并影響其他組織特征。
第三,超越了政黨的從屬性定位,充分發揮政黨自身的能動性。在國家—政黨—社會三者的關系中,西方語境下的政黨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中介和橋梁。相比于國家和社會,政黨是一種從屬性很強的概念。精英型政黨遠離社會和民眾,群眾型政黨則從議會外的社會群體中產生,而發展到卡特爾型政黨時,政黨與國家權力的關系愈加密切,但與社會和民眾則漸行漸遠。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直接決定了政黨或政黨政治的生存現狀,西方政黨普遍存在從屬于國家或社會中心主義傳統而能動性不足的現象。中國共產黨作為使命型政黨具有強大的主體能動性,發揮著統領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推動國家—政黨—社會三者的有機融合,形成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合力。中國共產黨不將國家和社會看作是對立或不相容的兩個領域,也未將政黨功能從屬于國家與社會,而是在實踐中自主選擇、構建與調整治理方式與方向,實現國家治理與社會治理相統一、治理與民意相統一,充分展現作為使命型政黨的主體性與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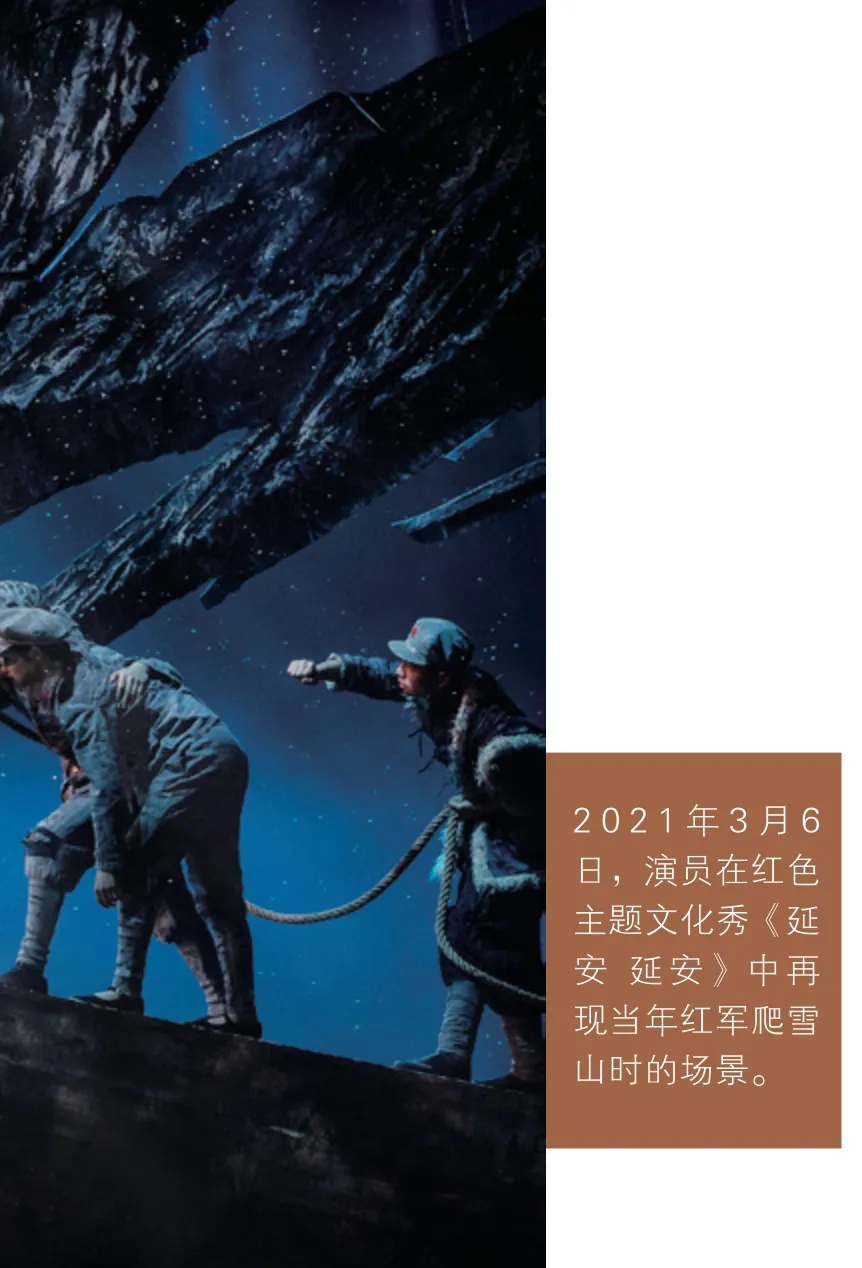
中國共產黨使命型政黨特質的主要優勢
所謂政黨使命,是指政黨基于歷史經驗、政黨及國家所處方位與環境,對其自身的奮斗目標、實現方式、價值方向與意識形態等的全面而系統性的認識。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使命擔當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優秀品質,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先進性的本質特征,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完成現代化國家建構的內在要求。作為使命型政黨,中國共產黨具有獨有的類型化特質,彰顯出百年大黨的獨特優勢,生動詮釋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的重大命題。
第一,秉持人民本位理念,強化政黨的使命擔當。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是黨執政興國的最大底氣。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 中國共產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始終堅守人民立場,把人民群眾視為推動歷史發展的前進動力,把人民放在黨和國家工作的最高位置。中國共產黨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堅守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人民的利益為利益,沒有任何特殊的利益,不代表任何特權階層和利益集團的利益,絕不違背人民的意志。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人民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不斷造福人民,始終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
“利民之事,絲發必興;厲民之事,毫末必去。”人民本位并非只是一個口號,不能止步于思想環節,而是要為人民群眾切切實實謀幸福,這正是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政黨的根本區別。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本位理念體現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上,體現在人民當家作主權利的行使中。中國共產黨在政治實踐中貫徹落實全過程人民民主,暢通意見表達渠道,保障人民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生動彰顯人民至上信念;堅持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各黨派、民族、團體、階層中廣求良策、廣聚共識,發揮各方面積極性,有效克服利益傾軋的弊端,有效拓寬民主渠道。相比之下,西方政黨持有的是“利益本位”“金錢本位”理念,政治格局僵化,難以做出利民決策,少數務實為民的政黨也難以撼動特權階級的利益,而當前迎合民意形成一定規模的政黨又持有極端價值觀念,難免陷入政黨認同危機。
只有人民本位、以人民為中心的政黨價值觀才能獲得人民衷心的認同。在新時代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將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黨的奮斗目標,堅持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推動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以實際成效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人民群眾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心倍增,由此對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念愈堅。

第二,堅持守正與創新的統一,永葆馬克思主義政黨本色。在守正創新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百年大黨永葆青春的關鍵所在,是使命型政黨的理論品格和思想基礎。尤其是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國共產黨始終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實踐,時刻銘記馬克思主義政黨本質,為實現共產主義最高理想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而不懈奮斗。一方面,以“守正”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守正,守的是真理性與科學性之“正”,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指導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解決問題,持續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毫不動搖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定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信心。另一方面,以“創新”思想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創新,創的是開放性與時代性之“新”,就是不僵化、不停滯、勇于改革。結合時代發展特征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不斷提高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水平,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開辟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新境界、探尋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塑造人類文明新形態,與時俱進回答時代之問、實踐之問、人民之問和世界之問。
守正不意味著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濫觴,創新也不是任由非主流意識形態的滋長。中國共產黨反對形式主義地對待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始終堅持以開放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真理對時代的適應性變化;中國共產黨也注重辨別各類非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取向與性質,積極引導與調控不同意識形態,堅守主流意識形態陣地。西方國家有些政黨為討好選民不惜煽動縱容民粹主義,有些政黨則完全淪為特定利益集團的選舉工具,這些均導致近年來西方政治極化現象愈加明顯。由于缺乏明確的理想信念和思想基礎,西方政黨政治精英大多目光短淺,不具備制定和執行長遠規劃的意愿和能力,民眾對政黨的信任度和認同度降低。由于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的固化,西方政黨凝聚力與號召力持續降低,政黨組織萎縮,政黨功能弱化,民主神話最終破滅。守正創新是以真理的原則發展真理,體現了普遍性與特殊性、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堅持守正與創新的有機統一,就是要永葆馬克思主義政黨本色,確保黨不變色、不變質、不變味。堅定政黨使命不褪色,才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行穩致遠。
第三,塑造嚴密高效的組織體系,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政黨組織結構是政黨效能發揮的基礎,政黨使命與政黨組織是“神”與“形”的關系,使命型政黨既要“凝神”,也要“匯形”,實現政黨使命需要“以神化形”,需要充分發揮黨深入人民群眾基層的組織優勢。中國共產黨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組織起來,構建涵蓋中央、地方與基層的嚴密組織網絡,實現了社會資源的有效整合與政治力量的有效動員。嚴密高效的組織結構使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和社會號召力不斷增強,由此進一步確保了黨的強大動員力、戰斗力和生命力。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成為百年大黨、鑄就百年輝煌,關鍵就在于始終維護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確保全黨的團結與統一,形成了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磅礴力量。

加強組織建設、完善組織體系、保證黨內法規公正嚴明是黨長期執政的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工作,是應對外部挑戰的堅固防線。完善黨的組織體系,規范各級黨組織的機構設置與職能,形成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的嚴密組織架構;完善黨的監督體系,強化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構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體制機制;完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規治黨和依法執政,嚴格遵守黨章及其他法律法規。相比之下,西方政黨組織內外的精英化傾向日益加劇,基層黨組織的虛化、弱化、空心化日趨嚴重。西方黨員的政治身份只有在投票選舉時才被喚醒,黨員的政治參與度低、忠誠度明顯淡化。西方政黨的社會功能也不斷弱化,缺乏必要的政治擔當和責任意識,黨內呈現出分裂不斷、內斗不止的局面。蘇東劇變的慘痛教訓,要求我們黨鑄就嚴密的組織防線,鍛造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是戰勝一切風險挑戰、實現黨的歷史使命、延續黨的非凡成就的必然要求。
第四,勇于自我革命,推動政黨的適應性變革。我們黨長盛不衰、穩步前行,外靠發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監督實現新跨越,內靠全面從嚴治黨、推進自我革命開創新格局。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的鮮明品格,也是中國共產黨經得住風浪、扛得住考驗、永葆青春活力的強大支撐。實現歷史使命,關鍵在于黨以高度的歷史自覺和強烈的主動精神持續推進自我革命,并以徹底的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的社會革命。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斷自我革命的實踐中淬煉而成的。黨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實踐中,需要時刻防范政治不純、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等問題,及時清除自身組織體制的陋習和弊病,才能在困難和逆境中化被動為主動,有效應對“四大考驗”“四種危險”。
“自我革命”遵循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念,實現了革命主體與革命客體之間的創造性轉化,強調“刀刃向內”,著重解決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問題,有效規避了西方政黨政治中執政黨與在野黨相區分、相對立的話語陷阱。中國共產黨肩負著偉大的歷史使命,始終保持管黨治黨“永遠在路上”的清醒和勇毅前行的定力,不斷提高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能力。西方政黨不僅缺乏內部變革的組織力量,而且缺乏主動變革的政治意識,主要通過外部政黨的挑戰和分權制衡的約束進行被動調適。西方政黨也曾出現少數卡里斯瑪型領袖試圖以自我否定、政治煽動的方式打破僵化的政治格局,但由于利益集團的牽絆和政治體制的固化,不僅難以達到理想效果,還可能帶來更大的政治風險。中國共產黨在自我革命中探索出自我成長的有效路徑,形成了優于其他政黨的獨特優勢,給黨和人民的事業注入了源源不斷的生機與活力。中國共產黨堅持自我革命,有利于推動黨性與人民性的有機統一,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和執政基礎,這是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

結語
從政黨的類型學意義上系統分析“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這一重大命題,是對新時代建設什么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一重大時代課題的具體闡釋。中國共產黨作為使命型政黨打破了西方語境下對一黨執政的偏見,變政黨間的對抗關系為合作關系,變政黨相對于國家和社會的從屬性地位為主體能動性的發揮,實現了對西方政黨的全面超越。中國共產黨不僅從理論上突破了西方的政黨類型標準和政黨話語體系,還在實踐上帶領中國人民走出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巨大劫難,使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型政黨特質,拓展了世界政黨類型學的分類譜系,并從政黨角色、政黨功能和政黨能力等方面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中國方案。以迎接新的百年為出發點,中國共產黨以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和巨大的政治勇氣,推動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在新的趕考路上,中國共產黨將以更加堅定的歷史自信和政治自覺,踔厲奮發、勇毅前行,不斷贏得更加偉大的勝利和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