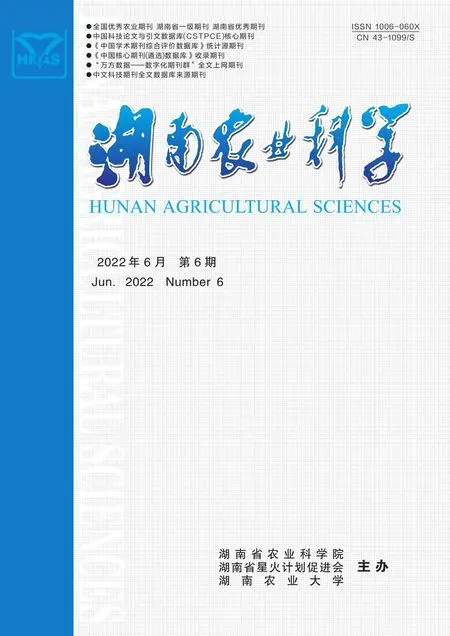基于風險管理的鎘砷污染稻田修復治理案例分析
高 嵩,易春麗,劉匯川,余 泓,潘淑芳,謝運河
(1. 祁陽市農業農村局,湖南 永州 426100;2. 湖南省農業對外經濟合作中心,湖南 長沙410005;3. 湖南省農業環境生態研究所,農業部長江中游平原農業環境重點實驗室,農田土壤重金屬污染防控與修復湖南省重點實驗室,湖南 長沙 410125)
湖南是我國有名的“有色金屬之鄉”和“非金屬 之鄉”,礦業經濟十分發達,但由于礦業采選存在數量多、規模小、分布散、基礎差等問題,且受利益驅動,部分地區歷史上非法違法開采現象普遍,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1]。近年來,湖南省耕地受鎘、砷、鉻等重金屬污染形勢嚴峻[2],尤其是2013 年的“鎘米風波”極大沖擊了湖南乃至整個南方稻米產業,敲響了當前農業安全生產和生態環境保護的警鐘,并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3]。針對性開展污染農田的修復治理,實現受污染耕地的安全利用是我國土壤污染防治攻堅戰的重要內容,基于重金屬污染風險構建修復技術體系,是實現重金屬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的重要形式[4]。祁陽市在世界銀行貸款湖南省農田污染綜合管理項目的支持下,基于稻米鎘砷污染風險,選擇祁陽市白水鎮和肖家鎮的典型重金屬污染稻田建立修復治理示范工程,以期為區域內同類型重金屬污染稻田的修復治理提供技術參考,也為大規模重金屬污染農田的修復治理提供管理經驗。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地點
項目示范區包括肖家和白水2 個,分別位于祁陽市白水鎮和肖家鎮,示范總面積504 hm2,其中白水項目區示范面積142 hm2,肖家項目區示范面積362 hm2;白水鎮項目區包含新中村和新華村2 個項目村,肖家項目區包含汪家坪村、牛嶺村、牛頭灣村、金星村4 個項目村。
1.2 試驗方法
2017 年,在綜合考慮地理地形、灌溉水系及污染源和污染特征的情況下,以項目村為治理單元,在水稻成熟期以“5+ ”(n 為治理單元以畝為計量單位的面積數)的密度,按網格法選擇有典型田塊進行取樣點位定位,并對稻谷和土壤進行 “一對一”取樣。稻谷測定糙米鎘、砷(無機砷)含量,用于鎘、砷污染的風險分級;土壤測定土壤鎘、砷總量,以及土壤pH 值、CEC,用于指導修復治理技術措施的制定。2018 和2019 年主要開展小面積試驗,未進行面上采樣分析;2020 年和2021 年開展大面積的示范,其取樣點位、測定指標和方法同基線(2017 年)。
土壤全鎘采用HNO3-HClO4-HF(體積比5 ∶1 ∶2)消煮,樣品消煮完全后趕酸至近干,加少量稀硝酸溶液溶解后轉移定容;糙米鎘采用HNO3-H2O2(體積比5 ∶2)微波消煮,糙米無機砷含量采用6 mol/L HCl 浸提法測定;土壤有效態鎘含量采用DTPA(二乙三胺五醋酸)提取方法進行,稱10.00 g 過20 目土樣,加入DTPA 浸提液(土 ∶ 水=1 ∶5)50 mL,震蕩2 h 后過濾,稀釋20 倍后待用;土壤有效砷采用乙酸銨提取方法進行,稱10.00 g 土樣,加入1 mol/L 的乙酸銨50 mL,25℃條件下180 r/min 震蕩1 h 后過濾,稀釋20~100 倍后待用。所有樣品鎘、砷含量使用ICP-MS(iCap-Q,美國Thermo 公司)進行測定。
1.3 稻米鎘砷污染風險分級
根據稻米重金屬鎘、砷含量與《食品安全國家標準》中的限量標準,按公式(1)計算稻米重金屬鎘、砷污染指數(Ei):

結合稻米鎘、砷污染風險指數確定風險等級和風險管控目標[4](表1),制定了以降鎘優先、協同降砷的安全利用策略,并針對性的制定技術實施方案。

表1 稻米重金屬污染風險分級體系
2 結果與分析
2.1 項目區鎘砷污染風險分級
根據基線數據可知(表2),肖家項目區共362 hm2,共設置取樣點位172 個。肖家項目區稻米鎘含量平均為0.29 mg/kg,砷含量平均為0.18 mg/kg,肖家項目區整體為鎘污染低風險;其中,金星村、牛嶺村、牛頭灣村、汪家坪村共4 個項目村稻米鎘含量分別為0.34、0.30、0.16、0.34 mg/kg,稻米砷含量分別為0.17、0.18、0.19、0.19 mg/kg,表明牛頭灣村為鎘污染無風險,牛嶺村為鎘污染低風險,金星村、汪家坪村為鎘污染中風險。白水項目區共142 hm2,共設置取樣點位75個。白水項目區稻米鎘含量為0.62 mg/kg,稻米砷含量為0.22 mg/kg,整體為鎘污染極高風險、砷污染低風險;其中,新華村、新中村共2 個項目村稻米鎘含量分別0.61、0.63 mg/kg,稻米砷含量分別為0.24、0.20 mg/kg,表明新華村為鎘污染極高風險、砷污染低風險,新中村為鎘污染極高風險。由于區域稻米鎘、砷含量點位達標率較低,因此,在制定修復治理技術措施時應對降鎘和降砷技術進行強化。

表2 稻米基線(2017 年)數據及鎘砷風險分級
2.2 分區治理技術
根據基線監測數據可知(表3),2 個項目區的土壤鎘平均含量分別為0.48、0.53 mg/kg,屬于鎘輕度污染;土壤砷含量分別為11.52、20.94 mg/kg,土壤砷未超標。2 個項目區的土壤pH 值分別為5.36、5.60,皆呈酸性;且土壤鎘活性較高,土壤鎘有效率分別達58.33%和62.26%。結合稻米鎘砷超標情況及土壤理化特征,確定了以石灰質復合材料[生石灰(CaO 含量70%)、石灰石(CaO 含量45%)、白云石(CaO+MgO含量45%)按照1 ∶3 ∶6 的比例混合而成的石灰復合產品] 進行土壤酸性調理、土壤調理劑(南京寧糧生產的硅基鈍化劑)進行鎘污染稻田的修復治理、鎘砷同步鈍化劑(岳陽康源邦爾提供的鎘砷同步鈍化產品)進行鎘砷復合污染稻田的修復治理的主體模式,并在優化田間水分管理(分蘗盛期適當曬田)的前提下進行組合,構建了污染稻田風險管控技術體系。肖家項目區主要為鎘污染,金星村和牛嶺村主要以石灰質復合材料+土壤調理劑進行修復治理,牛頭灣村和汪家坪村因有40%左右的點位稻米砷超標,采用石灰質復合材料+鎘砷同步鈍化劑進行修復治理;白水鎮為鎘砷復合污染,主要采用石灰質復合材料+鎘砷同步鈍化劑進行修復治理。每個項目村根據稻米鎘砷含量及超標程度,進行施用量的調整。

表3 土壤理化性質基線(2017 年)數據及修復治理技術模式
2.3 稻米鎘砷修復治理效果
分析2020—2021 年修復治理效果(表4)表明,肖家和白水項目區各項目村的稻米鎘、砷含量及其達標率表現出與項目區相同的趨勢,稻米鎘含量逐年下降,達標率逐年提升;稻米砷含量則下降緩慢,但實施第2 年的降砷效果和達標率皆提升顯著。

表4 修復治理后的稻米鎘砷含量及達標率
與基線數據相比,2020 年和2021 年白水和肖家2 個項目區的稻米鎘含量皆有較大幅度的下降,達標率顯著提升;肖家項目區稻米鎘平均含量由基線的0.29 mg/kg 下降至2020 年的0.20 mg/kg 和2021 年的0.06 mg/kg,分別下降31.03%(P<0.05)和79.31%(P<0.05),達標率由基線的48.56%逐漸增加至2020 年的62.32%和2021 年的96.13%;白水項目區稻米鎘平均含量由基線的0.62 mg/kg 下降至2020年的0.15 mg/kg 和2021 年的0.06 mg/kg,分別下降75.81%(P<0.05)和90.32%(P<0.05),達標率由基線的10.86%逐漸增加至2020 年的77.12%和2021 年的95.56%。6 個項目村的稻米降鎘效果皆表現出相同趨勢,表明6 個項目村4 個修復治理模式稻米降鎘效果明顯,且呈逐年增加趨勢。
與基線數據相比,實施2 a 后(2021 年)白水和肖家2 個項目區的稻米砷含量也有較大幅度的下降,達標率顯著提升,但2020 年2 個項目區的稻米降砷效果皆不理想,尤其是白水項目區的稻米砷達標率比基線下降了40.96 個百分點。肖家項目區平均稻米砷含量由基線和2020 年的0.18 mg/kg 下降至2021 年的0.14 mg/kg,下降22.22%(P<0.05),達標率則由基線的69.81%和2020 年的70.11%增加至2021 年的100%;其中2020 年模式一(金星村)和模式二(牛嶺村)的稻米砷含量與基線相當,但砷達標率略有下降,而模式三(牛頭灣村、汪家坪村)的稻米砷含量略有下降,達標率略有增加;經過2 a 的修復治理,2021 年肖家項目區3 種模式的稻米砷含量皆較基線明顯下降,稻米砷達標率達到100%。白水項目區平均稻米砷含量由基線的0.22 mg/kg 上升至2020 年的0.30 mg/kg 后又下降至2021 年的0.14 mg/kg,達標率則由基線的49.49%下降至2020 年的8.53%后又升至2021年的100%。可見,模式一和模式二對稻米砷含量的影響不明顯,模式三第一年對稻米砷具有一定的鈍化效果,但第二年降砷效果明顯;而模式四第一年增加了稻米砷含量,第二年降砷效果明顯,連續施用2 a后稻米砷達標率顯著提升。
2.4 對土壤鎘砷有效態含量及pH 值和CEC的影響
分析修復治理后土壤鎘砷有效態含量、土壤pH值及CEC 的影響(表5)表明,肖家和白水項目區各項目村的土壤有效態鎘、砷含量及土壤pH 值和CEC皆表現出與項目區相同的趨勢,土壤pH 值逐年增加,有效態鎘含量逐年下降,土壤有效態砷含量和CEC無明顯變化。

表5 修復治理后的土壤鎘砷有效態含量及土壤pH 值和CEC
與基線數據相比,兩個項目區修復治理后土壤有效態砷含量無顯著變化,但土壤有效態鎘含量皆下降明顯,肖家項目區土壤有效鈦鎘含量由基線的0.28 mg/kg 下降至2020 年和2021 年的0.22 mg/kg,下降了21.43%(P<0.05);白水項目區土壤有效態鎘含量則由基線的0.33 mg/kg 下降至2020 的0.27 mg/kg和2021 年的0.26 mg/kg,分別下降了18.18%(P<0.05)和21.21%(P<0.05)。修復治理顯著提升了土壤pH值,但也降低了土壤CEC 含量,肖家項目區土壤pH 值由基線的5.36 增加至2020 年的6.36 和2021 年的6.67,分別增加了1.00(P<0.05)和1.31(P<0.05);白水項目區土壤pH 值則由基線的5.60 增加至2020 年的6.36 和2021 年的6.64,分別增加了0.76(P<0.05)和1.04(P<0.05);兩個項目區修復治理后的土壤CEC 則較基線略有下降。
3 小結與討論
3.1 小 結
(1)基于稻米鎘砷含量建立污染風險分級體系,并結合土壤污染特征和理化性質,分別選擇石灰質復合材料、鎘鈍化劑、鎘砷同步鈍化劑等進行分區治理,技術對靶性高、修復效果明顯。
(2)經過2 a 的實施,采用石灰+鎘鈍化劑、石灰+鎘砷同步鈍化劑配合低砷積累品種和水分優化管理的技術模式,皆顯著提升了土壤pH 值(增加0.76~1.31)、降低了土壤有效態鎘含量(下降18.18%~21.43%),從而降低了稻米鎘含量(下降31.03%~90.32%),提升了稻米鎘達標率(增加47.57~84.70 個百分點);石灰+鎘砷同步鈍化劑配合低砷積累品種和水分優化管理的技術模式,通過2 a 的實施也顯著降低了稻米砷含量(降低22.22%~36.36%),稻米砷達標率達100%。
(3)針對大面積稻米鎘砷超標區域,以優先降鎘、協同控砷的策略進行修復治理,可同步實現稻米鎘砷的同步達標生產,但因根據區域稻米鎘砷超標風險程度和稻田鎘砷污染特征進行技術的優化調整。
3.2 討 論
稻田重金屬污染的修復治理,尤其是鎘砷復合污染稻田的安全利用一直是農業環境研究的重點和難點。湖南是我國重金屬污染嚴重的省份,2014 年,湖南啟動了長株潭重金屬污染耕地修復治理試點,試點取得了較好的成效。該試點以土壤鎘污染程度進行分區治理,但也面臨責任主體難以確認,修復治理資金缺口大,社會參與度低,修復技術尚不成熟等諸多困境,導致修復效果不穩定[4]。該范項目則基于稻米重金屬超標程度進行污染風險分類分級分區治理,修復技術綜合了稻米重金屬污染程度和土壤理化性質特征,并強化了責任主體參與程度,充分考慮土壤pH 值、有機質、CEC 等因素的影響,修復技術精準性更高、對靶性更強[5-6]。研究中,針對稻田土壤酸化嚴重的特點,通過施用石灰質復合材料進行pH 值調節,同時,針對稻米鎘、砷超標及土壤鎘活性特征,分別選擇單鎘鈍化劑和鎘砷復合產品進行修復治理,采用石灰質復合材料與硅基鈍化劑配施,降鎘效果更加明顯,也更加高效[7]。
受淹水落干交替影響,稻田鎘砷表現出完全相反的化學行為特征[8],稻米鎘含量的下降往往伴隨著稻米砷含量的增加[9-10],鎘砷復合污染修復治理難度極大。該項目中,白水項目區稻米鎘砷超標嚴重,采用石灰質復合材料調理土壤酸性,同時施用鎘砷同步鈍化產品對鎘和砷同步鈍化的技術策略。經過2 a 的連續修復治理,稻米降鎘效果明顯,土壤pH 提升顯著,土壤有效態鎘含量逐年下降,稻米鎘含量逐年降低。但稻米砷含量呈先升后降趨勢,表明鎘砷同步鈍化產品在輕度砷污染情況下效果明顯,而在污染程度較高時需要增加用量或者累積施用才能顯示其降砷效果。有研究表明,降砷效果需要通過加大用量或通過多年的累積效應[11-14],但其作用機理和調控機制還有待深入研究。
該項目以稻米鎘、砷含量進行污染風險管控,并以優先降鎘、協同控砷的策略開展了大面積的修復治理示范,2 個項目區實施第一年的稻米降鎘效果皆十分明顯,稻米鎘達標率得到顯著提升。肖家項目區通過石灰+單鎘鈍化劑、石灰+鎘砷同步鈍化劑進行鎘污染的修復,并通過低砷水稻品種和水分優化管理抑制了稻米的砷超標風險;而白水項目區通過石灰+鎘砷同步鈍化產品治理鎘污染的同時進行砷的鈍化,并結合砷低積累水稻品種和水分優化管理,也實現了稻米鎘砷污染的同步控制。可見,該項目技術路線和修復策略可實現大面積鎘砷污染稻田的修復治理和風險管控,但受不同地區稻米鎘砷超標風險和稻田鎘砷污染特征的差異,其修復治理對策和風險管控模式需要因地制宜的進行優化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