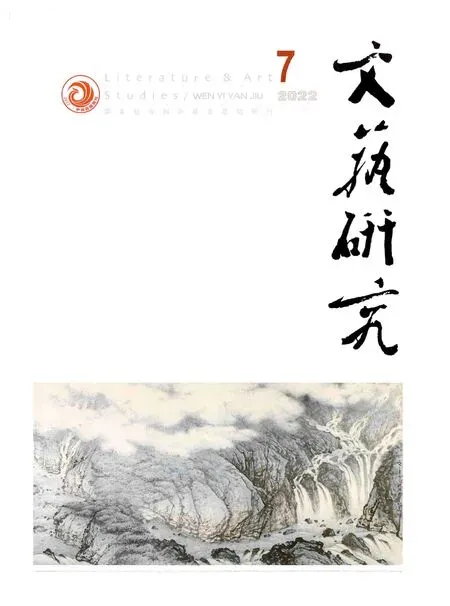“代行體”戲劇芻議
張長彬 仝婉澄
一、問題的提出
本文所謂“代行”一詞,并非一般語境中的代人行使職權之義。我們嘗試將其作為一個學術概念提出并使用,與戲劇學中的“代言”相并論,指扮作他者以代其發出動作、行為。作為戲劇學術語的“代言”一詞,由王國維提出。在其《曲錄》等作品中已出現此詞,而引起學界普遍關注的論述則出自《宋元戲曲史》:
現存大曲,皆為敘事體,而非代言體。即有故事,要亦為歌舞戲之一種,未足以當戲曲之名也。
唐代僅有歌舞劇及滑稽劇,至宋金二代而始有純粹演故事之劇,故雖謂真正之戲劇起于宋代,無不可也。然宋金演劇之結構,雖略如上,而其本則無一存,故當日已有代言體之戲曲否,已不可知。而論真正之戲曲,不能不從元雜劇始也。
元雜劇之視前代戲曲之進步,約而言之,則有二焉。……其二則由敘事體而變為代言體也。宋人大曲,就其現存者觀之,皆為敘事體;金之諸宮調,雖有代言之處,而大體只可謂之敘事。獨元雜劇于科白中敘事,而曲文全為代言。雖宋金時或當已有代言體之戲曲,而就現存者言之,則斷自元劇始,不可謂非戲曲上之一大進步也。
由于王國維對“代言”及“代言體”概念未予界定,后人理解不盡相同。統觀上述話語,不妨對其所謂“代言”作最樸素的理解,即表演者進入角色代他人發言。從第三則材料來看,王國維認為“代言”只是“戲曲上之一大進步”而已。換言之,王國維認為從“非代言”到“代言”,只是戲劇的一種量變,而非質變。再結合第二則材料,王國維認為不以“代言”形式演出者雖非“真正之戲曲”,但可能是“真正之戲劇”,只要其“純粹演故事”,如宋金雜劇。甚至連嚴格的故事也不演,王國維仍未否認其為戲劇,如唐代的歌舞劇及滑稽劇。這一觀念符合當今戲劇學界多數人的認識,否則,那些儀式劇、啞劇之流便無法納入戲劇學研究范疇。持這種觀念的問題在于:如果“代言”并非戲劇的構成要件,那是什么決定了戲曲之前的那些演劇形態——如宋金雜劇、唐歌舞戲及滑稽劇等——可以被判定為戲劇呢?
當前的主流回答或曰“扮演”,或曰“角色扮演”。然而,扮演的內涵非常豐富,其手段和類型也十分駁雜。關于扮演的類型,康保成的分類頗有啟發意義,他在《試論戲劇的本質與中國戲曲的特色》一文中把扮演分為自然角色扮演、社會角色扮演、游戲角色扮演、儀式角色扮演和戲劇角色扮演五類。該文對什么不是戲劇角色扮演進行了舉例,但并沒有進一步指明到底什么樣的角色扮演才是戲劇所專有。事實上,根據假扮對象的不同,這些角色扮演可以分作兩大類:第一類是“假扮作自身”的非天然狀態,自然角色扮演、社會角色扮演、游戲角色扮演、儀式角色扮演基本上都屬于這一類;第二類是“假扮作他者”的狀態,即戲劇角色扮演。人在自然、社會、游戲中的角色無論花樣如何繁多,大體上均沒有改變自我的身份,這種扮演都是對自己的扮演。而在戲劇中,人所假扮的皆是他人,是代他人做出行為、言語。因此,戲劇角色扮演區別于其他角色扮演的特殊之處便在于代他人言行,包括代他人發言和代他人行動。如果前者可以簡稱作“代言”,那么后者可簡稱為“代行”。“代言”與“代行”都有廣狹兩種涵義:“代言”狹義指代人說話,廣義指代人作出語言、動作、表情、思想等全面作為;“代行”狹義指代人做出動作,廣義指代人進行全面作為。本文所用“代言”與“代行”,均作狹義理解。
既然“代言”并非戲劇的構成要件,那是什么決定了戲曲之前的演劇形態可以被判定為戲劇呢?答案是“代行”。王國維認為戲曲之前的演劇形態并無“代言”形式,但同時又承認它們都是戲劇,即認定它們都擁有戲劇角色扮演的特質。顯而易見,這種“非代言”的戲劇角色扮演,只能通過“代行”的方式實現,現有文獻總體上支持這一推理。從邏輯上來說,“代行”已包含了戲劇成立的充分必要條件——凡扮作他者代之行動的行為便可視為戲劇角色扮演;反之,戲劇角色扮演只需“代行”一個條件即可成立,“代言”只不過是戲劇角色扮演的高級手段而已,其存在與否并不影響戲劇的成立。從歷史事實來說,王國維認為宋金時期尚無“代言體”戲劇,這一說法雖不免絕對,但將宋金以前的主流戲劇視為“非代言體”是基本準確的。換言之,宋金以前的這段時期可以看作是中國戲劇史上的“代行體”時代。
二、中國戲劇史上的“代行體”時代
本文所說的“代行體”,是指以“代行”為主要藝術手段的戲劇形態;而“代言體”,是指以“代言”為主要藝術手段的戲劇形態。中國成熟態的藝術戲劇——戲曲,兼用“代行”與“代言”兩種手段,盡管“代言”看起來效用更大,但離開了“代行”,則不成戲劇,故本文稱之為“兼代體”。
早期的中國戲劇以“代行”手段為主、“代言”為輔,之后“代言”手段逐漸發展,兩者于宋元時期合流,形成了戲曲,從此進入“兼代體”時代。在戲曲形成之前的這段時間,可視之為“代行體”戲劇時代。這一時期,“代行體”戲劇的主要形態先后表現為圖騰戲、角抵戲和歌舞戲。人的動作是這些戲劇形態的主要表現手段,并且是扮演活動的敘事骨架。有趣的是,“代行”不一定非要以真人去完成,各種形式的人偶也可以“代行”。于是,以上三種戲劇形態皆出現了其人偶模仿態,即相應形式的傀儡戲、影戲等形態,這些戲乃“代行體”戲劇的衍生形態。此中的高級形態還會發展出比真人“代行體”更具內涵的新形態,然后又被真人模仿,它們是“代行體”戲劇的二次衍生形態。以上事物的關系如下表所示:

“代行體”戲劇演化格局表
上表所呈現出的關系框架說明,如果沒有“代行”這一機制,很多事物便無由發生。以下依次探討圖騰戲、角抵戲、歌舞戲及其衍生形態的存在狀況及相互關系。
(一)圖騰戲及其衍生形態
圖騰,即神的象征或符號,既可以用靜態的圖飾表達,也可以用動態的扮演表達。圖騰戲則以扮演圖騰的動態形象為主,還可以扮演與圖騰相配合的其他形象,盛行于上古時期。上古戲劇研究最重要的成果當屬王勝華《中國戲劇的早期形態》一書,該書將中國戲劇的早期形態分為六種,其中前五種都可歸入圖騰戲,它們分別是以角色裝扮為中心的模仿形態、以狩獵表演為特征的擬獸形態、以逐除不祥為主要功能的巫術形態、以敬神祈福為目的的祭祀形態、國家宗廟祭祀的樂舞形態。這五種圖騰戲的形態,無一不以“代行”為主要演出手段。
茲以一個文獻遺留較為豐富的圖騰戲劇——漢代儺戲——予以說明。劉昭注補《后漢書·禮儀志》云:
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皂制,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仆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于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歹兇,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兇,赫女軀,拉女干,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后者為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
這段話所記錄的儺儀情形,重心似乎在于由中黃門領唱、侲子應和的那段驅儺辭。但嚴格來說,驅儺辭并不屬于儺戲的部分。前文說過,戲劇角色扮演的本質在于“假扮作他者”,這是區別于其他種類角色扮演的特殊所在。中黃門、侲子在儀式中的行為固然屬于角色扮演,但他們所扮演的只是自己的一種特殊身份,并未扮作他者。他們的唱辭表達了自己及其身后所代表人群的意愿,并未代他者發言。換言之,以使用“言”的角度去衡量,他們也沒有“代言”。因此,這些人只是儀式上的角色,而不是戲劇中的角色;他們只在儺儀之中,而不在儺戲之中。這場儺戲中的扮演者只有方相氏與十二獸,他們完全是以“代行”的方式進行表演。
儺戲雖發源于上古,但直至今日的大部分儺戲依然只是“代行”表演。另外要認清的是,儺戲并沒有獨立存在的地位,它們始終只是一種“寄生性戲劇”,即寄生在儀式中的戲劇。甚至可以說,一切圖騰戲都是“寄生性戲劇”。

(二)角抵戲及其衍生形態
角抵戲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指有故事性的,以《東海黃公》為代表;廣義指除此之外還包括雜技、幻術等非敘事性形體表演,又總名“百戲”或“散樂”。這兩種意涵的事物之所以能夠共名,在于其都寄托于形體表演。本文所討論的角抵戲都屬狹義范疇。角抵戲的起源,有“角力說”“蚩尤說”“擬獸說”等。當圖騰戲逐漸沉寂的時侯,角抵戲走向了前臺,成為秦漢乃至南北朝時代一枝獨秀的戲劇形態。
說角抵戲是“代行體”,一定不會產生異議。這里需要重點說明的是角抵戲的底層原理,這也是“代行體”戲劇得以成立的直接證據。角抵戲的代表劇目是《東海黃公》,《西京雜記》有相關記載:“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為幻術,向余說古時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為術,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發,立興云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于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為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漢帝亦取以為角抵之戲焉。”學界對這段材料的引用評說極多,卻很少有人對“取以為角抵之戲”這句話作出關注。所謂“取以為角抵之戲”,即把具有相關資質的故事編入角抵這種動作表演。這句話道出了中古戲劇的底層進化機制,即利用“代行”可以實現故事敷演,而故事又將“代行”式表演推向了意象詮釋的新高度。“代行”能夠承載故事,這一點在圖騰戲中就有初步體現,“取故事入角抵”是對“代行”承載故事能力的進一步開發。在此之前,圖騰戲中的“代行”只能表達片斷的意象,或將多個片斷的意象以弱邏輯甚至無邏輯的形式不連續地組接起來。將一個完整的故事融入角抵,可能仍然無法連續地傳達情節,故事的講述方式仍然是片斷式的串連組接(如《缽頭》之“歌八疊”),但這些片斷之間具有了強邏輯,這一點是“代行體”戲劇在這個時代的最大躍遷。另外,從語法上來看,“取以為角抵之戲”中的“角抵”顯然指廣義的角抵,即一般意義上的角力、幻術表演;而只有將故事編入角抵,狹義的角抵戲才能實現。換言之,“取故事入角抵”機制的發明造成了廣義與狹義的角抵戲分野。
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東海黃公的故事何以能夠被編入角抵?哪些特殊素質使它獲得了被編入角抵的資格?答案很明顯,因為黃公善幻術,能“立興云霧,坐成山河”,又曾與虎相斗,這些元素與傳統的廣義角抵相一致,因此方可編入角抵為戲。換言之,可以編入角抵戲的故事不是隨意的,而須自帶角力、幻術等元素。
據此還可以確定,傳說中的“魚龍幻化”“遼東妖婦”也屬于這一形態的狹義角抵戲。關于“魚龍幻化”,《漢書·西域傳》曰:“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顏師古注“魚龍”曰:“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于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于庭,炫耀日光。”黎國韜考定“魚龍幻化”就是漢代的戲劇,并斷言它的生成機制與《東海黃公》一樣,都是以采故事入角抵的方式實現的,其所采者為兩漢時期流行的“魚化為馬(龍)”故事。今從“代行體”戲劇發展路線的視角也可以證實這一說法:“魚龍幻化”與《東海黃公》一樣,實為該時期“代行體”戲劇的典型形態,它的故事之所以能被編入角抵,是因為其情節同樣具備適宜于廣義角抵表演的雜技、幻術等形體演出要素,如激水、跳躍、變形、作霧等。
“遼東妖婦”是曹魏宮廷中的一個節目,《三國志·魏書·齊王芳紀》裴松之注引司馬師《魏書》曰:“皇帝即位,纂繼洪業,春秋已長,未親萬機。……日延小優郭懷、袁信等于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戲,使與保林女尚等為亂,親將后宮瞻觀。又于廣望觀上,使懷、信等于觀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于觀上以為燕笑。”對此則記錄,王國維云:“則此時倡優,亦以歌舞戲謔為事;其作遼東妖婦,或演故事,蓋猶漢世角抵之余風也。”王國維出言較為謹慎,既云其為“歌舞戲謔”,又云其是“角抵之余風”,然都未予以論證。后來的學者認定其為戲劇者,幾乎皆視之作歌舞戲,并以為“妖婦”者乃妖冶之婦人。事實上,這里的“妖婦”不宜作“妖冶婦人”解,因為“她們”是男性優人所扮。更重要的是,若以妖冶誘人,則以近觀為佳,為何要在觀下作戲而其主要觀眾于觀上觀之呢?這說明它的表演需要較大的空間,只宜遠觀。什么樣的表演需要這么大的空間?“魚龍幻化”的表演可以提供對照,按照顏師古的說法,“魚龍幻化”的表演在庭、殿兩處空間輪番開展,下能入水,上可障日,演出占用空間極大。“遼東妖婦”之所以要于廣望觀下表演,其形態必與芙蓉殿前的“裸袒游戲”差別極大,也許它仍然未脫離裸袒淫褻的品質,但其表演方式必有特殊之處。其特殊之處當與“魚龍幻化”相通,即都包含幻術表演。因此,這里的“妖婦”理當作“會妖法的女子”解,廣望觀下的表演或應包括形體變化、興風作浪、角力戰斗等元素。這種表演符合古代“妖女”的一慣形象,一是精通妖法,二是美艷淫褻。由于上引文字出自群臣欲廢皇帝之奏章,故而只強調了其“嬉褻”的一面,未言及表演形式。據此可以斷定,“遼東妖婦”乃是與《東海黃公》、“魚龍幻化”性質相同的角抵戲,主要以幻術、雜技等“代行”表演敘遼東妖女之故事。
隋唐時期,傀儡戲的表演顯示出漢魏角抵戲的近似特征,它們應是此類角抵戲的衍生形態。如《大業雜記》載隋煬帝曾于三月上巳會群臣于曲水以觀水飾,水飾中最重要的項目為“刻木為之”的“七十二勢”,其木雕形象“皆能運動如生”,其中的一勢為“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表現的恰恰是角抵戲“魚龍幻化”的內容。“周處斬蛟”“巨靈開山”“劉備乘馬渡檀溪”等勢天然具有施用于幻術表演的特質,“孔子值河浴女子”“秋胡妻赴水”等則深具故事性與動作性,其題材很有可能也是直接來源于角抵戲。
如果說“七十二勢”所模仿的只是角抵戲的簡單畫面,還難以算得上“代行體”戲劇的話,那么唐代大歷中的“祭盤傀儡”就是完整意義上的角抵戲模仿了。封演《封氏聞見記》曰:“大歷中,太原節度使辛景云葬日,諸道節度使使人修祭。范陽祭盤最為高大,刻木為尉遲鄂公、突厥斗將之戲,機關動作,不異于生。祭訖,靈車欲過,使者請曰:‘對數未盡。’又停車,設項羽與漢高祖會鴻門之象,良久乃畢。缞绖者皆手擘布幕,收哭觀戲。事畢,孝子陳語于使人:‘祭盤大好,賞馬兩匹。’”這段話中的“良久乃畢”一語十分關鍵,從中可以確知此種傀儡表演有一定的時間長度,祭盤上的傀儡應以一系列的動作完成了對鴻門宴故事的表述。并且,由于傀儡的表現手段有限,傀儡戲對角抵戲的模仿最長于角力之一面,“尉遲鄂公”“突厥斗將”“鴻門宴”等節目都體現了這一特征。
(三)歌舞戲及其衍生形態
歌舞戲是“代行體”戲劇的第三種典型形態。歌舞幾乎與中國古代的每一種戲劇形態都有或深或淺的關系,而在戲劇史上能以“歌舞戲”稱名者,主要存在于六朝至兩宋期間。《通典·樂六·散樂》言:“歌舞戲,有《大面》《撥頭》《踏搖娘》、‘窟礧子’等戲。”《通典》以后,古人對于“歌舞戲”一語的使用并不多,即便使用也幾乎專門用來指代《大面》《撥頭》諸戲。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簽》又將參軍戲、假婦人、弄假大獵兒、排闥戲等歸入散樂之歌舞戲類,與《大面》《撥頭》等相并列。自王國維以來,學界對“歌舞戲”概念的應用較為頻繁,而對其外延的理解多有不同。以“代行”為根本要素觀之,則歌舞戲的范圍必然有所擴大。前文已言,“代行”就是扮作他者代之行動,根據這一原則,可將這一時期的歌舞戲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傳統所謂的歌舞戲,其特色是故事性較強,可稱之為“典型性歌舞戲”;第二類是寄生于“曲”的“代行”歌舞,其特色是故事性較弱,在具體節目中不占主體地位,可稱之為“寄生性歌舞戲”。
“典型性歌舞戲”乃由角抵戲演化而來,將漢魏角抵戲去其幻術并加強韻律歌舞,便是這類歌舞戲的大體面貌。“典型性歌舞戲”的發展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唐前時期,其代表劇目為《大面》《撥頭》《踏搖娘》,其特征是未完全脫去角抵色彩;第二階段為唐五代時期,其劇目以《唐音癸簽》新列入的參軍戲、假婦人、弄假大獵兒、排闥戲為代表,其特征是引入了“調弄”元素。
“寄生性歌舞戲”以唐宋隊舞為其代表。導致其歸屬長期陷入“舞”與“戲”兩可境地的決定性元素在其“舞”而不在其“歌”,換言之,即在于其“代行”與否,而不在其“代言”與否。如史浩《劍舞》,該作品對舞容的描述(即“鴻門宴”“公孫大娘舞劍器”兩個情節片斷)使人認為此節目具有了戲劇的性質。從整體來看,這些戲劇化的片斷只是一臺歌舞的構成元件,但如果對這兩個舞蹈單元進行獨立定性,那么它就是一種“寄生性歌舞戲”。早在漢魏時代,此類“寄生性歌舞戲”就已存在。東漢張衡《西京賦》曰:“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而襳襹。度曲未終,云起雪飛。”三國吳薛綜注曰:“洪涯,三皇時伎人,倡家托作之。”薛綜的注文彰明了當時的歌舞節目中存在“戲劇角色扮演”的成分。
王廷信曾提出一條中國戲劇形成路線,即“從‘托故事而歌舞’到‘以歌舞演故事’”。事實上,本文所說的“典型性歌舞戲”與“寄生性歌舞戲”就分別對應著“以歌舞演故事”與“托故事而歌舞”兩種機制。在隋唐之際,這兩種歌舞戲都十分簡陋,均面臨著如何發展成大型戲劇的難題。但它們所面對的具體困境并不相同:對于“典型性歌舞戲”來說,不存在向真正戲劇轉化的問題,其本身已是“以歌舞演故事”形態,它所要突破的是單純的“代行”式表演無法表現更復雜內容的難題;對于“寄生性歌舞戲”來說,它卻要歷經一個從“托故事而歌舞”到“以歌舞演故事”的艱難蛻變。當然,也有第三條路線可以選擇,那就是聯合發展。有證據表明,二者也曾經嘗試過聯合,如日本雅樂中就保存著由唐代參軍戲與唐大曲相結合的節目“盤涉參軍”。但總體來說,這兩種歌舞戲主要還是以各自獨立發展的姿態向大型戲劇慢慢靠攏的。
“典型性歌舞戲”的發展方法是引入俳優調弄的表演機制,即引入“代言”要素。前文把“典型性歌舞戲”的存在分為兩個階段,從兩階段劇目的名稱中就可以感受出其差異——第二期劇目的調弄色彩濃厚,這一特征正是來自俳優傳統。《踏搖娘》進入唐代以后的風格轉變也很能說明這一點。較之《通典》,《教坊記》對《踏搖娘》的描述多出這樣幾句話:“及其夫至,則作毆斗之狀,以為笑樂。今則婦人為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子’;調弄又加典庫,全失舊旨。”可見,導致《踏搖娘》“全失舊旨”的改編乃是唐代戲劇的一種新風氣。俳優調弄主要以言語為表現手段,這也就為“典型性歌舞戲”引入了“代言”機制,可以說隋唐五代時期的“典型性歌舞戲”已初步具備了“兼代體”的要素。
“寄生性歌舞戲”的發展軌跡十分晦昧,但仍有大量證據表明它們一直廣泛存在,尤以宋代的“官本雜劇段數”為明證。該劇目中的作品一半以上都帶有樂曲名,此現象應視為“寄生性歌舞戲”突圍成功的表現:在《六幺》《瀛府》《梁州》《薄媚》等一系列的曲目中,歌舞戲終于反客為主,由附庸一變而為主宰,由此,它們才被視作雜劇,而不再被視為舞蹈或樂曲。另外,敦煌遺書斯2440號卷背上的一件文書,被很多學者視為劇本,其實可以將它看作是從“寄生性歌舞戲”發展為“獨立性歌舞戲”的一種初期形態。它有角色扮演,有舞有歌,主題不蔓不枝,敘述了悉達太子出家緣起,故事有一定長度,當與“官本雜劇段數”中的部分歌舞類節目相近似。
歌舞戲也有其傀儡形態,《通典》等文獻所記載的“窟礧子”即屬此類:“‘窟礧子’,亦曰‘魁礧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樂也,漢末始用之于嘉會。北齊后主高緯所好。高麗之國亦有之。今閭市盛行焉。”這里所說的“窟礧子”應是一般意義上的傀儡表演,而非具體節目名稱。關于它何時用以演出歌舞,其歌舞是否演故事,這段話都沒有明說。《通典》將其與《踏搖娘》等歸為同類,或因這種傀儡表演是對“典型性歌舞戲”的模仿。
至此可見,三種形態的“代行體”戲劇在傀儡方面都有其模仿態。然而,傀儡戲的發展也并非完全被動,宋代的傀儡戲已發展出非常豐富的樣態,其中有些已超越了對真人表演的模仿。《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條曰:“杖頭傀儡任小三,每日五更頭回小雜劇。”《都城紀勝》“瓦舍眾伎”條曰:“凡傀儡敷演煙粉靈怪故事、鐵騎公案之類,其話本或如雜劇,或如崖詞,大抵多虛少實,如巨靈神、朱姬大仙之類是也。”據此可知,宋代的傀儡戲既有模仿真人雜劇的新品種“杖頭傀儡小雜劇”,又有自主發展而來的可以敷演長篇故事的“話本傀儡戲”。后者乃是說話伎藝“依相敘事”傳統與傀儡戲相結合的產物。孫楷第認為后世的戲曲即源于這種傀儡戲,這一說法雖未必成立,但這種傀儡戲必然會對真人戲劇有所啟示:劇壇上終于有了一種戲劇形態可以演述長篇故事,它為戲劇的發展指明了發展方向——扮演長篇故事。這個重要啟示的獲得與“代行”表演的存在休戚相關,因為導致“話本傀儡”可被視為“戲”而不僅是“話本”的唯一元素,就在于傀儡的“代行”表演。
通過以上對“代行體”戲劇發展歷程的梳理,可以得出如下認識。自上古迄宋金為“代行體”的戲劇時代,“代行”決定了這個時代絕大部分戲劇的“角色扮演”本質:圖騰戲、角抵戲幾乎全以“代行”表演,大部分的“典型性歌舞戲”以“代行”表演為主,“寄生性歌舞戲”“話本傀儡戲”亦因“代行”才被視為“戲”,唯有少數的“典型性歌舞戲”呈現出了“兼代體”的勢頭。
最后,再總結一下三種“代行體”戲劇的發育差異。圖騰戲以“代行”演意象,有故事意味,但無故事行進線索,以漢代大儺為代表。角抵戲以“代行”演故事,有故事行進線索,與歌舞戲相比,其“代行”手段更多體現在角力、幻術等非韻律性動作方面,以《東海黃公》為代表。歌舞戲分為兩類:“典型性歌舞戲”故事線索分明,“代行”手段既有角斗、雜技等非韻律性動作,又有合樂舞蹈一類的韻律性動作,以《踏搖娘》為代表;“寄生性歌舞戲”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之內都無法獨立存在,它寄生于歌舞之中,只演意象,不敘故事,其“代行”手段主要為韻律舞蹈,以唐宋隊舞為代表。此外,這三種“代行體”戲劇都有其傀儡戲或影戲模仿態,有些模仿態在戲劇發展的道路上先行一步,可以敷演長篇故事,這種能力是“代行體”時代中真人戲劇所不具備的。
三、“代行體”概念提出之價值
“代言”與“代行”,廣義上雖都可以理解為扮作他人以言行之義。但“代言”的廣義內涵是源于文化習慣而非語義邏輯,“言”無論如何也不能包含“行”,語義上“代言”無法兼有代人言行之義。“代行”則不然,“行”可以包括“言”,“言”不過是“行”的特殊形態而已,故用“代行”一語表扮作他人以言行之義,既有語義優勢,又符合認知習慣。但這并非我們提出“代行體”概念的根本理由。之所以提出這一概念,是因為“代言體”的說法造成了諸多誤會,它不僅模糊了中國戲劇史的事實真相,造成中國戲劇史的前后脈絡不通,還掩蓋了中外戲劇史的共同性質,致使中外戲劇的比較研究難獲要領。而“代行體”概念的提出,或可突破這些困局。
首先,它能平息何謂“真戲劇”的紛爭。王國維雖沒有否認元前有戲曲、宋前有戲劇,但又認為只有宋金以后的戲劇才是“真正之戲劇”。任半塘的戲劇史觀則與王國維不同,他認為宋前就有“真戲劇”,唐代尤盛,由此引起學界關于何謂“真戲劇”的大討論。任半塘《唐戲弄》提到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史)》近一百三十次,其中絕大多數與其討論的都是何謂“真戲劇”的問題。任氏唐戲研究的學術功績讓學人贊嘆,但時至今日仍有人對他“唐前有戲”的結論持不同意見或重視不夠。學界還有一種聲音即批評《唐戲弄》一書有“想象多于事實”的缺點,這種“缺點”的表現之一就是任氏用了不少筆墨去論證唐戲已有“代言”的表現手段。任半塘在接受王國維“戲劇本質觀”的前提下去反對其“戲劇史觀”,論證時當然會捉襟見肘,但當今學界主流其實已經認可了任半塘的戲劇史觀,否則宋前戲劇研究的學理基礎就不能成立。既然如此,任半塘在《唐戲弄》中論證未圓的問題就成了宋前戲劇研究界要集體面對的學術困境,具體來說就是要證明宋前的演劇為什么是“真戲劇”。當認識到戲劇的根本表現手段在于“代行”而不是“代言”時,這一難題便迎刃而解:從上古到唐代的戲劇都有“代行”因素,已具備“真戲劇”的充要條件。
其次,它能夠使宋元前后的戲劇史變得連貫統一。《宋元戲曲史》將中國古代戲劇史分為性質不同的兩段:宋金以前為“古劇”時代,“古劇者,非盡純正之劇,而兼有競技游戲在其中”;元代以降為“戲曲”時代,“真戲劇必與戲曲相表里”,“必合言語、動作、歌唱,以演一故事”。從本文首節所引《宋元戲曲史》之語可知,王國維認為關乎戲劇本質的兩個關鍵詞是“演故事”與“代言”,前者基于戲劇的藝術目的,后者基于戲劇的表現手段。但兩者都無法將前后兩段的戲劇史貫穿起來:“代言”乃突變基因,是宋前戲劇幾乎不具備的東西,無法統攝“古劇”;“演故事”在“古劇”中雖有所表現,但并非顯性特征,“古劇”的藝術目的顯然在于“炫技”以追求某種驚人效果,而不在于講故事,故事不過是戲劇難以擺脫的載體而已。因此,由王國維所草就的中國古代戲劇史的格局始終斷作兩截而無法彌合。這種“斷裂”乃認識上的斷裂,而非真實歷史的斷裂。若以“代行”表演為審視維度,中國戲劇史就有了一條貫穿首尾的主線。當我們找到這條主線,宋元戲劇的主要問題便不再是“代言”為什么會發生、“長篇故事劇”為什么涌現這類的突變性問題,而轉變成戲劇表演的藝術手段是如何一步步豐富的這類漸變性問題。當這類漸變性問題得到解決時,那些突變性問題自然也會有其答案,因為那些所謂的突變性問題并非中國戲劇發展的動因與目的,而只是“古劇”自然發展的結果而已。
最后,它能夠使中國戲劇與世界戲劇的研究進一步密切關聯。世界各地的戲劇發展其實都經歷過“代行體”與“代言體”兩個時代,只不過西方戲劇“代行體”時代非常短暫,“代行體”戲劇發育不夠充分。雖然如此,但也有文獻表明西方存在著形態豐富的“代行體”戲劇,如古希臘酒神祭祀活動中扮演狄奧尼索斯信徒的行為,又如亞里士多德《詩學》提到的以動作摹仿為表現手段的多里斯人的戲劇。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主流戲劇理論從古至今都強調“動作摹仿”是戲劇的本質表現手段。如亞里士多德說:“悲劇是對于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動作來表達,不是采用敘述法。”戲劇與表演理論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認為:“在舞臺上需要動作。動作、活動——這就是戲劇藝術、演員藝術的基礎。”蘇聯導演拉波泊指明演員的任務是:“再現人的動作來再現角色。”美國戲劇理論家約翰·霍華德·勞遜指出:“動作是戲劇的根基。”美國理論家喬治·貝克稱:“歷史無可置辯地表明,戲劇從一開始,無論在什么地方,就極其依靠動作。”因此,“代行體”概念的提出對中西戲劇研究交流具有如下幾點意義。第一,便于理解西方戲劇理論界強調“動作”的深層原因,與西方的戲劇研究者達成共識。第二,能夠使東西方戲劇的理論與實踐獲得交互印證。東方戲劇理論重“言”、實踐重“行”,西方戲劇理論重“行”、實踐重“言”,都無法獨立自洽,如雙方的戲劇理論都能“言”“行”并重,東西方戲劇的理論與實踐便能獲得交互闡釋。第三,承認“代行”是戲劇的基礎表現手段,中國戲劇史的起點便可與西方同步甚至更早,中國戲劇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便會進一步提高。若對標西方戲劇的發展事實而以“代言”為戲劇的基礎表現手段,則中國戲劇史的起點必晚至宋元。事實上,東西方早期戲劇的發展只是重心不同,起點上并無顯著差別,價值上也無高低之分。
有鑒于此,本文就中國戲劇中的“代行”問題做出了初步探討,并得出了如下認識:“代行體”戲劇也是“真戲劇”,中國戲劇史上的“代行體”時代十分漫長,中國“古劇”是世界上發展最充分的“代行體”戲劇,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價值。
①[15][33][34]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1、62—63頁,第6頁,第58頁,第32頁。
② 參見胡琳:《元雜劇代言體形態研究》,河北大學2014年碩士學位論文。
③ 如王勝華認為“扮演是戲劇最基本的特質”,而中國的主流辭書如《辭海》等,則以“演員扮演角色”作為戲劇的本質特征(王勝華:《扮演:戲劇的本質存在——對戲劇本質思考的一種發言》,《戲劇》1996年第1期;夏征農、陳至立主編:《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版,第2465頁)。
④ 康保成:《試論戲劇的本質與中國戲曲的特色》,《海內外中國戲劇史家自選集·康保成卷》,大象出版社2018年版。此文原載《古代文學研究集刊》第1輯,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
⑤ 世界上雖存在以“代言”為主要表現手段的戲劇,如廣播劇,但不存在以“代言”為單一表現手段的戲劇。廣播劇中一般也有表動作的配音且必然隱含與動作相關的信息,而且從廣義上來看,“言”本身也是一種“行”,所以世界上不存在能脫離“代行”的戲劇,而“代言”則可有可無。
⑥ 參見王小盾:《序》,王勝華:《中國戲劇的早期形態》,云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頁。
⑦ 《后漢書》卷九五,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127—3128頁。
⑧ 《后漢書》卷一三五,第3273頁。
⑨ 孫楷第:《傀儡戲考原》,《孫楷第文集·滄州集》,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40—146頁。
⑩ 參見張爽:《角抵戲研究》,江西師范大學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
[11] 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雜記》,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頁。
[12] 《漢書》卷九六,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928—3930頁。
[13] 參見黎國韜:《“魚龍幻化”新考及其戲劇史意義發微》,《文學遺產》2017年第4期。
[14] 《三國志》卷四,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29頁。
[16] 參見杜寶撰,辛德勇輯校:《大業雜記輯校》,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3頁。
[17] 封演撰,李一飛整理:《封氏聞見記》,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第631頁。
[18][27] 杜佑:《通典》卷一四六,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729頁,第3730頁。
[19] 參見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頁。
[20]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之《宋之樂曲》所提到“傳踏”“曲破”“大曲”等都屬于此類歌舞戲。
[21] 參見劉永濟:《宋代歌舞劇曲錄要》,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53—56頁。
[22] 蕭統編,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二,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59頁。
[23] 參見王廷信:《從“托故事而歌舞”到“以歌舞演故事”——中國戲劇形成之主脈》,《民族藝術》2004年第3期。
[24] 參見葛曉音:《從日本雅樂看唐參軍和唐大曲的表演形式》,《北京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
[25] 任中敏箋訂,喻意志、吳安宇校理:《教坊記箋訂》,鳳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頁。
[26] 參見任中敏著,楊曉靄、肖玉霞校理:《唐戲弄》,鳳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617—621頁;李正宇:《晚唐敦煌本〈釋迦因緣劇本〉試探》,《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李小榮:《敦煌雜劇小考》,《社會科學研究》2001年第3期。
[28][29] 孟元老等:《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29頁,第97頁。
[30] “依相敘事”乃徐大軍提出的一個概念,指源于變文的配圖輔助講唱之格式(徐大軍:《宋元通俗敘事文體演成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34—61頁)。
[31] 參見孫楷第:《近世戲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戲影戲考》,《孫楷第文集·滄州集》,第158—204頁。
[32][35] 參見張長彬:《感紅觀堂聯珠日,應是劇史合璧時——從任中敏和王國維看戲劇史研究的可能出路》,《曲學》第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36] 參見潘薇:《西方戲劇史》,大眾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2頁。
[37][38] 參見亞里士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中國戲劇出版社1986年版,第5頁,第12頁。
[39]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2卷,林陵、史敏徒譯,鄭雪來校,中國電影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頁。
[40] 拉波泊、查哈瓦:《演劇教程》,曹葆華、天藍譯,新華書店1950年版,第31—32頁。轉引自譚霈生、路海波:《話劇藝術概論》,中國戲劇出版社1986年版,第136頁。
[41] 約翰·霍華德·勞遜:《戲劇與電影的劇作理論與技巧》,邵牧君、齊宙譯,中國電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頁。
[42] 喬治·貝克:《戲劇技巧》,余上沅譯,中國戲劇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