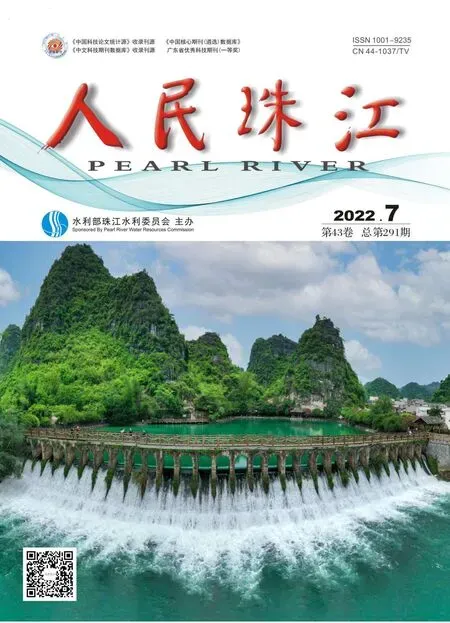氣候變化和土地利用變化對黃河源區徑流變化的累積影響評估
劉壯添,陳睿智,王 未
(珠江水利委員會珠江水利科學研究院,廣東 廣州 510611)
近年來,全球前200條河流中約1/3的徑流量發生了顯著變化[1]。其中,氣候變化和土地利用變化是徑流變化的主要驅動因素[2-6]。國內外學者目前廣泛采用Budyko框架研究徑流變化歸因[3,6-9],如Liang等[3]基于Budyko框架評估了氣候變化和水土保持對黃土高原14個主要流域徑流變化的貢獻;龍達等[9]利用Budyko框架分析了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對六沖河流域的影響。然而,當前的Budyko框架假定氣候和其他影響因素在某一時間點發生突變,往往僅評估兩段時期的平均徑流變化,因此難以反映氣候變化和土地利用變化的累積影響[10]。
黃河源區位于典型的干旱半干旱區,也是中國西北地區的主要水源地[11]。然而大量研究表明,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黃河源區水資源形勢嚴峻,如徑流顯著減少[12]、區域凍土[13-14]和草地退化[15]等。這些問題嚴重危及流域生態系統的穩定,制約了黃河源區的高質量發展。因此,精確刻畫氣候變化和土地利用變化的累積影響,對黃河源區水問題的成因剖析、水資源優化調度等具有重要的意義。
本文將采用基于時變參數的Budyko框架,細致刻畫過去50多年氣候變化和土地利用變化對黃河源區徑流變化的累積影響,以期揭示研究區徑流演變的內在機制。研究將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已有流域徑流變化歸因成果,為流域徑流演變內在機制分析提供參考借鑒。
1 方法與數據
1.1 研究區介紹
黃河源區(32°20′~36°10′N,95°53′~103°30′E) 是黃河的發源地,位于青藏高原東北部,流域面積12.2萬km2(圖1)。源區海拔從2 700 m 到6 183 m 不等,自西向東遞減。干流發源于青藏高原巴顏喀拉山脈,流經青海、四川、甘肅三省,止于唐乃亥水文站,全長1 553 km。該流域屬于高原山地氣候,年平均氣溫約-4~4℃,由西向東逐漸升高。多年平均降雨量510 mm,汛期(7—10月)降雨占全年的60%左右,時空分布不均。流域的景觀類型多樣,主要包括雪山、冰川、高原、山間盆地、山谷和湖泊等。其主要的土地利用類型為草地,約占區域總面積的80%以上[15]。

圖1 黃河源區水文站、氣象站與水系
1.2 數據來源
選取了吉邁、瑪曲和唐乃亥共3個水文站(圖1),收集了1960—2016年共計57 a的月徑流數據,數據來源于黃河水利委員會水文局。此外,也收集了同一時間段流域內15個國家氣象站的日降雨、日最小和日最大氣溫觀測數據,數據來源于中國氣象數據網(http://cdc.cma.gov.cn/home.do)。采用距離倒數插值法對日降雨、日最小和日最大氣溫數據進行插值處理[16]。3個水文站控制流域的基本特征見表1。

表1 水文站控制流域基本特征
1.3 研究方法
1.3.1水文要素變化分析
采用了降水P和潛在蒸散發E0來表征氣候變化。并且,采用Hargreaves方法[17]來計算潛在蒸散發E0,因為僅需要日最小和最大氣溫,公式如下:
(1)
式中Ra——地外輻射;λ——Tmean的汽化潛熱。
Mann-Kendall趨勢檢驗方法[9,18]已廣泛應用于趨勢分析,此次采用其分析3個水文站控制流域1960—2016年平均徑流、年平均降水和年平均潛在蒸散發的變化趨勢。對于時間序列X(t)(t=1,2,…,n),其趨勢估計量β為:
(2)
1.3.2基于時變參數的Budyko框架
Budyko框架清晰揭示了年徑流與其影響因素(降水、潛在蒸散發和流域特征)間的非線性關系,已廣泛應用于徑流變化歸因[5-8]。其中,Choudhury-Yang方程可估計實際蒸散發E,并已廣泛應用于黃河流域[3,18-20]。方程如下:
(3)
式中n反映下墊面特征,如土壤特性、坡度、土地利用和植被覆蓋等。
流域水量平衡方程為:
Q=P-E-ΔS
(4)
式中ΔS為流域蓄水量的變化,在多年的尺度,流域多年蓄水量變化可忽略不計。采用10年均值對年徑流、年降水和年潛在蒸散發進行處理,使ΔS為0。年徑流、年降水、年潛在蒸散發和年實際蒸散發從第t-9年至第t年的均值分別記為Qt、Pt、E0,t和Et,則式(4)可變為:
(5)
式(5)中的參數n在大部分研究中通常取某個常數值,不能反映下墊面的時變影響。Zhang等[10]提出依賴時間變化的時變參數nt,從而更好地刻畫氣候變化和土地利用的影響,見下式:
(6)
nt=α+β1t+β2t2
(7)
其中α是常數,β1和β2是回歸系數。由每年的年徑流Qt、年降雨Pt、年蒸散發E0,t可計算得到每年的時間參數nt來進行擬合。

(8)
(9)
所以,可得到從第t0年到第t年氣候變化 (Ac,t) 和土地利用變化 (Al,t) 的累積影響為:

(10)
2 結果
2.1 水文氣象系列的年際變化
圖3顯示了3個站點控制流域年徑流、年降雨和年潛在蒸散發從1960—2016年的年際變化。吉邁站、瑪曲站和唐乃亥站多年平均徑流分別為85.25、162.25、164.60 mm,多年平均降水分別為452.70、540.26、525.85 mm,多年平均潛在蒸散發分別為708.85、744.69、755.64 mm。

圖2 從第t-1年至第t年氣候變化和土地利用影響分解示意

a)吉邁站

b)瑪曲站

c)唐乃亥站
3個站點的年潛在蒸散發都顯著增加,但年徑流和年降雨的變化呈現出區域差異(表2)。吉邁站年徑流無顯著變化,但年降雨和年潛在蒸散發顯著增加,增加率分別為1.07、2.28 mm/a;瑪曲站年徑流顯著減少,減少率為-0.66 mm/a,年降水無顯著變化,年潛在蒸散發增加率為1.60 mm/a;唐乃亥站和瑪曲站相似,年徑流顯著減少,減少率為-0.59 mm/a,年潛在蒸散發顯著增加。

表2 黃河源區水文站年徑流、年降雨和年潛在蒸散發的MK檢驗結果
2.2 Budyko框架
時變參數n隨時間的變化見圖4。吉邁站時變參數n從1969—2000年左右逐漸增加,之后有所減少。瑪曲和唐乃亥站時變參數n總體呈增加趨勢。3個站點控制流域nt平均值分別為1.79、1.39和1.29,更大的n值意味著在相同的氣候狀態下,實際蒸散發更大,產流減少,區域干旱化。3個站點的回歸相關系數分別為0.71、0.92和0.85,均大于0.70,故回歸模型能較好地擬合時變參數n的變化。

a)吉邁站

b)瑪曲站

c)唐乃亥站
圖5顯示了3個站點控制流域從1969—2016年的時變Budyko曲線。從圖中可以看出,3個站點的氣候存在較大波動,其干旱指數(E0/P)多年均值分別為1.56、1.38和1.44。吉邁站的水文氣象點對變化較為復雜,其干旱指數和時變參數均存在非線性變化,而瑪曲站和唐乃亥站點對變化較為相似。

a)吉邁站

b)瑪曲站

c)唐乃亥站
2.3 累積影響評估結果
3個站點氣候變化的累積影響曲線較相似(圖6a)。氣候變化從1973—1990年增加了徑流,其累積影響值在1983—1990年較大,達到了10 mm以上。從1991—2003年氣候變化減少了徑流,在2003年,3個站點的累積影響值分別為-10.85、-20.91、-21.66 mm。2004年以后,整體上氣候變化增加了徑流,最終對徑流變化的累積影響值都是正值。
3個站點土地利用變化的累積影響曲線存在區域差異(圖6b)。吉邁站土地利用變化從1969—1996年持續減少徑流,1997年后效應減弱。瑪曲和唐乃亥站土地利用變化都持續減少徑流。3個站點最終土地利用變化的累積影響分別為-9.17、-32.09、-31.65 mm。

a)氣候變化的累積影響/mm

b)土地利用變化的累積影響/mm
綜合來看,吉邁站年徑流無顯著變化趨勢,這是因為氣候變化對徑流有所增加,土地利用對徑流的減少相對其他2個站點較少,氣候變化對其徑流變化起了重要作用。而瑪曲和唐乃亥站年徑流顯著減少,土地利用變化對徑流的持續減少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已有的研究[7]發現黃河源區徑流變化存在2個突變時間點(1989、2003年),這和本文研究結果相一致。吉邁站控制流域年降水顯著增加,其余區域降水變化不明顯(表2),其土地利用變化也更為復雜,黃河源區約63%的凍土位于吉邁[7],因此吉邁站的影響因素和趨勢變化與其他2個站不同。對于氣候變化,雖然源區潛在蒸散發一直顯著增加,但年降水變化方向并不單一(表2);對于土地利用,其變化因素較為復雜,包括草地退化和凍土退化[7,13-15],作用機制多元,所以不同時期土地利用和氣候變化對徑流的影響存在異質性。
3 結論
基于時變參數的Budyko框架系統評估了1960—2016年氣候變化和土地利用變化對黃河源區徑流變化的累積影響,結論如下:①源區3個站點年潛在蒸散發都顯著增加,其中瑪曲和唐乃亥年徑流顯著減少,但吉邁站年徑流無顯著變化;②回歸模型能較好地模擬時變參數n的變化,相關系數在0.7以上;③氣候變化對3個站點控制流域徑流的影響存在時間波動,氣候變化在1973—1990、2004年之后增加了徑流,而1991—2003年減少了徑流;除吉邁站部分時段外土地利用變化均減少了徑流。氣候變化對吉邁站徑流變化起了重要作用,而土地利用變化對瑪曲和唐乃亥站累積影響更大。
總的來說,基于時變參數的Budyko框架簡單但可靠,所需數據較少,能精確刻畫氣候變化和土地利用變化對徑流變化的累積影響,但對于時變參數的模擬仍缺乏充分的物理機制,今后仍需加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