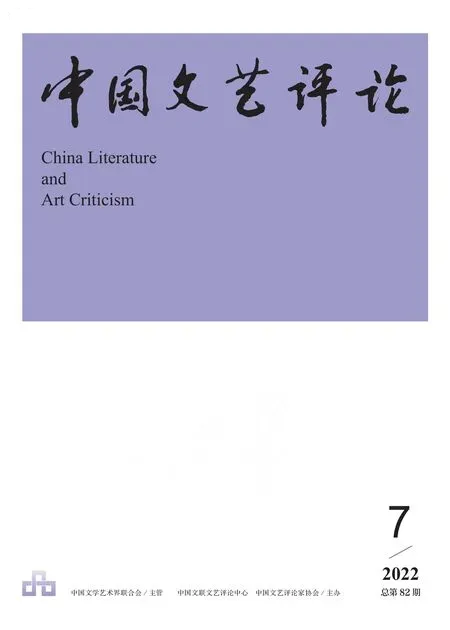論福柯讀《宮娥》
■ 陸 揚
一、《宮娥》
福柯于1966年出版的經典著作《詞與物》,扉頁上收入了17世紀西班牙著名畫家迭戈·委拉斯開茲(Diego Velázquez)的著名油畫《宮娥》(),并以之作為第一章的標題,就此展開不厭其詳的迷宮式解讀。福柯讀《宮娥》的開場白是:

圖1 [西班牙]委拉斯開茲 《宮娥》 油畫 318cm×276cm 1656年
這個開場白就叫人迷糊。畫家是委拉斯開茲本人自不待言,可是他明明看著前方,那是我們看畫的人、也就是畫作觀者的位置,他如何在他面前的這塊巨大畫板上,表現順著他捧著調色板的左手,一字兒排開的八個人物?又如何再加上后墻一塊長方形鏡子里國王和王后的隱隱約約的影像?是不是畫家面前有一塊巨大的鏡子,委拉斯開茲在對著鏡子畫畫?我們發現福柯甚至不能斷定將這11個歷史人物的神情惟妙惟肖固定下來的瞬間,是在這幅名作的收官階段,還是畫家尚在頗費猜測地構思畫面階段,甚至未及落下他的第一筆油彩時。惟其如此,我們有必要先來了解《宮娥》這幅17世紀西班牙古典油畫中的巔峰之作。
委拉斯開茲于1599年出生在西班牙薩維利亞(Sevilla),1660年在馬德里謝世,是國王腓力四世(Philip IV)宮中的首席畫家,也是西班牙文學藝術“黃金時代”最重要的畫家和巴洛克時期的領軍人物。他尤以描繪宮廷人物與貴族生活稱雄畫界,其代表作便是這幅撲朔迷離、后來被W.J.T.米歇爾(W.J.T.Mitchell)稱為“元圖像”的《宮娥》。19世紀初葉,委拉斯開茲成為寫實主義與印象主義畫家的楷模,馬奈(édouard Manet)說他是“畫家中的畫家”。20世紀,畢加索(Pablo Picasso)不計其數變形摹寫過《宮娥》,達利(Salvador Dalí)也畫過委拉斯開茲的《宮娥》,以探究繪畫中的“真理”。這幅讓歷代畫家、哲學家與藝術史家欲罷不能的《宮娥》,是委拉斯開茲1656年所繪,彼時他在宮中作畫已達三十余年。作品尺幅巨大,高318厘米、寬276厘米,現收藏于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館(Museo del Prado),這也是西班牙最大的博物館。
《宮娥》畫面的左側是巨大的畫架背面一側,畫家本人握筆站立,凝視著前方,那是畫面之外模特兒的位置,也就是我們觀者的站位。作為觀者,我們看不到委拉斯開茲在畫什么,以至于福柯都無從知曉畫家是畫完了呢,還是剛要啟筆。畫面中心是腓力四世年方五歲的女兒、金發披肩的小公主瑪格麗特·特里莎(Margarita Theresa),腓力四世與其第二任妻子瑪利亞娜(Mariana of Austria)的獨生女,彼時王室唯一的后裔。小姑娘身著束腰緊身上衣、巨大的裙擺,那是典型的皇家服飾,雖然一臉稚氣,卻已然有了君臨天下的氣勢。公主兩邊即是此畫后來得以易名的兩位小宮娥:左手邊是伊莎貝爾(Isabel),正欲向小主人致禮;右手邊是瑪利亞·奧古斯蒂娜(Maria Agustina),跪在地上,手拿飲料點心托盤,在請小主人用點什么。畫面右側邊上是一條狗和兩個小矮人,小矮人都是小公主的玩偶,其中德國人巴伯拉(Bárbola)注視著前方隱身模特方位,意大利人佩圖薩多(Pertusato)一只腳搭在狗身上,像要驅走黃狗的睡意。伊莎貝爾身后是小公主的監護人馬塞拉(Marcela de Ulloa),身著喪服,正在跟一名保鏢模樣的男子說話。景深處后墻門口的臺階上站著一名黑衣男子,那是委拉斯開茲的親戚——宮里主管掛毯事務的涅托(José Nieto),正注視著屋中場景,右手似推開門簾,讓更多自然光進入畫室。后墻中央偏左位置,與門楣平行的一面鏡子里,映照出腓力四世與王后影影綽綽的肖像。
國王夫婦應是畫家表現的模特兒,站位是在畫面之外,繪畫鑒賞者所在的方位。畫像總體有九位人物,加上后墻鏡中的兩個影子,這正是文藝復興以降古典人文主義題材繪畫的標準人數構思。16世紀意大利著名人文主義者阿爾伯蒂在其《論繪畫》中,解釋他鼎力推崇的“歷史畫”(istoria)時,即強調“歷史畫”貴在豐富性,而豐富性不僅僅是好在多變,而且要莊嚴冷靜、高貴節制,所以人數要有限定:
在阿爾伯蒂看來,“歷史畫”的豐富性最終落實在人物身體的互相協調上面。在這方面,委拉斯開茲的《宮娥》可謂在畫家的這個微妙且神秘的王室私人空間里,將平衡協調做到了極致。腓力四世跟兩個妻子一共生過12個孩子,只有兩個成年。畫中的瑪格麗特公主后來嫁給利奧波德一世(Leopold I),成為神圣羅馬帝國皇后。這是后來的故事,畫家當時自然不會知情。可是冥冥之中天意使然,右側過來的光線,高光聚焦在畫面中央的小公主身上,以至于衣著亮得近乎發白。小姑娘完全不理會她邊上兩個侍女,頭偏著,目光卻筆直射向畫架背后的正前方。那還是模特的位置,也是我們看畫的人的方位。是以新的問題出來了:抑或小公主原本就是畫像主角,被突然造訪的父母親嚇了一跳?
畫面左側的委拉斯開茲神情嚴肅,他給小公主畫像也好,給國王夫婦畫像也好,怎么把自己也畫了進來?這樣來看,鏡子的假設當是情理之中。《宮娥》的作者對鏡子肯定不會陌生,尼德蘭畫家揚·凡·艾克(Jan van Eyck)望遠鏡和顯微鏡式的北歐文藝復興的鏡像杰作《阿爾諾芬尼夫婦像》(),就掛在腓力四世宮中。
二、福柯讀《宮娥》
反觀福柯對《宮娥》的空間闡釋,又有一種后結構主義的深意。雖然1966年正是法國結構主義的高光時代,后結構主義尚還不知為何物。畫面左邊是委拉斯開茲站在畫架面前,巨大的畫架幾乎頂天立地,雖然只有背面一條給切進了畫面。福柯的評價是,觀眾只能看到畫架背后的邊緣,正面畫布上畫著什么,卻一無所見。觀眾能看到畫家全身,他剛從目不可及的畫布面前冒出來,恰恰處在左右搖擺的一瞬間,黑暗的身軀與明亮的臉面,介于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畫家正在凝視一個看不見的點,這個點應是他正在表現的對象,可是這個對象所在,正是我們觀眾的站位: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臉、我們的眼睛。是以委拉斯開茲正在觀察的那個景象就有了雙重的不可見性:這個方位并沒有見于油畫空間,然而這個盲點恰恰是我們作為觀者自己所在之地。我們看不見畫面,只能看到它的背面:高大的畫架。畫架上的畫布重構了畫面上缺場的我們所在的空間。表面上看,似乎情景簡單,不過是一種互動:我們在凝視油畫,畫家反過來也在畫中凝視我們,相看兩不厭。但是:
這一切意味著什么?福柯認為它們意味著這里所有的視覺都是不穩定的,主體與客體、觀眾與模特持續不斷地顛倒位置。而且因為畫面不可見,我們根本不知道這些視線之間是怎樣一種關系,同樣也在迷茫:我們究竟是在看呢?還是在被看?甚至,我們是誰?我們在做什么?概言之,主體消失了,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界限消失了。一切都只是這個看似確定,實際上飄忽游移、極不確定的秩序網絡之中的一個元素罷了。
福柯進而談到鏡子。福柯指出,這面后墻上位居畫面透視焦點處、映出國王夫婦影像的矩形小鏡,它壓根兒沒有照出屋中人物,既沒有照出背對鏡子的畫家,也沒有照出畫室里的其他人物。鏡子入畫是荷蘭畫家的傳統,在這個傳統里,鏡子只是在一個非真實的、修正、縮小而且彎曲的空間里,重復畫面里的東西。但是委拉斯開茲的這面鏡子,展現的并不是畫中景觀,它直接穿過被再現的整個圖景,照出畫面中幾乎所有人物都在凝神觀看的國王和王后,那也正是觀畫者所在的方位。那么,是不是國王與王后以目不可及的畫外視角,開啟了這個你看他、又看我,我也看你、又看他的相互凝視景象呢?福柯認為這是一目了然的。國王與王后位居視線交叉的中心地位,這從畫面中人物的尊敬目光,以及小公主與小矮人的一臉驚詫中,便可見端倪。但這個中心點又是無中心的中心,在所有衣著華麗的畫面人物中,鏡中的國王夫婦是最樸素、最蒼白的,而且最不真實、最為脆弱。畫中人物稍許移動一下,光線稍許變幻一下,他們就消失了。
福柯分析了委拉斯開茲《宮娥》這幅畫中的三組視線。以國王夫婦站位為中心,福柯認為在這里是交疊了三組視線:一是國王及王后作為模特的視線;二是觀畫者看畫時候的視線;三是畫家構思畫面時候的視線。這三種“凝視”功能在畫面之外的一個點上交合:它是被再現的對象,也是再現的出發點。在再現的畫面上它并不存在,然而它又確確實實在畫面中得到了投射。畫家的視線中看到模特,畫面上的畫家在將模特復制到面前的畫布上面。國王的視線中是自己的肖像,但是肖像在畫布上,畫布面對畫家、背對國王,國王在自己的位置上看不到畫布。在觀畫者的視線中,站位在國王中心方位,看到全部真實畫面。但是,福柯強調說,鏡子所表現出來的慷慨是虛假的;也許鏡子隱藏的同它揭示的一般多,甚至更多。他最終以下面這段話結束了他的著名的《宮娥》解讀:
這里的關鍵詞是“表象”(representation),這個詞在法文和英文中同形同義。在中文語境中,哲學界習慣譯作“表象”,如叔本華《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此書原名是,英譯名為。在文學和藝術批評界,它的傳統譯名是“再現”。在過去半個世紀里漸成燎原之勢的文化研究領域,它更通行的譯法是“表征”。表象也好,再現也好,表征也好,它們都同時可以作為動詞和名詞使用,也同時指涉過程和結果,學界因此有過關于representation的中譯名論爭。如任教杜克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的劉康就堅持這個詞的“再現”本義。但是《宮娥》里的再現縱是殫精竭慮,似也難有確定的所指。在福柯看來,在三種視線錯綜復雜的交織網絡中,主體和客體的那一層相似性不復可見,反之,一種后結構主義的秩序浮出水面,仿佛這個秩序就是主體,然而主體已然不見。再現一旦從相似性中脫穎而出,便成為再現的再現、純粹的再現,或者說,表象的表象、純粹的表象,表征的表征、純粹的表征。哪怕多年以后,它更變身為什么也不反映、什么也不再現的純粹“擬像”(simulation)也罷。
《宮娥》這幅油畫豈止只有后墻一面鏡子。畫家面前的畫布也是一面鏡子,映出他工作室里的整個場景。畫布上的鏡中影像,來源則似是國王與王后站位處的鏡子,假如沒有這面畫面之外的鏡子,委拉斯開茲再現他本人的自畫像其實不好想象。這兩面鏡子相互映照,最終成就了《宮娥》這個17世紀最為神秘的視覺哲學再現映像。誰在看,誰在表征,誰在被看,誰在被再現,實際上成為一個互相映照、互相循環的怪圈,終究沒有一個原始的視覺起點。主體消失了,作者不過是話語的體系使然,話語就是結構。而福柯的結構,一如他的《宮娥》解讀,展示的卻是解中心、多元化的典型的后結構主義范式。或者毋寧說,福柯的上述分析,可視為他在次年的著名講演《他種空間》中所提出的“異托邦”思想的一個預演。
三、米歇爾讀福柯讀《宮娥》
美國藝術史家W.J.T.米歇爾讀福柯的《宮娥》解讀,在呼應福柯讀《宮娥》謂主體消失、話語結構取而代之的同時,更圍繞“元圖像”主題展開。元圖像即圖像的圖像,或者說,指向自身或其他圖像的圖像、用來表明什么是圖像的圖像。以圖像自身來說明什么是元圖像,米歇爾同時舉證的例子有美國漫畫家索爾·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1964年發表在《紐約客》雜志上的漫畫《螺旋》(發表時名為《新世界》),畫中畫家以自己為中心畫螺旋形圓圈,高高在上地主導了底下的山丘樹木炊煙景觀,仿佛畫家就是上帝,創造了螺旋邊線上的風景。同時還有阿蘭(Alain)1955年發表在《紐約客》雜志上、后來被貢布里希稱為“風格之謎”(riddle of style)的《埃及寫生課》,畫中11位埃及的美術系學生正在給一個正面側臉的裸體女模特畫像。米歇爾不同意貢布里希將此畫解讀為一葉障目而“以不同的方式感知自然”,而是認為今天西方藝術系的學生也一樣用拇指來比量模特以確定比例,即是說,我們與其嘲笑埃及人,不如嘲笑我們自己。此外還有美國心理學家約瑟夫·加斯特羅(Joseph Jastrow)的《鴨—兔》:一個圖像朝左看是鴨子、朝右看是兔子,以及埃舍爾(Maurits Cornelis Escher)的《奈克爾立方體》()、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中的《雙十字》和英國漫畫家威廉·希爾(William Ely Hill)改寫1888年發行的德國明信片、發表在1915年11月美國《潑克》()雜志上后廣為流傳的《我的妻子與岳母》等。米歇爾認為上述這些圖像都是自我指涉的元圖像。分別來看,《鴨—兔》《奈克爾立方體》和《我的妻子與岳母》當屬于感覺和知覺關系錯亂的幻覺圖。所謂感覺,我們通常是指外部景觀的輸入;所謂知覺,則多指大腦對感覺積累的選擇、組織和闡釋過程。而當這一過程更進一步有語言文字強行介入的時候,那便有了讓福柯和米歇爾同樣欲罷不能的比利時畫家勒內·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這不是一只煙斗》。
在米歇爾看來,委拉斯開茲的《宮娥》是上面所有這些漫畫元圖像各個不同特征的集大成者。首先從形式上看,它就模糊了斯坦伯格《新世界》一目了然式的自我指涉與阿蘭《埃及寫生課》漫畫式自我指涉之間的邊界。《宮娥》再現了委拉斯開茲畫畫的場景,可是對于畫家究竟在畫什么,我們其實一無所知。因為我們只能看到畫布的背面。所以:
這是說,《宮娥》如福柯所言,是再現了古典主義的藝術再現或者說藝術生產場景。但米歇爾認為福柯的說法還不夠確切,因為《宮娥》再現復再現的方式,也還是古典主義的,是以福柯的“對古典再現的再現”,不妨更改為“對古典再現的古典再現”。米歇爾指出,比較來看,其他兩幅自我指涉的元圖像作品中,阿蘭的《埃及寫生課》是古典再現的框架中的古代再現,斯坦伯格的《新世界》則是后現代框架中的現代主義再現。
但是即便都被名之以“元圖像”,米歇爾也承認《宮娥》與《鴨—兔》一類的幻覺游戲完全不同:《宮娥》是西方繪畫史上的輝煌經典,《鴨—兔》不過是刊登在幽默雜志上的一幅無名漫畫,后來成為了心理學文獻中的插圖;《宮娥》是反映繪畫、畫家、模特、觀眾之間錯綜復雜關系的迷宮,百解不厭,《鴨—兔》不過是被用來確證一種零度闡釋,顯示視覺錯覺如何發生,一般并不認為它具有深刻寓意或者悖論意義。前者是黃鐘大呂,后者是雕蟲小技,若非維特根斯坦討論過“鴨—兔”問題,幾乎沒有人會記得它,它也肯定不會躋身元圖像之列。而問題是,假若福柯沒有討論過《宮娥》,它固然仍舊不失為偉大經典,但是同樣不會成為元圖像。
米歇爾認為,有如維特根斯坦用《鴨—兔》舉例來談視覺錯覺,福柯大談《宮娥》,也像維特根斯坦一樣,讓刻板僵化的學院派元圖像話語進入了特定的語言游戲,換言之,進入了兩人各自的“哲學”語境。維特根斯坦敦促我們不要去解釋《鴨—兔》,而來聆聽我們所說的東西,思考它與我們的視覺經驗之間的關系。福柯則提出,我們必須假裝不知道《宮娥》里的人物是誰,他們都在做什么,我們應當放棄導致我們不足以充分“可見事實”的那種語言,而求諸一種“灰色的無名的”語言媒介,惟其如此,它才可以成就《宮娥》從藝術史上的一件杰作到元圖像的歷程。簡言之,跟上述其他元圖像一樣,它也用再現的自我認識,通過追問觀者的身份來激活觀者的自我認識。
由是觀之,《宮娥》中的這一追問跟權力與再現密切相關,包括繪畫與畫家的權力,也包括作為隱含觀者的國王與王后的權力。這主要表現在委拉斯開茲把自己畫成宮廷仆人,然而通過安置在不起眼方位的那一面鏡子,機智且謹慎地表達了自己主宰和控制再現的一種主權,從而使反仆為主成為可能。不僅如此:
米歇爾與福柯英雄所見略同,都是重申畫面中觀眾缺場又在場的神秘視角。他表示欣賞福柯的說法:《宮娥》是給我們呈現了再現的整個循環景觀。這個循環圈里有三個支點:一是畫家在畫板上工作時占據的位置;二是畫中模特占據的位置,他們很可能就是鏡中的影像;三是觀者占據的位置。而這三個方位投射出來的“沒影點”分別是:一、門口畫家的親戚掛毯主管;二、后墻鏡子里的虛假影像,他們應是觀看這個場景的國王與王后;三、畫面中心的小公主,她也是父母以及我們觀眾的凝視對象。
在以上縱橫交錯的視線與視覺的交換網絡中,米歇爾再度確認了觀者的主體性就建構在無法再現的隱蔽空間里。他重申福柯《詞與物》中的著名描述:一切凝視都是不穩定的,在中間視線穿透畫板的地方,主體與客體、觀者與模特,顛倒了他們的角色。我們只能看到畫布背面,我們不知道我們是誰,我們是在被看呢,還是在觀看?米歇爾認為,《宮娥》的視覺顛覆能力也重構了我們對君主主體性的想象:我們將空間、光和設計的主宰歸于畫家,將民眾的主宰歸于歷史上的君主,將自己的視覺/想象領域以及外觀和意義的主宰歸于自我。所以,我們是現代的觀者,是我們私人空間“精神王國”的統治者。
所謂福柯是用他“灰色的無名的語言”在談《宮娥》,而由此將《宮娥》從藝術史的闡釋客體變身成了一幅元圖像,米歇爾指的是《詞與物》第一章第二節開頭的一段話。彼時福柯說,我們看畫時會糾結在一些不穩定的抽象名稱里不能自拔,諸如畫家、人物、模特、觀者、形象等,這是說不清楚的。我們只需要說,委拉斯開茲創作了一幅畫,在這幅畫中,畫家在畫室里或者君主的房間里,把自己也跟畫中人物一起再現了出來。小公主瑪格麗特端坐在中央,看他作畫。米歇爾注意到,福柯逐一交代了畫面上各個人物的名字,包括看不到的模特原身,只能在鏡子里見到模糊影像的國王夫婦。之所以逐一點名,福柯的說法是這些專有名字會避免含混,告訴我們誰是誰。但是,詞與物的關系遠不是這樣清楚明白的。米歇爾引用了福柯《宮娥》論中畫龍點睛的一段著名話語:
這是說肉眼所見不足道,我們眼睛看到的東西,很難用言詞恰如其分地表達出來,即便求諸形象的比喻也是枉然,繪畫的意義最終將由話語的結構來作解釋。米歇爾對福柯的這一立場,表示無條件的認同。
那么,福柯上面交代的人名又當何論?正是給人物安上名字,我們才知道了畫面上的人是什么人。亞里士多德在《詩學》的第四章中談摹仿,說摹仿的好處之一便是當主體不在場的時候,可以用再現的畫像來替代他的在場,從而達成認知功能,讓人一見便認出畫中人原是何許人也。莎士比亞在《仲夏夜之夢》的第五幕第一場中說,詩人可以給子虛烏有的東西加上一個居所和一個名字。有了名字,語詞與事物、與圖像的關系就變得清晰起來。如福柯本人所言,名字對于繪畫意義的傳達有點石成金之妙,我們可以指著圖像說,這是誰誰誰。換言之,悄悄地將說話的空間指示到注視的空間。不過米歇爾同樣發現,如此憑借相似性來尋找終極的解釋,固然是藝術史的使命,也許同樣也是再現理論的正當使命,然而它卻不是福柯的目標。福柯的目標是保持語言與視覺對象的開放性關系,將兩者之間的不相容性作為言語的起點,而不是障礙。所以,如若我們想要最大可能地接近語言與視覺對象,就必須清除名字,以保持詞與物的無窮的開放性。惟其如此,一如福柯所言,通過這一灰色的、無名的、因為寬泛無邊而總是過于精細和重復的語言,圖像可望一點一點地照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