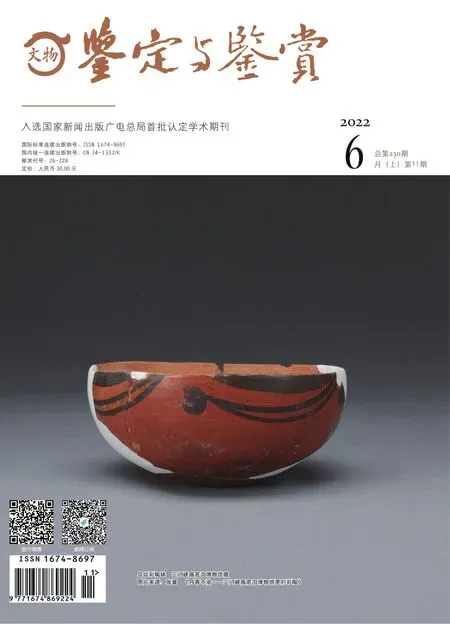三明市博物館館藏《清康熙六十一年經(jīng)幢》考
陳雪
(三明市博物館,福建 三明 365000)
經(jīng)幢是宗教石刻的一種。“幢”原為佛像前絲錦裝飾的立竿,因其上書寫經(jīng)文,所以稱為“經(jīng)幢”。為了保持千百年不毀,后演變?yōu)槭獭7鸾陶J為其具有破除災禍、往生凈土之功用。經(jīng)幢興于唐早期,盛行于唐中晚期及北宋,元逐漸沒落,明清有少量雕造。三明市博物館收藏一座清代經(jīng)幢,保存完好,字跡較為清晰,內(nèi)容可辯,是研究清代經(jīng)幢形制、功用,以及當?shù)孛癖娦叛觥⒚耖g習俗的珍貴實物資料。本文擬就經(jīng)幢的概況,考證建幢人族源情況及清代匠籍制度演變等。
1 《清康熙六十一年經(jīng)幢》概說
《清康熙六十一年經(jīng)幢》(圖1)是三明市博物館舊藏。經(jīng)幢高173厘米,石質(zhì),由幢頂、幢身、基座三部分組成,三個部分分別通過榫頭和卯眼結(jié)構(gòu)套裝而成。幢頂高38.5厘米,由腰檐和寶珠頂相疊而成,腰檐為仿木構(gòu)件,四角亭檐式,出檐各角微微翹起,沒有角梁、飛掾、掾子等細部雕刻,即有形而無細節(jié),較為簡單。幢身呈六邊形柱,高115.5厘米,每面等寬15厘米,五面刻字,一面留白。基座采用單層方形塊石,長40厘米,寬40厘米,高25厘米,素面無雕刻裝飾。經(jīng)幢使用的石材為花崗巖,花崗巖具有強度高的特點,不易加工,所以經(jīng)幢表皮顆粒較粗,除幢身略有打磨外,幢頂和基座可見鑿痕。總體而言,《清康熙六十一年經(jīng)幢》形制簡潔質(zhì)樸,裝飾雕刻少,卻端莊穩(wěn)重。

圖1 清康熙六十一年經(jīng)幢及平面圖
經(jīng)幢的文字置于幢身的5個面(圖2),陰刻楷書,直行左讀,雖然每面刻文的字數(shù)不同、間密不等,但行數(shù)卻有一定的規(guī)律,第1~4面每面刻文3行,第5面刻文1行,共13行180個字。茲將刻文迻錄且標點如下,其中文字不詳用“□”表示,分行以“/”標示:

圖2 清康熙六十一年經(jīng)幢平面圖
①嗟嗟!其塔之由來,仿釋氏以為之普救同類,無嫌姓族/之姝,男女共藏,各隨左右之分,生雖異室,死則同穴,勿/謂嗣褚之有無,迨春秋而悉,享于祭祀。弟□山神之筆。
②護歷萬載而致其安放,薄置義田,永為祀典。/佛曰:假此次邀福顯體,周年之釋祐,/謹記。
③建塔主巫可立諱永祿,仝妻余月娘,男興善、有德,/媳婦湯氏、黎氏,孫澤魯、澤龍、澤謀、/澤英、澤士,孫媳婦楊氏、丘氏、黎氏。
④肋,孔正迪,歸化匠人諶院生,居□。/祝永生永劫。/工樂 石匠雷兵。
⑤大清康熙六十一年九月十四 吉旦
刻文大意:建此塔是仿照佛教的做法普救同類,無妨親族的不同,按照左右尊卑之分,一起供奉;生雖不同室,死則同穴,不論有無子孫后代,到春秋都享有祭祀。同時提到,若佛能保佑其永久安放于此,會捐獻少量的田地,供養(yǎng)貧困族人,且永不斷竭。落款時間清康熙六十一年,即公元1722年。《清康熙六十一年經(jīng)幢》記錄了建幢緣由、發(fā)愿文,以及建幢者和刻工的信息資料、建幢時間等。
2 相關(guān)考釋
2.1 《清康熙六十一年經(jīng)幢》的功用
唐代,各地僧徒、信眾就廣樹經(jīng)幢,早期經(jīng)幢上雕刻最多的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據(jù)《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記載:“……于幢等上,或見或與幢相近,其影映身,或風吹陀羅尼上幢等塵落在身上。天帝,彼諸眾生所有罪業(yè),應墜惡道、地獄、畜生、閻羅王界、餓鬼界、阿修羅身惡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為罪垢染污。”其意是,若將陀羅尼經(jīng)刻于幢上,無論是建幢者、書寫者,還是遇見或靠近此幢者,或是被經(jīng)幢的影子照映者,甚至是經(jīng)幢上灰塵吹落在身者,都可以消除一切罪業(yè),免于墮入惡道。因此,信眾認為經(jīng)幢具有“破地獄”之功能,可拯救眾生免墮地獄。入宋以后,唐代頻繁出現(xiàn)刻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經(jīng)》的經(jīng)幢則較為少見,而“更趨于陋俗……更有如此幢僅刻咒語者,謂之‘真言幢’”。如宋徽宗大觀二年(1110),在山東益縣為僧人奉俊所建的經(jīng)幢,上刻“陀羅尼滅罪真言”“往生真言”“寶樓閣真言”“安土地真言”。山西省壺關(guān)南村出土一北宋元祐年的經(jīng)幢,其上刻“佛說金剛經(jīng)纂凈口業(yè)真言”“佛說生天真言”等。由此可見,宋時經(jīng)幢的內(nèi)容更為豐富,功能更為廣泛,具有消除罪業(yè)、超度亡靈而往生凈土等眾多功效。至明清,“刻《經(jīng)》者已寥寥無幾,或無《經(jīng)》而有‘啟請’。”雖然經(jīng)幢發(fā)生了種種變化,形制更為簡陋、內(nèi)容更為簡化,正如《清康熙六十一年經(jīng)幢》,沒有唐宋時期的佛像雕刻裝飾,沒有書寫經(jīng)文、真言、啟請,僅提到“仿釋氏以為之普救同類”,但其依然承載著滅罪、超度、祈望亡者早日輪回等功能。
經(jīng)幢一般置于寺院、通衢大道及墓旁。根據(jù)《清康熙六十一年經(jīng)幢》的內(nèi)容“……生雖異室,死則同穴,勿謂嗣褚之有無,迨春秋而悉,享于祭祀”推測,該幢應為墓幢。墓幢一般安放在墓道、墓中或墓旁,為亡者超度薦福而立,以契合“影轉(zhuǎn)福至、塵沾影覆”的宗教思想。又幢上刻“無嫌姓族之姝”“薄置義田”之句,“姓族”指同姓的親族,“義田”泛指贍養(yǎng)族人而置的田產(chǎn),所以推測該幢應是安放在家族墓地,為家族成員所建造。
哥們兒朝洛蒙換了背心褲衩,穿著趿拉板拖鞋,手里拿著蒲扇,挽著媳婦的胳膊,遛遛達達走出院子,走到街上去。這里雖然地處偏僻郊區(qū),但也分外熱鬧。物美和京客隆這樣大商場大超市街對街地開著,肯德基和麥當勞也各打各的廣告,各爭各的客流,各領(lǐng)各的風騷。街上走著穿著體面的城里人,巷子里蹲著建筑工地的民工。民工們光著膀子,在農(nóng)貿(mào)市場邊的大排檔里喝啤酒嚼青豆。話說得比天高,眼睛卻瞪大了往低處看。坡下,不遠處有一伙穿著暴露的年青女人在地攤前游蕩。她們用厚厚的脂粉遮掩住被太陽曬下的黑斑,皮膚粗糙,卻戴著暴龍眼鏡,不知是真的是假的。手機掛在脖子上,專揀劣質(zhì)便宜的東西拿,砍價砍得攤主無可奈何,急頭白臉。
2.2 建幢人族源情況
由《清康熙六十一年經(jīng)幢》第3面的內(nèi)容可知,該幢是巫可立攜同妻子、兒子、兒媳、孫子及孫媳等一家14人共同建造。巫姓,三明域內(nèi)主要分布在寧化、清流兩地,均為寧化開基始祖巫羅俊的后裔。《姓氏考略》載:“黃帝臣巫彭作醫(yī),為巫氏之始。”得姓始祖巫彭。在漫長年代,巫氏主要繁衍于平陽一帶(今山東的鄒縣)。據(jù)寧化《平陽巫氏房譜》記載:“東晉末,五胡亂華時,巫暹由山西平陽避亂兗州,轉(zhuǎn)遷閩之劍津,為巫氏入閩始祖。至隋大業(yè)間,巫暹裔孫昭郎率子羅俊遷閩之黃連峒,為巫氏開基始祖。”黃連峒轄今寧化、清流、明溪、建寧四縣。巫羅俊胸有抱負,率民“筑堡衛(wèi)眾,御寇拓疆”,成為黃連峒的領(lǐng)袖人物,后因上疏唐太宗,告知黃連峒地廣人多,應該授田定稅,并入版圖受皇室保護,因而得到唐太宗的嘉許,封為“黃連鎮(zhèn)將”。巫羅俊在黃連峒肇基立業(yè)后,其子孫后代不斷繁衍,族譜也進行了七次編修。在清光緒甲午重修《平陽巫氏房譜》(合房仝編)中,查明巫可立為巫羅俊元旺公房第四十二世孫。
《清康熙六十一年經(jīng)幢》中未提及該幢擺放的地理位置。據(jù)光緒甲午重修《平陽巫氏房譜》(合房仝編)的“墳圖志”記載,巫氏祖墓主要分布在清流縣永得里嵩溪、寧化縣招賢里汪家地、石城縣(江西)龍上里、禮上里等地,其中清流嵩溪的祖墓最多,據(jù)載:“……祖骸于清流嵩溪共三十六祖,散葬黃沙口、雷崗坊等幾處。”招賢里為今寧化縣水茜鄉(xiāng),招賢里汪家地的祖墓數(shù)量僅次于清流嵩溪,《平陽巫氏房譜》載:“在招賢里汪家祖山葬三十四世祖……一墳乃子彥公第三支元旺公房墓。”由此得知,《清康熙六十一年經(jīng)幢》應是擺放在寧化縣招賢里汪家祖山巫氏祖墓旁。
2.3 建幢人宗教信仰及當?shù)孛癖娦潘滋攸c
從《清康熙六十一年經(jīng)幢》的功用以及刻文中出現(xiàn)的“釋氏”(佛姓,釋迦的略稱;亦指佛或佛教)、“佛曰”推測,建幢人為佛教徒。據(jù)上述考證,建幢人巫可立一家是寧化人,寧化地處閩西,自元、明、清均隸屬于汀州府,《臨汀志》記載的閩西最早寺院“開元禪寺”,建于唐開元年間,說明此時佛教在閩西的傳播已經(jīng)比較成熟。佛教何時傳入寧化無從考證,但《寧化文史資料》中記載:“寧化宗教的傳播,以佛教為最早,信徒遍布城鄉(xiāng),唐代同光年間,即已建立慈恩古塔,是一明證。”由此可知,佛教已于唐同光(923—926)之前傳入寧化。史料表明,佛教自傳入中國,歷經(jīng)東漢依附、魏晉南北朝發(fā)展、隋唐鼎盛及宋代衰微四個階段,但這種現(xiàn)象在閩西并沒有出現(xiàn),宋元后佛教繼續(xù)發(fā)展,明清時期甚至還較唐、宋元有了更大的影響。據(jù)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寧化縣志》之“寺觀志”載:“寧化之得佛理者未數(shù)見,而樓佛之地大率三百余所。”此時寺廟庵堂數(shù)量眾多,遍布全域各鄉(xiāng)村,表明佛教極為盛行。
佛教傳入寧化,受當?shù)亓曀缀偷赜驐l件的影響,形成了具有濃郁地域性和世俗性的特征。其一,以定光佛和伏虎禪師為主體的禪師信仰。當?shù)匦磐匠3⒍ü夥鹋c伏虎禪師置于同一神壇,并有“定光伏虎”同一稱謂,亦稱“二佛”。定光佛宣揚佛教的輪回報應學說,興利除害;而伏虎禪師具有禱雨救旱、馴服野獸、賜嗣送子、避免戰(zhàn)禍等神力。“定光伏虎”滿足了當?shù)孛癖姷木裥枨螅蔀楫數(shù)孛癖姵绨莸谋Wo神。其二,僧人廣泛地出現(xiàn)在民間喪葬儀式上。康熙《警俗用浮屠》載:“人生壽夭系于天,即死神形不復全。縱使浮屠能薦撥,將何氣魄為招遷?香花凈水誠無用,法鼓金饒總是閑。囑咐兒孫依我訓,異端功果莫相傳。”“香花”特指香花和尚,這反映了僧人出現(xiàn)在喪葬儀式上,引起了一些人士的不滿和警覺,希望借助“警示”來破除此儀式。但由于佛教能與當?shù)氐膯试崃曀紫嗳诤希沟眠@一現(xiàn)象深入民心,廣為流傳,并得以保留至今。
2.4 工樂戶及匠籍制度
《清康熙六十一年經(jīng)幢》中提到“工樂,石匠雷兵”。工樂即“工樂戶”,隸屬官府,是官府在籍工匠,工樂戶的工匠部分從民間招募而來,但更多的是前朝遺留或本朝罪犯家屬。工樂名目北魏已有,唐代亦繼承舊制。《唐律疏義·名例》載:“工樂者,工屬少府,樂屬太常,并不貫州縣。”即工樂在各州縣沒有籍屬,而附屬于少府或太常等官府機構(gòu),說明其身份不自由,必須承擔指定的工役,在唐代屬賤民之列。宋代較之前有了變化,因為經(jīng)濟較發(fā)達,賤民的雇傭化程度越來越高,之前的賤民許多成了雇傭者,脫離了賤籍,唐以前出現(xiàn)的雜戶、工樂戶、兵戶等賤民在宋代前期都消失了。元代,為了便于強制征調(diào)工匠服勞役,便將工匠編入專門的“匠籍”,這就是古代匠籍制度之由來。明代沿襲了元代的匠籍制度,《大明律·人戶以籍為定》規(guī)定:“凡軍、民、驛、灶、醫(yī)、卜、工樂諸色人戶,并以原籍定。”即決定了匠籍世代不得脫籍,且必須服從官府相關(guān)徭役征發(fā)的規(guī)定,提供無償勞動。為緩和社會矛盾,順治二年(1645)清政府廢除了匠籍制度,但由于很快財政就入不敷出,于順治十五年(1658)又恢復征收匠班銀,匠班銀征收的依據(jù)是匠籍,據(jù)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寧化縣志》之“匠班志”載:“……寧化之工匠未有分役于二京者也,歲所征者三十九名,每征銀一兩八錢,計銀七十二兩,編為車班輪之,年遇子辰申則征十名,銀計一十九兩八錢,年遇丑巳酉則征十一名,計銀一十八兩,年遇寅午戌則征六名,計銀十兩八錢,年遇卯未亥則征十二名,計銀二十一兩六錢,惟閏年則□班,每名加征銀六錢,并解于工部,此寧化匠班之額也。”由此證明,此時的寧化依然實行“匠銀制”,民間仍然把身隸匠籍者稱為“工樂戶”,石匠雷兵應為在籍工匠。至雍正、乾隆時,推行地丁制度后,全國各地的匠班銀攤?cè)氲囟≌魇眨攀沟霉そ痴嬲龜[脫匠籍制度的束縛。
在“工樂,石匠雷兵”刻文旁,還并列落有“歸化匠人諶院生”字樣。歸化,明溪舊稱,彼時與寧化、清流同屬汀州府。匠人諶院生來自于隔壁縣城歸化,說明了這類工匠為自由之身,不必再服勞役,可以在其他地方勞動而獲得相應報酬,這也是清代廢除匠籍制度后,部分工匠脫離匠籍,其身份、地位改變的體現(xiàn)。
3 結(jié)論
注釋
①[佚名].大正原版.大藏經(jīng):第十九冊:密教部二[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351.
②王先進,王水根.山西壺關(guān)南村宋代磚雕墓[J].文物,1997(2):44-54.
③[佚名].僧奉俊尊勝經(jīng)幢[M]//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2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76-77.
④葉昌熾.語石 語石異同評:卷四[M].柯昌泗,評.北京:中華書局,1994:78.
⑤王樂慶.西安博物院藏《唐會昌二年銘經(jīng)幢》小考[J].文博,2019(2):56-62.
⑥魏德毓.交融與共生:閩西香花和尚與道教關(guān)系初探[J].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3):15-21.
⑦何綿山.淺談福建佛教的特點[J].宗教學研究,1996(2):69-73.
⑧鐘旎.閩西地區(qū)伏虎禪師信俗考辨[J].閩西職業(yè)技術(shù)學院學報,2018(4):19-23.
⑨杜士晉.連城縣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301.
⑩武建國.唐代的賤民[J].貴州文史叢刊,1984(3):75-83.
?劉俊文.唐律疏議:卷三:名例律[M].北京:中華書局,1996:64.
?盧忠?guī)?明清社會賤民階層研究[J].中國城市經(jīng)濟,2012(3):270-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