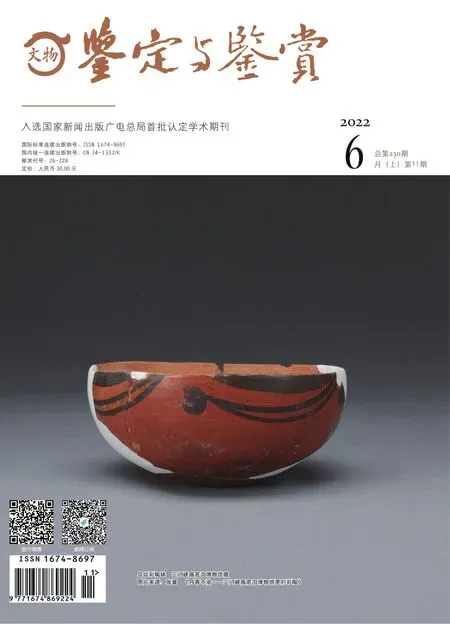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東阿縣張本家族墓地石刻保護研究
郭茜
(山東藝術學院,山東 濟南 250300)
鄉村振興戰略是習近平總書記于2017年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從而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進程。
1 東阿縣張本家族墓地石刻概況
1.1 東阿縣張本家族墓地概況
東阿縣在黃河沿岸,屬千年古縣,有中國阿膠之鄉、中國喜鵲之鄉的美譽。張本家族墓地位于東阿縣銅城鎮王宗湯村西300米處,該墓在20世紀60年代部分遭到破壞,2013年10月被山東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2 張本家族墓地石刻現狀
1996年7月,在農田基本建設時將該墓原有的陪葬石刻全部挖掘出土,并按原樣重新立于墓前和神道的兩側,其中石獅一尊、墓表一對、石虎一對、石羊一對、石翁仲兩尊(圖1、圖2)、石坊一座、誥封碑一通、石供桌一尊、石墓碑一通、石旗桿座一尊。由于石刻的石質材料抵抗侵蝕能力差,加之長期受到日曬雨淋,部分石刻出現了損害,如粉化、裂隙、表面溶蝕、水銹結殼、局部缺失等病害。墓地現由張氏家族后人看管,周圍也有種植農田和養殖家畜。

圖1 張本墓東側石翁仲保存現狀

圖2 張本墓西側石翁仲保存現狀
2 東阿縣張本家族墓地石刻價值
張本(1366—1431),字致中,明洪武年間曾做過江都知縣等職務。朱棣南下靖難之時,張本開城迎降,后升任揚州知府,并深為明成祖朱棣所重用,朱棣北征時,張本曾多次擔當督運糧草之任。張本為官非常的清廉,事跡曾被編入《明史·張本傳》:“成祖宴近臣,銀器各一案,因以賜之,獨本案設陶器。喻曰:卿號‘窮張’,銀器無所用。本頓首謝。”清廉的作風連皇家都看在眼中。明宣宗也曾為張本贈詩《花朝詩贈兵部侍郎張本》。張本一生為官秉正剛直、清正廉潔,對國家忠心耿耿、赤膽忠心;對民眾關懷備至、親力親為。這樣高尚的品質令人敬仰,為張氏后人做人做事都樹立了榜樣。張本墓中的墓志銘記載更起到了證史補史的作用,是一份難得的歷史文獻資料,具有極高的價值。
張本家族墓地石刻在規格、造型、紋飾、形制、技藝、構思等方面都自成一派,石刻矗立在神道兩側,呈規則排列,給人一種氣勢恢宏的感覺,使其成了山東地區明清時期石刻藝術的里程碑,既繼承了唐、宋時代的精華,又開啟了明、清時代的繁榮。張本墓神道石刻為研究明代禮儀制度、服飾、雕刻技藝、造型表現等都提供了極為難得的文物史料。
張本家族墓地石刻的藝術性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用點、線、面相結合的手法處理細部裝飾,將石雕的藝術性予以充分的發揮,其精美程度令人嘆為觀止。加之雕刻技法在石材上的嫻熟運用,使之表現出一種渾厚、凝重的立體效果。在凸起不平的畫面上用細膩平整的陰刻線具體刻畫物象的細部,形成粗獷和細膩的強烈對比,穿插其中的“面”使造型形象豐富而生動,“線”的大量運用體現審美觀念和藝術氣質的特點,通過線、面、體的巧妙運用,浮、圓雕特點的有機結合,產生了石刻特有的力量感、運動感(圖3)。

圖3 張本墓西側石翁仲背部雕刻細節
二是整個作品雕刻技法嫻熟、刀法多變,既有剔地平雕的陰刻手法,又有剔地浮雕的陽線方法,并且在線型的凹凸處理上十分注意,意從此處充分體現藝術家特有的審美觀和藝術修養,從而展現了雕刻技藝的高超。為了表現石刻較大的空間深度、石材較強的可塑性和氛圍較渾厚的效果,在整體上多采用圓雕的手法,局部則用淺浮雕的表現手法,以行云流水般流暢涌動的陰刻線條傳遞莊嚴肅穆的氣氛、和緩的思念之情。
三是每一件石刻作品都注重每一個細節的設置,在物象數量、造型的安排上都非常講究,例如吉祥數字“二、四、六、十”的選擇運用等。充分體現了后人對張本的情感和工匠的思想情感,從而顯現了后世人們對生活的熱愛,對張本前輩的尊崇,寄托了后世人們祈福求祥的美好愿望、情感。
四是張本家族墓地石刻充分結合了繪畫藝術在構圖和空間等方面的處理方法。比如石刻利用了透視學中透視與錯位原理、按照繪畫原則來處理空間大小關系,以此來達到表現目的,所以最終效果不僅給予人視覺上,而且包括觸覺上的震撼。所以這些石刻藝術作品在表現題材、內容構成、表現手法等方面都迎合了普通大眾的審美習慣,從而被普通民眾所欣賞。
張本家族墓地所承載的文化內涵給東阿地區人民注入了精神力量,也是個人精神、傳統文化、民間文化的見證,對于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促進社會和諧都有著積極的引導和借鑒作用。
3 東阿縣張本家族墓地石刻保護的必要性
3.1 順應國家和地區的政策
當前國家提出了鄉村振興的發展戰略,從各個角度對鄉村當前的凋敝狀況提出了新的發展要求。就文化傳統來說,山東地區自古以來就崇尚寓意深刻的文化環境,代表著特定時代和環境中人類活動的和諧空間,有著悠久歷史的、璀璨的齊魯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源泉。東阿縣張本家族墓屬于鄉村紀念性文化遺址,是鄉村民眾為了紀念和祭祀先祖、賢能節孝之人等而修建的,具有紀念先人、教育后人的目的。保護張本家族墓地石刻就是保護傳統文化,保護歷史的“活化石”,保護齊魯文化的“細胞”。
3.2 提升當地的文化地位
豐富的鄉村文化遺產可以提升當地文化軟實力,從而對周邊地區產生文化輻射作用,帶動周圍地區的發展。東阿縣張本家族墓地石刻作為珍貴的文化遺產,為當地鄉村文化振興提供了文化的實物憑證和資源依據,從而帶動當地以及周圍區域的發展,擴大文化輻射范圍,形成一個整體。通過與缺乏文化遺產實體和傳統文化內涵的相鄰地區橫向比較,其文化地位也會得以相應的提升。
3.3 保證當地的和諧發展
鄉村文化遺產潛在的功能很多,對人的傳統價值觀、道德觀都會潛移默化地產生影響,其中既包含著個人對童年記憶、家族對歷史記憶的喚起,又蘊含整個地區群體對祖先優秀品質與德行的傳承。東阿縣張本家族墓蘊含的文化是當地傳統鄉村文化的精華,伴隨著樸實的鄉村生活,在祖祖輩輩的心中回響,教化民眾、淳化民風,是鄉村社會延續的核心,是農村社會的穩定器,維護和保持鄉村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
3.4 促進當地的文明傳承發展
保護鄉村文化遺產,建立我們與先人之間的這種聯系,它具有雙重時空內涵,既為了銘記從前,也為了更好的現在。唯有如此,才會有綿綿不斷的文明傳承發展。保護東阿縣張本家族墓地石刻,正是“穿越時空”的與先人進行“交流”,此刻物質作為載體,時間作為介質,喚起現代人內心深處的先人標記和情感象征。而且傳承與發展更重要的意義是在于未來,以身作則來加強下一代青少年對家鄉文化標志記憶的認同感與傳承家鄉文明的使命感。
3.5 提高當地的文化口碑
在文化傳播過程中,口口相傳對于鄉村文化遺產的傳承至關重要,當地居民和游客的主觀傳播意愿決定了本區域鄉村文化遺產擴大傳播范圍的可能性。東阿縣張本家族墓地石刻的宣傳也需要普通群眾的口碑,讓越來越多周邊的村民來感受先人的文化內涵和道德品質,讓他們把親身體會向親朋好友推薦,真實可靠,信息全面,傳播力與影響力更強,是最好的推廣傳播手段。從而讓更多山東域內和域外的民眾產生了解、關注山東鄉村文化的意愿,從而提高山東地區鄉村的整體形象、文化地位與文化傳播貢獻。
3.6 增強當地民眾認同感、自豪感、凝聚力
各個地區的文化遺產不盡相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強著當地人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這種心理感受其實跟愛國之情相類似,只是作用范圍更小。區域文化遺產作為積極的價值導向,在人們對區域文化認同和自我價值認知過程中逐漸發揮作用,從而增強本區域民眾的自豪感、自信心和依戀情懷,內部力量也隨之凝聚增強。東阿縣張本家族墓地石刻作為典型鄉村文化遺產,成為張氏家族和東阿地區的和文化符號,具有精神集聚作用,能夠增強區域凝聚力。保護東阿縣張本家族墓地石刻,發揮其精神引領作用,使得民眾在地緣基礎上形成文化認同、情感依附,并且是“自愿認同”而非“強制性認同”。
3.7 增加當地財政收入
由于鄉村文化遺產本身所具有的特質,可以利用某些優勢培育出旅游文化產業,在引導旅游經濟發揮作用提高財政收入的同時,也更能發掘民族文化的深層內涵。東阿縣張本家族墓地石刻可以與周邊文化遺產共同形成文化遺產遺址旅游產業,形成經濟發展與文化的良性互動,促進鄉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才能更有效地促進文化發展,形成一個良性循環。但在開發過程中也要時刻注意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與文化內涵作為代價,不能一味地迎合游客注重經濟效益,這樣反而會本末倒置適得其反。
4 東阿縣張本家族墓地石刻保護策略
4.1 發揮文化價值,進行文物保護工作
東阿縣張本家族墓地石刻在歷史留存過程中,受制于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遭受到多種有害因素的侵蝕。自然環境的長期作用和制成材料的老化衰變致使其產生了形態各樣、特征迥異的損毀。
東阿縣張本家族墓地石刻本身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科學、工藝、社會價值,是東阿縣這一地區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實物證明,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史料信息。想要珍貴的文化遺產“延長壽命”,就必須相應地開展文物保護工作,遵循“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采用專業的技術和材料,最大限度地保護文物。
4.2 發揮地區優勢,與周邊遺址相結合形成文化片區
張本家族墓地所處區域承載著悠久的文化和歷史,其東南方向的姜樓鎮鄧廟村有龍山文化時期至漢代的聚落遺址——鄧廟遺址;鄧廟村的武當廟供奉著武當、三皇等石造像,這些石造像制作年代久遠,可以追溯到宋元時期,且制作精良,其中武當神的塑造在國內非常少見,體現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寓意深刻;張本家族墓距離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魚山曹植墓較近,僅10余公里距離。綜合來看,張本家族墓地同其周邊遺產資源具有一定和諧性。
近幾年武當廟和鄧廟遺址的修繕工作正在陸續進行,武當廟內精美的壁畫正在修復,鄧廟遺址作為具有代表性的聚落遺址,正在修繕一座遺址公園供人們觀賞游覽。從張本家族墓地去往武當廟、鄧廟遺址、魚山曹植墓道路非常順暢,各個文化遺址正好處于沿線位置。張本家族墓地應借助這些現有的資源,把文化遺產轉化成文化生產力,規劃周邊環境,利用地區優勢,與周圍的文化遺址共同發展,形成具有特色的文化旅游片區。通過對遺產間接經濟價值的開發,產生最直接的經濟效益。借助于文化遺產東阿地區的旅游品牌多了一重文化保障,也會更具吸引力。
4.3 發揮政策作用,制定法規以及鄉規民約
保護鄉村文化遺產基礎在于制定法規、標準,2008年4月,國務院公布了《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鄉村文化遺產遺址的保護有了總體法律規范。由于各個鄉村紛繁復雜的情況,村民自治達成的傳統鄉規民約,同樣具有針對性的約束作用。
張本家族墓地和石刻本來是屬于張氏家族后人管理,后來由于歷史變遷和其具有的獨特的價值,就逐漸擴大了責任范圍,村民、鄉鎮政府、相關文化部門都對其具有保護的義務。所以張本家族墓地的管理就比較特殊,一方面政府應該發揮主導作用,明確其重要的價值和地位,并制定相應的鄉規民約,給予經費、人員、方案等的支持;另一方面村民也應起輔助作用,履行鄉規民約中的責任,共同促進張本家族墓地更好的留存與發展。
4.4 發揮資源特色,開發衍生產品擴大影響力
如今隨著人們對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逐漸增強,文化遺產元素在文化產業開發中的創新性運用越來越普遍。許多文化產業公司利用文化遺產元素做設計,生產出很多衍生產品,比如故宮博物院的文創產品隨著“故宮六百年”這一熱點事件而影響力不斷擴大。所以開發文化遺產類衍生產品對文化遺產本身和文化產業來說都具有重要意義。
東阿縣張本家族墓地就具有非常豐富的文化遺產資源,比如石刻中的傳統元素:石獅、石羊的傳統形象;文武石翁仲身上的裝飾和服飾樣式、石碑上的文字等,這些文化遺產元素都帶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吉祥寓意,都是正面積極的。可以將這些元素以文字、圖像的形式進行傳播,比如加以設計之后印在飾品、卡片、衣服、日歷等物品上進行售賣。除此之外,還可以通過現今流行的新媒體渠道,比如短視頻、直播互動、小品等將文化遺產以虛擬作品形式向人們展示,使之成為鄉村文化遺產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同時成為更具商業價值的文化遺產品牌,從而擴大其社會影響力。
5 總結
在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剖析鄉村地區的文化遺產保護問題,以東阿縣張本家族墓地石刻保護為例,分析其遺址保護的必要性,探索規劃新策略和發展新措施。以此指引東阿地區文化遺產的規劃建設,同時促進鄉村振興戰略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