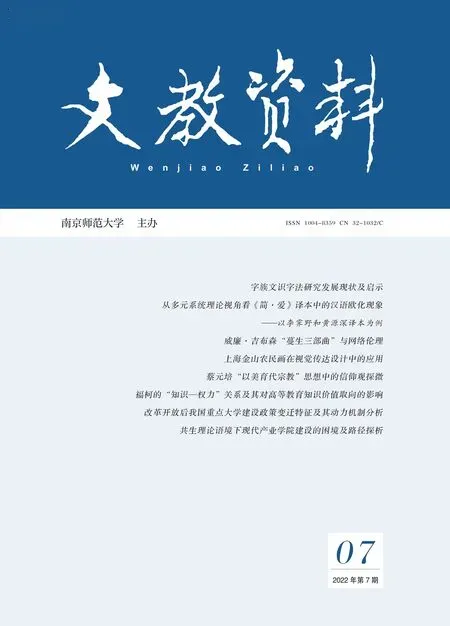改革開放后我國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政策變遷特征及其動力機制分析
薛文靜
(西華師范大學(xué) 教育學(xué)院,四川 南充 637000)
一、我國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政策變遷的政策演進
(一)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工程化萌芽階段(1977年—1990年)
1977年我國高等教育常規(guī)化建設(shè)開始進入正軌,黨中央吸取歷史經(jīng)驗和教訓(xùn),主張將運動式的發(fā)展思維轉(zhuǎn)化為漸進式的制度變遷。1977年鄧小平提出:“要抓一批重點大學(xué),重點大學(xué)既是辦教育的中心,又是辦科研的中心。”[1]轉(zhuǎn)變了之前仿蘇聯(lián)的教學(xué)中心模式,大學(xué)擁有了雙重任務(wù)即教學(xué)和科研,重點大學(xué)政策恢復(fù)迫在眉睫,為之后政策的出臺打好了基礎(chǔ)(見表1)。《關(guān)于恢復(fù)和辦好全國重點高等學(xué)校的報告》于1978年出臺,標(biāo)志著正式恢復(fù)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重點大學(xué)規(guī)模適當(dāng)擴大,增加到88所,占比全國高校的22%,到1981年,我國重大點大學(xué)數(shù)量一共96所。

表1 1977年—1990年涉及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的相關(guān)主要政策文件
由于高等教育自主權(quán)擴大,除了黨中央國家允許有更多的聲音,1983年匡亞明等教授提出“835建言”,建議中央:“像抓重點經(jīng)濟建設(shè)那樣,選定順應(yīng)現(xiàn)代科學(xué)技術(shù)與高教發(fā)展趨勢的50所左右高等學(xué)校,列入國家重點項目,集中投資”[2],將10所院校納入國家重點建設(shè)項目,稱之為“重中之重”項目,首次獲得中央專項補助款5億元,也標(biāo)志著重點建設(shè)項目啟動,到1987年重點學(xué)科啟動。
(二)世界一流大學(xué)統(tǒng)籌推進階段(1991年—2014年)
一方面,“重中之重”項目提高了一批高校的辦學(xué)質(zhì)量,重點建設(shè)項目與重點學(xué)科建設(shè)思路結(jié)合構(gòu)成了“211工程”“985工程”建設(shè)基礎(chǔ),另一方面,全球化到來,我國的社會經(jīng)濟實力不斷攀升,國家急需建設(shè)一批高質(zhì)量高水平的大學(xué)提供科技和發(fā)展的支持。這一時期,我國大學(xué)已經(jīng)開始效仿西方的大學(xué)模式,因此也開始進行世界一流大學(xué)的追趕戰(zhàn)略,大學(xué)轉(zhuǎn)入項目建設(shè)階段。1991年七屆人大四次會議批準(zhǔn)的《綱要》,形成了“211工程”的雛形,之后幾年原國家教委又發(fā)出《關(guān)于重點建設(shè)一批高等學(xué)校和重點學(xué)科點的若干意見》,“211工程”目標(biāo)正式設(shè)立,直至頒布《“211工程”總體建設(shè)規(guī)劃》,“211工程”正式拉開序幕。2012年第三期成果驗收,共112所大學(xué)進入國家項目范圍。
隨著經(jīng)濟全球化,我國越來越重視大學(xué)的地位和作用,1998年江澤民在北大建校100周年發(fā)表講話:“為了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xué)。”[3]1999年《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發(fā)布,標(biāo)志著“985工程”的第一期正式拉開序幕。2004年,二期建設(shè)擴大范圍納入高校39所,2010年三期實施,隨后2006年補充“985工程優(yōu)勢學(xué)科創(chuàng)新平臺”政策,共計33所高校入圍,2010年啟動“特色重點學(xué)科項目”政策,共計74所學(xué)校入圍。
2012年,我國高等教育開始進入內(nèi)涵式發(fā)展,追求質(zhì)量、強調(diào)特色、協(xié)調(diào)和創(chuàng)新發(fā)展。在此背景下,“2011計劃”“中西部高校基礎(chǔ)能力建設(shè)工程”“111計劃”等重點建設(shè)項目相繼實施(見表2)。

表2 1991—2013年涉及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的相關(guān)主要政策文件
(三)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xué)建設(shè)階段(2014年至今)
一方面,我國高等教育在2014年具有37.5%的毛入學(xué)率,早已在大眾化的梯隊里,因此我國的瞄準(zhǔn)了教育強國這一目標(biāo)。另一方面,創(chuàng)新是國家越來越強調(diào)的教育核心,人才需要引發(fā)傳統(tǒng)大學(xué)模式和現(xiàn)代科技創(chuàng)新模式產(chǎn)生沖突,而“985工程”作為傳統(tǒng)模式的延伸,需要一種新的模式替代,“雙一流”建設(shè)應(yīng)運而生。2014年,習(xí)近平在北大提出,“辦好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xué),必須有中國特色”,我國開始建設(shè)要具有中國特色的一流大學(xué),2015年國務(wù)院印發(fā)《統(tǒng)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xué)和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總體方案》,“雙一流”建設(shè)正式實施,9月公布第一批建設(shè)名單,其中有95所高校進入一流學(xué)科建設(shè)、有42所高校進入一流大學(xué)建設(shè)。這一階段是我國高等教育的內(nèi)涵式發(fā)展的關(guān)鍵,2018年指出一流大學(xué)要落腳于本科教育,2019年發(fā)布《教育部辦公廳關(guān)于實施一流本科專業(yè)建設(shè)“雙萬”計劃的通知》,提出到2021年,建設(shè)一萬個左右國家級一流本科專業(yè)點和一萬個左右省級本科專業(yè)點(見表3)。

表3 2014年至今涉及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的相關(guān)主要政策文件
二、我國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政策變遷的特征
(一)具體化:我國重點大學(xué)政策變遷由面到點
1.我國重點大學(xué)政策由注重數(shù)量建設(shè)轉(zhuǎn)向內(nèi)涵式發(fā)展
建國初期,我國各方面根基都比較薄弱,高等教育領(lǐng)域依然如此,在 1987年之前,我國的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政策都只落腳于大學(xué)自身的建設(shè),更加看重的是大學(xué)的數(shù)量,例如從1954年開始最初指定的6所重點大學(xué),5年之后擴大了10所,1960年擴大到64所,最后到1981年擴大到97所,占比當(dāng)時704所高校的13.78%;“835建言”后,我國高校最終重新只確定為15所,數(shù)量幅度大大降低,并且在國家在“七五”期間安排的專項補助投資比之前增加了 5億元,而相比于1982年,全國高等教育經(jīng)費總共僅為33.38億元。由此可見,在建設(shè)重點項目之前,我國重點大學(xué)政策主要注重重點大學(xué)的數(shù)量建設(shè),而在建設(shè)范圍由寬變窄后,經(jīng)費使用的針對性增強,重點建設(shè)的方向更加明確,重點大學(xué)的建設(shè)開始注重質(zhì)量發(fā)展,到2012年,我國開始走提高質(zhì)量的內(nèi)涵式發(fā)展道路,啟動創(chuàng)新探索。
2.我國重點大學(xué)政策重點建設(shè)呈現(xiàn)宏觀、中觀、微觀統(tǒng)籌推進勢態(tài)
在1983年之前,我國重點大學(xué)的建設(shè)主要是以學(xué)校整體為單位進行的,由于關(guān)注整體建設(shè),我國經(jīng)費有限,因此只能涉及少數(shù)學(xué)校,但在1978年我國開始進行重點學(xué)科的建設(shè),而在1983年間,重點學(xué)科以二級學(xué)科為建設(shè)對象,涉及的高校數(shù)量雖然相較于之前大大增加,但學(xué)科建設(shè)涉及基礎(chǔ)建設(shè)的范圍少,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經(jīng)費撥款的壓力。到“雙一流”建設(shè)時期,實施“雙萬計劃”,政策開始向微觀專業(yè)點進行延伸,不再停留于學(xué)科的中觀層面。
(二)深入化:我國重點大學(xué)政策變遷由淺入深
1.我國重點大學(xué)政策關(guān)于建設(shè)目標(biāo)方面不斷深化
“211工程”的建設(shè)目標(biāo)是:建設(shè)若干所高等學(xué)校和部分重點學(xué)科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985工程”的建設(shè)目標(biāo)是:建設(shè)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學(xué)和一批國際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xué);到2015年指出“雙一流”建設(shè)目標(biāo)是:到2020年,若干所大學(xué)和一批學(xué)科進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學(xué)科進入世界一流學(xué)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學(xué)和學(xué)科進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學(xué)進入世界一流大學(xué)前列,一批學(xué)科進入世界一流學(xué)科前列,高等教育整體實力顯著提升;到本世紀中葉,一流大學(xué)和一流學(xué)科的數(shù)量和實力進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強國。2019年“雙萬計劃”提出,2019年—2021年,建設(shè)10000個左右國家級一流本科專業(yè)點和10000個左右省級一流本科專業(yè)點。由此可見,在政策目標(biāo)上,我國建設(shè)目標(biāo)在逐漸深化。
2.我國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在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中的地位進一步提升,國家對其資源上的支持加大
首先,在“835建言”之前,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是中央財政對高等教育的統(tǒng)一撥款,但在這之后,我國的撥款方式轉(zhuǎn)變?yōu)椤熬C合定額+專項補助”。其次,我國對重點建設(shè)項目的資金支持大幅度增加,1982年,我國高等教育經(jīng)費總共僅為33.38億元,但就“211工程”建設(shè)來說,“九五期間”的資金總量約達到186.3億元,其中27.55億元是中央專項資金;“211工程”中央計劃在“十五”投入60億專項資金,其中的建設(shè)資金為187.5億元。1999年,教育部對北大、清華兩所高校就計劃撥款18億元,“985工程”僅中央轉(zhuǎn)型資金投入一期達到了142億元,二期達到了191億元[4],三期達到264億元。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清華北大獲得50億元經(jīng)費,“雙一流”建設(shè)過程中,有超過20個省市自治區(qū)發(fā)布了自身的“雙一流”建設(shè)計劃,建設(shè)投資規(guī)模超過1000億元。[5]由此可見無論建設(shè)目標(biāo)還是建設(shè)過程,我國重點大學(xué)的建設(shè)政策都在不斷深化。
三、我國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政策變遷的動因與路徑分析
(一)我國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政策變遷的動因
1.外因分析:政治民主化、經(jīng)濟體制變革動因
政治民主化提高了政策制定的科學(xué)性。1978年改革開放的號角吹響,我國開始適當(dāng)擴大高校辦學(xué)自主權(quán),但仍然以國家本位的大學(xué)集權(quán)管理模式占主導(dǎo)。[6]直到我國開始從學(xué)習(xí)蘇聯(lián)轉(zhuǎn)向?qū)W習(xí)西方,并且2010年后我國進入全民深化改革的政治背景下,“211工程”“985工程”以及“雙一流”建設(shè)的政策制定不再只依靠中央,而是在制定過程中廣泛征求社會專業(yè)人士和大眾的意見,把科學(xué)決策與民主化具體統(tǒng)一。例如高校的選擇從最初的政府決定到專家評議再到非競爭性選拔的過程都體現(xiàn)了我國政治民主化使得我國重點大學(xué)政策越來越科學(xué)化。
經(jīng)濟體制變革推動我國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政策戰(zhàn)略地位的轉(zhuǎn)變。我國經(jīng)濟體制開始向市場經(jīng)濟體制作出轉(zhuǎn)變。在1984年之前,我國一直處于計劃經(jīng)濟時期,高校的重點建設(shè)主要聽從政府的政令,其服務(wù)直接作用于計劃經(jīng)濟的發(fā)展。我國注重工業(yè)發(fā)展,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主要對工科大學(xué)進行重點建設(shè),培養(yǎng)理工人才為社會服務(wù)。改革開放之后,1984年10月中央頒布《關(guān)于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經(jīng)濟體制轉(zhuǎn)向市場經(jīng)濟體制,并且我國也開始進行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zhàn)略的實施,高校的重點建設(shè)是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社會經(jīng)濟實力增強,我國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政策的資金撥款也逐漸增多,例如中央政府用于“985工程”的資金比投入“211工程”的資金大幅度增加,北大在“211工程”一期獲得建設(shè)資金總計1.25億元,而“985工程”一期獲得的資金達到18億元,“雙一流”建設(shè)期,北大科研經(jīng)費不低于28億元。可見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在我國的戰(zhàn)略地位越來越高。
2.內(nèi)因分析:教育管理體制變革動因
教育管理體制的變革是我國重點大學(xué)政策變遷的內(nèi)在動力。我國作為后發(fā)經(jīng)濟國家,在發(fā)展初期通常需要過度依賴行政主導(dǎo)發(fā)展經(jīng)濟,其他社會服務(wù)領(lǐng)域也是完全依賴行政主導(dǎo)模式,在“教育革命”爆發(fā)之后的時間里,我國教育事業(yè)與發(fā)達國家的距離逐漸拉大,1985年頒布《中共中央關(guān)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認為政府應(yīng)該適當(dāng)管理學(xué)校事務(wù),同時加大學(xué)校的權(quán)利,擴大高等學(xué)校辦學(xué)自主權(quán)。在之后市場經(jīng)濟開始穩(wěn)定成熟后,我國高等教育的自主權(quán)都在適當(dāng)擴大,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的自由度也在擴大,例如之前我國大學(xué)重點建設(shè)幾乎由政府劃定范圍,但“211工程”“985工程”加入了專家評議,不再只由政府做主,“雙一流”建設(shè)引入了非競爭性評價。另外,在之前重點建設(shè)中往往采用單位制,進行學(xué)校整體建設(shè),容易造成精英教育挫傷其他高校的積極性,而之后的學(xué)科建設(shè)以及現(xiàn)在的專業(yè)建設(shè),評判范圍更廣,高校自由度增強,整個政策更加靈活,教育管理體制是其政策變遷的內(nèi)在動力。
(二)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政策變遷的路徑分析
1.關(guān)鍵節(jié)點分析:我國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政策變遷的路徑調(diào)整
隨著社會的大環(huán)境變化,我國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政策路徑也經(jīng)歷了幾次重大調(diào)整,其中大致分為以下兩個關(guān)鍵節(jié)點。
第一個節(jié)點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學(xué)校的自主權(quán)。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同時為高校改革引入了一點市場的因素并且提出了擴大辦學(xué)自主權(quán)的訴求,為了避免曾經(jīng)激進的變遷模式,鄧小平的領(lǐng)導(dǎo)下選擇了改革開放,即“路徑障礙,試誤反彈”,即對過去的政策不斷進行補充和修正,是一種漸進變遷的模式。由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現(xiàn)代化目標(biāo),我國的高等教育也要服務(wù)于這項經(jīng)濟方針,但由于之前學(xué)校發(fā)展受損嚴重,因此之后一方面我國開始對重點大學(xué)政策進行常規(guī)化的恢復(fù),另一方面我國在試探中已經(jīng)逐漸明白蘇聯(lián)的培養(yǎng)模式不適合中國國情,因此我國開始轉(zhuǎn)向?qū)ξ鞣浇逃卫砼c制度的學(xué)習(xí),開始注重人才國際化,培養(yǎng)具有國際眼界的人才,以應(yīng)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挑戰(zhàn),因此出現(xiàn)了我國重點大學(xué)工程化建設(shè)的萌芽,即“211”“985”等一系列工程。
第二個節(jié)點是在我國“雙一流”建設(shè)開始的時期。當(dāng)時國家正經(jīng)歷了“985”“211”建設(shè)時期,此過程中逐漸遇到了很多問題,例如學(xué)科建設(shè)重復(fù)、學(xué)校身份固化等,各類重點大學(xué)相關(guān)政策很多,如果對其進行有效整合可以提高政策效率。2014年,習(xí)近平在北京大學(xué)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我們的一流大學(xué)需要有中國特色。沒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趨,依樣畫葫蘆,是不可能辦成功的。因此,創(chuàng)辦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xué)之路的建設(shè)設(shè)想應(yīng)運而生,2015年我國“雙一流”建設(shè)政策正式登上舞臺。
2.我國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政策變遷的路徑依賴
學(xué)習(xí)效應(yīng)抑制我國重點大學(xué)政策的變革。個體與組織為了在一項制度中找到適應(yīng)點進行有效恰當(dāng)?shù)幕顒印N覈M行重點大學(xué)的管理工作已經(jīng)60余年了,形成了較為穩(wěn)定的體系,例如關(guān)于大學(xué)自主權(quán)的問題,即使很早之前就在引入,但相較于西方國家來說,我國大學(xué)的自主權(quán)仍然很小,國家很難轉(zhuǎn)變以國家為主導(dǎo)的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制度。因此在這一方面,重點大學(xué)政策的建設(shè)會進行自我強化。
高成本阻礙我國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政策的創(chuàng)新。高成本分為沉沒成本和變革成本兩類,沉沒成本是一種歷史成本,一項政策確立以及正式實施會耗費大量成本,因此我們?nèi)菀壮霈F(xiàn)“協(xié)和謬誤”效應(yīng),即如果我們投入了一項政策但發(fā)現(xiàn)其不適用時,我們?nèi)菀讓㈠e就錯,很難推翻這項政策,如果放棄這項政策就會造成對之前投入的沉沒成本的浪費。同時,制度創(chuàng)新必然意味著增加改革成本,其中包括政策制訂、實施成本以及政策摩擦成本、決策者的政策風(fēng)險成本,等等。比如實行“211工程”就會相應(yīng)調(diào)整招生培養(yǎng)政策、財政政策,等等,但本身這些政策就已經(jīng)相輔相成,環(huán)環(huán)相扣,對其變革會花費大量成本,但如果基于以前的重點大學(xué)政策成本就會小很多,并且所承擔(dān)的政策責(zé)任風(fēng)險也會大大減小,因此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政策變遷容易陷入?yún)f(xié)同效應(yīng),阻滯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政策演變的創(chuàng)新性和積極性,進入路徑依賴。
四、我國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政策變遷存在的問題及優(yōu)化建議
運用歷史制度主義縱觀新中國成立以來幾十年的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政策變遷過程,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我國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政策變遷屬于漸進性的制度變遷,制度漸進變遷貫穿于新中國成立以來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政策變遷的全過程。目前我國處于“雙一流”建設(shè)階段,這是我國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政策的時代進程,我們可以從中得出以下問題及完善建議。
“雙一流”建設(shè)需要防止指標(biāo)化過重。“雙一流”建設(shè)方案提出目標(biāo)、基礎(chǔ)、標(biāo)桿、動力,但事實上以績效為標(biāo)桿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其他幾個基本原則。在大學(xué)眼中,只有這個原則才是真真切切看得見摸得著的,比如對于某些大學(xué)績效看的是學(xué)校進入ESI前1%的學(xué)科數(shù),以此方式作為量化進行區(qū)分,但過度指標(biāo)化會使得運用不正當(dāng)?shù)姆绞竭M行數(shù)據(jù)粉飾,例如不計成本惡意挖人,當(dāng)今評選科研人數(shù)也會計算占比,一些學(xué)校出資獲得科研人員只是為了達到指標(biāo)卻將人才閑置,這是一種極其浪費資源的方式。因此我們在“雙一流”建設(shè)的過程中,應(yīng)該避免步入急功近利的框架,大學(xué)的首要功能是人才培養(yǎng),我們必須對績效有正確的理解與認識,完善績效評定之外的多元評定方式,對人才輸出質(zhì)量進行追蹤評估,只有真正提升大學(xué)的水平,在校的學(xué)生才會有學(xué)校榮譽感,從而將外在激勵轉(zhuǎn)化為內(nèi)在激勵,重點大學(xué)建設(shè)才能與人才質(zhì)量建設(shè)進入良性循環(huán),防止辜負大學(xué)的核心使命,避免“雙一流”的形式化建設(shè)。
“雙一流”建設(shè)需要防止筑起精英教育與單一化的高墻。重點大學(xué)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屬于精英高等教育部分,在集中財力進行精英教育建設(shè)時,我們樹立了有形的標(biāo)桿,對此來說會有兩種弊端:挫傷普通高校的積極性、不利于實現(xiàn)多樣化。關(guān)于高校的積極性,我們需要審視“雙一流”建設(shè)這種模式應(yīng)該屬于常態(tài)還是非常態(tài)發(fā)展。對比起過去的“211”“985”,“雙一流”建設(shè)已經(jīng)開始擴大建設(shè)范圍,但我們?nèi)詰?yīng)該思考,建設(shè)過程中這道防線應(yīng)該在哪里。另外,“雙一流”建設(shè)是以中國特色建設(shè)為目標(biāo)的,劃定范圍其實是在樹立標(biāo)桿,例如從三部委公布的“雙一流”建設(shè)名單來看,在全部學(xué)科中文科或者與文科相關(guān)聯(lián)的學(xué)科占比約23.9%,理工科占比50%以上,這種建設(shè)偏差,會給出大學(xué)或?qū)W科信號,理工科或理工大學(xué)更受重視,影響其他大學(xué)的建設(shè)方向,長此以往中國特色將難以實現(xiàn)。因此“雙一流”建設(shè)過程中應(yīng)該擴大學(xué)校入選范圍,從大學(xué)整體到學(xué)科再到專業(yè),我國的建設(shè)進程對這個問題已經(jīng)在不斷優(yōu)化,但仍可以做得更好。另外應(yīng)將學(xué)科入圍類別占比作統(tǒng)計,防止過度偏向,才能建成不同層次和類別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一流大學(xué)和學(xué)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