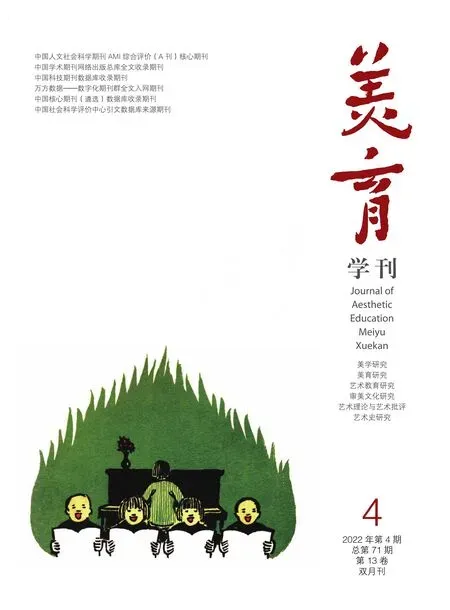民國時期高校中復合型藝術師資培養研究
趙梓銘
(哈爾濱師范大學 美術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80)
晚清民國時期,我國小學大多實行級任制,由于師資不足以及教育經費的問題,中小學中由一名教師兼任多門課程的現象廣泛存在,在藝術課程中也是如此,本文稱其為復合型藝術師資。在新學制前,大多是由一名教師兼任圖畫和手工兩門課程,因此早期的師范美術教育也是以開辦圖畫手工專修科的方式來培養相對應的師資。但是這種局面在新學制頒布后開始發生轉變,由于美育思想的傳播,促使音樂課在中小學中的地位得到提升,美育、藝術教育的理念開始將音樂課納入藝術科范疇,那么面對三門藝術課程,藝術師資的培養應該如何進行?由于高等師范學校此時已開始改組,這個問題需要由美術學校來解決。
一、音樂課的介入對原有 “圖畫手工”模式的沖擊: 圖音組與圖工組的出現
在應對復合型藝術師資培養的問題上,上海專科師范學校是最早做出新回應的學校,確切地說,是由于上海專科師范學校的理念,才影響并造就了需要做出新回應的環境基礎。上海專科師范學校的吳夢非、劉質平率先在1919年將音樂課教師納入藝術師資培養體系,并推動了美育、藝術教育中的理念轉變,劉質平起草了新學制中小學音樂課程綱要,從制度方面確定了中小學音樂課的地位,隨后才有了各個美術學校對于新的藝術課程師資要求所產生的新回應。
上海專科師范學校與此前美術學校所開設的藝術課程最大的不同是將音樂納入了師范藝術教育的范疇,這源于李叔同的藝術培養。吳夢非、劉質平、豐子愷三人師從李叔同,都有學習音樂的經歷。該校設有一間專門的音樂教室,音樂課程教授內容包括樂典、和聲學、練聲、視唱、獨唱、合唱、鋼琴、風琴、作詞、作曲等。李叔同還編輯《白陽》雜志,并發表了許多介紹藝術的文章,包括《西洋器樂種類概說》等。吳夢非等三人在李叔同的培養下成為兼通美術和音樂的跨界人才,其中劉質平從浙江兩級師范學校畢業后,留學于日本東京音樂專門學校。在音樂方面,劉質平鉆研更深,成為上海專科師范學校音樂課程的主要教師,后至上海美術專門學校創辦音樂系,成為上海、浙江一帶有影響力的音樂教師。
在蔡元培提出“美育代宗教”學說后,由吳夢非等人推行的中華美育會及《美育》雜志等相關領域中逐漸形成將圖畫、手工、音樂概括為藝術科的觀念,廣義上還包括文學,上海專科師范學校就建立在此“藝術科”概念的基礎之上,并在20世紀20年代的美術學校中達成廣泛的共識,即認為圖畫屬于平面藝術,手工屬于空間藝術,音樂、文學屬于時間藝術。既然屬于藝術,就要強調其中的審美屬性,從上海專科師范學校開始開展師范美術教育的學校,普遍將一些沒有實用性卻具備審美因素的手工內容加入課程中,如紙工、黏土工等。這些手工課內容曾在20世紀10年代實用主義盛行的時期被排斥,美育學家的訴求是希望將手工課發展為工藝美術。
這種觀念的碰撞在1923年制定新學制中小學藝術課程綱要中爆發出來。在和音樂課相關的問題上,1923年2月9日于江蘇省教育會干事會開會時,吳研因看到劉海粟提交的關于課程綱要的文章后稱,將藝術科分為繪畫、工藝、樂歌三門課是很好的,但是建議將樂歌科獨立出來,或者將其與體育科合并在一起。因為以往都是圖畫和手工由一人兼任,樂歌和體育由一人兼任,如果將三門課都納入藝術科門類下,教師教授繪畫、工藝、樂歌三門課則內容太多,也不現實。而劉海粟堅稱,樂歌屬于藝術,就應當在藝術科門類下,現實應當以學理為發展方向,而不是學理向現實妥協,如果那樣則沒有改革學制的必要了。吳研因則認為,劉海粟是在拿藝術家的眼光來制定小學藝術科課程。劉海粟堅持要將樂歌囊括在藝術科門類下,有他的考量。在新學制之前,音樂課在我國一直不被重視,屬于隨意科。在20世紀10年代高等師范學校爭相開辦圖畫手工科時,音樂課還只是作為普通陶冶性質的課程在學習,并沒有形成專門的科系,音樂課在學校系統內的普及要遠晚于圖畫和手工兩門課,筆者認為這和音樂課缺乏實用性有密切關系。直到五四運動后,新的美育觀念興起,才將音樂整合進藝術科的概念中。音樂課和新文化運動提倡的新文學一起發揮的作用在于,將圖畫和手工兩門課從“實業救國”的理念中剝離出來,進而走上藝術化陶冶的道路。如果不將音樂納入藝術科范疇,藝術的審美屬性不容易顯現,圖畫課很容易跟隨手工課走上實用主義的老路。因此藝術陶冶理念的發展,與上海專科師范學校將圖畫、手工、音樂三門課作為教學內容,進而到該校高師分為圖畫手工和圖畫音樂兩科的這種學科設置,有著密切的關系。只有將音樂納入正式科系中,才能促使圖畫和手工兩門課顯現出其藝術屬性。
那么如何解決圖畫、手工、音樂三門課在藝術師資培養中的課程問題,上海專科師范學校對于中等師范和高等師范采取了不同的培養方式:在中等師范方面,該校設有普通師范科,教授圖畫、手工、音樂三類課程,以培養小學藝術科師資;而在高等師范方面,則采取了圖畫音樂組和圖畫手工組這樣的分組教學模式。對于小學師資和中學師資培養的區別,在教育界一直有這樣的看法:認為小學師資所教授課程程度較低,因此可以采取“廣而泛”的培養策略,在藝術科部分,即培養能夠教授三門藝術課程的教師;而在培養中學師資方面,則可以相對更加“專門”一些,至于“專門”到何種程度,不同的學校有著不同的想法。上海專科師范學校在這一方面采用了兩兩分組的方式,即培養能夠教授圖畫和音樂課的教師,以及能夠教授圖畫和手工課的教師,希望在“廣”和“專”兩方面達到一定的平衡,有所兼顧。隨后由上海專科師范學校發展起來的上海大學美術科、上海藝術大學、上海中華藝術大學,以及上海美專等都采取了上海專科師范學校的分科方案,這也是吳夢非提到的,“本科分圖畫音樂部與圖畫手工部兩部,近年來我國藝術學校都已仿行了”。
上海美專在辦學之初并沒有完全采用上海專科師范學校的分科方案,該校于1921年招收第一屆高等師范科,該科的課程具有新學制靈活選修的特點,在總課表中包括了圖畫、手工和音樂三部分課程。學生如果修習滿三個主科,就頒發本科畢業證書;如果只修習其中的兩科,如圖工、圖音、音工,則頒發兩科結業的選科畢業證書;如果只修習一門主科,則只頒發一科結業的選科畢業證書。在上海專科師范學校已經有了圖工、圖音的分科方案后,劉海粟仍然堅持實行這樣一套靈活選科方案。在前文提到的劉海粟和吳研因關于音樂科和體育科合并的爭論中,劉海粟堅持音樂作為藝術應該和圖畫、手工統轄在藝術科的范疇內,因此劉海粟的這套靈活選科方案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希望學生只學習一門或兩門主科,而是期望學生能夠學完三門主科。鑒于音樂對于這時剛剛起步的美育理念的重要性,培養兼顧圖畫、手工和音樂三門藝術科課程的教師是劉海粟所期望的,也對藝術教育的整體發展最有利。但就實際情況來說,吳研因的一個看法是正確的,那就是學習三門主科對于學生來說課業過于繁重。在上海美專于1921年至1923年共招收的5屆高等師范科學生中,僅有一人修完三門主科拿到本科證書,而該科畢業生總計164人,表1反映出很多問題。

表1 1921年至1923年上海美專高等師范科 畢業學生人數表[4]
首先,課程標準中提到的允許修習音樂、手工兩門主科的情況,在實際中由于無人報考并不存在。其次,單獨修習手工或音樂課程的學生數量皆為1人。最后,在修習兩門主科的學生中,大部分選擇了圖畫手工系。選擇圖畫音樂系較少的原因是學生本身對音樂的興趣就要少于圖畫,對于這一點可以參考單獨修習圖畫系的學生為14人,遠多于單獨修習手工系和音樂系的學生這一情況。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圖畫和手工同屬于美術范疇,互相關聯;而音樂雖然是藝術,但屬于聽覺藝術,學習圖畫對學習音樂沒有促進作用,學生在已有圖畫方面的基礎上,再學一門音樂相當于從零起步,反之亦然。在單獨修習主科方面,學生最喜歡的是圖畫,這符合一般人喜歡繪畫的特點。學生不喜歡學習手工,可能是因為手工課程相對更加辛苦、勞累,更像工匠。五四運動后,繪畫已經開始向新文學的方向發展,開始有了啟蒙性,有了更高的精神性。相比之下,手工課仍然在“實業救國”的理念下發展,容易讓學生聯想到職業學校或工人在工廠做工的場景,所以單獨修習人數過少。至于音樂方面,可能和上海美專本身是美術學校有關。此時上海美專還沒有開設音樂系,因此就已經潛在地將對音樂感興趣,或有音樂基礎的學生篩選掉了一部分,相當于在熱愛美術的學生中尋找熱愛音樂的學生,這樣自然會很困難。至1923年新學制課程綱要正式推出后,上海美專調整了師范專業的學科設置,于1924年開始招收新制藝術教育系圖工組、圖音組和音樂組。音樂組僅第一屆招生2人,此后再無招生。此次改制后的藝術教育系明確了圖工和圖音兩組,取消了此前的靈活選修方案,可見上海專科師范學校于1919年就已確定的分科模式是較為適應現實狀況的。此后我國大城市的美術學校大多采用了這種分科方式,如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武昌藝術專科學校等。
在上海專科師范學校之后,緊接著開辦高等師范美術教育的學校除了上海美術專門學校外,還有北京美術專門學校,這兩所學校由于所處的地方環境、所持的觀念不同等原因,在課程上有所不同。
北京美術專門學校在歷史上曾兩度開辦高等師范科,又兩度停辦。第一次于1920年開始招收第一屆高等師范科,至1922年升格為專門學校時,該校有高等師范科三屆學生,此后停辦了高等和普通師范科。第二次于1934年從北平大學獨立為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后開辦藝術師范科,于1936年被教育部要求關閉藝術師范科。教育部認為藝術師范科課程與其他科大同小異,為節省經費,將現有學生分別并入其他各科。根據1922年學校的師范科課程,以及1936年關閉師范科時,開設有圖工、雕塑、繪畫等科,可以得知兩度開辦師范科,其課程內容應大致相同,皆是以教授圖畫和手工兩門課程為主。與上海的幾所學校不同的是,該校并沒有將音樂納入高等師范科的教學范圍。但這并不代表北京藝專沒有培養過音樂師資,它在1925年改為藝術專門學校后開始招收音樂系學生。該系雖然沒有并入師范科,但筆者認為學校并不介意“用培養藝術家的方式來培養師資”,其音樂系畢業生的就業方向多為中小學音樂教師,起到了事實上培養音樂師資的作用。如慕鄒在成立北平華北學院藝術教育專科時稱,北平的藝術專門學校所培養的人才過于專門,并不適應中小學需求,顯然這里指的就是北京藝專。
到20世紀20年代新學制頒布之后,北京師范大學于1924年招收圖畫手工科時仍然沒有對音樂課一事有所回應,反倒是北京女子師范大學于1924年開辦了音樂專科,培養音樂師資,但此時該校圖畫手工科已經停招。可知,北京地區在藝術師資培養方面,由于種種原因,傾向于將美術和音樂兩者分開培養。如徐悲鴻在1928年調任北平大學藝術學院院長時,曾主張將藝術學院改為美術學院一樣,所反映的是這一地區的教育實施者對美術和音樂兩者之間的界限有著更為明確的劃分,不像江南地區更看重美術和音樂在教育上的相通之處。
二、內陸地區師資培養的不同 嘗試:三科兼修與專任 繪畫師資的培養
由于藝術科觀念的形成,像劉海粟最初一樣,堅持三科兼修的學校有很多,大量中等師范學校都是這種教學模式,但在高等學府中也采用這種模式的學校,就是成都師范大學。
20世紀20年代初高等師范學校大部分改組綜合類大學后,圖畫手工科也陸續關閉,在這之后仍然還在開辦藝術師范教育的是成都師范大學。成都高等師范學校工藝圖畫科學生于1924年畢業后,相關專業一度停招,1927年改組為成都師范大學后開始招收第一屆藝術專修科,并于1931年改組為四川大學,該科整合入教育學院,于同年招收最后一屆藝術專修科后停招。該校藝術專修科學習圖畫、手工和音樂三類課程,說明在高等師范領域也有堅持三科兼任培養模式的學校。但這和上文提到的上海多所學校不同的是,不同地方的經濟發展狀況不同,影響學校采取兼任或專任培養模式的主要原因是畢業生的就業學校是否有財力聘請多位教師。上海的中學普遍可以聘請兩到三位藝術課教師,劉質平、劉海粟等人都在上海的中學擔任過單獨的音樂或美術教師。如果中學聘請兩位藝術課教師,那么需要其中一位有兼任兩門課程的能力,因此兩科兼任的培養模式在上海可以發展開來。據此推測,我國西南地區各學校經濟狀況并不寬裕,成都師范大學藝術專修科的學科設置更適合地方區域發展。
同時,這還意味著在北京以外的地區,新學制以來的“藝術科”概念已經滲透入師范大學。誠然,北京師范大學和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在美術和音樂師資的培養上具有明確的學科劃分。但此前成都高等師范學校除開設圖畫手工科外,同時還開設樂歌體操專修科,如吳研因所言,將音樂和體育劃分在一起培養師資是一個傳統,具有一定的歷史慣性。而到1927年成都師范大學在開設藝術專修科的同時還開設體育專修科,這說明經過新學制時期的思想傳播,學校已經越來越接受“音樂屬于藝術”這一觀念,故將音樂劃入藝術專修科,而獨立設置體育專修科就是為了遵從這種學理。
除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地的美術學校外,我國內陸地區也有許多美術學校,本文將這些美專稱為“地方美專”,將大城市的美專稱為“核心美專”,兩類學校有著較為顯著的區別。我國近代美術專門學校的發展始終圍繞著一個核心議題,那就是將西方藝術介紹到中國,以及在和西方藝術的互動中如何發展我國固有的藝術——中國畫。那么,學校的教師是否有留學經歷就顯得很重要,核心美專的教師大多有留學經歷,是將西方藝術介紹到中國的直接傳播者;而地方美專的教師大多為核心美專畢業,是將西方藝術從我國發達地區介紹到內陸地區的傳播者,也即二次傳播者。因此,兩類學校除了從發展上來講有這樣的前后波次關系外,其他方面也具有不同的性質。核心美專由于地處大城市,有全國生源供應,辦學相對穩定,且持續時間較長,大多從20世紀20年代初一直發展到全面抗戰爆發,甚至有的學校在抗戰爆發后仍然可以轉入后方辦學多年。地方美專大多在20年代中后期開始發展,經費緊張,辦學條件簡陋,或學制較低,或科系覆蓋面窄。和本文密切相關的是,它們在師范教育的發展上也呈現出鮮明的區別。
在考察了奉天美專、廈門美專、西南美專等開設高等師范科的基礎上,筆者認為,地方美專在師范教育方面大體上并不采取培養復合型藝術師資的模式,在課程中以繪畫課占據主要地位,手工課和音樂課大多是缺失的。這有幾方面的原因:首先,音樂教育在我國近代起步較美術要晚得多,從1919年上海專科師范學校開設高師圖音組開始,至1922年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培養專門音樂人才,再至1924年及1925年上海美專和北京藝專相繼開辦音樂系,我國才開始有成規模的音樂專業。因此,地方美專在經費緊張的情況下難以聘請到足夠多的音樂教員是一個問題,另一個問題就是購置音樂設備的費用開支。其次,和音樂課情況類似的是手工課部分。在上海美專及原高師的手工課中,都需要學校設置專門的手工教室,即手工工場,這里面需要配備各類手工所用的材料,如木頭、金屬、黏土、石膏、竹子等,同時需要刀等工具,以及金工課所需的機器設備。這些設備都占據著學校重要的開支。而地方美專本身在維持學校運轉方面就已經十分勉強,顯然無法再增加開支。地方美專經費緊張的原因在于這些學校多是私立學校,缺乏政府資金支持,也無法通過提高學費來為學校籌得資金,這就使得手工和音樂兩門課的開辦存在著經濟上的困難。最后,這里面也有重視繪畫的觀念所在。經過20世紀20年代初美育及藝術教育理念的發展和傳播,以“人生的藝術化陶冶”為核心的美育理念在上海一帶倡行,并通過上海學校的畢業生回鄉辦學的方式,將這些觀念傳播到地方。這些地方美專的創辦人多為在國內求學的藝術學生,他們視藝術創作及傳播藝術理念為理想,因此開辦的學校也更傾向于繪畫,而不是實用性更強的手工課。
三、復合型藝術師資培養的高峰: 國立中央大學教育學院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于1927年由江蘇省立藝術專修科并入,稱藝術教育專修科,分國畫、音樂、手工三組,學制二到三年。1929年9月藝術專修科改為藝術教育科,改為四年制,從專修科提升為大學本科,改分國畫組、西洋畫組、工藝組和音樂組四組。該校藝術教育雖然是師范教育,但十分注重專業能力的培養。該科系培養宗旨有三點:其一,具有相當技巧、美的認識、普通教育常識,充中等學校師資;其二,有高深技巧,具創作能力,備教學時以個人制作供觀察;其三,對于教育制度及方法等問題之研究,備貫徹美化教育的實現。該科認為合格的中學藝術師資的前提是具有相當的創作能力,因為只有具備了創作能力,才能夠在教學時通過教師自己的示范給學生以正確的引導。顯然,“言傳身教”是該系注重創作培養的理論依據。
除必修課外,選修課程內容包含兩部分:一部分為除該組以外的另外三組藝術課程,如國畫組選修西洋畫、工藝和音樂課;另一部分為文學、哲學及社會學科課程。第一學年藝術選修課每周授課時數共4課時。第二學年在此基礎上,加入文學、哲學、社會各學科內容,這一部分每周授課時數為6課時,加上前三組藝術選修課共10課時。第三學年第一學期和第二學年相同,從第二學期開始三組藝術選修課程增加為每周6課時,加上文學、哲學選修課每周共12課時。第四學年第一學期與第三學年第二學期相同,第二學期藝術選修課課時減少為每周4課時,共10課時。
該科課程存在著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從該科的分組方面看,學校似乎并沒有像前面提到的實行多科兼任的培養模式,并且在升格為本科后,圖畫課內部分成國畫和西洋畫兩組。這個分科方式多是培養專業創作人員的科系所實行的,但每組內同樣設置了選修課程來輔修其他三組的課程內容。由于改為本科后學制延長,所以即使選修課的單位課時并不多,但年限增長后也使學生具有能夠兼任多門藝術課程的能力,這就使該科也具有復合型培養模式的性質。但這種多科兼任又與上海學校所采取的圖音、圖工模式不同,國立中央大學藝術教育科的培養方式兼顧了學生在某個藝術領域的專業深入,以及在四門藝術課程中的廣泛涉獵這兩方面,因此該校學生在某個藝術門類的專業程度要高于上海學校兩兩分科的模式。
第二,該科除藝術類課程外,還關注到對學生教育學方面的培養。該科囊括了這一時期師范教育普遍要涉獵的教學環節:教育學、教學法學習,教材研究,教學實習。這些都是當時我國其他美專所無法全面包含的。
第三,需要關注的是該科對圖案畫和用器畫的課程安排。圖案畫和用器畫原本都屬于圖畫課的范疇,西洋畫組和國畫組都注意到了圖案畫的教學是值得肯定的,只是課時很少,這也符合20世紀20年代以后在師范教育中的美育風氣,即寫生創作既是圖案畫學習的基礎,也是整體繪畫學習的目的。因此,相對于高師時期,此時的圖案和繪畫之間的界限開始變得清晰起來。而用器畫已經從西洋畫組和國畫組中刪去,變為工藝組的專業課,同時加上該組內更多課時的圖案畫。該科踐行了自新學制以來的觀念,那就是以藝術表達和實用為界限來劃分圖畫和手工兩門課,也即形象藝術課和工用藝術課,這是該科和其他美專顯著不同的地方。經過這樣的重新劃分,圖畫課部分開始等同于繪畫,而原本圖畫課中實用的部分,圖案畫、用器畫和制圖開始更多地被納入工藝課的范疇,這標志著圖畫和工藝兩門課之間的定位區別越來越顯著。因此,可以看到工藝組中加入了物理、化學、機械學等曾經在高師才有的課程配置,這是工藝課走向實用化的必然結果。
第四,該科的文理課程安排也具有鮮明的特點。前面提到工藝組開設了物理和化學兩門課,這是繼承自高師的“科學化藝術”觀念。同時,在選修課中還安排了為數不算少的人文學科課程,這是五四運動以來將藝術和人文學科構建起密切聯系的風潮所致。此外,各組通習課除了黨義、國文、外國文是必備課程外,還加入了生物課,這是為奠定藝術的寫實主義基調而做出的鋪墊,可以追溯到20世紀10年代以繪制博物科標本和解剖圖為內容的實用主義圖畫課導向,而在此出現的生物課,筆者認為更多的是為藝用解剖學做基礎而設立,其實是見證了繪畫從繪制標本到科學寫生這一思路的轉變。
第五,該科國畫組的教學主要課程名為“實象模寫”。雖然此時徐悲鴻已在該科教學,并在之后擔任西畫系主任,但他的寫實教學并未深入影響到國畫組,也就是說此時的國畫組教學還沒有實行新中國成立后的那種“徐悲鴻模式”。從課程名稱上也可以看出,如果在國畫組推行西式素描的話,這門課就會稱素描,而不會稱“實象模寫”,因此這門課的內容應包含具有國畫特點的寫生及臨摹兩種教學方式,這與其他大多數美專在國畫教學上仍然保留大量臨摹環節是一樣的。
第六,該藝術教育科關注到了高等藝術師范教育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如藝術培養的專業性、藝術涉獵的廣泛性、教育技能的培養和學生的基礎素質培養。這些內容之所以能夠在該科實現,是因為其本科學制所賦予的4年修業年限,以及每組每周的超長課時量。該科國畫組和西洋畫組每周課時量平均都超過35課時,而工藝組達到40課時,同期上海美專圖音組和圖工組的每周課時量平均為28課時和32課時。這些得以保障的根源在于該校作為同期舉全國之力建設的大學經費充足,該科配有手工工具400余件、樂器60余件,其余繪畫工藝用具百余件,但該科學生并不多。1930年第一屆藝術專修科畢業24人,1931年畢業20人,1932年畢業4人,1933年第一屆藝術教育科畢業8人,1934年畢業7人,1935年畢業32人,1936年畢業4人。7年間該科僅畢業99人,每個學生都能得到較好的培養。
至1931年該科工藝組停辦。1933年國立中央大學教育學院修訂了各科課程標準,藝術科培養目標改為:1.培植純正堅實之藝術基礎,以造就自立發揮之藝術專才。2.養成中學及師范學校之各種藝術師資。3.養成藝術批評及宣導之人才,以提高社會之藝術風尚,而陶鑄優美雄厚之民族性。該科在關閉工藝組、修改了課程標準后,培養性質發生了較大變化。
首先,保留了通修課。各組通修課,即黨義、國文(每周3課時),英文(每周3課時),普通體育、軍事訓練。在選修課方面和1929年的課程標準一樣,雖然名為選修,但實際上是必修。因為在各組各學年應修學分統計表中,選修課部分應修學分為所有選修課學分之和,因此這個選修課的概念只是表明了選修課和必修課所具備的不同意義或性質,并非學生真的可以在這幾門課程中選擇學習。
其次,隨著工藝組的停辦,西洋畫組和國畫組的工藝課也全部停辦,連帶著用器畫也被取消,這就使得該科成為專門學習繪畫的科系,開始具有和地方美專一樣以繪畫為主導的性質。1934年該科學生費成武、劉騏生、夏同光等認為實用美術對于國家生產前途至關重要,因此發起組織中國實用美術研究社。不知其中是否也有因工藝教學缺失而需要學生自行補充的原因。
最后,各組之間兼修培養的模式被取消。1929年的課程設置中,各組學生除了學習本組的課程之外,還要學習另外三組的課程,以擴展其在藝術造詣方面的廣度。1933年修訂課程標準后,這一環節被取消,西洋畫組不再學習國畫,音樂組也不再學習繪畫。雖然國畫組仍然要學習西洋畫,但這是另一個問題。選修課所保留的是人文學科課程,如中外通史,這和1929年的課程設置是一致的。兼修培養模式被取消所導致的就是培養人才的專業化程度加深,西洋畫組除學習英文外,還在選修課中加入三學年的德文、法文課程,相當于為學生留學深造打下基礎。而教育學課程只在國畫組和音樂組開展,在西洋畫組中被取消,同時還取消了各組的教育實習。國畫組中的中小學繪畫教學法課程由呂鳳子教授,此時可能是國畫組和西洋畫組在對待科系發展上產生了分歧,西洋畫組教師更希望以培養藝術專業人才為培養目標,當然這也更符合該年藝術教育科修訂的新的培養目標。
綜上,國立中央大學教育學院藝術教育科的師范教育在1927年后的幾年間兼顧了藝術師資與專業人才、審美教育與實用教育兩方面的實施,1933年后開始轉向以培養藝術專業人才為主。本文認為發生這種轉變的原因在于原藝術教育科主任李毅士的離職。李毅士于1930年離職,由汪采白接任,后唐學詠于1931年接任藝術科主任。
李毅士對師范美術教育有自己的看法。首先,他贊同美育促進德育的看法。更重要的,在對待藝術師資課程的設置上,他認為技術練習應占40%,藝術理論及藝術教育原理應占10%,普通教育常識及藝術教學法應占10%,普通常識應占40%。李毅士的觀點和師范教育界的觀點有相合之處,認為藝術師資的普通常識課程不宜過少,藝術教師缺乏常識會導致坐井觀天,唯藝術獨尊,反倒會招學生反感。雖然從五四運動以來的美育觀點普遍強調藝術與科學的區別,但李毅士認為不能因藝術與科學不相關就不學習科學,因為現在是科學的世界,藝術必須在不違背科學原理的情況下方能立足,教員要使學生了解藝術和科學的共通之處。如果教員不學習科學會導致學生迷信藝術而厭惡科學,或使學生受科學的熏陶而鄙視藝術,這都是發展藝術教育的人所不希望看到的,因此藝術教師豐富自身的科學素養是擴大藝術教育影響力,以及彌合藝術和科學之間鴻溝的關鍵。
四、復合型師資培養的學理基礎
這一時期的藝術師范教育由于經費所限大多采取了兼任師資的培養方法,但是在兼任兩門課方面,卻可以有不同的組合方式。圖畫、手工、音樂三門藝術課再加上體育都是中小學中的“副科”,是不參與升學考試的科目,因此在教師兼任方面通常會將這四門課程兩兩組合,形成對應的師范科。最常見的是圖畫手工科,因為圖畫和手工同屬視覺藝術,雖然有審美和實用這兩種不同的傾向,但相對于音樂和體育來說,圖畫手工之間的共性要大于差異性。既然圖畫和手工結成了一個組合,那么很自然地音樂就和體育結成了一個組合,就像吳研因說的一樣,體育音樂師范科在20世紀10年代早期就已經在我國師范學校中存在了。重慶藝專校長范眾渠在計劃增添體育音樂系時稱,體育可以使人身體強健,而音樂能夠使人心靈高尚,因此音體結合可以使人身心發展趨于平衡。和圖畫手工科不同的是,音樂體育科更早地被認為和學生的身心愉快有著密切聯系,尤其是舞蹈和體操之間的密切關系,使得將音樂和體育師資融合在一起培養顯得更加合理;而那時圖畫手工科更多的是承擔著輔助科學與實業發展的生產功能,這是20世紀10年代流行的觀點。五四運動后,在蔡元培和中華美育會的推動下,圖畫開始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審美活動中,因此在劉海粟和吳研因的爭執中,劉海粟要求音樂應該和圖畫、手工等藝術學科結成組合,而不是體育。圖音組和圖工組的出現就是這種觀念轉變的產物,在此之后的高等學校中,如北京師范大學等確實將體育系獨立出來,成為單獨培養體育師資的體育專修科。而在同期的美專中,音樂師資仍然和圖畫師資同處一科。顯然在這樣一種關系中,音樂處于中間位置:如果從身體運動、律動的角度看,它和體育更密切;如果從藝術屬性看,它和圖畫、手工更密切。因此即使到了30年代,仍然有學校開設音樂體育系,如重慶美專和奉天美專。
此外,一些師范學校也有著不同的嘗試,如奉天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曾開設體育美術專修科,20世紀10年代早期的一些體育專門學校中也多兼開美術課程,培養能夠兼任體育和美術兩門課的師資。體育和美術之間相對來說自然沒有那么多相似性,但是由于這兩門課對于社會的重要性,在教育資金和師資不充足的情況下是被優先考慮的。近代我國被西方列強打開國門后,“東亞病夫”的頭銜成為我國精英人士的心病,改善勞動人民的身體素質至關重要,這不僅關系到生產力,也關系到國防問題,因此體育課很早就被中小學校重視。而美術由于涉及生產問題,也受到關注。相對來說,音樂由于其較為純粹的藝術性與欣賞性,在普及教育中的地位是最靠后的,這才促成了體育美術科這種復合型師資培養模式的出現。
另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是圖畫和手工這兩門課內部各部分之間的培養問題。圖畫課作為一個整體,內部涉及幾個二級領域的教學,即繪畫(包括國畫和西洋畫)、圖案學和用器畫(制圖),其中圖案學和用器畫處于圖畫和手工兩門課的交叉領域。雖然繪畫是主要部分,但圖案學和用器畫也是必不可少的教學環節。蔡耀煌談過這個問題,他說有的學校派一個學中國畫的教師來教圖畫課,結果這個教師既不能教西洋畫也不能教圖案畫。也就是說,如果按照藝術家培養模式中的中國畫和西洋畫的分組教學展開的話,是不能勝任中小學教師的職責的,故就需要藝術師資掌握中國畫、西洋畫、圖案學和用器畫四部分的知識技能,這也是美專中非師范科學生就任中小學教師時所面臨的問題。這些學生雖然投考的是非師范科,但是在畢業后大部分學生的就業仍然走向了中小學教員這一職業,這勢必導致中小學藝術課教學質量的低下,也是為藝術教育學者所詬病的主要方面,同時也是藝術專業教育和藝術師范教育應當有所區分的根本原因。
綜上,在20世紀20年代的高等師范藝術教育發展中,音樂課的加入促使了此前高等師范學校中圖畫手工科模式發生轉變,而這種轉變是由美育思想中對藝術學科建設以及課程藝術性的重視引起的,藝術師范教育的教學內容應和中小學課程內容相匹配。同時,經過師范美術教育的多年發展后,1939年時鐘道贊談到勞作教師的培養問題時稱,過去的三年專修科學制對于培養勞作教師時間太短,建議改專修科為系,增加教育年限,提升師范教育的學制,改為本科。勞作師資在30年代面臨的培養困境其實是整個藝術學科師資培養都存在的問題,只不過勞作教育由于涉及30年代的民生國本問題而得到了重視,其根源是技能學科的師資應該如何培養的問題。我國歷來輕視技能學科,認為其只是一門技術,所以在學制和修業年限上并不能和文理科取得平等的地位。從《奏定學堂章程》頒布那時起,就在基礎教育中劃分了正教員和專科教員這兩類,正教員教授數理化、史地政等理論學科,而專科教員教授圖畫、手工、音樂、體育等技能學科,這也是日后在高等教育領域劃分本科和專修科的最早依據。美術等學科由于是技能學科而得不到和其他理論學科一樣的學科地位,導致學生日后在報考這類專業時無法得到和其他理論學科相同的學歷水平。新學制頒布后曾允許單科大學這一規制存在,因此這一時期有上海藝術大學、中華藝術大學、新華藝術大學、國立杭州藝術院、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學院(原國立北京藝專)等本科學制的藝術學校出現。但在這些學校里,高等師范美術科始終是三年修業程度,處于專修科水平,師范教育學歷低的問題并沒有隨著專門學校以及藝術大學的升格而得到改善,它只影響到專業教育。美專在1929年頒布《專科學校組織法》后產生過抗議降級改專的活動,但在此之前實施四年制專業教育時,也少有人為師范美術教育的專修科學制發聲。在這樣的觀念下,藝術師范教育及基礎教育中藝術教育水平的低下就可想而知。而在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的實踐中,通過提升藝術師范教育的學制地位,有效地解決了此前關于復合型藝術師資在培養中課時量過大的問題,雖然該模式沒有持續地推進下去,卻是我國較早地對這一想法所采取的積極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