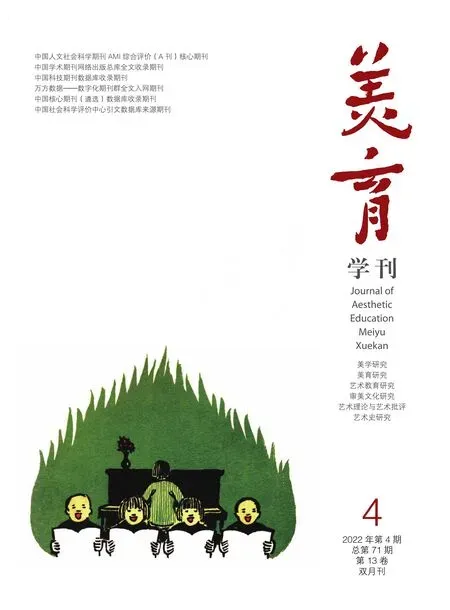《藝術列傳》與中國藝術史學“三大體系”的關系
李倍雷
(東南大學 藝術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6)
藝術學科屬于人文學科范疇,這是學界沒有爭議的共識,藝術學理論下有藝術史等二級學科。我們這里主要探討藝術史學的“三大體系”問題。需要指出的是,藝術史不應局限在某個門類藝術的范圍內,否則無法看清某一門類在藝術史中的位置,看不到門類藝術之間的相互關系,也不可能考慮到其他門類因素之間的共同作用,故需要避免以門類藝術史立場,僅看到獨特性(局部性)而看不到藝術史的整體性的弊端。這是我們探討建構中國藝術史學“三大體系”——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基本前提。“三大體系”中,以學科體系立心,以學術話語立道,以話語體系立命;建構當代中國藝術史學“三大體系”則需要立足于“二十六史”《藝術列傳》以及有關傳統藝術經典文獻,依“經”立道。“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故此“二十六史”《藝術列傳》等相關經典文獻支撐中國藝術史學“三大體系”的建構。中國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立心)、學術體系(立道)和話語體系(立命)又是相互關聯的整體而不是分離的。中國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是在藝術的范疇內專門探求藝術現象變遷和藝術史實的變化規律,立足于中國藝術譜系;中國藝術史學的學術體系則是闡釋與揭示藝術史學科的本質與普遍規律的系統理論知識,立足于時代精神;中國藝術史學的話語體系則是對藝術史學科的系統理論知識,專業性的概念、詞語的表述和詮釋,其語言釋名是話語體系觀念、思想等的形式載體,立足于時代主題。我們主要分析和探討中國藝術史學“三大體系”與“二十六史”《藝術列傳》以及相關經典文獻的關系。
一、《藝術列傳》與中國藝術史學的 學科體系
有關中國藝術史學的學科性質和定位在學界盡管存在不同的看法和觀點,但總體上說都認同中國藝術史是匯通各種藝術門類的整體、宏觀、綜合的藝術史,即通常說的一級學科藝術學理論所屬的二級學科的藝術史,對藝術史的這種學科認知是我們探討中國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的邏輯前提。也就是說,我們要構建的是一個包含有音樂、舞蹈、美術、戲曲、曲藝、戲劇、影視、設計等多門類史學的橫向交叉組成的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這是藝術學科內部學科橫向的交叉關系;另外還存在藝術史與其他人文學科的交叉關系,如與歷史學(考古學)、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文學等交叉的史學關系。在討論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之前,我們先要澄清一個與藝術史相關的“藝術學”的學科問題。對于“藝術學”的不同認知,就存在對“藝術史”的不同認知。
有些學者只要一提到“藝術學”,就立即與德國的一些美學家關聯在一起,如馬克斯·德索瓦爾(Max Dessoir,1867—1947)、烏提茲(E.Vtit,1883—1965)等,并以德索瓦爾《美學與一般藝術學》(1906)為“藝術學”建構的標志,認為藝術學的起點就是德國美學家所建構的“藝術學”。故此,只要提及“藝術學”,就言必德索瓦爾。不可否認,20世紀初德國美學家意識到美學無法解決藝術的問題或者說美學呈現出“窮途末路”的跡象,于是德國的美學開始轉向藝術學,出現了具有終結西方傳統美學意義的《美學與一般藝術學》專論。應該說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以德國為首的西方美學“轉向”的變化,從而為西方的藝術學的建構奠定了基礎。但我們也要注意到,20世紀初歐洲德語圈同時還出現了“比較藝術學”和“比較音樂學”并行不悖的現象。這種現象意味著20世紀初的歐洲,在有關“藝術”的概念中并不包含“音樂”,且“比較藝術學”中的“藝術”實際上是我們現在說的“美術”,故稱為“比較美術學”或許更為合適。20世紀70年代,日本學者山本正男(Yamamoto Masao,1912—2007)將德語圈學者的“比較藝術學”研究成果與日本學者有關“比較藝術學”的研究成果匯集在一起,命名為《比較藝術學》,共六大卷,顯示了20世紀初期、中期的“比較藝術學”實為“比較美術學”成果。我們這里提到這個現象,其意義在于說明20世紀初德國的“藝術學”是以“美術”為主體的“藝術”概念與內涵,且并不包括“音樂”“舞蹈”等內容,與我們所探討的“藝術學”是不同的學科性質和學科定位。
我們提到的一級學科“藝術學理論”,是1994年創建于東南大學藝術學系的原二級學科“藝術學”升為十三大學科門類后的學科名稱,這是典型的具有中國特色“藝術學”的學科性質、學科特征和學科定位,即有著自己的藝術學理論定位的學科體系。它是在美術理論、音樂理論、舞蹈理論等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整體的、宏觀的和綜合的研究,探討藝術普遍性、共性和規律性的問題,“藝術史”的學科定位就是在這種整體、宏觀、綜合的“藝術學理論”框架下展開的史學研究,這是中國藝術史學科的基本定位。中國藝術史則也應該按照一級學科“藝術學理論”所屬“藝術史”的學科定位建構其史學的學科體系。也就是說,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同樣是在匯通不同藝術門類史的基礎上,進行綜合、宏觀和整體的藝術史研究,探討藝術史的一般規律、藝術史的變遷、藝術史的普遍性和藝術史的原理等史學問題;有的學者也稱為“跨藝術門類的藝術史”,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只是提法不同而已。但是要真正認識到中國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則需要與中國正史的《藝術列傳》聯系起來,也就是說從“二十六史”《藝術列傳》的“譜系”史學視角認知中國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
所謂學科,在某種程度上講,就是指特定范疇中所形成的一系列探討、分析與研究對象的性質、規律所規定的學理要求。我們結合“二十六史”《藝術列傳》內涵和譜系來探討中國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問題。“二十六史”《藝術列傳》內涵范疇與譜系是當代中國藝術史學學科體系的基本范疇與基礎,由此所形成的對它們的性質、規律所作的規定的學理探究是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范圍。在“二十六史”《藝術列傳》中,最值得關注的是《魏書·術藝列傳》《隋書·藝術列傳》和《清史稿·藝術列傳》。《魏書·術藝列傳》在《方術列傳》的基礎上變遷并超越了“方術”內涵,在變遷為“術藝”的概念中豐富與發展了“方術”的內容與內涵;《隋書·藝術列傳》有一個重要變化,其意義不亞于《晉書》用“藝術”概念立類傳,《隋書·藝術列傳》的意義在于對“藝術”作了分類,其“小序”云: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御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辨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圣人無心,因民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
《隋書·藝術列傳》開始為“藝術”分類,形成“陰陽”“卜筮”“醫巫”“音律”“相術”“技巧”六大類,是中國古代“藝術”譜系,也可以說是《藝術列傳》中關于“藝術”的“體系”的正式形成。《清史稿·藝術列傳》是“二十六史”《藝術列傳》的“收官”之傳,它除了恢復《魏書·術藝列傳》的內容和為“藝術”概念立類傳以外,同時還將近代的科學技術、機械制造等內容,納入“藝術”的范疇,是《考工記》有關“藝術”譜系的延伸。如將近代科學家徐壽(1818—1884)、戴梓(1649—1726)和丁守存(1812—1883)等及其活動事項列入其傳,構成了中國傳統藝術的范疇,也可以視為藝術史學科體系的重要特征。從《清史稿·藝術列傳》的“緒言”中,我們看到了中國文化系統中的藝術史范疇與體系。《清史稿·藝術列傳》“緒言”云:
自司馬遷傳扁鵲、倉公及《日者》《龜策》,史家因之,或曰《方技》,或曰《藝術》。大抵所收多醫、卜、陰陽、術數之流,間及工巧。夫藝之所賅,博矣眾矣,古以禮、樂、射、御、書、數為六藝,士所常肄,而百工所執,皆藝事也。近代方志,于書畫、技擊、工巧并入此類,實有合于古義。
這段“緒言”闡述了中國文化系統中“藝術”的歷史脈絡與變遷路徑,以及所包含的內涵與內容,實則也是“藝術”的譜系展示。《隋書·藝術列傳》將“藝術”分為“陰陽”“卜筮”“醫巫”“音律”“相術”“技巧”,這是“二十六史”中對“藝術”的一個基本架構,到了“收官”類傳的《清史稿·藝術列傳》,是在此基礎上積累性的演進與發展,重新建構了“藝術”的體系,以“禮、樂、射、御、書、數為六藝”的基本結構,再納入“書畫、技擊、工巧”,并在《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藝術類》的基礎上,形成“陰陽術數之藝”“醫經卜筮之藝”“巧思術伎之藝”“禮樂書畫之藝”“技擊射御之藝”“音律歌舞之藝”的“藝術”系統和譜系關系,這是一個整體的、宏觀的和綜合的藝術體系,用今天的學科視野看,就是中國傳統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但若對照正史《藝術列傳》的整體、宏觀和綜合的“藝術”體系,遺憾的是,我們當下的中國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幾乎沒有建立在這個整體的、宏觀的和綜合的傳統史學“藝術”體系的基礎上,而是受到西方分類影響形成了音樂史、美術史、舞蹈史、設計史、戲劇史、影視史等分門別類的史學學科,至今沒有形成一個以“二十六史”《藝術列傳》體系為基礎的中國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
誠然,“藝術”概念的內涵與內容是動態演變的,時至今日,“藝術”概念與內涵所發生的演變以及分類系統,遠離了中國傳統藝術系統和內涵,但這種變化另有其原因。換句話說,今天的“藝術”內涵標準不是中國傳統藝術系統建構起來的標準,更多的是在“Art”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標準,乃至一提到中國的“藝術學”就必言德索瓦爾為起點,看不到《藝術列傳》的整體面貌。如果以“Art”為基礎,無論怎樣建構中國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都是在“Art”框架與脈絡下的學科體系,難以成為真正的中國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這是當前建構中國藝術史學學科體系最大的瓶頸。要改變這種狀況,中國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應該是體現“二十六史”《藝術列傳》的體系、脈絡、譜系與內涵,實現的是整體的、宏觀的和綜合的藝術史觀的學科體系,而不是切割為各自獨立、互不相關、極為簡單的音樂史、美術史、舞蹈史體系。分門別類切割或細化學科的思維方式與“二十六史”《藝術列傳》思維方式完全不同,這其中顯現出中國思維方式與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特征。通常而言,整體、宏觀和綜合的思維方式基本上是中國文化思維方式,在這種思維方式下形成的“二十六史”《藝術列傳》必然呈現的也是整體、宏觀和綜合的“藝術”體系,雖然我們說《隋書·藝術列傳》對“藝術”進行了分類,但僅僅是作為整體化的分類認知,而不是切割為不相關聯的類別,在這些分類的認知系統中,往往是相互包容的。譬如《藝術列傳》中的“醫術”與“占卜”的關系就是“巫醫”一體的系統;“卜筮”也不是孤立的,也與“陰陽”有某種關聯,“卜筮”與“陰陽”的關系就在“數術”的系統中。再譬如“禮”“樂”“射”“御”“書”“數”在“六藝”系統中是一個整體關系,無論是納入官學還是私學中都是作為整體的學習對象。又《后漢書·伏湛傳》云:“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李賢注:“藝謂書、數、射、御,術謂醫、方、卜、筮。”盡管“藝”與“術”是兩個系統,但屬于一個整體。無論是李賢對《藝術列傳》的類別認知,還是對“藝術”的注釋,都體現了對“藝術”整體認知的史學觀念。所以,我們說《藝術列傳》的整體性、宏觀性和綜合性的史學特征及其藝術內容,應該成為當代中國藝術史學學科體系的重要坐標。當代有很多傳統中沒有的新的藝術形態出現,譬如“影視藝術”“影像數碼”或“數字藝術”等與現代高科技結合的新型藝術形態,但科技與藝術在《藝術列傳》中本身就是天然一體,在該方面有其天然的藝術思維和思想觀念,故此容納當下新藝術形態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是完全可以納入中國藝術史學的當代發展與創新的學科體系范疇中建設的。從這個層面上講,我們看到了《藝術列傳》與中國藝術史學學科體系的必然聯系。由此可知,中國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最大特征就在于匯通所有藝術門類,進行整體、宏觀和綜合的史學研究,探討藝術史的共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規律,包括藝術起源、藝術變遷、藝術流源、藝術特征、藝術產生、藝術考古、藝術文獻,以及藝術與其他人文學科關系的普遍性、共性的一般規律和特征,研究追問人類社會所產生的藝術的發展演變過程中帶有普遍性和規律性的問題。
二、《藝術列傳》與中國藝術史學的 學術體系
學術是將學科的本質內涵和內容作專門的系統性、理論性的研究,最終成為學科的系統化、體系化的理論形態與方法形態,并形成一個時代的學術思想與學術觀念。學術體系要立足于時代精神。藝術史學的學術體系是將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進行一種現代化、具體化、深入化、系統化與體系化的研究,形成具有新時代精神的學術思想和學術觀念。中國藝術史學的學術體系建設,須以中國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為前提,融入新時代精神,方有可能建立自己的藝術史學的學術體系。換句話講,中國藝術史學的學術體系是在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基礎上所形成的系統性的理論與方法,以及一個有新時代精神的中國藝術史學的學術思想和學術觀念。上述我們說的中國藝術史學的學術體系如果成立,那么它必然是與“二十六史”《藝術列傳》有關聯的中國藝術史學的學術體系,也必然是建立在中國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基礎上的。
中國藝術史學的學術體系要高度地體現出自身的理論與方法,就體現出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底色的理論、觀念與思想,體現中國新時代精神;中國藝術史學的學術體系是在專門系統性的中國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的研究中所形成的,區別于其他學科對象的學術體系的、相對獨立的藝術史學思想、觀念的學術體系。“二十六史”《藝術列傳》的內容與內涵蘊藏著普遍性與特殊性、轉折性與延續性的歷史價值和史學意義,是中國藝術史學學科體系的基礎,那么中國藝術史學的學術體系必然也要體現出這個基礎的歷史文化的底色。中國藝術史學的學術體系所顯在的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就應該蘊含中國文化系統中的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這是當今中國藝術史學的學術體系建設的必要條件。以往在中國藝術史學的學術體系建設方面,存在著照搬“他者”的學術體系的現象,這是某種歷史原因造成的。民國時期研究中國藝術史的學者,首先受到日本藝術史家的影響,模仿他們所撰寫的藝術史的學術體系以及體例而撰寫中國藝術史。譬如模仿日本藝術學者大村西崖(1867—1927)撰寫的《東洋美術史》《支那美術史雕塑篇》的史書體例,陳師曾(1876—1923)撰寫的我國第一部《中國繪畫史》(1921),盡可能地保持了中國文人藝術的特征,特別是他撰寫的《文人畫之價值》(1921)顯示了中國特征的藝術史研究的學術理論價值,當然首先使用了外來的“美術”概念名之為“美術史”,從內涵到概念并非我們說的“藝術史”。以后的學者所撰寫的“美術史”多受到“改良中國畫”和“革‘四王’畫的命”等觀念的影響,中國藝術史學的建構一路向西,逐漸脫離了《藝術列傳》的文化系統和藝術觀念的底色,很多觀念、思想和概念都采用了西方美術史的,譬如“古典主義”“寫實主義”“浪漫主義”“表現主義”,乃至“移情說”“意味說”等概念,架構中國藝術史學的理論與方法系統。時至今日,“闡釋學”“圖像學”“風格學”“敘事學”理論與方法風靡中國藝術史學的研究領域,幾乎都是西方的史學理論在架構中國藝術史的研究,其研究方法基本上來自西方。再譬如,探討藝術起源必然是西方的幾種起源說,即模仿說、游戲說、巫術說、勞動說,并以德國藝術史家格羅塞(Ernst Grosse,1862—1927)《藝術的起源》為典范。然而,格羅塞考證藝術起源所用的材料多是他認為的“原始民族”,即與現代文明社會相比較為落后的“野蠻民族”,而不是考古學意義上的遠古社會的原始民族。格羅塞自己就坦言:“歷史和考古學都是無濟于事的,我們只能從人種學里獲取正確的知識。”他從人種學中去尋找他所需要的“原始民族”,即以文化或文明層次高低來確定“原始民族”,他認為“一個民族的‘原始性’分量的輕重問題,和該民族文化程度的高低問題,是同樣重要的”。格羅塞的藝術起源說的前提存在問題,結論也必然存在問題。而有關中國藝術的起源說,以往編寫的藝術史學幾乎很少提及。這就是藝術史學的學術體系需要重建和重新思考的問題。另外,有的藝術史學與藝術理論研究又回到了20世紀德國“前藝術學”的架構狀態中,即再次用“美學”架構“藝術”,難以真正詮釋和揭橥中國傳統藝術的本質特征,并以“美學”代替了“意境學”,導致中國藝術史學顯示不出中國自己的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顯示不出新時代的中國藝術史學的思想和藝術史學的觀念與精神,即缺失了新時代精神的中國藝術史學的學術體系。
中國藝術史學的學術體系建設的文化底色,是以“二十六史”《藝術列傳》為支撐,以“十三經”為基礎,以中國史學“三大體例”為結構。我們這里重點提到“二十六史”《藝術列傳》,是因為前面提出中國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與“二十六史”《藝術列傳》有直接相關,那么其學術體系必然也與“二十六史”《藝術列傳》存在緊密關系,這也是我們重點探討的內容。《晉書》是首次用“藝術”概念立類傳的正史,它涉及我們探討的學術體系范疇問題,我們先看《晉書·藝術列傳》“小序”是如何闡述“藝術”的: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兇,審存亡,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弼成人事;既興利而除害,亦威眾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于此。
《晉書》使用“藝術”概念立傳并非沒有基礎,而是在“術藝”的基礎上形成的,且前面還有“方術”概念和類傳。我們曾經梳理過“二十六史”《藝術列傳》的體系,認為其前身是《史記》的《日者列傳》《龜策列傳》和《后漢書·方術列傳》,由此又變遷為《魏書·術藝列傳》。中國的“方術”與天文直接有關,前面我們也提到了“陰陽”“占卜”“醫巫”“數術”“巧思”等都與人類早期認識自然緊密相聯,尤其是與天文、歷法、地理等認知直接相關。譬如《隋書·藝術列傳》在詮釋“藝術”類型中的各個“祖師”時云:
然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灶、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敘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者,仰觀俯察,探賾索隱,咸詣幽微,思侔造化,通靈入妙,殊才絕技。
這里就不難看到藝術類型與天文歷法存在極大的關系。言陰陽者自不必說,與天文關系非常緊密;巧思者則有奚仲、墨翟、張子平和馬德衡等,奚仲造船之祖,墨翟光學之祖,張子平即張衡造渾天儀、地動儀等天文儀器,馬德衡即馬鈞屬于機械制造專家,制造翻水車、改進織綾機等。僅巧思類直接與天文聯系的就是張衡創制的渾天儀、地動儀,是古代研究天地規律的重要物質成果。有關造車船與中國古代“天地觀念”的關系,在《考工記》中有詳細記載:“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可見中國古代機械設計制作與天地觀念緊密相連。中國古代“天文”又轉化為“人文”的文化觀,從而影響到中國古代的藝術。中國藝術對色彩的要求也與“天地觀念”有關,同樣在《考工記》中有詮釋:“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黼;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足見中國的色彩觀念與方位自然萬物有關,是典型的“觀念色”。另外,音律與“緹室候氣”即“候氣術”有關,這本屬于天文歷法的技術,但音律卻因此也被測量出來,即“黃鐘律呂”。如《后漢書·律歷志上》云:“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涂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動。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通常說“十三經”之首的《易經》是中國文化的起點,而《易經》則是仰觀天象俯察地理的結果,文化源頭來源于天文。《周易·賁》云:“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經》把“天文”與“人文”的關系說得很明白。我們為什么提到中國古代天文歷法這個問題,就因為傳統的“藝術”學術體系與天文歷法有關,更重要的是天文歷法是中國文化的源頭,沒有“天文”就沒有“人文”。在天文歷法觀中建立起來的人類知識體系,必然顯示其“天”“人”關系的重要性,也正是在這個知識體系中才建構出了“人道”與“天道”統一的“天人合一”的形而下“藝術”系統。因而《藝術列傳》“小序”都隱含了這層意思,它以記敘的方式載錄了從事各種“藝術”類型的人物及其事項活動。在與天文歷法系統關系中建立起來的藝術范疇、內涵及其理論,都隱含了傳統藝術史學術體系的中國特征。我們所熟知的“氣韻生動”“心師造化”“中得心源”“以形媚道”“含道暎物”“以神法道”“澄懷味象”“應會感神”“神超理得”“意象”“意境”等形而上的思想觀念,以及在其構圖形式上的“知白守黑”“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的形而下的技巧與創作觀念,幾乎都源于這個知識系統。《老子》的“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在藝術結構的運用中,即可形而上又可形而下,來回往復其間,誠如中國藝術形態體現的正是《易經》所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的形而上的觀念意識。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為此有一個關于“言”“象”“意”的邏輯論證:“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以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二十六史”《藝術列傳》卻又用天文天象之“道”詮釋形而下之“器”中所顯示的具體巧藝,而中國傳統“藝術”之名下的“器”又能進“道”,如《隋書·藝術列傳》中的“藝術”分類即是如此。同時,“方術”“術藝”“藝術”“方技(伎)”上位概念下的各種巧藝之“名”(下位概念)的內涵和內容十分豐富,也不是當今“藝術”(Art)能夠涵蓋的。不僅如此,由“方術”到“術藝”再到“藝術”“方技(伎)”又再復出“藝術”之變化,顯現了《藝術列傳》富有內涵的譜系性的演變過程。“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正因為“二十六史”《藝術列傳》豐富的內涵和生動的譜系性的演變過程,彰顯出中國傳統藝術史學術體系的特征。
我們舉一個有關“術”“藝”概念的實例所隱含的學術體系問題。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云:“昔者孟蜀有一術士稱善畫,蜀主遂令于庭之東隅畫野鵲一只,俄有眾禽集而噪之。次令黃筌于庭之西隅畫野鵲一只,則無有集禽之噪。蜀主以故問筌,對曰:‘臣所畫者藝畫也,彼所畫者術畫也,是乃有噪禽之異。’蜀主然之。”《圖畫見聞志》中的例子,讓我們看到了郭若虛通過黃筌之口,將繪畫分為“術畫”和“藝畫”。“術”與“藝”顯然在郭若虛這里是一個層次問題,但也符合《術藝列傳》到《藝術列傳》演變的脈絡話語體系的“術”與“藝”概念,而且郭若虛說的“術”與“藝”暗指畫品,即“能品”(術畫)和“神品”(藝畫)。為什么我們說“藝畫”屬于“神品”而不是“逸品”呢?是因為黃筌屬于宮廷畫師,依然如郭若虛說“黃家富貴,徐熙野逸”是也,黃筌表達的是皇家氣派與富貴,徐熙表達的是野逸中的隱逸與淡泊。關于“逸品”,唐志契《繪事微言》還有一個分類:“蓋逸有清逸,有雅逸,有俊逸,有隱逸,有沉逸。”很明顯,有關“術畫”“藝畫”的概念隱藏在繪畫史中的“畫品”觀念,與“二十六史”《藝術列傳》中的“術藝”觀念有關。這些在藝術史中所形成的學術體系,不僅是我們要傳承研究的,更是當今發展和創新的學術體系的基礎。由此上述與“二十六史”《藝術列傳》相關的中國傳統藝術史學的學術體系,是當今中國藝術史學學科體系的根基所在。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然包含了文化復興,文化復興方得文化自信。那么,在藝術方面的“復興”,就是對中國傳統早已建構的藝術體系的復興,這既是我們復興的對象,也是中國藝術史學學術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總之,基于上述中國藝術的文化內涵、理論與方法,我們不僅看到了中國藝術史學的學術體系與“二十六史”《藝術列傳》有天然的聯系,也與正史中其他列傳、志和《易經》等文獻有關系,這些聯系與關系恰恰是中國藝術史學學術體系的構成基礎,是建設具有中國氣派、中國文化、中國精神的藝術史學學術體系的基礎。
三、《藝術列傳》與中國藝術史學的 話語體系
話語體系表面上看去好像是一個話語表述的問題,但實際隱藏著“話語權”。在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中實則體現著一個“話語權”的主導性是否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問題。“話語”也是新時代的主題,所以話語體系建設要立足于新時代主題,從這個角度思考其建設問題,這應該是我們理解的“話語體系”。藝術史學“話語”雖然不像哲學社會科學“話語”的意識形態那么凸顯,但藝術史學屬于上層建筑,其“話語”同樣存在意識形態的屬性,更有鮮明的民族性的特征。故此,我們認為藝術史學的話語體系隱藏著“話語權”,這意味著在建構中國藝術史學話語體系的同時,我們也在建構藝術史學的“話語權”,或者說建設藝術史學話語體系是新時代的主題之一。
當下有一種“話語”趨向是,當我們面對西方的文化藝術理論、研究方法和概念時,往往是積極地“響應”而不是帶有臧否判斷的有力“回應”。譬如說西方話語體系中的“本體論”“神話學”“圖像學”“闡釋學”“風格學”“敘事學”“紀念碑性”“機械復制”“靈韻”“贊助人”等理論或概念,很多情況下我們的一些學者是趨之若鶩、不厭其煩地詮釋西方的這些理論、方法或概念,真正做到有力量的“回應”不多見。這種狀態下的“響應”必然喪失的是自己的話語體系(話語權)。如果沒有話語體系(話語權),那么所建設的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就會成為“空殼”或者是“他者”的話語體系。當然也有一些學者意識到這些問題,把這種只知“響應”而不知“回應”的現狀稱為“話語逆差”,并提出了自己的判斷:“與中國對西方的巨大‘話語逆差’相伴隨的,是國內一些‘著名學者’不過是對西方話語掌握較為熟練的二道販子,‘以洋為重’或‘挾洋自重’的不正常學術生態成為常態。更為嚴重的后果是,以西方經驗為基礎、以西方思維方式為導向、以解決西方所遇到的問題為指向的西方學術話語,難以準確地解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同樣如此,用西方學術話語也解決不了中國藝術的當代實踐,解決不了新時代的主題。因而,我們面對西方文化理論、方法和概念需要的是“回應”而不是“響應”。“回應”就要“話語”建設,要“回應”西方理論話語,就需要在自身的文化系統中去尋找能夠“回應”的理論、方法和概念。
“二十六史”《藝術列傳》是整體架構在“天文”“陰陽”“候氣”等基礎上對各種形而下的技巧以及掌握其運用能力的人的記述與詮釋,即“敘列人臣事跡,令可傳于后世”的類傳,體現出形而上的普遍性(天文歷法)和形而下的特殊性(各門巧藝)的融合關系。《藝術列傳》從“日者”“龜策”演變為“方術”列傳,又演變為“術藝”“藝術”列傳,再變遷為“方技(伎)”列傳,又復回為“藝術”列傳,這里既體現出《藝術列傳》的轉折性,又體現了延續性的歷史特征,這種“波瀾壯闊”的演變正是“二十六史”《藝術列傳》的歷史價值與史學意義所在。正所謂“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不僅如此,“二十六史”《藝術列傳》這里還有自身話語系統的歷史價值和史學意義,如“天文”“歷法”“陰陽”“候氣”“音律”“日者”“龜策”“方術”“術藝”“藝術”“方技(伎)”“工藝”“巧思”“巧技”“巫醫”“相術”等概念,這些概念所體現的也是中國藝術思想、藝術觀念、表述方式及其語言特征——話語系統。《藝術列傳》所體現的這些話語系統,對我們今天中國藝術史學話語體系的建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也是構建當代中國藝術史學話語體系的基礎和范式。
“藝術”這個概念的話語最早見于《后漢書》,《后漢書》有三處(安帝紀、伏湛傳、劉珍傳)提到“藝術”,這是個基本常識。我們前面提到了李賢對《后漢書·伏湛傳》提出的“藝術”概念做了具體的內涵注釋,即“書、數、射、御”與“醫、方、卜、筮”。不難看出“藝術”屬于中國文化中的概念和特定內涵與內容,并在“二十六史”正史中用“藝術”立類傳——《藝術列傳》,這些事實構成了典型的中國藝術史學的話語概念、內涵和特定的內容范疇。我們認為最早在《后漢書》中提出的“藝術”概念及李賢的注釋,就是中國古代藝術的學術體系同時也是藝術的話語體系的體現,而西方“Art”的概念則是通過日本學者的翻譯傳布到中國,成為民國時期的學者用來與《后漢書》“藝術”進行對應,成為我們今天使用的詞匯,但西方“Art”隱含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與中國“藝術”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是不一樣的。
鑒于上述史實,我們說“二十六史”《藝術列傳》與中國藝術史學的話語體系的關系,從宏觀上講就在于立足“二十六史”,依“經”立藝之道,在弘傳中國經典國學中立足于新時代主題建設自己的藝術史學話語體系。筆者曾撰文《立藝之道,曰經與史》表達這個理念和理論,中國傳統的“經”與“史”是建構當代中國藝術史學話語體系的根本,尤以“二十六史”《藝術列傳》為建設當代中國藝術史話語體系的基礎,換句話表述就是,將“二十六史”《藝術列傳》的話語體系傳承、發展與創新,構成當今中國藝術史學的“話語體系”。李賢對“藝術”注釋的“書、數、射、御、醫、方、卜、筮”既是藝術整體的內容,也是傳統藝術表述和詮釋的概念,而這些內容和概念在“二十六史”《藝術列傳》均有闡述和分類。如果說“二十六史”《藝術列傳》與中國藝術史學的話語體系有關聯,就在于“二十六史”《藝術列傳》的話語體系在今天看來就是中國藝術史學的話語體系建設的主要基礎與資源。這也印證了人們常引用的那句話:“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中國“二十六史”《藝術列傳》就是當代藝術史。當然,所謂的“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不是直接將“歷史”作為“當代史”,而是將“歷史”繼承發展為具有自己話語體系的“當代史”,沒有自己真正的“歷史”是無法成為“當代史”的,這才是所謂“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的本意,而且這個“當代史”的核心實質就是新時代主題的當代話語、學術話語,或意識形態話語權。
歷史學者侯旭東認為:“史學研究不能止步于考證實事,還需要構建解釋,這條路很漫長。對中國而言,目前恐怕首先要從基本概念的重新厘定開始。這些概念不應是盲目照搬西方,而要立足過去的事實潛心歸納與定名,‘到最基本的事實中去尋找最強有力的分析概念’。立基于此,逐步構建出關于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種種解釋,貢獻于人類。”這就是說,我們今天要建設自己的藝術史學話語體系,首先基本概念就需要立足于傳統史實,重新思考厘定、歸納定名出自己的概念,而不是盲目照搬西方的概念和觀念而冠名,當今中國藝術史學的話語體系建設也應如此。“二十六史”《藝術列傳》開篇就是引用《易經》的“以卜筮者尚其占”話語,然后直指其內涵與功能是“定禍福,決嫌疑,幽贊于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而這個“話語”在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開篇作了傳承性的建構,即“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是知存乎鑒戒者圖畫也”。“二十六史”《藝術列傳》這種“話語”隨處都在被巧妙地傳承。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所言,“《易》稱:‘圣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又曰:‘象也者,像此者也。’……制為圖畫者,要在指鑒賢愚,發明治亂”。郭若虛這里主要說的圖畫“自古規鑒”問題,有意思的是《圖畫見聞志》還用了《歷代名畫記》中的話語“所謂與六籍同功,四時并運”來結束。這表明了藝術史學的話語體系的延續。
我們再看一個中國傳統藝術話語建設的例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記載張璪的一句畫理,即“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造化”“心源”屬于中國古代畫學話語的重要概念并折射出豐富的內涵,這句話反映出“視覺”轉向“意覺”再轉向“心覺”的藝術創作過程,故傳統藝術文化中將繪畫稱為“心畫”即是如此。同時,將音樂歸為“心聲”亦是如此。《樂記》說“音由心生”便是證明。《禮記·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史記·樂書》依《樂記》亦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經”“史”互證,闡述了音樂由心發,故為“心聲”,這已部分提到了中國有關藝術起源的問題(有關中國藝術起源問題另文探討)。這正印證了立藝之道,曰經與史。宋代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在“論氣韻非師”中說:“楊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這就意味著當我們對傳統的“心畫”“心聲”進行建構性的闡釋時,可以通過傳統藝術的話語,如心畫、心聲、心源、造化、實景、真景、空境、神境、妙境、意象、意境等進行藝術史學的話語體系建設,而不是挪用西方藝術的話語。故此這個話語邏輯能在清人笪重光的《畫筌》中得出:“空本難圖,實景清而空景現;神無可繪,真境逼而神境生”,“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不僅如此,笪重光還為繪畫藝術的“意境”提出了三個境界層次:“實景”“真景”和“妙境”。笪重光依據傳統藝術系統建構性地闡釋了中國藝術的“意境”(境界)問題,這個闡釋性的建構是有傳統依據的,也是經得起實證的。我們可以概括為“視覺層面的視象——意覺層面的意象——心覺層面的心象(創象)——最終追求的是意境(境界)”,并可以視為當今中國藝術史學話語體系的范疇。
蘇軾云:“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學,百工之于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顏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蘇軾《書吳道子畫后》)蘇軾認為在唐代已經建構成了一個包括詩、文、書、畫的完善的藝術知識體系。蘇軾的邏輯起點從“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開始,這是《禮記·考工記》中的闡述,同時也在《藝術列傳》中作為“巧思”“工藝”有其闡述。這個論點由“知者創物”開始而累積與發展,到唐代的藝術知識體系已是“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從詩、文、書、畫的各自脈絡中,蘇軾看到了藝術史的話語體系的完備建構均有其代表性的人物。蘇軾的這個總結給我們當今中國藝術史學的話語體系建設提供了體現時代主題的生動案例,顯示了傳統藝術話語建設對當今藝術史學話語體系建設的意義與啟示。
從以上幾個例子中我們也不難發現中國傳統藝術話語的本質特征。一提到“本質”這個概念,也就涉及“話語”本身。晉代劉智《論天》:“言暗虛者,以為當日之沖,地體之蔭,日光不至,謂之暗虛。凡光之所照,光體小于蔽,則大于本質。”“本質”這一概念的出處在中國傳統經典文獻中,表明了自身的價值與意義。
我們說中國藝術史學話語體系建設與“二十六史”《藝術列傳》有關,不僅是傳統資源問題,還在于賦予傳統資源新內涵,從而體現出當代的價值與意義。但是賦予傳統資源新內涵不是貼上一些西方概念和詞匯就等于是創新或迎合了當代性。譬如在闡釋藝術史的理論時,似乎離不開用“本體論”來闡釋藝術,甚至認為本體論是建構藝術史學話語體系的途徑之一。但事實上,當我們在使用“本體論”時,其實已經失去了話語。“本體論”(Ontology)的詞語表述首先由17世紀德國經院學者戈科列尼烏斯(Rudolphus Goclenius,1547—1628)創用,“本體”或“本體論”是西方哲學體系中常用的一個概念。我們常常陷入“本體論”“認識論”“功能論”“方法論”的路徑中,提出建構某種學術體系或話語體系。當我們翻開有關探討藝術史建構或藝術學理論建構的成果時,幾乎沒有一個能夠脫離由“本體論”打頭陣的著述,似乎不用“本體論”,中國藝術史學的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就無法建構。假如以“本體論”打頭陣建構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那么到底是不是有骨氣的中國學術話語體系,這就需要質疑了。藝術無“本體”之說,也就無“本體論”了。其實,我們完全可用自己的“本質”的概念和話語。
因此,從本質上講,中國藝術史學的話語體系建設要體現中國傳統民族語言和中國新時代的主題。這需要從兩個方面理解:一是體現傳統文化的當代傳承與創新的語言體系,體現中華民族語言、觀念的表述范式的語言體系。自己的概念在話語體系中尤其重要;二是反映出中國當代精神照射下的藝術史學的話語建設,當然必須將傳統文化脈絡話語體系轉化為與時代精神一致的藝術史學的話語體系,即體現新時代主題的話語體系。這兩方面是形成中國藝術史學話語體系的主要途徑并使其能夠在當代具有實踐性。話語體系建設的目的在于它的實踐性和學理的主動性,實踐性是話語體系的重要目的之一。馬克思說:“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在某種意義上講藝術史學的學術話語即是實踐的產物,是建立在藝術實踐基礎上的學術話語。我們注意到一些藝術史家或藝術理論家,高談闊論似乎還行,卻沒有一點藝術實踐的經驗,故而從概念到概念,極容易產生挪用或移植西方藝術概念和話語的現象,在藝術史學的話語中喪失自我。因此,完全沒有藝術實踐的史論家的理論話語,是無法證明其理論的真理性的,多數情況下套用西方話語體系強加在中國藝術史學的話語體系中,用西方的概念強說中國的藝術。理論話語主動性亦即我們說的“話語權”,也因此我們說中國藝術史學的話語體系的當代建設,還應該準確、充分地關注和反映世界藝術的核心價值以及人類精神共識下的藝術觀念和藝術形態,同時要適應中國及世界藝術演變或發展的走向,而不是故步自封或刻意固守,實行單邊獨行而取代他國或他民族藝術觀念和藝術形態建設一個面向世界的中國藝術史學的話語體系,應該說這是中國藝術史學話語體系的新時代主題。
總之,藝術史學的話語體系是由一系列的基本概念、觀念和思想組成的,并且通過語言把這些概念、觀念和思想連接起來。概念是人類理性認識、表達思想內容的詞語形式,故而概念體現了人類思想、觀念的基本內涵,反映了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特有之屬性。藝術史學的話語體系就是由一系列概念形成基本語言,從而把思想、觀念和學理連接起來進行詮釋或闡述。在詮釋或闡述當代中國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與學術體系中形成表達中國藝術史學的話語體系。換句話說,中國藝術史學的話語體系應該由一系列的中國文化中的基本概念、觀念和思想相互連接構成,用中國的概念闡釋藝術史的史學理論與史學內容,這就是我們說的藝術史學的話語體系。
四、結語
當今我們對中國藝術史學“三大體系”建設的思考,就在于要回答中國藝術史學所面臨的問題。最突出的問題是,在中國藝術史學的“三大體系”中存在“Art”的西化意識比較嚴重的狀況,很多觀念、概念、內涵及其原理不是來自中國傳統文化脈絡、路徑、藝術譜系及其內涵,多數情況下“響應”或“默認”了西方“Art”的概念和觀念的學科、學術和話語。同時,我們也很難看到真正的專業學術術語的表述,倒是看到更多概念化的詞語表述,而這些概念化的詞語在很多學科的話語表述中幾乎同時出場,如主體論、客體論、本體論、認識論、先驗論、功能論以及主體間性、客體間性等,這些概念不僅西方化話語比較嚴重,而且幾乎都是哲學的詞語概念,失去了藝術學的學術話語。坦白地講,這些根本不是藝術史學的專業話語。不可否認藝術史學包含了哲學的思考,但它本身不是哲學。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主要闡明要以“二十六史”《藝術列傳》為基礎建設“三大體系”,立足于中國藝術譜系建設學科體系,立足于時代精神建設學術體系,立足于時代主題建設話語體系,使中國藝術史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中國化、專業化和時代化。概括地說,中國藝術史學要構建自己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并使中國藝術史學的“三大體系”相互印證而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