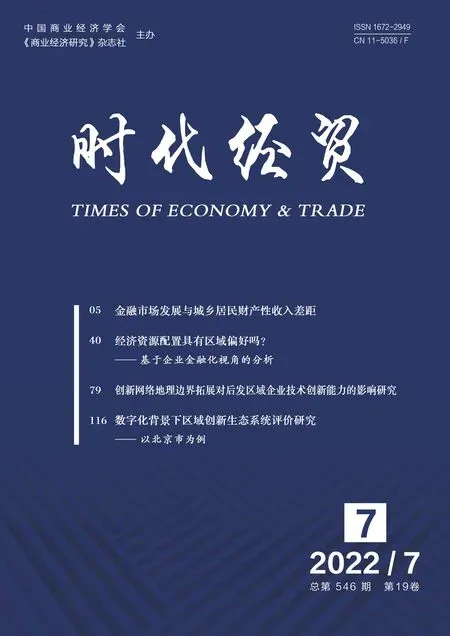企業跨國搬遷中移民與本土創業公司成功率差異研究
韓 捷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北京 100191;2.哈爾濱工業大學 黑龍江哈爾濱 150006)
引言與文獻概述
如果存在某種增值策略,那么這種策略一定會被風投和創業者所推崇。在資產管理領域,戰術性調配資產占比捕捉短期的市場機會可以獲得比被動應對更好的業績;在企業管理中,配置供應鏈到一個具有成本優勢的區域會同時使公司和此區域人民獲益;在國家層面,確定首都的地理位置是政治體制穩定的必要條件。如上所述,遷移作為一種策略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時空跨度。在資產管理的例子中,戰術性調配資產可以臨時打破長期戰略投資協議所規定的資產配置;在企業管理的例子中,特朗普曾呼吁美國制造商將其生產線遷回美國。這些例子表明,遷移作為一種策略會影響不同規模的經濟。
在風險投資領域,學者對企業家和風投公司選址有過研究。Camp(2002)認為,風險資本更傾向于投資靠近其工作地點的初創企業,因為這種鄰近性有利于盡職調查、監測和咨詢;Gupta & Sapienza(1992)發現,早期風險投資者投資目標的地域范圍比后期投資者小;Chen等(2010)認為,初創企業會有意選擇靠近風險投資者,這樣他們可以共同利用某些地域范圍內的稀缺資源,如人才市場和學術圈,其結果是形成了具有自我強化效應的創業企業-風投生態。
為了分析初創企業的遷移原因并推導因果性,需要在回歸模型中嵌入工具變量,然而這一變量的缺失表明初創企業之間具有很強的異質性且遷移的決策主要是內生性的。分析表明,遷移現象是罕見的,特別是在實體經濟中,遷移會損失廠房和設備的初始成本,文獻回顧也表明這種現象很少被研究。Cumming等(2009)研究了風投公司支持創業公司遷移,他們發現亞太地區的風投公司將其投資對象遷移到美國,比本土的投資產生了更大的回報。本文通過Cox生存模型進一步研究這一現象,研究結果有助于風投資本和創業者理解遷移策略及其影響,同時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
研究設計
(一)數據處理
購買PitchBook截至2019年的初創企業數據,隨機選擇924家在美國注冊的初創企業進行研究。通過Crunchbase、Opencorporates、LinkedIn等搜索引擎和數據庫研究創始人簡歷、公司成立時間,判斷某樣本公司是否為遷移公司,重新確定公司來源。
對數據做分組處理以避免過度擬合的特殊性。國家數量從27個集中到4組,即美國、英國、歐盟和其他;行業從25個壓縮到6組,包括通信和媒體(C&M)、軟件、醫療、消費者信息服務(CIS)、商業支持服務(BSS)和其他;融資年限從20年縮短為5組,范圍從2000-2019年。
(二)模型描述
由于數據的右側截斷性,選擇Cox比例風險模型對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相比于Logit模型,Cox模型加入了時間維度,使用了更多的信息 。
本文的數學模型為公式(1):

(三)變量定義
表1中列出了變量名稱,根據變量屬性進行分組,即初創企業特征、風險投資特征、固定效應和記錄創業成功的啞變量。重點考察選擇表1中以下變量:r、onlyHR和CoHQ分別表示搬遷策略、搬遷一個單獨的總部或創建一個共同的總部;SyndicateSize、Rounds、TotalUSD和VCAge是四個連續變量。SyndicateSize記錄風險投資的總人數,代表獨立的第三方的認可;Rounds記錄總的融資輪次,是衡量初創企業的時間框架,與融資總額和財團規模正相關;TotalUSD記錄融資總數;VCAge是風投公司的年齡。所有相關變量中的ln前綴表示對連續變量的對數處理,轉絕對增長為相對增長。

表1 變量描述
考慮數學模型的求解方法為最大似然法,選擇18-20個預測變量(P),確保每個變量至少有20個數據支持,借用公式“樣本量=(20×P)/(事件分數)”計算最小樣本數量,其中事件分數是概率小于0.5的因變量結果,由此計算出最小樣本量為876,本次樣本總數滿足要求。在其他情況下,因變量事件分數太小,因此需要更大的樣本量。在這種情況下,不進行回歸分析。
表2為非虛擬自變量的相關性矩陣。所有預測變量的平均變量膨脹系數(VIF)為2.46,低于10的標準,所有單獨的VIF值也都低于這個閾值(最高值為4.69)。

表2 連續變量相關性矩陣
實證分析
(一)單一變量比較
表3顯示了兩個對照組,即未搬遷的r=0組和已搬遷的r=1組,比較結果顯示指代成功的指標無顯著的差異。ExitProceed顯示出相似的中位數,這意味著成功退出的公司之間具有同質性;TotalUSD顯示搬遷后的初創企業獲得的資金總額略高(10%的顯著性),但這不是一個好的跡象,因為更高的成本并沒有轉化為更好的表現;融資輪次的差異檢驗顯示出高度的顯著性,較高的融資輪次在遷移的公司中更為普遍;專利所有權的差異也很顯著,但僅有的兩家擁有專利的公司是在搬遷的創業公司中。

表3 單變量比較
搬遷后的初創企業有更多的投資者參與,如財團規模所示(5%的顯著性)。在這些投資者中,他們的年齡和累計投資組合規模是相近的。對于財團規模的差異,搬遷吸引了來自原始國家和目標國家的投資者,但這些投資者在衡量經驗的年齡和累計投資組合規模方面沒有大的差異。這個差異也可以通過觀察創業開始年份來解釋,搬遷的初創企業更早開始創業(1%的顯著性),這意味著更早地接受資金和更多的融資回合,而融資輪次與財團規模呈正相關。基于目前的數據分析可引出一個邏輯假設,即遷移策略會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加入公司,而非更多的投資者引發了遷移策略。
搬遷與連續創業者沒有顯著關聯,但從一開始就在美國設立總部的創業公司更有可能擁有美國投資者。另一個顯示投資者無法預見遷移策略的變量是AgeFirstVC變量,它衡量的是公司成立后到第一輪風投融資的時間,第一筆風險投資是最重要的,也承擔著最大的風險,一個不顯著的測試意味著搬遷不會改變這一投資決定,反之亦然。最后,t變量顯示搬遷后的初創企業比他們的同行需要更多的時間來退出,這對時間加權的資本回報來說是一個不利因素。
(二)Cox生存模型回歸結果分析
本節使用Cox生存模型對數據進行回歸,從遷移方式、遷移行業、遷移起點和遷移時間四個角度進行研究(見圖1)。遷移方式回答初創企業如何搬遷,比較單獨總部和共同總部的搬遷情況;遷移行業回答了搬遷發生在哪些行業,比較兩個搬遷成本較低的行業;遷移起點回答了創業企業來自哪個地區,并選擇歐洲和英國作為研究群體;遷移時間回答了市場時機是否對創業成功有影響。

圖1 研究模型
1.遷移方式分析。第一個回歸系列回答了創業企業是如何搬遷的,是搬遷原有的總部還是設立另一個總部。由模型提出假設H1:遷移策略不能夠有效提升創業公司的成功率;H1.1:總部遷移或建立新的總部均不能提升創業公司成功率。
模型顯示(見圖2),在多數時間點上,遷移策略都會大大降低成功的機會。換句話說,在任何時間點上,搬遷后的公司成功率更低,或者需要更長時間才能成功。兩種遷移策略單獨作為自變量時不具有顯著性。

圖2 基于遷移策略的生存分析
連續創業者、財團規模和成功率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可以解釋為假設獨立的盡職調查,則更多的投資者意味著公司的價值被不同的第三方多次證實,是一個體現公司持續向好的指標。連續創業者理論上可以增加創業企業的價值和成功率,然而這一變量并不顯著(在Cox模型中的顯著性為10%),因為這個變量本身不能揭示一個團隊的整體協同作用。
風險投資輪次與融資總額呈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61),但在Cox模型(見表4)中與創業成功有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分析這一現象的原因,將少于三輪融資的初創企業與超過三輪融資的企業進行比較(見圖 3)發現,在不同長度的持有期下年長和年輕的初創企業表現不同。在樣本中,第一組有559個觀察值,第二組有365個觀察值,大部分的風險投資少于4輪,這意味著風投應當謹慎接手高輪次的初創企業。

圖3 融資輪次于創業成功時間

表4 以遷移方式為控制變量的回歸模型
2.遷移行業分析。第二個系列的回歸從遷移行業角度對樣本進行了分析。提出假設H1.2:即使是更容易搬遷的輕資產行業如IT、軟件和商業支持服務業(BSS),在搬遷后也不容易成功。
把通信和媒體行業作為基線組,回歸模型(見表5)顯示單獨的軟件和BSS行業都與更好的創業成功率正相關,但搬遷后的軟件和BSS行業并沒有顯示出高的顯著性,這意味著即使是如今可以無辦公場所經營的行業,也應謹慎決定搬遷。另外,研究結果還顯示通信和媒體行業的表現比軟件和BSS行業差,原因在于壟斷者的市場份額已經被大的現有企業如歐洲的德國電信和西班牙電信以及美國的AT&T和Verizon占據。

表5 以遷移行業為控制變量的回歸模型
另一個沒有顯示在回歸表中的行業是醫療行業。它是僅次于軟件業的第二大成功行業,但卻是樣本中在其他類別行業之前第二難以做出遷移決策的行業,分析可知對實驗室固定資產和臨床專家的依賴使其難以做出遷移決策。
3.遷移起點分析。第三個系列的回歸回答了“來自哪里”的問題。提出假設H1.3:創業企業的源頭對搬遷后企業的成功無顯著影響。
表6結果顯示自英國搬遷的公司比歐盟搬遷的公司更有可能成功,國家起源和成功強烈地暗示了英國和美國人民之間的殖民聯系、文化同源性和身份認同。從更廣泛的角度看,從貨幣和非貨幣資本的角度進行論證,后者包含了社會和文化資本的概念,兩種非貨幣資本與社會網絡、員工招聘、團隊協同、進一步的融資機會和收購者的偏好有關。在初創企業中,由于缺乏業績記錄、信息不對稱以及非專業投資者的存在,投資決策將不可避免地依賴于后兩種無形資本。

表6 以遷移起點為控制變量的回歸模型
4.遷移時間分析。最后一系列的回歸回答了“何時”的問題,即時機是否會像股票市場一樣影響業績?提出假設H1.4:遷移時機不會對遷移后的創業企業產生顯著影響。
鑒于搬遷公司退出的中位數為9年,回歸選擇了兩個時間段,一個是2000-2002年,另一個是2003-2007年,基線組是2008-2011年。在這兩個時間段內有53家公司進行了搬遷,但這些有足夠時間退出的搬遷公司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績效差異。而最近得到資助的初創企業難以在短時間成功,因此在這一區間的樣本不做遷移策略分析,如表7所示。與金融市場不同的是,在金融市場上時機的選擇會造成損失,而在實體經濟中技術表現出穩健性和對市場情緒的漠視。繼續上一節的內容,這意味著對于那些必須搬遷的公司來說,決策的依據最好是在地點和人員的協調上,而不是在時間上。

表7 以遷移時間為控制變量的回歸模型
結論和啟示
公司遷移作為一種策略并不能提高業績,相反它增加了創業企業成功的時間成本,拖累了資本的時間加權回報。客觀來看,遷移策略擴大了退出市場范圍和投資者數量。財團規模是一個強有力的業績指標,因為它反映了感興趣的投資者的獨立盡職調查的次數;低固定資產的行業更有可能搬遷,但即使是最容易搬遷和成功的行業,如軟件和商業支持服務行業,搬遷的影響也不大;搬遷后的英國初創企業表現更好,揭示了英美兩國人民之間的殖民聯系、文化同質性和身份認同。最后,公司遷移到美國會推遲成功的時間,這一發現不能推廣到其他目標國家,原因是來自歐洲和英國的搬遷者與美國本土創業企業相比,沒有來自亞洲的初創企業那么大的差異性,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這些遷移發生在政治經濟結構相似的中心和準中心國家。同時限于樣本數量,遷移目的國和遷移源自國均不能推廣到美、英、歐以外的國家和地區。
中國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帶動世界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的能力日益凸顯,而美國作為一個全球霸權國家仍在許多領域占有主導地位,選擇美國作為搬遷目的地的論據可以遠遠超出回歸模型所揭示的信息。不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風投和創業公司在挖掘實體經濟潛力和推動科技走向應用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不言而喻。未來的課題可就如何建立具有正反饋效應的“風投-創業”商圈以及“風投-學術-創業”產學研有機結合的體系并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勢繼續進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