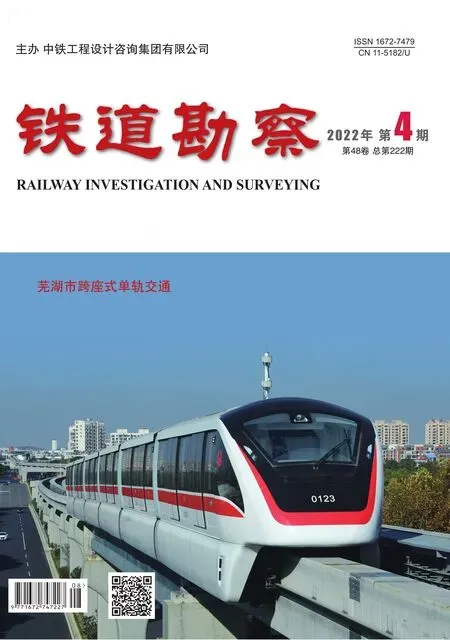廣花盆地東北部巖溶地質特征及對城際鐵路隧道影響分析
2022-08-04 12:53:56柳柳王俊
鐵道勘察
2022年4期
關鍵詞:特征
柳 柳 王 俊
(中鐵工程設計咨詢集團有限公司,北京 100055)
廣花盆地位于廣州市北部,為一個北高南低、北北東向壟狀丘陵間隔分布的傾斜平原,是我國典型的覆蓋型巖溶發育區。該地區巖溶具有“上土下可溶巖”的地層組合特征,在地下水、外部載荷等作用下易引發巖溶塌陷地質災害。隨著在覆蓋型巖溶區工程建設的推進,已有學者通過分析鉆探數據,統計見洞率、巖溶率、溶洞規模以及充填物等信息揭示巖溶發育的強弱程度[1-6];在此基礎上,部分學者進一步研究巖溶發育地段的巖性、地質構造及水文地質條件,總結不同因素對巖溶發育的影響規律[7-14]。隨著對巖溶塌陷機理研究的深入,羅小杰等建立了不同土層組合的巖溶塌陷類型,為評價巖溶塌陷風險提供了新的思路[15-16]。另外,也有學者針對塌陷與儲運條件-巖溶、塌陷物質-覆蓋層以及塌陷動力-地下水三大巖溶塌陷影響因素分析,評判巖溶塌陷的易發性等級和風險事件發生后果等級,為巖溶區工程建設選擇和塌陷災害治理提供依據[17-19]。
結合珠三角城際鐵路新塘經白云機場至廣州北項目白云機場至廣州北段(以下簡稱新白廣城際白北段)工程建設,通過研究區域地質資料,結合鉆探和孔內攝像等方法,對覆蓋層和基巖類型、溶洞發育位置和尺寸等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總結巖溶平面和垂直分布特征,并進行巖溶風險分級評價,為隧道設計、施工和巖溶加固措施提供建議。
1 工程概況
新白廣城際鐵路自新塘站引入白云機場,通過花都區平布大道后接入廣清城際廣州北站,其中白云機場至廣州北站段(白北段)受白云機場及花都區建設規劃要求,采取隧道形式通過。……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中學生數理化(高中版.高考數學)(2022年3期)2022-04-26 14:04:16
數學年刊A輯(中文版)(2020年1期)2020-05-19 00:30:36
空間科學學報(2020年2期)2020-04-01 03:50:40
瘋狂英語·新策略(2019年10期)2019-12-13 08:43:28
中等數學(2019年8期)2019-11-25 01:38:14
當代陜西(2019年10期)2019-06-03 10:12:04
新聞傳播(2018年11期)2018-08-29 08:15:24
廣西科技大學學報(2016年1期)2016-06-22 13:10:38
河南科技(2014年23期)2014-02-27 14:1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