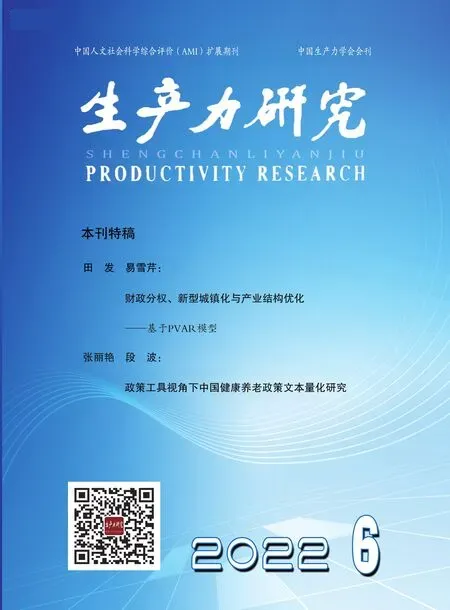長三角區域隱含碳排放的分解及預測研究
趙 祺,鄭中團
(上海工程技術大學 數理與統計學院,上海 201620)
一、引言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出口貿易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我國承擔了在國際貿易中轉移的隱含碳排放。目前,低碳化發展已經成為全球共識,長三角城市群作為世界級城市群之一,具有重要戰略地位,2020 年GDP 高達20.5 萬噸,占全國的20.18%,在出口貿易中,碳排放量較大。“十四五”規劃中對節能減排提出了具體的目標要求,大力推動“雙碳”進程,“低碳經濟”和“綠色經濟”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長三角地區在碳減排中應扮演著重要角色[1-2]。實現節能減排目標需要有科學的理論分析作為依據,長三角地區隱含碳排放研究將為長三角地區發展低碳經濟、實現節能減排、走經濟可持續發展道路提供政策建議。
二、參考文獻
貿易隱含碳是指從原材料到最終消費品的整個生產鏈中產生的所有二氧化碳[3],主要利用生命周期法和投入產出法來測算隱含碳[4-5]。閆云鳳和忠秀(2012)[6]對我國進出口貿易隱含碳利用投入產出模型研究,并對各個出口部門與行業進行分析,得到我國生產多于消費排放的隱含碳,共排放隱含碳有2.99 億噸,我國出口隱含碳最主要的產業為密集型制造加工業。王珊珊等(2019)[7]利用生命周期法對中國農業、電力等行業的碳足跡進行測算和評估,提出優化市場結構,減少碳排放的建議措施。
隱含碳排放的因素分解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指數分解方法(IDA)[8-9];二是投入產出結構分解方法(SDA)[10-11]。李晨等(2018)[12]基于LMDI 指數分解方法研究中國水產品貿易隱含碳排放轉移的影響,得出規模效應的增加導致貿易隱含碳排放的上升,水產品進出口的結構效應和強度效應對隱含碳排放有負面影響。尹衛華(2019)[13]運用SDA 結構分解法分析了我國出口貿易碳排放強度變化趨勢及其驅動因素,得出直接碳排放系數效應、技術結構效應和出口貿易效應是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強度變化的主要因素。
碳排放預測模型可分為兩類:一是混合構建模式,二是直接構建模式[14-15]。在直接構建模式中,最小二乘回歸法、嶺回歸法和STIRPAT 模型存在穩定性不足、參數難以確定等缺點。李陽和陳敏鵬(2021)[16]基于指數(LMDI)模型、STIRPAT 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識別了中國農業非CO2排放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中國農業非CO2排放量整體呈上升趨勢,到2050 年仍未達峰;低情景下CO2排放量整體呈下降趨勢。薛黎明等(2017)[17]利用SVR 模型對河北省1990—2015 年碳排放及其影響因素數據進行訓練和檢驗,得到了具有準確性較高的碳排放預測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投入產出算法
本文采用投入產出法測算長三角地區出口隱含碳排放量。投入產出法是由Leontief 首次提出的,該方法主要用于分析各部門的投入產出關系;生命周期評價法主要衡量產品生產周期中的碳排放量,獲取數據和實際操作比較困難;而投入產出法主要測算整個產品生產過程中的能源消耗,計算其二氧化碳排放量,數據易得,誤差小。投入產出表分別從投入、產出以及二者之間關系共3 個角度來闡述,本文采用投入產出法來測算隱含碳排放。一般投入產出模型為:

根據上式則有:

其中,X 為總產出,A 為直接消耗系數,I 為單位矩陣,Y 為最終產品列向量。長三角某地區出口額向量為Y,A 為中間投入產出矩陣,有N 個產業,E 為各產業直接碳排放系數向量。其中Y 是N×1 的矩陣,A 為N×N 的矩陣,E 為1×N 的矩陣。則該地區因出口而隱含的碳排放表示為:

其中,(I-A)-1-I 為完全消耗系數矩陣。(I-A)-1為列昂惕夫逆矩陣,碳排放強度系數對貿易隱含碳測算有重要影響,也稱為直接能源消耗系數矩陣,代表了不同部門的能源使用效率,用ei表示:

Ci表示第i 部門的能源的消費量,ei代表第i 部門產生總產出Xi所直接釋放的碳排放量。
碳排放量數據要根據能源消耗量通過公式計算得出,依據Kaya 恒等式進行修正,本文采用IPCC2006 的計算方法,計算各能源碳排放量及碳排放系數,各類能源的碳排放系數,如表1 所示。


表1 各能源CO2 排放系數λ 值(萬噸/萬噸)
(二)影響因素SDA 結構分解模型
SDA 方法將隱含碳排放的變動分解成幾個基本因素變化之和,主要方法有:加權平均法、兩級分解法、保留及不保留交叉項四種。相比兩級分解法具有計算量少、減少誤差等優勢,將從第0 期到第t期分解得到的各因素總影響效應取平均值,得到各因素影響效應值[18]。本文基于兩級分解法對影響長三角貿易碳排放的因素進行分解。

f(△Ed)為能源消耗的強度效應,表示各行業生產技術、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導致碳排放強度發生變化;f(△L)為投入結構效應,表示技術變革引起的中間投入結構的變化;f(△ys)為能源結構效應,表示各部門能源結構的變化導致貿易隱含碳的變化;f(△yv)為需求規模效應,表示最終產品的需求變化導致對碳需求的變化。
(三)支持向量回歸預測模型(SVR)

在公式(10)中,η 是根據數據樣本進行識別的系數,a 為常數。用最小化函數進行系數η 的估計:

式中,λ 為標準化常數,最小值函數也可表示為:

(四)數據來源與處理
我國投入產出表目前可獲取的地區投入產出表為2002 年、2007 年、2012 年和2017 年中國區域間投入產出表,本文所要測算的為2003—2020 年長三角帶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的數據,本文借鑒閆云鳳和忠秀(2012)[6]研究,假設短期內(1~5 年)一個地區的生產技術結構不會變化太大,對于相鄰年份的數據,用已有年份的投入產出表代替,即2003—2008 年、2009—2014 年、2015—2020 年的數據則以2002 年、2007 年、2012 年、2017 年所選用的長三角地區區域燃料消費量數據,取自于2003—2020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的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的區域能耗平衡表。碳排放數據通過碳排放系數測算和能源的消費量計算而得,碳排放因子和標準煤轉換因子來自《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指南》的IPCC 指南。
四、模型應用與結果分析
(一)長三角區域各部門貿易隱含碳分析

圖1 2003—2020 年長三角區域各省市出口貿易隱含碳
從圖(a)所示,2003—2020 年長三角區域各省出口貿易隱含碳整體趨勢為上升—下降—上升趨勢,排放總量最大的省份是浙江省,最少的是上海市。其中,2000 年,浙江省、安徽省、江蘇省和上海市的年均隱含碳在長三角區域占比分別為56.21%、3.69%、36.8%和3.29%。2008 年各省在長三角區域占比分別為60.22%、13.33%、35.22%和32.33%,較過去幾年四省的排放總量都有了明顯增長,受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率下降,2009—2010 年的隱含碳排放總量上升。2011—2015年,各省的隱含碳年均排放總量有所下降,說明“十二五”規劃提出的建設資源節約型、綠色發展的政策對隱含碳排放的成效顯著。相比于2003 年,2020年浙江省、安徽省、江蘇省和上海市隱含碳排放總量分別上升了2.19 倍、0.35 倍、1.24 倍和0.33 倍。
從圖(b)所示,2005—2020 年長三角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量最大的五個部門為S3(紡織業)、S8(化學工業)、S15(電氣機械和器材)、S12(通用設備)、S4(紡織服裝鞋帽皮革羽絨及其制品),年均排放量分別為2 664.44 萬噸、1 733.81 萬噸、1 994.98 萬噸、1 823.45 萬噸,1 437.34 萬噸,年均占比分別為18.91%、12.17%、11.66%、10.25%,9.58%。S3、S12 碳排放系數的波動幅度較大,S4 和S8 發展較為平穩,所占比重分別從2005 年的21.09%、27.57%降至2020 年的16.97%、9.15%,主要由于出口貿易額及完全碳排放系數的下降。長三角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最少的三個部門從高到低依次是S19(非金屬礦物制品)、S1(非金屬礦和其他礦采選產品)、S16(廢品廢料及其他制造業)。
(二)長三角隱含碳排放影響效應分析
利用投入產出表對2003—2020 年長三角各部門隱含碳排放量的變動進行分階段隱含碳排放量總量的影響效應分析,結果如表2 所示。

表2 長三角出口貿易隱含碳效應分解(萬噸,%)
由表2 可知,2003—2020 年各效應對長三角地區隱含碳排放總量的變化在不同階段各不相同,如能源消費結構的變化有利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產品需求規模效應在各時期均為正,不利于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減少。綜合來看,2003—2020 年,需求規模效應從9 885.9 萬噸下降到1 527.52 萬噸,大于其他三個效應之和,使得二氧化碳排放減少。2003—2020 年能耗強度和能源結構變化是各行業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減少的結果。能源結構效應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總量1 307.73 萬噸,能耗強度效應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總量3 520.5 萬噸,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影響因素。
(三)各區域隱含碳排放影響效應分析
長三角各區域隱含碳排放影響效應分析如圖2所示,在2003—2008 年期間,浙江省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總效應最大,為6 802.84 萬噸。在2009—2014年期間,江蘇省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總效應最大,為2 670.61 萬噸在。2015—2020 期間,上海、江蘇省和安徽省的總效應為負值,浙江省的總效應為正值,為2 311.98 萬噸。

圖2 長三角各省市2003—2020 年出口貿易隱含碳分解
對于上海市,在2003—2008 年,能耗強度效應和需求規模結構效應使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需求規模效應使二氧化碳排放總額增加了285.808 萬噸。在2015—2020 年期間能源總效應合計下降514.683 萬噸,能源消耗結構與產業結構的變動起到主要作用。
對于江蘇省,在2003—2008 年產業投入結構效應使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減少727.544 萬噸,但需求規模效應使總效應增加130.51%,導致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大量增加。在2015—2020 年能耗強度使得總效應減少1 262.152 萬噸,產業結構使得總效應減少959.864 萬噸。
對于安徽省,在2003—2008 年,需求規模效應使其增加139.776 萬噸,占總效應228.68%,遠大于能耗強度效應。在2015—2020 年期間,需求規模效應和能源結構效應占二氧化碳排放總效應的95.94%,使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大量增加。
對于浙江省,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上升主要由于能耗強度與需求規模效應的增加,占總效應的83.11%;在2015—2020 年期間,需求規模效應使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上升1 859.896 萬噸,占總效應的80.45%。
(四)支持向量回歸影響因素預測分析
本文以長三角地區為例,將其2005—2014 年和2015—2020 年的碳排放量及其影響因素數據分別作為訓練樣本和測試樣本。對所有樣本數據進行歸一化處理,選取最佳參數構建并檢驗模型,結果如圖3 所示。

圖3 2005—2025 年長三角區域碳排放量趨勢圖
由圖3 可知,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MAPE)為0.051,均方根誤差(RMSE)為0.95 誤差值較小,因此該模型具有良好的學習和推廣能力。將2021—2025年人口、人均GDP、二產占比和能源強度影響因素預測值歸一化后代入碳排放預測模型,得出2021—2025年人口、人均GDP、二產占比和能源強度下影響因素預測值如表3 所示。

表3 2021—2025 年碳排放量預測值及其影響因素數據
從影響因素變化趨勢來看,2021—2025 年,長三角區域的人均GDP 呈穩步增長趨勢,人均GDP增量分別為0.330 萬元/人、0.270 萬元/人、0.61 萬元/人、0.649 萬元/人。在這五年里,二產占比處于下降趨勢,說明在未來五年里,長三角地區戰略性新興產業將加快發展,產業結構優化發展,服務業總體增速將高于傳統主要行業。而能源強度分別為0.153 5 噸/ 萬元、0.148 8 噸/ 萬元、0.144 3 噸/ 萬元、0.139 9 噸/萬元和0.135 7 噸/ 萬元,呈下降趨勢。預計2025 年長三角區域碳排放總量達到120 595.41 萬噸,2021—2023 呈上升趨勢,2024—2025年呈下降趨勢。所以未來五年長三角區域碳減排之路依然很嚴峻。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第一,本文利用投入產出法對長三角區域各省對外貿易隱含碳測算得出:2003—2020 年整體趨勢為上升—下降—上升,排放總量最大的省份是浙江省,最少的是上海市。2016—2020 年各省市隱含碳排放處于波動上升趨勢。長三角區域各部門隱含碳排放量存在較大差異,均處于緩慢上升趨勢。
第二,利用SDA 跨期結構分解對長三角區域隱含碳排放量總量的影響效應分析得出:能源結構的變動有利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需求規模效應使得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增加。能源結構效應和能耗強度效使其減少,整體隱含碳排放呈緩慢下降趨勢,表明技術進步是碳減排的主要驅動力。
第三,最后利用SVR 模型預測得出在未來五年里,我國第二產業在長三角地區仍占較大比重,對長三角區域的碳排放總量影響較大。同時長三角區域碳排放總量2021—2023 呈上升趨勢,2024—2025年呈下降趨勢。所以未來五年長三角區域碳減排之路依然嚴峻。
(二)對策建議
長三角地區經濟的持續增長必然會對能源消費提出更高的要求。為解決經濟發展要求與碳中和目標互為約束的問題,長三角區域出口貿易需要優化產業結構,大力監管能源密集型產業、促進出口貿易低碳高質量發展,重視低碳技術發展和科技創新。
第一,持續改善長三角城市群的產業結構,優化貿易能源消費結構。增加清潔能源的比重,逐步降低對煤炭的依賴,發展低碳經濟。
第二,有效推進低碳環保技術改進。政府應加大對人才、科技的投入,提高環低碳環保技術的研發能力。促進各地區綠色低碳發展。
第三,提升長三角城市間的合作減排力度。大力推動“雙碳”進程,促進長三角區域內隱含碳排放轉移的減少。結合各城市碳排放的變動趨勢和“十四五”發展規劃政策,推動各城市綠色高質量發展,實現碳達峰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