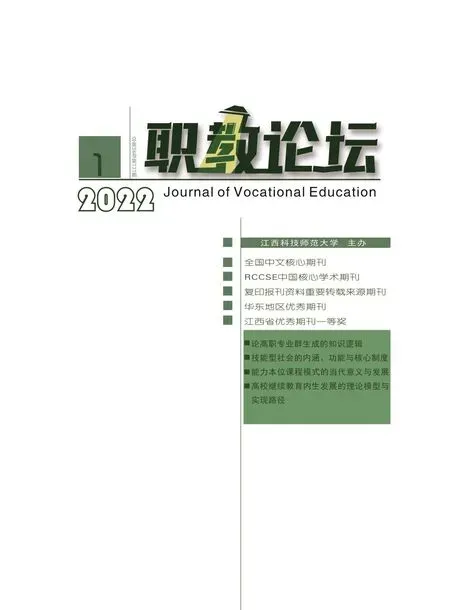近代以來西方職業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引進與傳播研究
□馬君 王藝霏
早在公元前,我國就有了職業教育的萌芽[1]4,但直到進入近代社會,各類西方職業教育理論思想在不同傳播主體的引介下輪番登場中國后,中國職業教育理論才逐漸形成并體系化。回顧梳理西方職業教育理論在我國的傳播歷程主要出于以下三點考慮。
一是摸清新中國成立之前我國職業教育理論起源的需要。 歷史上,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與近代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但其較為系統的學術根源卻是來自于西方。隨著世界各國教育交流的廣泛與深入,交流傳播對我國職業教育的影響也越來越凸顯。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正確對待職業教育交流傳播的歷史,科學地總結歷史傳播中的經驗,是關系到我國職業教育能否真正走向世界的重大問題。二是彌補關于這一時期職業教育學術傳播史研究的不足。中國教育現代化屬于后發外生型[2],為了職業教育的發展,中國在全世界廣泛拜師,向德國、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學習從未止步,但是中國職業教育學術史上對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持續研究卻非常少見。以“西方”“職業教育”“傳播”為關鍵詞在中國知網上進行主題搜索,僅獲得6 篇文獻。 這些研究要么是局部歷史陳述,要么是借助于教育學傳播特點進行宏觀敘述,都沒有系統地梳理近代以來西方職業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具體傳播歷程及其特點。三是這些理論思想本身具有的重要價值亟需深入挖掘。 20 世紀后半葉以來,隨著我國教育科學的不斷進步,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對我國近代以來的教育交流史進行梳理,如周谷平、田正平和鄒振環等學者,出版了《中外教育交流史》《近代西方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和《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等書籍,都為職業教育理論東西方交流的歷史梳理提供了方向與指引。西方職業教育理論比中國職業教育理論的發展時間早,其在中國的傳播是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見證者、參與者與推動者。 這些西方職業教育理論思想能夠被選擇,最終漂洋過海來到中國被學習和鏡鑒,展示出了理論自身強大的生命力,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一、傳播背景
縱觀中國職業教育學術發展史,實質上是一次東西方跨文化傳播的歷史。 一般來說,跨文化傳播包括單向性的直接傳播、通過第三方交流的媒介傳播以及一方傳播主題刺激另一方傳播主題的激起傳播三種類型,對應近代以來西方職業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形式, 分別為個別傳教士的單向傳播、通過報刊譯介的媒介傳播以及中國學者編譯職業教育書籍的激起傳播。 這些傳播之所以能夠進行,離不開以下三方面的背景因素。
首先,從理論本身來看,這是國內外職業教育理論發展的必然趨勢。 一方面,西方職業教育理論進入中國是世界職業教育理論發展擴充的必然結果。 17 世紀,西方的一些教育家和思想家開始向傳統的師徒制挑戰, 提出了建立職業學校的理論,初步孕育了職業教育學。 19 世紀工業革命浪潮波及歐、美兩洲,職業學校在發達國家普遍建立,歐美職業教育學進入了萌芽階段。 19 世紀末到20 世紀初,資本主義狂潮席卷世界,人類社會進入第二次工業技術革命時期。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上從自由競爭走向壟斷,各國先后通過立法建立了正規的職業教育制度。 從那時起,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交通工具的改進,再加上西方殖民主義為了拓展世界市場, 用大炮和兵艦迫使中國等亞洲國家國門洞開,西方職業教育理論在其裹挾下不請而至。 外國人進入開始中國大規模傳播西方職業教育理論,拓展了西方職業教育理論的廣度,使得職業教育理論在全球開始傳播并發展。 另一方面,這是中國職業教育理論難以內生困境下的必然之舉。中國的職業教育實踐雖然源遠流長,但明清長期的閉關鎖國使得近代以前的中國職業教育理論一直處在較為原始的狀態。沒有完整職業教育理論指導的職業教育實踐就像是無頭的蒼蠅得不到有效發展,而職業教育實踐的落后又使得職業教育理論難以內生。在這種困境下,向國外引進學習便是發展中國職業教育理論最便捷、最高效的方式之一。 西方職業教育理論傳入中國,是順歷史潮流之舉,能夠促進西方職業教育理論的豐富與完善,同時也有利于提高職業教育的國際影響力。
其次,從我國實際情況來看,這是我國職業教育實踐發展的現實需要。 明末清初之際,中國近代工業在封建制度上破土而出,我國開始出現資本主義的萌芽。清政府舉辦的洋務運動創辦了我國最早的近代軍事工業、燃料工業、采掘工業、交通運輸工業和電訊工業等, 后來又創辦了少數民用工業,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的發展。這些近代大工業生產方式的出現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對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的需求量暴增,要求把科學技術作為強國富民的手段,沖擊了建立在自給自足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封建傳統教育,從而帶來了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重大變遷。中國傳統以《四書》《五經》為內容的教育再也不能適應這種潮流,職業教育作為與大機器生產有著密切聯系的教育類型,必然會出現新的教育模式來取代傳統的培養模式,引進西方職業教育理論就是必然的選擇。于是開始出現傳播學習西方職業教育理論的中國人。例如,以左宗棠、李鴻章和張之洞為代表的清廷洋務派, 他們在辦洋務、搞實業過程中深深地認識到,要擺脫清政府在政治和經濟上所面臨的困境,走富國強兵的道路,就必須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于是,他們在辦洋務、搞實業的同時,積極學習西方職業教育思想,努力培養各種能掌握機器生產技術和使用先進武器的人才。 李鴻章在為創設天津武備學堂上皇帝的奏折中曾寫道:“我非盡敵之長,不能制敵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備,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1]29。雖然洋務派倡導新學的主張實質是為了維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統治,但是他們先進的職業教育思想沖擊了幾千年來讀經學史的傳統教育,使中國職業教育有了良好的開端。
再次,從國內外傳播交流來看,是因為這些理論思想與中華文化之間具有文化契合性。眾多的外國職業教育理論能夠在中國傳播, 除了當時政治、經濟等外部的背景性因素,更深層的原因是這些思想與中華文化、中國知識分子精神、中國教育傳統的內在契合。 以杜威為例,據聽過杜威講課的楊亮功回憶,杜威“不善言辭,有時使用艱深字眼令人難解”[3],在枯燥無味且語言不通的情況下,杜威的職業教育理論能傳遍中國大江南北似乎不合常理。但是仔細研究杜威具體的職業教育理論就可以發現,促使杜威廣為人知的不是外部因素,而是杜威職業教育理念本身的原因。杜威的職業教育理論根植于20 世紀初的美國,那時的美國經過南北戰爭后經濟迅速發展,承襲西歐教育傳統而建立起來的美國教育體制越來越難以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美國化民主社會的需要,無法有效解決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系列伴生問題。而以解決社會問題為己任的杜威主動以社會作為研究范疇, 強調民主主義與教育的關系,要求人類認識自己生活在集體化時代,要創造一種新的個人主義。他在杜威學校按照自己“學校即社會”的理念,致力于把學校建設成為社會生活的方式,使個人因素和社會因素相互協調。 杜威的這些思想,與中國傳統道德觀念所追求的集體主義、內圣外王、德政教化等異曲同工。 而此時處在民國時期的中國社會同樣也經過了幾十年的痛苦轉型和艱難演進,在經濟和文化教育方面都進入了發展的轉型期和關鍵期,清末以來形成的中國化的赫爾巴特學派教育學難以適應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對于人才的需求以及新文化運動對于教育的新要求,這時在美國廣受推崇的杜威教育理論來到了中國,滿足了當時中國迫切呼喚新的教育價值觀、教育思維和教育思想的需要,因此能夠在中國廣泛傳播。
二、傳播的歷程及其特點
清末民國時期是繼隋唐時期佛學東來、明清時期西學輸入以來,第三次外來文化大規模地輸入中國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4]。 這一時期西方職業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根據不同的層次和水平,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包括以零星介紹為主的職業教育理論傳播階段、以日本為中介的職業教育理論傳播階段和以美國為藍本的職業教育理論傳播階段。
(一)以零星介紹為主的職業教育理論傳播階段及其特點(1900年之前)
根據黃炎培的研究,光緒三十年山西農林學堂總辦姚文棟在《山西農林學堂添聘普通教習祥文》一文中最早使用“職業教育”一詞:“論教育原理,與國民最有關系者,一為普通教育,一為職業教育,二者相成而不相背”。雖然“職業教育”一詞直到20 世紀初才在我國出現, 但職業教育實踐早已產生,國外相關職業教育理論也早已在中國傳播。 1900年之前是近代西方職業教育理論在中國傳播的第一個階段。
清末,大批傳教士傳教過程中夾雜著的職業教育理論喚醒了國內知識分子開眼看世界職業教育的意識。德國同善會傳教士花之安是清末最早來華的傳教士之一,早在1873年他就在中國出版了《德國學校論略》, 這是鴉片戰爭后比較系統地論述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的開山之作。它介紹了德國各類中等技術學校及高等專門學校,提出在西方培養國家需要的人員,比如火輪車者、電報者、書信館、大農師、森林管理者等,都是“非考取以為官者”。 1897年,美國來華傳教士林樂知也與光緒進士任廷旭一起合譯了森有禮的《日本的教育》,并題中文書名為《文學興國策》。書中對美國職業教育進行了詳細介紹: 為了適應工業革命后各類產業迅速發展的需要,美國設立了各類職業技術學校以造就各類專業人才,“使他年學業有成,或精于機器,或熟于駕駛,或工于造船,或巧于建屋,或明于五金,或善于制造,無一非國中有用之人”[5]。
除了主動來華傳播的傳教士,清政府迫于內外壓力,還曾派遣時任京師同文館總教習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前往日本、美國、法國等七國考察教育,丁韙良在考察結束后撰寫了《西學考略》,對西方職業教育發展的情況進行了詳細介紹:一些大學增設工科、農科,且隨著現代工業及產業的發展,“營造館”“冶礦館”“機器館”“農政館”“船政館” 等各類專業技術學校也不斷出現。這都為晚清政府推行職業教育改革提供了良好的鏡鑒,成為了當時指導清政府職業教育改革的一本重要參考書。 除此之外,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也開始傳播西方職業教育理論,代表性人物中有駐外公使郭嵩燾、黃遵憲,還有留學生顏永京等。而第一個系統引介歐美和日本職業教育理論的中國人是商人出身的鄭觀應[6],他于1893年正式出版的《盛世危言》曾在當時社會中受到熱議和推廣,至今仍有啟發意義。
除了個人自發翻譯外,一些機構也進行了有組織的翻譯,比較有影響的是江南制造總局設立的翻譯館以及美國傳教士舉辦的廣學會。 1867年,江南制造總局為應對火藥、炮法、汽機等知識的匱乏而設立翻譯館,聘請徐壽、華蘅芳以及外國傳教士傅蘭雅等人譯書,涉及兵學、電學、工程等多個類別。而美國傳教士1887年創辦的廣學會主要出版基督教教義基礎的圖書,職業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攬要》,書中對于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英國工匠境遇的描述使人們對當時英國的織匠等職業有了新認識:“至于織匠,一則因大兵之后國殤相望,穿衣人之少,一則因新創織布機器人力不能敵,故傭值竟賤一半”[7]。另外還有1896年京師同文館增設的東文館,翻譯了《電理測微》《藥材通考》等應用科學書籍,開創了國內官辦日語譯介職業教育的先河。
這一階段的傳播特點可以概括為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傳播主體的壟斷性。 以西方傳教士為主體,雖然駐外公使和留學生等中國社會群體也參與了西方職業教育理論的引介,但卻是一個極小的群體,翻譯力量薄弱,而懂外語的知識分子更是鳳毛麟角,無法獨立實施翻譯行為。
二是傳播動機的差異性。傳教士對西方職業教育理論的傳播主要是為了更好地傳播宗教,嚴復曾在他的《譯書略論》中指出花之安等傳教士“譯書之宗旨:傳路德教(基督教)”[8]。 而此時進行教育理論傳播的中國人多屬于洋務派,他們主要是想為洋務學堂培養軍事人才,以此維護清王朝的統治。 例如江南制造總局設立的翻譯館翻譯的書籍 《制火藥法》《行軍指要》《克虜伯炮說》等,都具有明顯的實用性與軍事性。
三是傳播內容的零散性。傳教士們大多根據自己的判斷和喜好來選材,散見于其他譯著中,膚淺而又零碎。例如花之安在他的《德國學校論略》一書中介紹了“技藝院”“格物院”“農政院”等職業學校[9]。后來,丁韙良出國考察后撰寫的《西學考略》也介紹了隨著現代工業及產業的發展而不斷出現的“營造館”“冶礦館”“機器館” 等各類專業技術學校的情況。郭嵩燾也曾在其游記《倫敦與巴黎日記》中提到了法國圣西的“農田學館”“通商學館”“草木學館”等實業學校。
四是傳播途徑的單一性。主要采用中外合作翻譯模式,基本上是外國傳教士口述,中國人筆錄,錯誤率較高且效率低。絕大多數的中國傳播者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外國傳教士的“傀儡”,他們對選擇合適的傳播途徑與內容既無權利更無意識,使得這一時期的傳播大多難以落地。
五是傳播效果的局限性。 從成效來看,并沒有引起社會廣泛重視。 在清末,由于傳教士所選擇翻譯的東西與中國人實際需求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他們的論著大多沉寂在歷史的長河之中,并未對中國職業教育產生深度影響。 而中國本土的有識之士,要么受政治經濟條件制約,要么由于語言文化不通,大多對于國外職業教育理論傳播與學習限于皮毛層次,隨機性較強且系統性差。
(二)以日本為中介的職業教育理論傳播階段及其特點(1900—1910年)
晚清的教育近代化,日本直接或間接地發揮了很大作用。 甲午中日戰爭后,很多中國人逐漸意識到發展近代教育的重要性。 而當日本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獲勝后, 這一認識更促使中國開始以日本為中介著手構建近代化教育事業,由此西方職業教育理論開始借道日本大規模地向中國傳播。 這一階段以考察為主要手段,以學務官紳為主要力量,以教育理論書籍為主要載體,西方職業教育理論大量傳入我國,形成了近代西方職業教育理論在中國傳播的第一個高潮。
19 世紀70年代初中日建交以后,中國官紳東渡游歷、考察者漸多,寫出了一批通過介紹日本職業教育來傳播西方職業教育理論的游記著作。1898年,清政府第一次派遣官員姚錫光赴日考察,后姚錫光在其所著的《東瀛學校舉概》一書中詳述了日本官立、公立、私立三種類別學校的辦學狀況,涉及多所職業教育性質的學校[10]。 1901年9月,清政府下興學詔后又下令各省督撫遴選在職官員和學生派送至日本游歷游學。 此后,更多學者紛紛赴日考察教育,回國后撰譯介紹、出版了大量著述。其中較有影響的是吳汝綸的《東游叢錄》[11]。 書中涉及學校教育機構40 所左右,詳述了商船學校、水產補習學校、實業補習學校、高等工業學校、東京職工學校以及東京裁縫學校、共立女子職業學校等日本實業學校辦學實踐狀況和學校職業教育的相關理論。 另外,還有1903年繆荃孫的《日游匯編》在今天看來也具有先進性,書中繆荃孫首次關注到了日本“一壁講求實業,一壁研究師范”的職業教育師資培養方式。從理論上強調和區分了實業師范和普通師范的異同,“初級師范,只學普通學。故實業師范,不啻合實業學校與師范學校而為一校也”[12]。
隨著清政府的大力倡導,1904年后的教育官員赴日考察學務逐漸制度化,全國上下掀起了一股赴日考察學務的熱潮,為中外職業教育交流史上之罕見。下表為1900年至1910年部分赴日考察職業教育游記的相關書籍及作者。

表1 1900—1910年赴日考察職業教育游記一覽表
從現有資料來看,20 世紀的前幾年,派遣官紳到日本游覽學習是為了給下一階段全方位地學習日本作準備。 1904年由張之洞、張百熙等擬定的《奏定學堂章程》則標志著清政府正式大規模學習日本。
相比于上一階段,這一階段的傳播特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傳播動機的官方性。 1900年至1904年前后,正值清政府醞釀頒布新學制時期,訪日的官紳或受張之洞、劉坤一等清廷重臣委托,或間接與朝廷有關系。他們考察后傳播的理論主要集中在教育制度、教育宗旨等大政方針方面,其理論最終直接影響到了清政府的教育政策制定。例如“癸卯學制”的參考材料之一就來自于去日本實地考察學務的姚錫光向張之洞上的《查看日本學校大概情形手折》。
二是傳播載體的包容性。當時幾乎所有的報刊均設有教育專欄。 相較于圖書專著來說,報刊的內容包容性強, 可以包容大量的文字和照片等信息。例如我國最早的教育專業刊物 《教育世界》自1901年創辦之后,翻譯引介了《實業學校令》等多個職業教育理論與規范。另外,報紙的價格低廉,內容通俗易懂,對于受眾也有較強的包容性。
三是傳播主體的主動性。傳播主體由傳教士到派遣官員這一角色的轉變,標志著國人初步掌握傳播西方職業教育的主動權、話語權。但同時,雖然這一階段的傳播者比上一階段的數量激增,而真正為中國職業教育發展作出貢獻的人卻依然屈指可數。他們中很多人只是簡單譯介或描述西方職業教育而不加批判,使得這一時期的職業教育發展仍較緩慢。
四是傳播效果的廣泛性。 一是如羅振玉《教育世界》和吳汝綸《東游叢錄》為新學制的建立起到了輿論導向和宣傳介紹的作用,直接影響了清政府實業教育制度的確立。 二是1904年以后赴日的具體辦學人員和中下級學務官員,其理論傳播的重點都主要放在了如何辦學方面,影響了省州縣職業教育的具體實施情況。三是西方職業教育理論幾經轉手后通過日本傳入中國, 使得理論質量難以保證,這就促使學者們挖掘學習一手資料,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中國學者對職業教育理論的研究興趣。
(三)以美國為藍本的職業教育理論傳播階段及其特點(1911—1949年)
隨著日本軍國主義野心的日益暴露,以日為師逐漸式微。 而美國此時減免了部分庚子賠款作為中國留學生赴美留學計劃的基金,于是美國逐漸成為中國人心中的榜樣。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國境內的日本教習幾乎全部回國,中國人開始直接學習美國職業教育理論,一直持續到1949年。 其中1911年到1915年是過渡期,20 世紀20年代達到了西方職業教育理論在中國的第二次傳播高潮,直到民國后期走向衰落。
在過渡時期,中國“地寶不發,實業界之組織尚幼稚,人民失業者至多,而國甚貧”[13]。 擔任民國教育總長的蔡元培針對我國實際情況,提出了“實利主義教育,以人民生計為普通教育之中堅。 ”[14]此后,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迫切希望通過學習美國的職業教育進而實現教育救國理想,出現了很多象征著職業教育理論相對獨立的職業教育學著作。 根據《民國時期總書目》,這一時期的傳播著作可分為三個方面。 一是以美國為主,對各國職業教育的沿革與現狀進行宏觀介紹。 例如1915年黃炎培訪問美國后出版的《黃炎培調查美國教育報告》對美國的職業教育狀況、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聯絡的方法等都進行了詳細介紹。二是出版了關于職業教育教學理論和教學方法等方面的譯作,其中包括首次對職業心理學進行關注的鄒恩潤《職業智能測驗法》[15]。三是出版了專門研究國外職業教育發展的著作和論文集。其中朱元善的《職業教育真義》是我國最早的成體系的職業教育理論著作, 該書以譯介為主,摻以朱元善個人研究,被稱作“20 世紀初中國職業教育學的拓荒之作”[16]。
這一時期譯介的部分職業教育類具體書目如表2 所示。

表2 以美國為藍本的西方職業教育理論傳播書目一覽表
除了通過資料學習國外職業教育,當時還邀請了一些美國教育專家來中國講學,其中杜威的來華交流格外矚目。杜威把職業教育視為平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學生常道直將杜威在北師大講授的教育哲學整理編譯為《平民主義與教育》,書中第二十六章從職業教育的意義、職業教育與實業教育等方面專門論述了職業教育的內涵。 另外,杜威在蘇州和福州以《教育與實業》為題發表的兩次演講、在中華職教社等處以《職業教育之精義》《職業教育與勞動問題》等為題的多次演講,都對什么是職業教育進行了詳細論述,對中國職業教育的理論體系構建和實踐發展都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17]。
隨著對美國教育理論的深入學習,這一時期的中國教育界經過中國與外國、傳統與現代的多方位比較,最終選擇了以美國職業教育為藍本發展中國職業教育,并從學制等方面不斷深入與加強。
這一階段的傳播特點主要包括以下六個方面。
一是傳播動機的明確性。此時職業教育理論的傳播是“一種通過分享、交換信息進行相互識別的互動過程”, 中國學者學習國外逐漸有了明確的學科發展意識。受此目標驅動的學者們想通過學習國外職業教育理論為自己所用,以此來完善中國職業教育理論并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實踐樣態。
二是傳播主體的自主性。這一階段的傳播者逐漸有了主動選擇思想與流派的意識,出現了如蔡元培、胡適等對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的人物。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國教育家介紹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最早資料是蔡元培將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納入他所提倡的實利主義教育范疇。而介紹杜威思想最積極的“中介人”是胡適,他積極參與發起邀請杜威來華的活動,還在北京大學開設“杜威著作選讀課”, 培養了解并傳播杜威職業教育理論的一大批新青年。
三是傳播內容的專業性。這一階段既有對一般理論與國際職業教育現狀的描述,也有對國外經典著作的翻譯,還有基于學科發展的理論引介。 例如1935年劉鈞對德國凱興斯泰納所著的 《工作學校要義》進行了翻譯,還有首次關注到兒童職業陶冶問題的楊鄂聯、彭望芬所翻譯的《小學職業陶冶》等。這些書籍從專業視角探討了職業教育多方面的思想理論,為中國職業教育學科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初步理論準備。
四是傳播時間的持續性。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以美國為藍本的職業教育理論在中國持續傳播了三十余年,這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其歷時之久、規模之大、對中國之影響遠超其他國家。盡管在后期以杜威為代表的美國教育思想受到了一定的批判,但是反思的力量始終是相對弱小的,影響力一直持續到了新中國成立之時。
五是傳播途徑的直接性。 相比于之前,這一階段學者們在翻譯西方職業教育論著的時候不再使用中間媒介,而是從產出國直接學習;不再以翻譯二手理論著作為主,而是直接翻譯原本為主。報刊連載的浪潮也逐漸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正式出版的完整的職業教育理論著作,更加強調“著”“譯”結合。
六是傳播載體的多元性。《教育與職業》是民國時期僅有的一份對職業教育進行長時間專門關注的刊物, 在其創辦期間至少將41 個國家的職業教育狀況介紹到中國, 尤以介紹美國的文獻為最多。除此之外,還出現了中華職業教育社對于西方職業教育理論進行專門傳播。 自1917年至1949年,中華職業教育社共出版著作110 余種,包括國外職業教育經驗介紹、職業教育論文集及該社的事業介紹等多個方面[18]。
三、主要影響與當代啟示
近代西方職業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不僅影響了中國職業教育理論體系的構建,也影響了中國職業教育實踐的發展。 在當下職業教育大發展時代,如何正確看待這些歷史,并從傳播活動中汲取經驗,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一)主要影響
1.為中國職業教育學科的誕生奠定了理論基礎。 在近代西方職業教育理論思想傳入中國之前,中國未曾有人提出過有關職業教育理論的系統學說。直到1917年,朱元善編譯的《職業教育真義》全面地探討了關于職業教育的意義,才成為了我國第一本成體系的職業教育理論著作。書中首次將職業教育的意義區分為兩個重要方面,即對于個人和對于社會的意義。而對職業教育個人意義的重視是當時中國職業教育理論所未能意識、未能重視的方面,直到后來這種思想才為學界認同并多所闡釋。還有鄒恩潤編譯的《職業智能測驗法》也是當時國內第一本關于職業心理學的系統著作。職業指導在當時的中國屬于“一件創聞的事”,鄒韜奮通過撰寫文章和著作比較詳細地介紹美國等職業指導發達國家職業指導運動的興起和發展情況,增進了國人對職業指導的了解和接受。
不論是朱元善還是鄒恩潤,他們都試圖從世界職業教育發展的大籮筐中,挑選出適合中國職業教育學發展的先進理論。最終,這些理論在黃炎培、顧樹森等有識之士的推動下,開闊了中國人關于職業教育的視野,使國民認識職業教育的同時,也加深了人們對職業教育的理解,為新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參照,啟發了國人對職業教育理論進行進一步探討與研究,也為中國職業教育學的產生奠定了理論基礎。
2.推動了中外職業教育理念的交流。 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一部教育史就是一部各民族教育相互交流并不斷創新的歷史。 清朝國門被打開后,來自德國、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傳教士逐漸開始在中國傳播西方職業教育思想。 甲午中日戰爭以后,眾多出國參觀的中國學者和官員對西方職業教育的情況進行細致觀察后,從制度、政策和實踐多個方面,使用書籍或演講等形式向國內廣泛進行介紹。 1910年之后,在胡適等人的邀請下,美國教育家杜威和孟祿等學者也先后在中國傳播其思想,為中國帶來了先進的職業教育理念。
在職業教育思想的傳播過程中,外國人和中國人、傳播者和受眾雙方思想在交流過程中有接觸、有交鋒,更有促進與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對雙方職業教育思想的升華與實踐都有所啟發。杜威曾在即將離開中國之時說:“這兩年是我生活最有興味的時期,學得也比什么時候都多。 中國是一個教育的國家,外來人能在知識上引起好奇心,感情上引起好理想,并且也能引起同情心,故到中國來旅行者很是有益”[19]。
隨著國內外職業教育交往的頻繁,中國當時的職業教育與國外新思想新理論不斷碰出火花,促進了中國職業教育與國際的接軌,使得中國職業教育學人明確地意識到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有必要參考世界各國職業教育發展的大體趨勢,激發了世界職業教育理論的碰撞與發展。
3.促進了中國職業教育理論水平的提升與實踐的變革。 民國時期,我國無論是個人生存發展還是關乎國民生計的社會發展都迫切需要職業教育,但是由于缺少辦學經驗、缺乏理論指導,職業教育開展得并不順利。一些回國的留學生主動承擔起這份責任, 積極把西方職業教育理論引介到國內,闡釋了職業教育的含義、目的等基本理論問題,使國人認識和了解了何謂職業教育、為何辦職業教育。他們還講述國外職業教育的實施過程,使接受并倡導職業教育的人士知道如何開展創辦職業教育。例如莊澤宜留美期間就撰寫了數十篇介紹美國職業教育的文章在國內發表,顧樹森通過江蘇教育研究會出版了 《德美英法四國職業教育》《職業教育表解》等專著。 這些文章和譯著為國人介紹了世界先進的職業教育思想,使中國傳統的實業教育逐步與世界先進的職業教育逐漸接軌,促進了中國職業教育理論的產生與更新。他們在對國外職業教育的不斷引介中,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職業教育的重要性并力行倡導職業教育,他們為中國職業教育體制從傳統到現代轉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促進了現代職業教育在我國生根發芽。
回顧中國職業教育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的每一步都有國外職業教育的影子,從洋務運動建立實業學堂,到頒布正式確立職業教育獨立體系的“癸卯學制”,再到女子職業學校的創辦,一次次國外新思想的引進,都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中國人對于職業教育的認知,促進了中國職業教育實踐的改革及理論水平的提升。
(二)當代啟示
1.從傳播內容來說,要立足于中國職業教育實踐。杜威曾在我國作講演時說:“一國的教育絕不可胡亂摹仿別國”[20]。 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的職業教育政策和理念都不相同,職業教育的側重點和發展程度也不盡相同。西方職業教育理論在我國出現的一開始,就是為了彌補中國和西方之間的職業教育發展差距,就是為了推進我國職業教育的改革,為中國職業教育實踐尋找更多的理論指向。
近代西方職業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經歷了從零散到系統再到本土化發展的過程,廣大職業教育學人博采眾長、融匯中西,在職業教育領域進行了豐富的理論與實踐探索,各種職業教育理論兼容并包,異彩紛呈,逐漸走出了一條扎根中國大地的道路。 黃炎培先生曾在《怎樣辦職業教育》中講到“中國職業教育欲擺脫對西方職業教育學術研究的強大依賴性, 就必須考慮本民族的特點和需要,扎根中國實踐,開展職業教育學術研究”[21],但如果一味不加辨別地模仿,就只能是“邯鄲學步”。 新中國成立后,昔日國弱民窮的中國發生了煥然一新的歷史巨變,職業教育作為一種高度實踐性的教育類型,必須處理好理論與實踐、國內與國外的關系,在深入了解中國職業教育實踐的基礎上學習西方職業教育先進理論,充分考慮教育理論的連貫性與適用性,以理論滋養實踐,做到理論與實踐的深度融合。
2.從傳播者來說,要培養高素質的本土職業教育研究者。 在民國時期,進行職業教育理論傳播的傳播者有傳教士、商人、官員等各種類型,多樣的傳播者在中國職業教育學發展之初,受限于我國當時落后的經濟發展狀況,盡可能地利用各自渠道引進國外理論確系無奈之舉。但同時由于其專業水平的限制, 使得職業教育經驗的研究遠多于理論的研究,造成職業教育理論停留在表層泛泛而談。 中國職業教育學是舶來品, 學科理論至今尚未系統化,再加上外在依賴性較強,職業教育學的專業化程度一直不髙。 面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強大的文化抗震性使得我們必須考慮國外職業教育理論在中國的適應性問題,也就必須要培養具有專業素養的本土研究者。
目前我國職業教育理論引介雖然在前人的努力下邁出了堅實的步伐,但仍存在片面化、單一化等問題,引進、模仿、轉變也不再是傳播的重心。 當前中國職業教育學要想高質量持續發展,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這些都對我國職業教育理論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隨著世界職業教育的發展,我國職業教育理論的引進與傳播以我國實際為起點,積極培育職業教育內在力量,培養具有敏銳的問題意識和恰當的方法論的研究者,盡快增加反思與探索職業教育學的角度, 突破單一、封閉的思維方式,努力結合中國職業教育實踐,傳播并發展具有專業化的理論體系,從而在世界職業教育領域確立中國職業教育理論的話語地位。
3.從傳播效果來說,要更加強調理論的影響力。根據拉斯韋爾的“5W 傳播模式”來看,傳播效果是傳播的最終目的。跨文化傳播的效果指文化本身能得到受眾的認同,在受眾心里建立起正面積極的形象,并對受眾的價值選擇產生一定的影響。 教育思想的傳播是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傳播的最終目的是要達到文化的發展與創新。雖然在本質上中國與西方理論是一種雙向關系,但是在我國職業教育理論的發展在一開始是通過學習與模仿西方成長起來的,對大部分西方理論的傳播與研究往往是單向度的,中國學者花許多時間和精力大量地譯介西方各種職業教育理論,但并沒有引起中國教育學界的重視,更談不上西方社會的關注。 而中國職業教育要想發展,關鍵在于要以中國為中心進行創新。 一味地譯介西方理論著作而不加批判、不強調影響力,充其量不過是西方理論的信徒或代言人,也就不具備與西方國家平等交流和對話的資本。
回顧西方職業教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歷史可以發現,中國傳播者對于外國職業教育理論的傳播從未間斷,但是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許多游記甚至很多著作都沉寂在了歷史的長河中,最終沒有達到應有的傳播效果,使得職業教育學在教育學領域的影響力不大,中國職業教育學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甚微。這些都說明了職業教育理論的譯介與傳播要從傳播效果出發,要努力尋找并傳播對中國職業教育學建設的有效資源,不斷提高扎根中國大地的職業教育理論影響力,這樣才能凝聚與西方職業教育理論平等對話的資本,辦好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