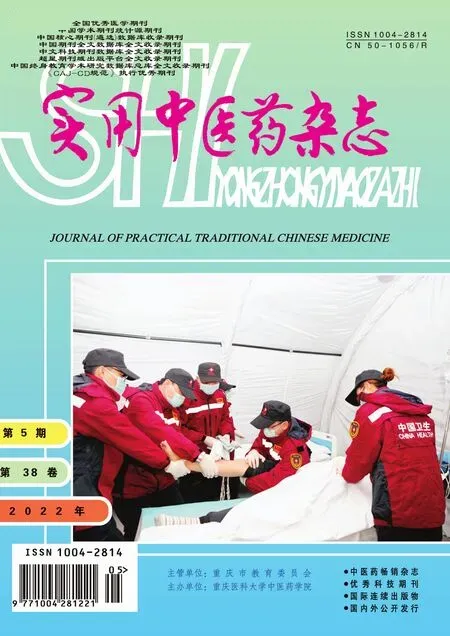血府逐瘀湯聯合前列地爾治療缺血性腸病臨床觀察
閆正超,紀文巖
(1.青島大學2015級在職碩士研究生,山東 青島 266071;2.青島大學附屬海慈醫院/青島市中醫醫院心血管一科,山東 青島 266071)
缺血性腸病(ischemic bowel disease,IBD)是由多種原因引起腸壁灌注不良而導致的缺血性腸道損害,早期臨床癥狀多見腹痛、腹瀉、便血等,持續加重者可出現腸壞死并發腸穿孔及腹膜炎[1]。IBD的主要病理基礎與腸道血管病變、血流量不足,凝血功能障礙有關,其發病率與年齡呈正相關,我國發病人群中老年患者占90%[2]。有研究表明,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及近期手術史為IBD的獨立危險因素[3]。IBD起病較急,常無特有臨床表現,加之部分患者因一過性病程并未就診,因此本病易誤診、漏診[4]。本研究用血府逐瘀湯聯合前列地爾治療IBD療效較好,現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共50例,均為2017年5月至2021年7月我院治療患者。均以腹痛為主要臨床表現,其中腹痛合并便血29例,腹痛合并嘔吐、腹瀉7例。合并腦梗死9例,合并高血壓病27例,合并冠心病17例,合并糖尿病11例,合并高脂血癥7例。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各25例。觀察組男13例、女12例,平均年齡(61.1±10.26)歲,平均病程(2.2±1.30)年。對照組男12例、女13例,平均年齡(60.4±8.23)歲,平均病程(2.1±1.21)年。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納入標準:符合缺血性腸病診斷,具有腹痛、腹瀉、嘔吐、便血等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中血漿D-二聚體升高,便常規隱血陽性,結腸鏡及腹部CTA提示IBD。簽署知情同意書。
排除標準:炎癥性腸病、腸道腫瘤、感染性腸病,合并嚴重的心、肝、肺、腎疾病,患有其他重大疾病無法配合治療,不同意簽署知情同意書。
2 治療方法
兩組均予禁食,抗感染,積極治療原發病,營養支持等治療。另用前列地爾10ug溶于0.9%氯化鈉注射液,靜脈滴注,每日1次。
觀察組加用血府逐瘀湯。桃仁12g,紅花9g,當歸9g,生地黃9g,川芎6g,赤芍6g,牛膝9g,桔梗5g,柴胡3g,枳殼6g,甘草3g。水煎服。
兩組療程均為14天。
3 觀察指標
檢測血漿D-二聚體,正常值<500μg/L。
參照Baron內鏡評分標準[5]制定IBD結腸鏡評分:正常黏膜計0分,黏膜充血水腫而無糜爛、潰瘍及出血計2分,黏膜充血水腫伴散在糜爛、潰瘍計4分,黏膜充血水腫嚴重、潰瘍及糜爛明顯計6分,黏膜顏色顯現出暗紫色、形成大片潰瘍和斑片狀出血計8分。
用SPSS25.0軟件分析,計量資料以(±s)表示、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4 療效標準
臨床治愈:臨床癥狀及體征消失,結腸鏡檢查無異常,大便常規檢查及隱血陰性,D-二聚體水平恢復正常,停藥7天內無復發。好轉:臨床癥狀及體征基本消失,結腸鏡檢查示結腸黏膜充血水腫消失、糜爛或潰瘍面減小,大便常規檢查及隱血陰性,D-二聚體水平降低。無效:臨床癥狀、體征及結腸鏡無改善,大便常規隱血持續陽性,D-二聚體水平未降低甚至持續增高,需轉外科治療。
5 治療結果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見表1。

表1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例(%)
兩組治療后腹痛消失時間比較見表2。
表2 兩組治療后腹痛消失時間比較 (d,±s)

表2 兩組治療后腹痛消失時間比較 (d,±s)
images/BZ_46_224_843_1193_1071.png
兩組治療前后血漿D-二聚體水平比較見表3。
表3 兩組治療前后血漿D-二聚體水平比較 (μg/L,±s)

表3 兩組治療前后血漿D-二聚體水平比較 (μg/L,±s)
組別 例 治療前血漿D-二聚體水平治療后血漿D-二聚體水平 P觀察組 25 753.1±178.11 169.8±131.72 <0.05對照組 25 748.3±139.57 332.6±250.10 <0.05 P>0.05 <0.05
兩組治療前后結腸鏡評分比較見表4。
表4 兩組治療前后結腸鏡評分比較 (分,±s)

表4 兩組治療前后結腸鏡評分比較 (分,±s)
組別 例 治療前 治療后 P觀察組 25 5.4±1.38 1.0±1.17 <0.05對照組 25 5.2±1.29 2.1±1.87 <0.05 P>0.05 <0.05
6 討 論
IBD是由于腸壁缺血缺氧而導致的急慢性炎性病變,主要表現是腹痛和便血。中醫學對于缺血性腸病并無明確記載,觀其癥狀,可歸為“腹痛”或“便血”范疇。IBD多發生于有心腦血管疾病的老年患者,老年人臟腑氣機衰減,氣虛運血無力,使血行瘀滯,或久病入絡,血脈瘀阻,血行不暢。一方面血行不暢、血脈瘀阻致使血不循經而出血,而離經之血若未能及時排除,會蓄積體內形成新的瘀血,妨礙新血生成及氣血正常運行。IBD的中醫辨證為氣虛血瘀。血瘀或出血為標,氣虛為本。由于IBD起病較急,急則治其標,故而治療應以活血化瘀為首要原則,瘀血去而新血自生,新血生而癥狀自除。
血府逐瘀湯首見于《醫林改錯》,具有活血化瘀,行氣止痛之功。由桃紅四物湯合四逆散加牛膝、桔梗而來。方中桃仁破血逐瘀兼能潤燥,紅花祛瘀止痛,赤芍、川芎活血祛瘀,生地黃、當歸清熱涼血、養血潤燥,桔梗、枳殼一升一降善于調理氣機,牛膝活血通經、引血下行,甘草調和諸藥。全方有活血不傷陰,理氣不傷氣之效。研究證明,血府逐瘀湯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發揮作用:①抑制炎癥反應:可以降低血漿中超敏C反應蛋白、白介素、腫瘤壞死因子等炎性指標的濃度,抑制炎癥反應[6-7]。②調節血脂:降低家兔血清總膽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全血黏度(高、中、低切)以調節血脂、改善血液流變學[8]。③抗血小板凝集:降低血清內皮素、血管性血友病因子、血小板α-顆粒膜蛋白的水平,從而達到抑制血小板活化,改善血栓前狀態的作用[9]。
D-二聚體是纖維蛋白降解后的特異性產物,對檢測血栓及其溶解過程具有重大意義。王康康等[10]通過對IBD患者,非IBD患者及健康者的血漿D-二聚體進行比較,發現IBD患者組明顯高于另外兩組,且特異性達到97%。周洪美等[11]對IBD患者和健康者急性期(第1天)、亞急性期(治療第7天)和恢復期(治療第14天)的血漿D-二聚體進行檢測,發現急性期IBD患者血漿D-二聚體水平明顯高于健康者,且D-二聚體的濃度與患者的病情變化及嚴重程度相關。因此可以認為血漿D-二聚體在IBD的診斷與病情判斷中具有重要意義。但現有研究中樣本量都較少,可能存在誤差,還需進一步加大樣本量來證明血漿D-二聚體在IBD中的診斷意義。
血府逐瘀湯聯合前列地爾可以縮短腹痛消失時間,降低血漿D-二聚體水平,降低結腸鏡評分,臨床療效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