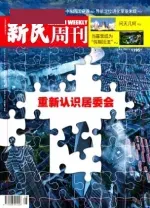社區工作者面對的現實問題
王煜

2021 年11 月19 日,來自北外灘街道的優秀選調生、北外灘街道社區工作者、青年志愿者參加“彩虹俱樂部世界咖啡屋”青年議事會。
2022年春季的全域封控,不僅讓上海的居民重新認識了居委會,還更多地接觸了“社區工作者”這個名稱。
社區工作者到底在做什么,他們和“社會工作者”有什么聯系?為什么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走上社區工作者的崗位?他們能否當好居民身邊“最親近的人”?
社區工作者,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22年7月最新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2022年版)》社會公示稿中,被歸類為“村和社區工作者”,定義是“從事村和社區黨建、治理、服務工作的人員”。在現實中,人們最常接觸的社區工作者一般就是走進居委會能見到的工作人員,包括居民區書記和居委會成員。
在現實中,人們最常接觸的社區工作者一般就是走進居委會能見到的工作人員,包括居民區書記和居委會成員。
1985年出生的高晶晶是上海市徐匯區龍華街道上縫新村居民區黨總支書記,她已有十余年的社區工作經歷。“我還在讀大學時,就擔任了家里所在居民區的團委書記,協助居委會做了一些工作,對社區工作者有所了解。”因此,在大學畢業之后的第二年,她通過徐匯區的社區工作者招聘,先是到龍華街道辦事處的辦公室崗位工作了兩年,后來又應聘當時的“專職黨群工作者崗位”,開始進入居民區工作至今,上縫新村已經是她任職過的第三個居民區。在她看來,對社區工作的熱忱,是她選擇這份職業的初衷,也是一直以來的動力。
與高晶晶這樣的“原生”社區工作者不同,1981年出生的王奕萍到龍華街道龍南五村居民區工作之前在企業擔任高級銷售,后來考慮到就近照顧家中老人,3年前應聘了社區工作者。比她早一年多到這個居民區工作,如今擔任居委主任的張艷有類似經歷:1976年出生的她,之前擔任外企的銷售部門管理人員,工作忙碌經常需要出差;后來因為家中老人生病需要照顧、孩子也需要撫養,做了幾年全職太太后,選擇成為一名社區工作者。
社區工作者的崗位要求中,對戶籍或實際居住地要在本居民區的轄區范圍內有明確規定。這種“屬地化”原則可以讓社區工作者擁有與社區的天然情感連接和一定的了解,同時必然讓“離家近、方便照顧家人”成為一部分人最初選擇崗位的動機。這也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如今社區工作者中女性居多的現狀。
“2014年上海市委‘一號課題’發布了“1+6”文件,也就是‘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的系列文件,很大程度上就是推進社區體制改革,強調社會治理的重心在城鄉社區、核心是人。其中有專門的一個文件對社區工作者的界定、職責、管理、待遇等各方面做了比較詳盡的規定。”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工作系副主任、副教授徐選國告訴《新民周刊》記者。他說,在“1+6”文件逐步落實后,社區工作者的待遇逐年提高,較以往有了顯著提升。
據報道,2019年浦東新區社會工作者指導薪酬基數為8211元/月;黃浦區2020年為9000元/月,寶山區從2020年7月開始調整為約9200元/月。待遇數額每年會根據情況進行動態調整。
“1+6”文件之后,上海社區工作者普遍年輕化、學歷層次也提升明顯。高晶晶說:以前,社區工作者里還有不少從退休人士返聘回來的“阿姨爺叔”;而當前,社區工作者的出生年份集中在1975到1985年的區間,并且“90后”已經逐步登上舞臺。
徐選國觀察發現:近幾年,各區面向高校畢業生招聘社區工作者成為趨勢;同時,越來越多社會工作專業的大學生畢業后到社區工作。這讓社區工作者招聘的競爭性越來越強,近些年有的社區工作者崗位報名和錄取比例達到20:1,有的甚至達到將近50:1。
他還發現:有一部分在社會組織從事專業服務好幾年的社會工作者,也選擇考入社區工作者崗位。在他看來,社區工作者的隊伍將越來越年輕化、專業化,他們掌握的理念、方法可能逐漸推動傳統社區工作模式的變革與創新。
“工作比較穩定,也比較輕松”,這是王奕萍在入職之前對社區工作者的想象。然而,當她真正開始這個崗位的工作時,發現和想象有很大的差別。2019年8月她在龍南五村居民區入職,負責衛生條線的工作,推行垃圾分類成為重頭任務。“工作量真的是滿滿的,和‘輕松’二字完全不搭界了。”后來新冠疫情暴發,居民區防疫的重任一直延續至今,她和居委同事們的超負荷工作已成常態。當初想著“照顧自家”,最終“以社區為家”。
在很多社區工作者看來,實地走訪轄區內的居民,面對面地了解他們的情況、幫助他們解決問題,這應該是社區工作的重要內容。“不能只在微信群里發發通知,那樣是沒有感情的,何況還有不少老人不會用微信。”例如,龍南五村和上縫新村都是戶數2000多、人數近4000的大居民區,而社區工作者只有六七名,平均每人要負責聯絡300多戶居民,即使是重點走訪,也是相當耗費時間精力的。“有的居民需要我們上門走訪很多次,他才會熟悉我們、建立起對我們的信任。”高晶晶說。
然而在實際中,社區工作者往往要應對來自上級各個政府部門大量的評比、檢查、督查等事務性工作,要花很多時間在搜集各類數據、填寫各種表格上,用于走訪居民的時間被大大壓縮。“有的居民說:你們怎么總是在敲電腦、玩手機呀?可我們真的不是在玩,我們也不想一直在填表啊。”一名社區工作者無奈地向《新民周刊》記者表示。
最讓他們有挫敗感的,還在于這些數據報送或臺賬工作常常是重復性的,各個部門之間問居民區要同樣的數據,同一個部門也會在短期內讓居民區報送好幾次一樣的信息。而且,這些信息的填報平臺,有的必須在電腦上操作、有的在手機App上、有的在小程序里、有的要做成表格文件……社區工作者不得不在十幾個平臺間來回切換。數字化并未帶來工作的高效,反而增加了社區工作者的負擔。
“上面千條線,底下一根針”是前些年人們常用來形容社區工作者狀態的話語,從“1+6”文件以來,上海各級政府也在嘗試為社區“減負”,但似乎效果并不明顯,有的社區工作者還發出了“這幾年負擔是越‘減’越多”的感慨。
事務性工作太多,服務居民的時間必然就會減少。這種矛盾在平時可能還不明顯,但在2022年春季上海因新冠疫情采取的全域封控中,社區工作者和居民之間的矛盾集中爆發。部分居民認為社區工作者“不接地氣”,而社區工作者為轉運陽性感染者、消殺環境、組織核酸檢測、為居民配藥、發放生活物資等,往往已竭盡全力、心力交瘁。龍南五村是龍華街道最早開始封控的居民區。“2022年3月16日到5月31日,我和書記、主任助理三個女人就住在居委的一間小屋子里,抗疫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在一起抱頭痛哭,哭完了還是繼續工作。”張艷回憶那段日子時表示,雖然有不被理解時的痛苦,但每當自己的付出得到居民的認可,她們心中又總是充滿了感動,獲得價值的認同。
長時間的全域封控是一種特殊狀態,它把社區工作者和居民之間的關系處理推到了再也無法回避的焦點。徐選國表示,他走訪了大量的社區工作者,感覺他們目前時常處于一種“疲態治理”之中,永遠沒有盡頭地做著瑣碎的事情。“非常規狀態下社區工作者全力維護著社區大眾的安全,如果回歸常態化階段,應該大量減少他們日常化的行政事務,讓社區工作者回歸社區、回歸生活、回歸與社區居民大眾緊密連接的生活情景中來,讓他們與居民真正朝向建設社區生活共同體的方向努力。”

疫情期間,6337a3bebfdc17b2d8cb2dc14e37b015張艷(左)在崗工作。
職業上升通道的局限,也是社區工作者隊伍發展面臨的現實問題。高晶晶當年應聘的“專職黨群工作者”,給出了“在社區工作滿6年且考核優秀后可以轉為事業編制”的政策,但如今這樣的機會已不再有了。目前,從一般的崗位開始,社區工作者可以升為居委副主任、主任,或者擔任居民區副書記、書記,但這些職位并不對應任何事業編制,僅書記可以享受參照事業編制的待遇;他們也無法直接被提升到行政體系中去。
“我們還是希望能再對優秀的社區工作者開放一些對應的事業編制,或者讓社區工作經歷成為他們將來自行考取公務員之后能被實在認可的基層工作經驗,這樣有助于提升社區工作者崗位的吸引力。社區工作確實還是需要更多優秀的人才加入的。”高晶晶表示。
盡管編制方面難以突破,但社區工作者仍然可以通過學習培訓來增強專業技能。近年來,各地都為社區工作者組織培訓,鼓勵他們考取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證書。社區工作者常自我簡稱為“社工”;不過在高校、社會組織等領域,“社工”對應的含義一般是社會工作、社會工作者。
有效整合社區志愿者的力量,同樣是社區工作者要考慮的關鍵問題。
這兩個“社工”既有區別也有聯系。社會工作者工作的場景不只在社區,而且更加專業化;而社區工作者在實踐中經常需要運用社會工作的理論與技能,在他們通過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考試后,也可以同時成為持證的社會工作者。
已經獲取中級社會工作師證書的高晶晶認為,掌握社會工作的能力,可以讓自己的社區工作更有持續性,更成體系。而正備考助理社會工作師的王奕萍也表示,社會工作中的一些原則和案例,對處理實際工作提供了幫助。
除了自身成為有資質的社會工作者,與來自第三方專業社會組織的社會工作者合作,也是社區工作者突破自身瓶頸的有效方法。非常實際的一個問題是,《居民委員會組織法》中規定居委成員人數只能在5—9人,那么即使加上書記、副書記,一個居民區的社區工作者崗位最多在10人左右,而現實中上海的居民區常見的配備在六七人。人數太少,而要完成的服務居民的工作太多,就必然要靠整合不同領域的力量來補充。

2021年度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考試上海莘城學校考點。
當前,中央為基層治理設計的機制是“五社聯動”,包括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社區志愿者和社會慈善資源。其中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者是其中的關鍵組成部分。“像老居民樓加裝電梯這樣的社區事務,我們就引入了第三方的社會組織,他們的社會工作者,能為居民提供非常細致到位的咨詢服務。社會工作者對居民區里困境群體的幫助,也實實在在為我們分擔了許多工作。”張艷說。
有效整合社區志愿者的力量,同樣是社區工作者要考慮的關鍵問題。上海的全域封控中,志愿者為社區做出了巨大貢獻。“我們驚喜地發現,那些封控中涌現出來的年輕志愿者,并沒有很快散去,而是持續地在為居民區服務。”王奕萍說,現在每周的例行核酸大篩工作里,依然有不少年輕志愿者特別活躍。工作日晚上的篩查,他們一下班就往小區里趕,連飯都顧不上吃;周末早上的大篩開始得很早,他們也放棄難得的睡懶覺的機會,總是準時上崗。“我想,抗疫的‘大考’讓他們與我們互相了解與理解,以后我們也一定會和他們緊密合作,讓他們成為服務社區的中堅力量。”
近年來,民政部還在全國推進鄉鎮(街道)社工站建設,這里的“社工”,指的是社會工作者。截至2022年6月30日,全國已建成鄉鎮(街道)社工站2.1萬余個,5.3萬余名社會工作者駐站開展服務,七個省份實現了鄉鎮(街道)社工站全覆蓋,17個省份覆蓋率已超過50%,全國覆蓋率達56%。
“民政部推進的社工站建設,最直接的目的是為了補齊全國基層民政力量薄弱短板、實現民生兜底保障的功能,而這種普遍性的社工站角色和職能在上海基層治理中已經得到較好的實踐了。”徐選國認為,上海的社工站建設定位應該是發揮資源整合平臺作用、精準輸送社會服務領域的“高精尖服務”、積極應對社區的復雜治理議題。
在徐選國看來,如果能推動高質量社工站建設且崗位薪酬有競爭力的話,那么,它對目前社區工作者中持有中級社會工作師證書且具有豐富工作經驗的人員而言是一個好去處。進入社工站,同樣能為社區服務,彰顯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