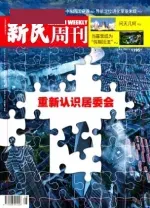在上海:沒名字的歌無名字的你
鄭渝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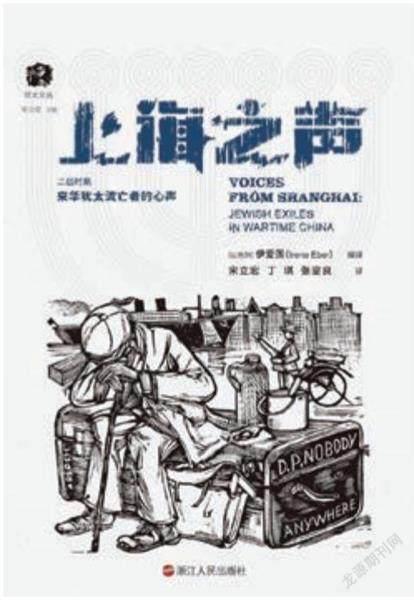
浙江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了納粹大屠殺幸存者、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東亞研究講席教授伊愛蓮主持編譯的《上海之聲:二戰時期來華猶太流浪者的心聲》一書。這本書的文字取自檔案館、私人收藏與20世紀三四十年代猶太社團在上海主辦的報刊,記述了在滬猶太難民的心聲,文體包括信件、日記、詩歌和短篇故事,再現了他們艱難跨越語言文化、信仰體系和民族傳統的障礙而努力謀生的心路歷程。
書中收錄的文字的作者大多名不見經傳,其作品也無法做到所謂“載入史冊”,但這并不能因此下結論說他們的記述沒有意義。
他們記錄了那個時期一個復雜的上海。上海是當時世界上最錯綜復雜的都市社會(著名歷史學家魏斐德語)。自鴉片戰爭后,上海開埠以來,當地發展為一個擁有數百萬人口,聚集著50多個國家居民的都市。
俄國十月革命以后,就有猶太人遷徙到了上海,到了20世紀30年代,其規模已達6000—7000人。
猶太人在當時的上海辦報,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上海擁有龐大的中外文出版業,本身就有報刊行業;而上海的電影業當時也相當發達,居民已經習慣去電影院收看國產新片以及引進的好萊塢大片。再加上咖啡館文化,這讓猶太人能夠快速地融入到上海的市民文化之中。《上海之聲:二戰時期來華猶太流浪者的心聲》書中列舉談到,安妮·維廷在書信中說,“只要掙錢多,就能在上海過上歐式生活,而忘掉這里是亞洲。上海有最漂亮的公寓,這里有別墅、公園、劇院、電影院、音樂會、藝術家,還有帶屋頂花園的美式百貨商店”。
1937—1938年,上海的實際控制已經轉為日本,但在1941年12月之前,工部局仍然是租界的管理者。工部局一定程度上試圖阻撓猶太難民進入。而猶太人只能尋求規則的漏洞。
進入上海的猶太難民迅速營造了包括出版、戲劇和廣播在內的文化生活。這顯現了猶太人的文化創造力,以及上海民眾對他們的包容性。猶太難民相當程度上為上海的多元性所感嘆,埃貢·瓦羅在《是的,那就是上海》詩中宣布“現在我們(也)在此處”。猶太難民多聚集在虹口地區,當地在1937年曾被日軍猛烈轟擊,因而需要重新修繕、改建和重建,猶太難民不無樂觀地建起了或恢復了出租公寓、咖啡館、餐廳,重現了虹口的咖啡館文化。
這種戰爭中的“穩態”繁榮,隨著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宣告結束。大部分猶太報紙停刊,在滬的許多猶太記者因而失業。而猶太社團之間的勾心斗角也削弱了這一族群的創造力和適應性——在滬的猶太人、猶太社團之間發生矛盾,其實也不難解釋,許多猶太人較早到來,屬于俄國或伊拉克籍;而陸續到來的原籍德國或波蘭的猶太人,彼此之間必然難以抑制矛盾的生發。
書中收錄的許多文字,對中國,特別是對上海民眾飽含深情。約斯爾·莫洛泰克在《上海》一詩中直言不諱地說,相較于猶太難民,日占狀態下中國,老百姓苦苦煎熬,處境更加艱難。詩作中描繪了公共租界的心臟地帶南京路到處是廣告、酒吧和燈飾,還有拉黃包車的苦力,但這只是為富有的中國人、為西方人而設的,也是為當時占領上海全境的日本人而設。對于苦力為代表的中國底層民眾而言,無論跑得多快、多么勤奮,都始終處于一個饑餓的狀態。
這是一本由19世紀英國著名鳥類學家約翰·古爾德及其團隊繪制的中國鳥類圖鑒。
此書整理收錄了古爾德繪制的519種中國高清鳥類手繪插圖,跨越時空,再現一百多年前古爾德畫筆下中國鳥類的靈動與優雅。為使其更符合現代科學分類體系,中國林科院濕地研究所劉剛、廣西科學院朱磊,根據現代鳥類分類系統,對古爾德繪制的這些中國鳥類分目重新編排,修訂每個物種的中文名、學名、英文名、科屬種信息、分布范圍、保護級別等,使其兼具藝術與科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