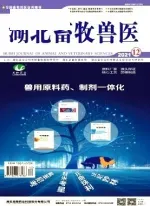流域橫向生態補償機制的問題與對策
——以徐州黃河故道為例
鮑俊含,劉欣妤
(江蘇師范大學,江蘇徐州 221100)
流域橫向生態補償機制是以達到全流域生態、經濟、社會效益可持續發展為目的,綜合各方力量,結合地方實際,協調參與到流域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的各方利益的一種制度安排[1],在上下游之間建立一個共同承擔保護治理成本,共享經濟生態效益,達到共治共贏局面的機制。
由于水的流動性,流域的上下游從本質上說是一個整體,而上游的生態環境通常比較脆弱,保護要求高,治理難度大,因此上游常常無法獨自負擔治理保護的費用;下游經濟一般比較發達,雖然本身也會有一些水質污染等環境問題,但是相較于上游,治理難度較小,并且生態環境也比上游更加堅韌;被嚴重破壞的上游生態環境會給下游發展帶來很大影響。所以,通過采用流域橫向生態補償機制的方法來加以協調,上游治理保護的一部分費用由下游來負擔,減輕了上游治理的經濟壓力的同時還可以帶動上游地區的發展;同時,上游地區要賠償下游地區,從而彌補由于上游生態環境惡化導致下游地區的損失。采用建立流域橫向生態補償機制的辦法,可以進一步督促流域上下游地區共同擔起流域水環境的保護和治理責任,同時還都能獲得一定的補償,使上下游都愿意為了流域的美好生態環境而努力,進而推動流域內的生態、經濟、社會效益的可持續發展。
1 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意義
建立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主要是改善流域水環境質量、促進區域經濟協同發展、加強地方政府協作等方面,以期從根本上實現流域內生態、經濟、社會效益的可持續發展。
1.1 改善流域水質
改善流域的生態環境是建立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直接目的,生態補償協議由流域上下游間共同商議建立,通過上下游間同心同力的合作治理以及相互補償,流域水環境質量會得到明顯改善。
2018 年2 月,云南、貴州、四川三省共同簽訂建立赤水河流域生態補償機制協議。赤水河流域總體水質狀況為“優”,流入長江的水質連續3 年保持在Ⅱ類水平,全流域水質穩定在Ⅲ類水平及以上,從根本上提高了流域水環境質量,使得百姓喝水放心,用水安心,切實保障了赤水河流域居民生活水平。
1.2 經濟協同發展
通過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部分下游企業會投資上游的相關行業,既可以幫助上游企業發展也可以使自身發展獲得更好的生態效益,從而促進收入穩步增長,實現生態、經濟和社會效益共贏的局面。例如在赤水河流域,存在中國貴州茅臺酒廠(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這樣的大企業,同時也存在全國著名貧困縣鎮雄縣。在2018 年,中國貴州茅臺酒廠(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等5 家赤水河流域下游的企業共同抵達鎮雄縣進行捐款,對赤水河源頭居民保護赤水河生態環境做出的努力貢獻表示感謝,這正是生態補償行為。同時,四川郎酒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還采取了一系列行動,比如設立郎酒生態與自然保護基金、投資吳家溝生態釀酒區,既能夠延長自身產業鏈,提升產業品牌形象,又促進了赤水河流域周邊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幫助上下游經濟、生態協同發展。
1.3 加強地方交流
2016 年財政部、環境保護部、發展改革委員會、水利部共同制定了《關于加快建立流域上下游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指導意見》,指出“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主要由流域上下游地方政府自主協商確定,中央政府對跨省流域建立橫向生態保護補償給予引導支持,推動建立長效機制”[2]。可見,中央政府在推動各流域橫向生態補償機制建設過程中,采取的并不是“一刀切”策略,而是做到將權利下放,要求地方政府之間相互協調、相互配合,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加強地方政府之間的交流,接受公眾監督,共同承擔責任,為實現流域的可持續發展而共同努力。
2 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應用
各地紛紛建立起了流域橫向生態補償機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浙江省在2005 年頒布《關于進一步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的若干意見》,首先進行了錢塘江流域的試點,取得成功后,于全省范圍內開展生態補償機制建設,成為了中國第一個在全省范圍內開展生態保護補償的省份;2008 年1 月,江蘇省頒布了《江蘇省太湖流域環境資源區域補償試點方案》,以污染環境者進行賠償、破壞生態者進行賠償的方式,建立了環境損害補償機制;2012 年,安徽、浙江兩省頒布了《新安江流域水環境補償試點實施方案》,這是全國首個跨省建立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方案,自該方案實行后,新安江流域水質連續9 年都能達到補償考核標準,千島湖地表水水質也始終達到Ⅰ類標準,該方案還給其他省份跨省建設流域橫向生態補償機制提供了寶貴經驗;2018 年4 月,重慶市頒布了《重慶市建立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實施方案(試行)》,對于全市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建設進行總體規定和系統設計,并選取若干個流域進行試點,建立起讓保護者受益、受益者付費的生態補償機制。2021 年5 月,河南省與下游山東省簽訂了《山東省人民政府河南省人民政府黃河流域(豫魯段)橫向生態保護補償協議》,這是在黃河流域建立跨省流域橫向生態補償機制的首個協議,協議要求根據水質的不同標志要求以及水質的變化情況給予不同標準的補償。
3 徐州黃河故道橫向生態補償機制實施情況分析
流域橫向生態補償機制已經在較多地方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就各個地方而言,仍然存在不足之處,為探索生態補償機制在小流域水資源的適用效果,以徐州黃河故道為例進行分析。
3.1 徐州黃河故道現狀
黃河故道自1855 年后一直沒有貫通,所以被稱為“廢黃河”,盡管經過了多次治理,但始終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水質令人擔憂。黃河故道貫穿整個徐州市,其生態環境關系到周圍居民生活水平以及整個徐州市的形象。黃河故道的生態環境并不容樂觀,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水源不足,水質較差。因為黃河故道在徐州范圍內流速較慢,加之堤壩較高,兩岸水流不易匯入,水量較小;同時沿途還會接收違規排放的工農業廢水和生活污水,尤其是沿著黃河故道建設綠色走廊,興起農業小鎮等旅游點,排放污水增多,使流域水質更差。
二是河道的淤積情況嚴重。河道的平均淤積深度已經達到1.5 m,導致河流流動不暢,防洪標準偏低,甚至無法抵擋5 年一遇洪水,已經違背了當初將黃河故道打造為市區主要防洪排澇河道的目標。
三是河道連通性較差。徐州在黃河故道多設梯級式控制的水閘,將連續的水體分隔成眾多河段,河段之間難以連續流動,遇到緊急情況需要開閘才能放水,再加上黃河故道橫斷面變化大,河道彎曲,水流紊亂,導致故道連通性較差[3]。
3.2 徐州黃河故道在實施生態補償機制中的問題
徐州黃河故道的生態問題突出,生態保護壓力大,生態治理難度大。因此,在國家政策的號召下,建立因地制宜的生態補償機制,是推進徐州黃河故道流域保障、改善民生的重要舉措。然而,在建立與實施因地制宜的生態保護補償機制過程中,其補償主體、補償標準、補償方式等存在無法滿足小流域生態問題治理方案可持續性的問題。
3.2.1 政府間區域協作性低 徐州黃河故道涉及的區域范圍廣、人口多、經濟發展差異大,治理黃河故道流域生態問題是一個大工程。由于徐州黃河故道流經4 縣(市)5 區,涉及到上下游間跨區域、跨地方政府的協作治理。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需要地方政府之間協商來實現利益互補。然而,對于地方政府來說,驅動工作開展的重要原因是上級政府的指示與地方利益。由于不同區域,特別是上下游間的利益訴求差異較大,對于流域保護的行動意識也存在較大差異。地方政府間從各自角度出發的利益考量也為溝通交流建立了一堵無形的圍墻,間接導致了區域協作性低。
黃河故道流域上下游涉及的各縣(市)、區地方政府間沒有達成統一調度的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實施方案,沒有秉承“共建、共商、共享”的發展理念建立黃河故道流域生態保護補償平臺。除此之外,徐州市對于生態保護補償機制重視程度低、實施力度小。地方政府專項財政資金中可直接用于生態保護補償的占比較小,實施難度大。
3.2.2 政企間利益矛盾顯著 徐州黃河故道流域分布多個省級工業園區。由于地方政府治理生態環境必然會觸及企業、工廠的利益,引起政企之間的利益矛盾。對參與市場競爭的企業來說,考慮到治污成本較高,逃避其生態責任成為了普遍現象。
徐州黃河故道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還不完善,導致流域上下游的責任承擔差異大。上游的治理壓力較大,生態責任和生態保護意識不主動、不積極;而對于下游來說,大多依賴上游的生態治理成果,負擔的生態責任較小。上下游的責任承擔差異也導致區域間政企協作治理的效能較低,且易產生政企之間、上下游企業之間的信任危機與利益沖突。
除此之外,為保障地方財政收入,一些地方政府對于追求高效益但無視高污染的企業持放任態度,地方保護主義盛行。這也進一步加劇了政企間的利益矛盾,不利于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實行。
3.2.3 生態補償標準不科學 由于未建立統一的生態保護補償平臺,生態保護補償主客體在不同補償層面不一致,復雜的補償關系難以厘清,環境賬、經濟賬難以算清,致使黃河故道流域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落實受限[4]。
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標準科學性不足,其計算主要指標為損失的水量或水質,對于損失的水資源的生態功能價值未做量化分析。在估算損失水量或水質時,由于流域面積廣所導致的地方政府相關部門監管不力、數據來源復雜等也降低了補償標準科學性。
3.2.4 生態保護補償意識缺乏 在徐州地區,政府與公眾的生態保護補償意識缺乏,導致實施難度較大。地方政府對于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相關理論僅停留在文件綱領層面,深入了解程度低。同時,大部分公眾對于生態保護補償的意義、方式等不了解,導致公眾的監督工作參與度較低。
4 解決對策
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手段之一。徐州黃河故道流域生態保護補償范圍廣,地方政府協作性低,涉及的相關利益者多,既需要政府投入專項財政資金支持生態建設,又需要地方政府之間、政企之間的區域協作治理與公眾的監督。徐州黃河故道流域生態保護補償需要因地制宜,以亟待解決的問題為突破口,從而保障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實施。
4.1 明確區域協作下的政府責任
徐州市將市區河道管理處與黃河風景管理處合并,成立統一的市區主要河道管理機構,各區(單位)也相應成立河道管理所[5]。在此基礎上,設立有權利協調地方政府間協作治理的政府部門,或是賦予其實際職權,并建立相關法律條文體系進行支撐,避免在流域保護上出現各自為政的局面。
4.2 建立因地制宜的科學生態保護補償機制
政府要摒棄過去傳統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生態修復模式,轉變為“預防與治理并重”的態度。在此基礎上,研究分析全國范圍內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先進案例,結合徐州黃河故道流域的基本情況,因地制宜地開展地方政府主導的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相關理論研究工作,以期實現其生態可持續性。
相關部門要參考流域內區域和企業間的差異性,可溯源地獲取流域內生態基礎數據,建立科學的生態價值評估和生態保護補償標準體系,進一步明確橫向生態保護補償的主客體,確定補償對象與補償方式,客觀、科學地實施流域內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方案。
4.3 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的法律保障
生態環境問題是社會問題,也是法律問題。要在現存的法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環境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指導下,制定符合徐州黃河故道流域的支持跨區域協作治理的地方法規,在生態保護補償標準、補償主體、補償對象等方面提出明確的、有針對性的細則,并以生態保護補償的上位法做支撐,以確保其實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