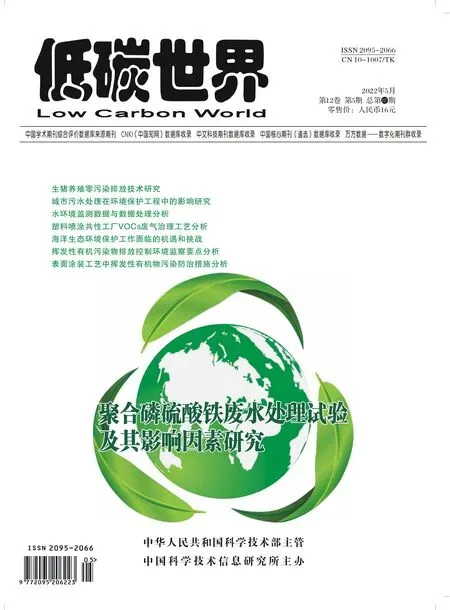山東省碳排放的空間演進與建議
郭 慶
(山東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0 引言
現有研究大多通過能源消費數據測算得到省域和城市數據來分析中國碳排放的時空格局,然而,即便在同一省(區、市),各縣域單元的碳排放也會存在差異。
本文采用中國碳核算數據庫(CEADs)中2010—2019年的省級能源清單作為參考,并以其中2010年和2019年的省級能源清單進行方差分析,為便于統一計算,本文僅選用萬噸標準煤為單位的能源進行計算。
1 山東省二氧化碳排放的區域差異
1.1 山東省二氧化碳排放的區域特征
調查分析2007—2017年期間山東省二氧化碳排放量環比增長率統計數據發現,山東省二氧化碳排放總體上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其中雖然存在起伏,但總體趨勢明顯。且城市之間碳排放增減步調相對統一,全省的碳排放存在一致性,說明城市之間的協調性較好。
1.2 山東省二氧化碳排放的區域差距及分解
本文通過泰爾指數及分解的方法測算了山東省二氧化碳排放的總體區域差異,并進行了分解(表1)。無論是山東省二氧化碳排放的總體區域差距,還是區域內差距、區域間差距大致上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過程中雖然存在一定的波動,但整體趨勢卻是很明顯的。在區域差距的來源上,區域內差距對山東省二氧化碳排放總體區域差距的貢獻率始終大于區域間差距。這一結果表明影響山東省二氧化碳排放的區域差距主要原因是區域內差距,并且在短時間內區域間差距無法超越區域內差距成為山東省二氧化碳排放地區差距的決定性因素。值得注意的是,1997—2017年的20年里,區域差距雖然呈現明顯的變化趨勢,但其變化規模實際上比較小,雖然我國是在2021年7月16日啟動中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上線交易,并在同年10月26日印發了《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但早在2014年的《中美氣候變化聯合宣言》中,我國就已經提出過2030年實現“碳達峰”的目標,但通過2014—2017年的數據來看,區域內差距作為區域差距主要來源的情況并未得到改善,區域內差距過大的情況仍然存在。如何平衡區域內差距,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仍是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大難題[1]。

表1 山東省二氧化碳排放的地區差距的分解
1.3 山東省能源結構方差分解
基于山東省能源的結構組成,本文利用方差分解方法計算了原煤、精煤、其他洗煤、煤球煤餅、焦炭、其他焦化產品、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油、液化石油氣、煉廠氣、其他石油產品、其他能源對山東省能源的貢獻率,如表2所示。通過表2可以看出,2010—2019年,原煤的貢獻率從57.89%下降到32.17%,而焦炭的貢獻率從25.25%上升到50.19%,取代了原煤的首要地位,相對于原煤,經過高溫煉焦處理后形成的焦炭,在供能和環保方面都更具有優勢。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煤球、煤餅的貢獻率從2010年的1.22%下降到2019年的0.61%,但其實際消耗量卻從527.22萬t上升至831.83萬t;柴油的貢獻率從2010年的3.76%上升至2019年的5.10%,但其實際消耗量卻從1445.17萬t下降到1251.31萬t。通過表2可以發現山東省本身的能源結構較為單一,2010—2019年近10年間的變化是主要能源從未處理的原煤轉變為經過處理的焦炭。而作為清潔能源的天然氣等卻使用較少。直接燃燒原煤會對環境造成巨大傷害,不僅會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同時也會釋放出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煙塵、放射性飄塵、氮氧化物等污染物,這些物質會直接危害人畜,導致生物機體癌變,產生酸雨,形成溫室效應。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初期就曾因為燃燒原煤付出過慘痛的代價,其中最為典型案例是20世紀十大環境公害事件之一——“倫敦煙霧事件”:倫敦在20世紀50—60年代大量使用煤炭等化石燃料,產生的廢氣和煙塵籠罩在城市上空造成嚴重的空氣污染[2]。

表2 2010—2019年山東省能源消費方差分析
2 山東省碳排放區域差異的影響因素
2.1 人均GDP
依據庫茲涅茨環境污染的倒U曲線可知,隨著人均GDP的增長,環境污染的程度會呈現先不斷加深,后逐漸下降的趨勢。通俗解釋,即在經濟發展水平低、人均收入水平低的時候,人們通常更注重物質生活而忽略環境因素,而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人們則更加重視環境因素。因此,人均GDP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水平、人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標,也是影響二氧化碳排放區域差異的重要因素。
2.2 人口因素
不同城市、縣域單元的人口規模、城市化水平、人口結構等不同,在城市化進程中,人口向城市遷移,非農業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不斷提高,而不同城市、縣域單元情況不同,因此,這也是影響二氧化碳排放區域差異的重要因素。通常情況下,非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越高,即城市化程度越高,二氧化碳排放就越高。人口素質也是影響一個地區二氧化碳排放的因素,人口素質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往往具有更好的環保意識,會選擇低碳生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選擇新能源汽車等環保行為。
2.3 技術發展水平
技術進步能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過去落后的高耗能、低產量產業。同時技術的進步也可以改善能源結構,例如,采用更為先進的開采技術,開采海洋中存在的大量可燃冰。而目前我國對可燃冰的開采仍存在許多問題,通過技術突破,以可燃冰、天然氣等清潔能源取代高污染的傳統化石燃料,可以有效減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煙塵的排放。據統計,90%以上的人為二氧化碳排放是由于消費化石能源造成的,可見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改善能源結構是當前亟須解決的問題。此外,對于風能、太陽能、地熱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效益也是影響二氧化碳排放區域差異的重要因素,不同地區對于開再生能源的重視程度、開發力度不同,而如果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將會產生推動能源結構升級的重要動力,推動實現2030年“碳達峰”的目標。因此,技術發展水平是影響二氧化碳區域差異的重要因素[3]。
2.4 產業結構
相對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在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方面都具有明顯優勢,而且第三產業的產出水平也較高,因此,不同城市、縣域單元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占GDP比重高低將會將影響二氧化碳區域差異。具體體現為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越高,則該地區二氧化碳的排放水平越高;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越小,則該地區二氧化碳排放水平越高。即使在第二產業內部,不同地區使用清潔能源的產業占總產業的比重的高低不同也會導致區域差異的出現。因此,產業結構也是影響二氧化碳區域差異的重要因素。
2.5 對外開放程度
對外開放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但對外開放促進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可能會帶來一系列的環境問題。目前,學術界關于對外開放的環境效應存在兩種相反的學術流派。一部分學者將對外開放視為對環境的積極因素,他們認為通過對外開放,東道國不僅可以學習國際先進環保技術,還能夠通過“干中學”、競爭等機制提高環境全要素生產效率,因為對外開放是有利于保護環境的。而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對外開放會對發展中國家帶來一系列的環境問題,因為發展中國家為了吸引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通常為高污染產業),往往會競相采取降低環境標準的方式,這將會導致一部分發展中國家成為發達國家的“污染天堂”。無論對外開放究竟是有利于環境,還是有害于環境,都表明對外開放水平是影響環境的重要因素,也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區域差異的重要影響因素[4]。
3 結語
本文依據山東省2007—2017年期間140個縣域單元的二氧化碳碳排放數據和山東省2010—2019年省級能源清單,采用泰爾指數分解和方差分析的方法,全面分析了山東省二氧化碳排放的空間分布、區域差異及其動態演進過程得出以下結論:①在20年的時間里山東省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期間雖有起伏,但總體上是呈上升趨勢,從32 043萬t上升至75 405萬t,年均上漲8.80%,隨后在75 405萬t上下波動,并沒有明顯下降的拐點。②山東省二氧化碳空間分布格局大致呈現東高西低的分布格局,東部的青島、煙臺、濰坊等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要高于西部的聊城、菏澤等城市,這與當地的對外開放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相關性。位于東部沿海地區的青島、煙臺等地區具有更好的區位優勢,對外開放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更高,另一個依據便是濟南,濟南的位置位于山東省的中西部地區,但由于濟南是山東省的省會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因此其二氧化碳排放水平較高。③在區域差異上,山東省二氧化碳排放在20年期間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并且總體區域差異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市級行政單元的內部差異是總體初一的主要來源,區域內差異的貢獻率穩定保持在79.6%~85.4%,占據絕對優勢地位,區域間差異對總體區域差異的影響相對有限。
——山東省濟寧市老年大學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