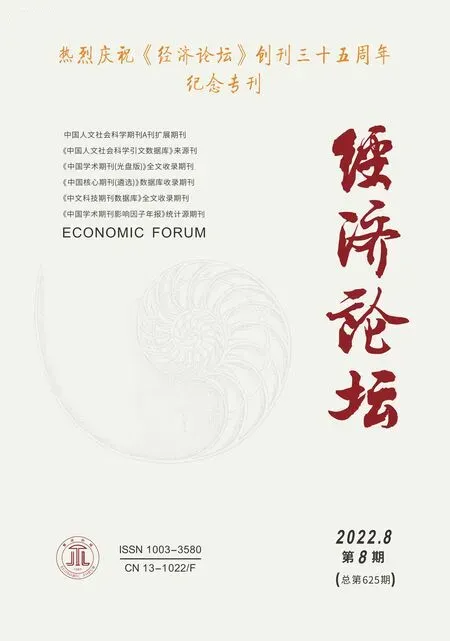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理論框架、國際經驗和政策建議
李勇堅
(1.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北京 100028;2.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北京 100102)
導言
中小企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占了全部企業數量的99%。新冠疫情的沖擊,推動很多中小企業加快了數字化轉型的步伐,實現了新的增長與發展。Bloomberg Media Studios and IBM(2020)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疫情對企業數字化起到了明顯加速作用。有研究機構指出,這種加速作用的影響將超過10年(Twilio,2020)[1]。這也導致了咨詢公司IDC在2020年時預測全球數字化轉型支出在2023年將達到6.8萬億美元[2],而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10月,IDC的預測數據僅為2.3萬億美元[3]。
中小企業的數量占據了全球企業數量的絕大部分,數字化的基礎較差,數字化轉型的潛力較大。2019年11月29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秘書長Angel Gurriá在全球中小企業數字化倡議的首屆圓桌會議開幕演講時指出,“沒有中小企業的參與,就沒有可持續的數字化轉型!”(Sandrine Kergroach,2020)。越南信息與傳媒部管理司副司長阮仲堂在2022年推進“協助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計劃”會議上指出,數字化轉型企業的產能與利潤比未進行數字化轉型企業多了一倍,全面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將為亞太地區貢獻超過3萬億美元的GDP,其中為越南GDP貢獻300億美元[4]。對新加坡2019年第一季度的經濟調查發現,采用數字工具的公司的價值平均提高了25%,生產力平均提高了16%[5]。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體現出了較大的生產力潛力,這使很多國家都將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作為其數字化戰略的重點。OECD(2020)的數據表明,經合組織34個國家已制定了國家數字戰略,以國家戰略全面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6]。歐盟的“數字指南針”(Digital Compass)提出,到2030年,90%以上的歐洲中小企業至少達到基本的數字化強度,而在2020年僅為60%[7]。
在我國,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也得到了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發布的《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分析報告(2021)》指出,在中央各部委發布的與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相關的“十四五”規劃中,53%的規劃將數字化轉型列為重大任務或重點工程;而在地方層面,85%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十四五”規劃中將企業數字化轉型列為重點任務。我國中小企業的數量超過4000萬家,這些企業對數字化轉型有著巨大的需求,通過數字化轉型,能夠使中小企業更好地融入產業鏈、供應鏈,并提升企業內部的生產、運營、管理、營銷等多方面的效率,更高效地開拓市場,從而提高抗風險能力,并緩解融資難問題(騰訊,2021)[8]。從發展現實來看,我國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仍處于起步階段。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2022)[9]指出,79%的中小企業仍處于數字化轉型的初步探索階段,12%的企業處于應用踐行階段,而達到深度應用階段的企業占比僅為9%。騰訊(2021)將企業的數字化過程分為四個階段,即基礎探索期、簡單操作期、復雜應用期和全面實踐期,經過量化打分可以發現,處于四個時期的企業分別為41.3%、38.1%、19.0%、1.6%,處于數字化初期的企業占比接近八成。
本文通過對中小企業理論進行創新,認為數據化理論與工業互聯網理論構成了中小企業數字化的基礎。在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理論分析的基礎上,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國際經驗進行深入分析,根據理論框架與國際經驗,針對我國中小企業數字化的現狀,提出了全面推動我國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政策建議。
一、理論框架
雖然數字化轉型已實踐多年,但仍缺乏統一的定義(騰訊,2021)。IBM認為,數字化轉型實質上是將客戶驅動、數字優先的方法應用于從業務模式到客戶體驗再到流程和運營各個方面。數字化使用人工智能、自動化、混合云和其他數字技術來利用數據,推動工作流程智能化,形成更快、更智能的決策,并對市場變化進行更實時地響應[10]。數字化在理論上應該包括兩個維度[11],第一個維度是數據化,即將物理世界轉換為數據,并利用數字技術對數據進行處理,以模擬物理世界運行的過程。第二個維度是聯網,也就是通過工業互聯網,將物理世界中的相關部分聯系起來,從而實現數字化運行整個生產經營過程。
(一)數據化理論
數字化轉型建立在數據化的基礎上。也就是說,通過將物理世界進行數據表示,利用各類數字技術,對物理世界進行模擬,從而推動物理世界運行效率提升。其背后的基礎邏輯是數據傳輸、轉換、改造、運用、模擬、共享等方面的成本要遠低于對物理世界進行同樣操作的成本。而這種數據化的過程,也會帶來組織體系等各個方面的變革。這樣,數字技術能夠融入從產品設計、生產制造、營銷、售后服務的整個過程,給整個實體經濟體系帶來革命性影響。
在這個意義上,數據化理論的核心是將物理世界以數據方式進行模擬,再以算法和算力對物理世界特定運行過程進行模擬。由于數據和算法模擬具有成本等諸多方面,所以數字化轉型的核心是將物理世界數據化,包括人、物、環境等進行數據搭建,通過數據化搭建,超越物理世界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從而獲得更高的效率,產生更廣闊的市場。
數據化能夠超越物理世界的局限。利用數字技術,通過對物理過程的模擬,能夠對制造過程進行更多維度的探索,從而使工廠、車間和生產線找到最優的智能轉型升級路線和方案,而不會對物理世界的資源造成浪費。由于元宇宙中可以同步實施多種方案的模擬,這也能夠加快對物理世界迭代過程。
數據化也使制造過程中各要素發生了巨大改變。傳統制造系統的核心要素可以用5個“M”來表述,即材料(material)、裝備(machine)、工藝(methods)、測量(measurement)、維護(mainte?nance)。而數據化后區別于傳統制造系統的核心在于第6個“M”,即建模(modeling),第6個“M”利用數據來驅動其他5個要素,從而解決和避免制造系統的問題。
數據化意味著數據具有很高的價值。在傳統的企業生產經營模式下,企業內部也會產生很多數據,但企業無論是分析還是利用數據,都專注于其內部的數據,這并不能將數據的價值完全發揮出來。而數字化轉型的重點,是實現數據的跨企業共享。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一份報告(WORLD ECONOMIC FORUM&Boston Consulting Group,2020)認為,根據最佳實踐,僅通過專注于制造流程優化,數據共享的潛在價值估計超過1000億美元[12]。具體而言,數據共享可以在五個方面增加價值:一是增強資產優化。結合來自同一類型機械的多個用戶的數據,使制造商能夠改進算法,例如,實現預測性維護。因此,共享數據可以通過增加機器正常運行時間和產品質量來優化資產性能,從而為所有利益相關者創造雙贏局面。二是跟蹤價值鏈上的產品。通過獲得價值鏈的“端到端”可見性,制造商可以快速響應意外事件并減少庫存。三是跟蹤價值鏈上的工藝流程。制造商利用生產流程中的數據,能夠確保供應商遵循商定的生產流程,供應商可以使用這些數據作為證據,以證明其有效地遵守了嚴格的法規要求。四是交換產品數字特性。共享有關產品形狀和成分的數據使制造商能夠同步和優化互聯生產流程。五是驗證出處。利用數據,能夠使產品生產過程透明化,從而確保產品可溯源。
(二)工業互聯網理論
從數字化轉型的實踐來看,數據化主要是解決模擬、可視化、分析等虛擬空間問題。而工業互聯網則解決感知、連接、控制等物理世界與虛擬世界聯系的問題。
工業互聯網將新一代信息技術引入產業部門實現深度融合,對國民經濟各個產業內在的運作流程、運行機制、生產要素、研發設計、生產方式、組織模式等各個方面都產生深刻影響,能夠推動中小企業提升效率、降低成本、提升技術能力、提高產品質量、降低資源消耗、防范金融風險,是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基礎。
自2012年GE提出工業互聯網的概念以來①,工業互聯網與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方面的研究在持續增加。唐國鋒等(2021)[13]對2012—2021年的工業互聯網相關論文進行計量分析表明,在此期間,相關的中文文獻有914篇,英文文獻有858篇。
在理論上,工業互聯網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是感知。要實現數字化,首先必須使系統能夠感知到物理世界的狀態。而工業互聯網借助大量的傳感設備、物聯網等,實現對物理世界的實時感知。正是基于感知,才能實現對物理世界的模擬、優化和控制等。在國外,工業互聯網(Industrial Internet)更多地被稱為工業物聯網(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例如,在唐國鋒等人(2021)統計的858篇與工業互聯網相關的論文中,其中555篇關鍵字中涉及工業物聯網,168篇涉及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而關鍵字涉及工業互聯網的僅有51篇。
其次是連接。工業互聯網不單純是將數據進行鏈接,還對人、機、物、系統進行深度融合,將虛擬空間與物理空間連接起來,從而形成信息物理空間(Cyber Physical System,CPS)。將數據與物理空間聯系起來,不但能夠實現對物理世界的實時感知,更能夠實現實時控制和優化。這不但能夠替代勞動力、降低人員成本,更能夠對各種流程、參數及工序等進行綜合優化,從而減少浪費、降低庫存,減少原材料、能源等投入,并節約土地、降低排放,從而更大幅度地降低成本。
再次是開放。在生產端,工業互聯網能夠實現與產業鏈、供應鏈中的主體進行實時動態連接,所有相關主體能夠跨越時空聚集在虛擬空間中,各種相關的數據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共享,從而構建起覆蓋全產業鏈、全價值鏈的全新制造和服務體系,實現更高效的協同。工業互聯網能夠與消費互聯網之間進行耦合,能夠將消費偏好、研發、生產、倉儲、營銷、市場競爭、供應鏈等諸多方面的信息進行整合,形成工業大數據,使供給側與需求側智能匹配,對消費者需求進行更為精確地響應,從而協助解決生產過剩、供給效率低下等傳統生產模式無法解決的問題
最后是平臺。工業互聯網的發展必然會帶來平臺化的趨勢。通過平臺化,能夠在更大范圍內匯聚資源,從而降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門檻和成本。在我國,具備一定行業、區域影響力的工業互聯網平臺數量超過100個,連接設備數量超過7600萬臺套,工業機理模型數量達58.8萬個,服務企業超160萬家。
二、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國際趨勢
中小企業在各國經濟中都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全球主要國家都高度重視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尤其是新冠疫情以來,為了解決中小企業所面臨的困難,各國更是出臺了大量支持政策,以加速推進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
(一)各國中小企業數字化趨勢
由于中小企業在數字化的資金、技術、人才、信息和意識等諸多方面的差距,各國中小企業數字化水平普遍低于大型企業。European Invest?ment Bank(2020)的數據表明,只有不到30%的微型企業實施了至少一種數字技術,而在大型企業,這一數據達到80%。平均而言,2018年經合組織國家大、中、小型企業中進行大數據分析的企業分別占34.1%、18.8%和10.6%[14]。
在電子商務應用方面,OECD(2020)指出,2019年大企業使用電子商務的比例為44%,電子商務占其營業額的比重為24%,但在小企業中僅占21%、10%。2017年時大企業使用大數據分析的比重為33%,而中小企業占主體的全部企業中,僅有12%的企業使用大數據分析。從增長來看,近年來使用大數據分析的企業增量也主要在大企業。
中小企業數字化水平在不同行業和不同業務環節有著明顯的區別。OECD(2021)[17]的調查表明,一般而言,信息、科研、建筑、物流或零售貿易等行業數字化進程較快;信息和通信服務業中從業人員使用計算機和網絡處理工作事務的中位比例為93.6%,專業、科學和技術服務業為88.6%,建筑為45.9%、運輸和倉儲為51.1%、批發為70.6%、零售貿易為70.3%,而行政和支持服務行業僅為36.2%,住宿和食品服務僅為31.8%。在企業內部,一般行政事務和營銷運營的數字化水平較高,在企業與政府在線互動、使用電子發票、社交媒體或在線銷售方面,中小企業和大公司之間的差距較小。
新冠疫情對中小企業數字化是一個非常大的促進作用。OECD(2020)[18]在2020年全球范圍內進行的商業調查顯示,自2020年5月起,中小企業對數字技術和在線銷售的采用有所增加,自新冠疫情以來,高于70%的中小企業正在更多地使用數字技術,盡管各國之間存在很大差異。美國商會的一項調查也顯示,數字化趨勢正在加速。在2020年4月至5月期間,將部分或全部員工轉變為遠程辦公的小企業比例從12%增加到20%,已經開始將其零售業務轉向數字化手段的小企業從10%增加到17%[19]。
(二)各國政府對中小企業數字化支持政策的趨勢
各國政府大力支持中小企業數字化,其政府措施包括技術開發支持、人才技能培訓、金融支持、數據保護能力或數據安全、電子政務政府、高質量基礎設施、公共平臺和設施等方面。
1.加強頂層設計,將中小企業數字化作為其國家數字化戰略的重要部分。全球大部分國家都已發布了數字戰略,而這些戰略中,幾乎都包括了中小企業數字化的內容。在具體政策方面,包括支持中小企業采用云計算等新型數字化資源、對中小企業數字化所帶來的數據安全問題重點關注并納入國家數字安全戰略、支持建設數字化生態、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等。
例如,丹麥國家數字增長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小企業:數字計劃”,該計劃以“電子商務中心”為特色,旨在幫助中小企業進行在線銷售。
2.建立數字化服務公共平臺,降低中小企業數字化門檻。中小企業數字化往往面臨著認知、工具、知識等諸多方面的障礙。面對這些障礙,很多國家政府推出了公共服務平臺,為中小企業數字化提供知識、工具等方面的資源,以消除中小企業數字化方面的顧慮和障礙,降低數字化轉型的門檻。
2018年,法國政府推出了一個在線平臺“FranceNum”(www.francenum.gouv.fr),該平臺上匯聚了大量與數字化轉型相關的公共與私人專業顧問,中小企業只需要登錄該平臺,并說明其規模、位置和業務領域,明確所需要咨詢的問題,問題可以涉及創建數字化戰略、增加在線業務、開發客戶、在線銷售、增強內部流程、培訓和招聘、保護公司、更好地使用數據、整合不同的工作方式等,專業顧問不僅能夠提供相應的咨詢意見,還能夠提供有關可用融資方案的信息。
式中:TH為湖南節假日期間客流量的增加值,S為節假日的時長,相關系數R=0.965 8,方程擬合度較高,即節假日每增加(或減少)一天,客流量將增加(或減少)2 799.6人次。
澳大利亞政府構建了數字化轉型在線指南,為各種規模的公司提供有關數字化的信息,中小企業可以利用該在線指南,獲得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在線指導。平臺還與地方政府有合作關系,新南威爾士州政府運行設計系統指南,其中包括與虛擬團隊管理相關的數字協作工具和平臺目錄。設計系統指南提供了每個工具的信息摘要,促使企業與在線平臺互動,以實現更好的內部溝通。
丹麥政府于2018年啟動了“電子商務中心”平臺,該中心旨在促進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和電子商務發展,2018—2021年政府就該項目總計撥款4500萬丹麥克朗。中心平臺向中小企業提供有關如何加強在線銷售的個性化策略,并將很多實踐案例轉化為可用的電子商務解決方案供企業參考。此外,中心還為中小企業數字化提供各類現金資助,中心也實施各類提高管理人員數字化能力的舉措。
3.在疫情防控期間出臺特別支持政策以加速推動數字化。新冠疫情給中小企業帶來了不利影響,數字化對中小企業擺脫不利影響提供了良好的工具。Sage調查發現,80%的中小企業認為數字化采用對于企業復蘇和創造就業至關重要[20]。因此各國政府都將推進中小企業數字化作為應對疫情危機的重要手段。在政策方面,既有對原有政策的強化,也有針對疫情的新政策出臺(見表1),有些國家甚至對原有的監管架構進行了變更。例如,智利對其《勞動法》進行了修改以規范遠程辦公。

表1 OECD主要國家對中小企業數字化支持政策
三、政策建議
從整體上看,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過程,需要立足于各種力量協同的視角,協調政府部門、平臺、產業、企業、非營利性組織等多方主體,貫通數據、土地、人力、技術、資本、信息等生產要素,連接供需兩端,促進產業融合發展,智慧打造現代化產業鏈和供應鏈,從而以主體協同、要素聯動、產業融合、供需連接、雙鏈互促、智慧治理的理念為指導思想,全面形成良好的數字化生態,為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創造良好的條件。我國應根據國際上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方向和政策趨勢,建立促進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政策體系。
(一)鼓勵中小企業參加各種數字化相關的培訓,提升數字化技能
中小企業數字化的首要障礙是意識與認知問題。中小企業往往對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的發展階段缺乏了解或有理解偏差,意識不到企業轉型發展的必要性和未來轉型的必然性。從實地調研來看,很多中小企業主對數字化只知道基本概念,對其基礎條件、具體流程、發展階段等缺乏了解,因而不知道數字化轉型具體為何物。大多數企業領導對于數字化轉型概念的認知都是十分模糊且片面的,導致企業缺乏轉型的主動性。有人認為智能制造就是數字化轉型,也有人認為使用了一些工業軟件就是數字化轉型,甚至還有人將在線營銷系統等同于數字化轉型(騰訊,2021)。還有一些企業家對人工智能的概念有誤解,可能將人工智能的當前發展與通用人工智能(AGI)混淆(Roffel&Evans,2018)[21],這使其對人工智能在企業數字化轉型中的作用無法清楚地認知。由于認識不足,很多中小企業缺乏推動數字化的主動性。加拿大商業發展銀行2020年6月對1000家中小企業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21%的小型中小企業不打算改變其業務實踐,而大型中小企業的這一比例僅為4%。
在國外,許多國家提供稅收優惠,以降低公司培訓員工的成本。培訓費用可以部分或全部以免稅形式從公司年度利潤中扣除。針對中小企業,往往會提高扣除比例,以激勵企業參加培訓。另外,政府還重視利用企業主網絡和協會來推動知識共享,促進數字化技能提升。政府也可通過對“經紀人”或中介機構的獎勵,來推動這些機構積極為企業提供低成本的培訓(OECD,2021)。
我國可以借鑒這些政策,建立起中小企業數字化技能培訓的政策支持體系。具體政策包括:一是將中小企業進行數字化所支出的培訓等費用,視為研發費用,在稅前直接抵扣。二是建立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知識平臺,平臺上既匯聚與數字化相關的專業服務機構(如解決方案提供商),也有相關研究機構,還有各類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最佳實踐。同時,平臺上還提供數字化轉型的各類工具,形成工具庫。三是加強中小企業的管理技能培訓與提升。由政府部門采購各種數字診斷工具,并免費提供以幫助中小企業識別其管理缺陷;開展各類涵蓋業務戰略、運營模式、流程管理、績效管理、領導力、治理、敏捷性和創新等多種與管理技能相關的培訓課程和研討會,以幫助中小企業適應數字化轉型帶來的管理挑戰。四是試點支持一批數字化培訓機構。這些專業化的培訓機構針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問題,量身定制相應的培訓方案,從而為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精準的知識支持。
(二)為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
中小企業一般數字化基礎較差,在推動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往往需要購置大量硬件和軟件,即使利用云計算能夠節省部分算力投資,企業也需要在機器改造、傳感設備、流程優化、數據傳輸等方面投入大量資金。而中小企業一般經營規模較小,利潤較薄,在資金儲備方面不夠,推動數字化更容易受到資金的約束。從國外經驗來看,各國政府一般都會以政府補貼的方式為中小企業數字化提供直接的資金支持(參見表1),但這部分的資金非常有限,并不能滿足中小企業數字化的資金需求。更多的辦法是通過金融科技、金融創新等方式來滿足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資金需求,包括利用數字身份驗證、分布式賬本技術(DLT)、大數據和市場借貸等技術,提供創新服務,減少信息不對稱和交易成本,解決中小企業獲取融資的結構性障礙(OECD,2021)。據調查,OECD 38個國家中的27個正在鼓勵開發金融科技解決方案,提供更便捷的服務、更有效的信用風險評估和更低的交易成本,以消除中小企業的融資障礙。另外,還有國家支持金融科技平臺、融資平臺等平臺建設,以解決中小企業數字化融資問題(Koreen、Laboul&Smaini,2018)[22]。
針對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所面臨的資金難題,可以借鑒國外相關政策經驗的基礎上,出臺系統化的中小企業數字化融資政策:一是對政府資金進行整合,集中力量,發揮政府資金的引導作用。在我國,中小企業數字化涉及多個部門,這些部門都會有一些扶持資金,地方政府也有相應的資金或基金。現在的問題是這些資金比較分散,沒有很好地起到種子作用,沒有發揮政府資金對社會資本的帶動作用。因此,要對各個部門、各級政府、各類資金進行整合,從而形成對中小企業數字化的資金支持合力。二是要提高政府資金使用的績效。建立綜合多個指標的政府資金效應評價和追蹤問責機制,從而使政府資金的效用最大化。三是推動金融科技應用,利用金融科技為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要建立數據共享機制,使企業數字化所獲得的數據能夠利用區塊鏈、隱私計算等技術與金融機構共享,使金融機構能夠打開企業生產的黑箱,從而對企業的信用情況進行精準的評估,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四是積極試點與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相關的創新金融產品。要匯聚各方力量,建立起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財務模型,對其投入與產出進行精準測算,一方面可以堅定企業推動數字化的決心,使其能夠投入更多的資金和資源到數字化轉型中;另一方面,清晰的財務模型也是提供更多創新金融產品的基礎,在財務收支明確的情況下,金融機構就能夠利用各種金融工具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
(三)以單一環節單一技術為突破,利用技術應用的互補性,推動多種數字技術加速應用
OECD的調研結果表明,數字技術具有較強的互補性,通過對云計算(CC)、客戶關系管理(CRM)、供應鏈管理(SCM)、企業資源計劃(ERP)和大數據分析(BDA)等相關數字技術在企業擴散的情況進行量化分析結果表明,數字技術應用擴散具有較強的互補性,技術A的采用隨著技術B的采用而增加。因此,在支持推動中小企業數字化方面,可以采取“一點突破,多點聯動”的方式,先在一個基礎較好的環節、技術領域進行突破(李勇堅、豐曉旭、李堅飛,2020)[23]。
在政府政策方面:一是要強化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數字化轉型需要有高速網絡、算力設施、數據中心等基礎設施支持。這些基礎設施是發揮數字技術互補性的重要條件。二是通過優先支持中小企業使用云計算等基礎設施的方式,推動中小企業進行數字化突破。云計算門檻較低,已形成了軟件即服務(SaaS)等商業模式,有利于作為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突破口。而云計算作為數字化的重要基礎設施,將帶動中小企業引入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相關技術,更好地實現技術互補。近年來,國家大力推動“上云用數賦智”,其政策要點正是通過企業上云帶動數字化。三是鼓勵數字化解決方案服務商開發一些輕量化的低成本應用,使企業能夠更快地切入到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例如,在布局云計算硬件設施,推動基礎設施即服務(IaaS)的同時,也要鼓勵服務商開發出一批符合中小企業需求的軟件即服務(SaaS)產品。四是推動一批數字互補技術的試點示范項目。通過示范項目和案例,尋找更高效的技術互補空間,從而使技術互補性更好地發揮出來。利用示范項目進一步發揮以供應鏈、產業鏈中數字化水平較高的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龍頭企業以數字化采購、生產協同、設備共享、數據共享等方式,推動中小微企業融入數字化生態,從而由點到線到面逐步提升數字化水平。五是鼓勵行業內領先企業根據中小微企業的特點提供一批更符合需求的解決方案。要根據行業、企業的具體情況,抓住行業數字化轉型關鍵共性問題和企業個性問題,開發出一批前期投入較小、見效較快、上手容易的轉型方案,使企業消除對數字化轉型的畏難情緒,從而減小轉型阻力。重點鼓勵開發者找準中小微企業的痛點,開發一些解決中小企業行業共性問題的輕量級應用。
(四)建立數據文化,構建數據標準、數據收集、數據交易、數據共享、數據安全等方面的制度體系
數據是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核心要素。從調研結果來看,中小企業仍沒有建立起良好的數據文化,沒有形成良好的數據管理實踐。盡管中小企業生產和處理從后臺到前臺的大量數據,但中小企業往往缺乏整理、管理和保護這些數據的能力。除了未捕獲的數據外,收集和存儲數據的數量或質量可能不足以獲得有意義的洞察力,數據的價值難以發揮出來(Bianchini&Michalkova,2019)[24]。而且,中小企業的生產設備等規格型號不一,出廠年限不統一,信息化數字化水平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導致數據格式、數據收集方法不一致,企業內部數據重復和數據孤島現象并存。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在數據安全方面的能力不足,隨著數據收集量的大幅度增加,數據泄露的風險也會大幅度增加。
在政策方面,需要進一步完善數據文化,擴大數據要素應用空間,從而使數據在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中的核心作用進一步發揮出來。一是要建立數據標準體系。數據標準體系是數據收集、數據處理、數據移植等工作的基礎。通過標準化,能夠使中小企業收集的數據能夠全面融入產業鏈、供應鏈,從而為全產業鏈數字化打下基礎,也為解決方案服務商提供個性化的數字化方案提供基礎資源。二是要建立數據共享機制。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其具有使用的非競爭性,數據在使用過程中,會產生更多的數據,這一特征也使得數據共享能夠為數字化轉型帶來更多的助力與效益。在政策上,應建立數據可移植制度,鼓勵企業在行業、供應鏈、產業鏈內進行數據共享,從而使中小企業能夠獲得更多的數據來推動數字化轉型。三是要建立數據流通交易制度。數據作為數字化的核心要素,需要不斷地交易流通才能將其價值更好地發揮出來,要通過數據定價、數據中介、數據使用等多個環節的措施,促進數據交易。四是要完善數據安全措施。中小企業缺乏有效評估和管理風險的意識、資源或專業知識,在數據安全等方面具有能力、意識等方面的缺陷,要鼓勵運用區塊鏈、隱私計算、數據沙箱等技術,解決數據共享、流通過程中的安全問題。
(五)建立寬容失敗的環境
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必然產生更多的新商業模式、新業態、新組織形式,在監管上需要更為包容。針對數字化創業失敗的情況,不能過度懲 罰 (Adalet McGowan,Andrews and Millot,2017)[25],要推動構建軟件、硬件、數據、開發、測試、安全、應用、標準等諸多方面協同的數字化生態。
注釋
①參見GE公司于2012年11月發布的白皮書《Industrial Internet:Pushing the boundaries of minds and machi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