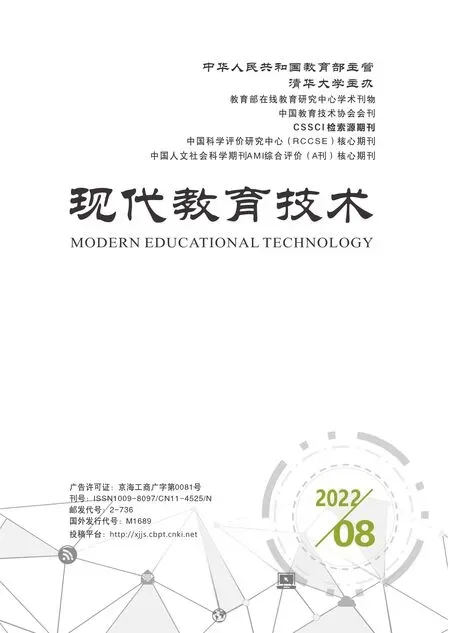什么影響了人工智能教育的教學效果?*——基于教師技術認知和教學實踐層面的分析
李世瑾 顧小清
什么影響了人工智能教育的教學效果?*——基于教師技術認知和教學實踐層面的分析
李世瑾 顧小清[通訊作者]
(華東師范大學 教育信息技術學系,上海 200062)
目前,人工智能已被逐步應用于教育實踐,而教學效果決定了人工智能教育的實踐進程。為保障人工智能教育的有序推進,文章以1638位中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從技術認知和教學實踐兩個層面,采用量化方法分析了人工智能教學效果的影響因素,以及不同性別、學歷、教齡、學段、學科教師在教學效果方面的差異化表現。研究發現,影響人工智能教學效果六個因素的效應水平依次為:組織支持>課堂文化>能力感知>價值感知>活動內容>教學設計;不同性別、教齡、學段教師的教學效果存在顯著差異,但在學歷、學科上的差異表現未達到顯著水平。基于研究結果,文章從協同多元力量、關注實踐差距、優化設計內容等角度針對人工智能教育實踐的開展提出建議,以期科學推動人工智能教育實踐,提升人工智能教育的教學效果。
人工智能教育;教學效果;技術認知;教學實踐
新一代人工智能為教育生態注入了新動能,同時也激發了教育工作者參與智能化實踐的熱情和信心。然而,理性看待人工智能教育的實踐效果,其現實表現并不盡如人意。一項元分析結果表明,智能導學系統對學生成就的正向效應值僅為0.09[1]。若借助智能技術干預,會讓表現不佳的學生感到恐懼,甚至加劇學生的同質化傾向[2]。此外,人工智能教育實踐還存在一定的風險,如李世瑾等[3]從管控視角闡釋了智能技術還原教育世界的本體風險、認識風險、價值風險和倫理風險,并從復雜性治理范式、多主體協同機制、多元創新方法論等層面提出了應對智能教育風險的出路;吳河江等[4]指出了人工智能教育應用的潛在風險類型,并提出了有效規避策略。此外,還有學者運用復雜系統科學理論,提出人工智能教育面臨實踐質量不充分、基礎理論研究較薄弱、實踐應用領域不均衡等問題[5]。基于現有研究不難發現,有關人工智能教育的實踐效果審視聚焦于方法推介或風險闡釋層面,鮮有研究從量化視角回應其影響因素與效應水平。因此,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法,從教師技術認知和教學實踐兩個層面,分析人工智能教學效果的影響因素,并探究不同性別、學歷、教齡、學段、學科教師在教學效果方面的差異化表現,以期為推動人工智能教育實踐提供合理依據和有效參照。
一 研究設計
1 調查問卷編制
本研究編寫了“中小學人工智能教育的教學效果”調查問卷,采用李克特五點量表計分,內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情況調查,包括性別、學歷、教齡、學段、學科等人口學信息,以及教師對人工智能教育的了解程度、技術操作熟練度和實踐態度等應用情況;第二部分為人工智能教學效果的影響因素調查,分別從“技術認知”和“教學實踐”層面進行系統分析。
①技術認知層面:技術認知是教師對人工智能教學的主觀認識和實踐傾向,其中,能力感知與價值感知是影響教師開展人工智能教學的關鍵因素[6][7]。能力感知是教師認為自身具備開展人工智能教學的能力程度,而價值感知是教師相信開展人工智能教學對自身工作績效和教學目標的實現程度。基于此,本研究借鑒Davis[8]、Venkatesh[9]等設計的技術接受度量表,圍繞能力感知和價值感知兩個子維度,共設計了6道測試題。
②教學實踐層面:教學實踐是教師開展人工智能教學的真實體驗,以及實踐進程中面臨的行動挑戰。結合人工智能教學實踐的內涵,本研究參照改革教學觀察協議(Reformed Teaching Observation Protocol,RTOP)[10],分別從人工智能教學設計、活動內容、課堂文化、組織支持四個子維度,共設計了14道題。其中,人工智能教學設計強調使用智能化教具,幫助學生創造性地解決復雜問題;活動內容重視通過陳述性和程序性的組織方式,勾勒人工智能應用的具體情境,培養學生的人工智能素養;課堂文化關注人工智能教學的愉悅氛圍,包括積極的交流互動和良好的師生關系;組織支持則是人員隊伍、智能裝備、經費保障和管理制度對人工智能教學的支持力度。
③教學效果:教學效果關注教師、學生和應用效益等方面的變化情況,基于人工智能教學效果的界定范疇,本研究參照Wang等[11]設計的人工智能教學問卷,圍繞教學效率、學業成就、智能應用效益設計了3道題目。
2 問卷信效度檢驗
經計算,調查問卷各維度的信度系數均在0.9以上,說明問卷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效度檢驗方面,KMO值為0.969,Bartlett’s球形檢驗的c2值達到0.05顯著水平,即測試題的相關矩陣之間存在共同因素,適合進行因子分析。進一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并經過方程最大化正交旋轉,從問卷的原始指標萃取出6個主因子,分別對應能力感知、價值感知、教學設計、活動內容、課堂文化、組織支持,此時因子荷量均在0.600以上,總體方差解釋為69.976%,滿足統計學因素負荷量大于0.45和累積解釋變量大于60%的要求,說明該問卷效度良好。
3 數據收集過程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樣和方便抽樣相結合的方式確定調查對象:首先采用整群抽樣法從34個省級行政區隨機抽取東部、中部和西部15個樣本省級行政區作為一級抽樣單位,然后從15個樣本省級行政區隨機抽取48個地級市作為二級抽樣單位,最后按照方便抽樣原則抽取96所中小學作為三級抽樣單位。在整個抽樣過程中,本研究將“開展人工智能教育實踐”作為遴選標準。2021年7月,本研究采用網絡問卷形式,開展了為期四周的數據采集工作,共收回1758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1638份,有效率約達93%。

圖1 人工智能教學效果的測評分析框架
4 數據分析過程
數據分析過程如下:首先,根據有效調查問卷確認教師開展人工智能教學的基本情況;然后,從技術認知和教學實踐兩個層面,探討能力感知、價值感知、教學設計、活動內容、課堂文化和組織支持對教學效果的具體影響;最后,探究不同性別、學歷、教齡、學段、學科教師在各影響因素和教學效果方面的差異化表現,具體如圖1所示。
二 研究結果
1 教師開展人工智能教學的基本情況
本研究中,中小學教師的基本情況包括性別、學歷、教齡、學段、學科等人口學信息,以及教師對人工智能教育的了解程度、技術操作熟練度和實踐態度等應用情況,如表1所示。
2 人工智能教學效果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首先分析了樣本數據的相關性,發現能力感知、價值感知、教學設計、活動內容、課堂文化、組織支持兩兩之間均顯著相關,且這六個因素與教學效果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753、0.736、0.759、0.822、0.839、0.628。之后,本研究采用多元線性回歸與路徑分析,探索各因素對教學效果的影響水平,結果發現:能力感知(=0.000<0.05)、價值感知(=0.000<0.05)、教學設計(=0.031<0.05)、活動內容(=0.001<0.05)、課堂文化(=0.000<0.05)、組織支持(=0.000<0.05)對人工智能教學效果均有顯著影響,且共同解釋教學效果總變異量的78.7%。
3 不同性別、學歷、教齡、學段、學科教師的差異化表現
①不同性別教師的差異化表現:男教師和女教師在教學效果上存在顯著差異(=0.003<0.05),且男教師表現更佳(t=3.011)。具體來說,不同性別教師在能力感知(=0.001<0.05,t=3.446)、價值感知(=0.000<0.05,t=3.670)、教學設計(=0.008<0.05,t=2.641)、活動內容(=0.019<0.05,t=2.356)、課堂文化(=0.027<0.05,t=2.209)、組織支持(=0.015<0.05,t=2.443)等維度均存在顯著差異,且男教師的表現水平均優于女教師。
②不同學歷教師的差異化表現:不同學歷教師在教學效果上的差異表現未達到顯著水平(=0.279>0.05),但不同學歷教師在能力感知(=0.031<0.05)、價值感知(p=0.009<0.05)、教學設計(=0.023<0.05)、活動內容(=0.003<0.05)、課堂文化(=0.006<0.05)、組織支持(=0.003<0.05)等維度均達到顯著差異水平。進一步通過事后多重比較,可以發現:能力感知、價值感知、教學設計、活動內容、課堂文化等維度的效應水平為博士>碩士>本科>專科,而組織支持維度的效應水平依次為博士>碩士>專科>本科。
③不同教齡教師的差異化表現:不同教齡教師在教學效果上存在顯著差異(=0.000<0.05),且效應水平依次為2年以下>2~5年>11~15年>6~10年>16年以上。具體來說,不同教齡教師在能力感知(=0.000<0.05)、價值感知(=0.000<0.05)、教學設計(=0.000<0.05)、活動內容(=0.000<0.05)、課堂文化(=0.000<0.05)、組織支持(=0.000<0.05)等維度均存在顯著差異。進一步通過事后多重比較,可以發現:能力感知維度的效應水平依次為2年以下>2~5年>11~15年>6~10年>16年以上,價值感知維度的效應水平依次為2~5年>11~15年>2年以下>6~10年>16年以上,教學設計、活動內容維度的效應水平依次為2~5年>2年以下>11~15年>6~10年>16年以上,而課堂文化、組織支持維度的效應水平依次為2年以下>2~5年>11~15年>6~10年>16年以上。
④不同學段教師的差異化表現:不同學段教師在教學效果上存在顯著差異(=0.000<0.05),且效應水平依次為小學>初中>高中。具體來說,不同學段教師在能力感知(=0.003<0.05)、價值感知(=0.000<0.05)、課堂文化(=0.031<0.05)三個維度存在顯著差異,但在教學設計(=0.767>0.05)、活動內容(=0.285>0.05)、組織支持(=0.185>0.05)三個維度不存在顯著差異。進一步通過多重比較,可以發現:能力感知、價值感知維度的效應水平依次為小學>初中>高中,課堂文化維度的效應水平依次為初中>小學>高中。
⑤不同學科教師的差異化表現:不同學科教師在教學效果上的差異表現未達到顯著水平(=0.320>0.05)。具體來說,不同學科教師在教學設計(=0.236>0.05)、活動內容(=0.539>0.05)兩個維度不存在顯著差異,但在能力感知(=0.000<0.05)、價值感知(=0.021<0.05)、課堂文化(=0.045<0.05)、組織支持(=0.000<0.05)四個維度存在顯著差異,且體育、信息技術、物理和通用技術學科的教師表現較佳。
三 研究討論
1 教師的技術認知和教學實踐對人工智能教學效果有正向影響
根據研究結果可知,教師技術認知和教學實踐層面的六個因素均能正向影響人工智能教學效果,且效應水平依次為組織支持>課堂文化>能力感知>價值感知>活動內容>教學設計。這意味著要提高教學效果的首要任務是提供充分的組織支持,創設智力流動的文化環境。也就是說,當使能條件越豐富時,教師的努力期望愈加明顯,實踐成效也越顯著[12]。這是因為,人工智能教學是前進性和曲折性的統一體,當組織支持或課堂文化越理想時,教師就越能感知到人工智能教學的現實必要性,也就越容易產生實踐動力和信心,從而獲得更高水平的教學效果。
能力感知和價值感知對人工智能教學效果的影響次之,其原因可能在于教師的能力感知越充分,就越傾向于創新設計教學內容和活動流程,主動走出傳統教學的舒適區。在這個過程中,教師對人工智能教育的價值感知和實踐信念也較高,期待通過持續投入時間和精力,促使教學實踐發生顛覆性創新。因此,我們應充分激發教師能力認知的積極心理和效能期待,并驅動教師開展人工智能教學,從而循序漸進地提升人工智能教學效果。
活動內容和教學設計也正向影響人工智能教學效果,即可以通過選擇、組織、設計合理的活動內容和教學支架,來保障教學實踐的有效性。Mayer[13]強調基于科學的教學設計原則,能夠塑造學生積極、努力的人格傾向與心理范式,幫助不同認知水平的學生在刺激聯結中建立技術應用的融合模式,最終實現對技術知識的內化與重組。因此,科學界定人機協同的技術規則,選取合理的課程資源和智能工具,正是人工智能教育實踐科學落地的關鍵。
2 不同性別、學歷、教齡、學段、學科教師的差異化表現分析
根據研究結果可知,在性別方面,男教師的教學效果更加顯著,且在各影響因素上的表現均優于女教師。這是因為,源自技術感知優勢,男教師對人工智能教學表現出更為濃厚的興趣,且更愿意付出足夠的努力,探索人工智能知識和教學實踐策略[14]。因此,在中小學人工智能教學實踐的進程中,必須高度關注女教師的消極表現,可利用同儕影響和榜樣示范等途徑,調節女教師對人工智能技術應用的感知偏頗,從而縮小不同性別教師智能化教學效果的差距。
在學歷方面,不同學歷教師的教學效果并不存在顯著差異,但在各影響因素上的表現存在顯著差異,且博士、碩士學歷明顯優于本科、專科學歷。這是因為,人工智能教學實踐尚處于探索階段,不同學歷教師群體的認知水平和精力投入整體處于中間狀態,故教學效果整體不存在顯著差異。但由于博士、碩士學歷的教師已經體驗過人工智能實踐項目或具有人工智能學習經歷,因此其更容易適應人工智能教學實踐流程,也更愿意探索智能化實踐策略。
在教齡方面,不同教齡教師在各影響因素及教學效果上均存在顯著差異,且效應水平依次為2年以下>2~5年>11~15年>6~10年>16年以上。通過對比可知,教齡處于5年以內的教師多為新晉年輕教師,他們期待快速提升教學績效,加上年輕教師比較擅長創新探索與創意實現的活動設計,故能夠取得相對滿意的教學效果。而教齡處于10年以上的教師多為年長型教師,他們由于長期受傳統教學理念的熏陶,容易對人工智能教學產生恐懼甚至排斥心理,同時受職業倦怠的影響,其努力程度和績效期待也隨之降低,故在人工智能實踐教學中表現不佳。
在學段方面,不同學段教師在能力感知、價值感知、課堂文化、教學效果上存在顯著差異,且相較于高中教師,小學、初中教師的表現更佳。這是因為,學習是情境性活動,關注實踐共同體合法的邊緣性參與[15]。也就是說,小學和初中階段強調學生探究意識及創意想法的萌生,故教師期待通過人工智能實踐活動,激發學生積極創新的動機意識。而高中階段的教學任務及課業負擔更為繁重,教師普遍重視學生學科知識和專業技能的習得,以及教學活動的“有效輸出”。在這種情境下,教師的主觀意愿和實踐信念也隨之弱化,很難獲得相對滿意的教學效果。
在學科方面,不同學科教師的教學效果并不存在顯著差異,但在能力感知、價值感知、課堂文化、組織支持上存在顯著差異,且排名前三的學科為體育、信息技術、通用技術。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人工智能的發展熱潮起源于體育競技產業[16],體育教師由于長期受智能體育的專業熏陶,更愿意持續投入足夠精力,設計兼具創意與成效的活動流程;而信息技術、通用技術教師作為國內人工智能課程資源的骨干設計者,能夠依托原有創新經驗,將人工智能元素有效融入教學設計和組織活動,因此主觀層面的能力感知、價值感知、課堂文化、組織支持等表現相對較佳。
四 中小學開展人工智能教育實踐的建議
基于上述中小學人工智能教學效果影響因素與差異化表現的討論結果,本研究針對中小學人工智能教育實踐的開展提出以下建議:
1 協同多元力量,豐富人工智能教學的組織文化
本研究發現,組織支持和課堂文化正向影響教學效果,且影響系數分別位居前兩位。由于人工智能教學是一項系統化工程,因此協同多元力量、完善組織保障機制、優化課堂實踐氛圍是提升人工智能教學效果的堅實基礎。一方面,要發揮高等院校、教育研究所、企業、中小學校等支持聯盟的資源優勢,建立人工智能實踐共同體;加強職前、職后教師培訓支持,通過在高等教育課程體系中增設人工智能教育實踐項目,讓“準教師”盡早了解人工智能教育知識,定期舉辦人工智能教育專題研討活動,或通過真實項目、在線虛擬培訓方式,讓職后教師充分體悟人工智能教學設計流程。另一方面,要營造輕松、智能的學習氛圍,鼓勵不同學科背景、經驗水平的教師協同反思教學問題,并基于“建立愿景→改善心智→自我超越”的教學變革路徑,實現從“邊緣參與”到“充分參與”的角色認知轉化。此外,還要通過創新教學的彈性激勵,如通過提升薪酬、遴選人工智能“明星教師”或“種子教師”等途徑,持續激發教師的努力期望。
2 關注實踐差距,提升人工智能教學的勝任感知
任何新興技術在應用進程中都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實踐主體的質疑,本研究所發現的能力感知和價值感知正向影響教學效果就證實了這一點。基于此,有必要強化中小學教師的主觀積極性,并培養其集體感:首先,要充分發揮輿論平臺的積極導向作用,激發一線教師的實踐動力,尤其是女性、教齡偏長、學歷偏低的教師群體,鼓勵教師努力將知識儲備與教學經驗外化為行動舉措,提升其開展人工智能教學的勝任感知。其次,借助人工智能實踐共同體的幫扶機制,幫助不同教師樹立高度認同感與實踐價值觀,同時依托多元主體協同力量和關鍵腳手架等,持續激發教師的創新人格特質與實踐信心。最后,尊重教師的話語權和行動力,持續為其主觀層面的“勝任感知詞典”(即勝任特征集群、成功與錯誤行為示例和行動等級描述等),提供情感包容的心理養分支持。例如,參照“素養=(知識+能力)態度”結構模型[17],分別從人工智能創意知識、人工智能智力管理、人工智能教學設計等層面,提升教師勝任感知的文化涵養。
3 優化設計內容,打造人工智能教學的教練群體
本研究已證實,教學設計和活動內容正向促進教學效果。實際上,行動科學研究者早已認識到,教學不應僅停留于觀念層面,還必須從實踐行動層面明晰具體的教學設計及其相對應的行為操作[18]。首先,要注重內在提升,以教師熟悉的課堂場域為抓手,將人工智能知識建構“明學于心、實踐于行”,持續拓展教師的人工智能教學設計力[19]。通過觀摩人工智能示范課堂,讓教師在真實情境中分析、建構、內化整合人工智能的學科教學知識(AI-PACK),促使教師產生人工智能教學實踐的“心流體驗”,形成主動適應人工智能教學的感知力、行動力和洞察力。其次要重視外部陶冶,即拓展人工智能實踐場景,豐富一線教師對智能化氣息的感知。通過建立人工智能實驗室,或在科創中心、創意工作坊、走廊、屋頂或綠色空間等融入人工智能技術,滋養人工智能與學校場域融合共生的文化底蘊。需強調的是,人工智能教學設計和活動內容的重點并非是要求教師熟練掌握相關技術原理,故應避免智能認知的負荷超載,尤其是應保證女性和教齡偏長的教師能在足夠了解人工智能教育應用的前提下,積累智能化教學經驗并提出實踐策略。
五 結語
人工智能的教育應用并非一蹴而就,本研究通過分析教學效果的影響因素,以及不同性別、學歷、教齡、學段、學科教師的差異化表現,進一步明確了中小學人工智能教育的推進方向與行動舉措。未來,研究團隊將持續推進以下工作:①研究樣本雖遍布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但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天津、河南、四川、寧夏等地域,研究結論的適用范圍可能受限于地域情境。未來將擴大樣本數量,開展更大規模的實證調查研究,以形成更具普遍意義的推進策略。②人工智能教學效果的影響因素,遠比研究涉及的變量及其變量關系復雜。后續將采用動態建模和仿真實驗的方法,引入更多實踐變量,調節變量的影響路徑與作用機理。③結合學校發展情境對人工智能教練群體進行專門培訓,同時整合已驗證的有效教學干預方案,形成“最小風險”“可重復、可共享”的人工智能有效教學提升路徑與整體實施策略。
[1]Steenbergen H S, Cooper H. A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 on K-12 students’ mathematical learning[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3,(4):970-987.
[2]Lin H C K, Chen M C, Chang C K. 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solid geometry by using an augmented reality-assisted learning system[J].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2013,(6):799-810.
[3]李世瑾,胡藝齡,顧小清.如何走出人工智能教育風險的困局:現象、成因及應對[J].電化教育研究,2021,(7):19-25.
[4]吳河江,涂艷國,譚轢紗.人工智能時代的教育風險及其規避[J].現代教育技術,2020,(4):18-24.
[5]徐莉,梁震,楊麗樂.人工智能+教育融合的困境與出路——復雜系統科學視角[J].中國電化教育,2021,(5):78-86.
[6][11]Wang S Y, Yu H T, Hu X F, et al. Participant or spectator? Comprehending the willingness of faculty to use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 i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20,(5):1657-1673.
[7]Federica I. Preservice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utors for learning[D].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20:73-82.
[8]Davis F D.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J]. MIS Quarterly, 1989,(3):319-340.
[9]Venkatesh V. Determinants of perceived ease of use: Integrating control,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emotion into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00,(4):342-365.
[10]Piburn M, Sawada D. Reformed teaching observation protocol(RTOP): Reference manual[OL].
[12]Luckin R, Cukurova M. Design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in the age of AI: A learning sciences-driven approach[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9,(6):2824-2838.
[13]Mayer R E. What should be the role of computer games in education?[J]. Policy Insights from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16,(1):20-26.
[14]Wellner G, Rothman T. Feminist AI: Can we expect our AI systems to become feminist?[J]. Philosophy & Technology, 2019,(2):191-205.
[15]Brown J S, Collins A, Duguid P. Situated cognition and the culture of learning[J].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989,(1):32-42.
[16]Yu Y, Gao P. Application of computer-aided intelligent training in sports control[J].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0,(4):588-591.
[17]蔡清田.素養:課程改革的DNA[M].臺北: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70.
[18]Geuss R. The idea of a critical the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61-63.
[19]Terblanche N. A design framework to creat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ach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vidence Based Coaching and Mentoring, 2020,(2):152-165.
What Affects the Teaching Eff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spects of Teachers’ Technology Cognition and Teaching Practice
LI Shi-jin GU Xiao-qing[Corresponding Author]
Nowaday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en gradually applied in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determines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In order to ensure the orderly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this paper took 1638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used quantitative method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eaching eff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eachers’ differentiated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genders, education backgrounds, teaching ages, school periods and subjects, from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technology cognition and teaching practice. It was found that the six factors influenc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aching effect, when listed from high to low according to their effect levels, were organizational support, classroom culture, ability perception, value perception, activity content and teaching design. The teachers’ teaching effects in different genders, teaching ages, and school period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However, this differences in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nd subjects did not reach a significant level.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actic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ordinating multiple forces, paying attention to practice gaps, and optimizing design content, in order to scientifically promot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practice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 teaching effect; technology cognition; teaching practice

G40-057
A
1009—8097(2022)08—0092—08
10.3969/j.issn.1009-8097.2022.08.011
本文為2019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人工智能促進未來教育發展研究”(項目編號:19ZDA36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李世瑾,在讀博士,研究方向為學習科學與技術設計、智能教育,郵箱為shijinliEdu@163.com。
2021年10月11日
編輯: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