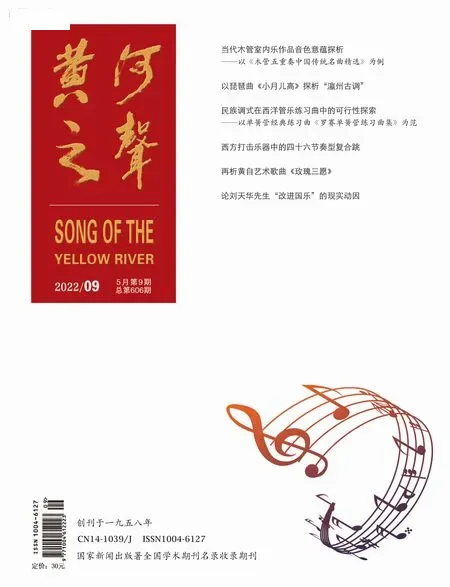淺析古箏曲《春到湘江》演奏技巧對(duì)音樂(lè)風(fēng)格的影響
劉 玥
引 言
一首作品風(fēng)格的形成,由作曲家本身的創(chuàng)作意圖和音樂(lè)構(gòu)思作基調(diào),其中還應(yīng)當(dāng)包含有作品的各個(gè)音樂(lè)要素,比如節(jié)奏節(jié)拍、速度力度、和聲、織體、曲式及伴奏音型等;還有后人在繼承中的表達(dá)和創(chuàng)新,例如對(duì)作品原譜標(biāo)記的重新理解和詮釋?zhuān)踔涟ㄑ葑嗾咴谖枧_(tái)表演中的再度演繹。可以說(shuō),一部作品不單是由編創(chuàng)者發(fā)明創(chuàng)造,同時(shí)也是需要后繼人的不斷調(diào)整革新的。
本論文將以古箏作品《春到湘江》為例,通過(guò)對(duì)演奏技巧在內(nèi)的音樂(lè)語(yǔ)言,作品曲式結(jié)構(gòu)及舞臺(tái)表演二度創(chuàng)作等幾部分的分析和說(shuō)明,來(lái)論述各個(gè)部分對(duì)其音樂(lè)風(fēng)格的影響。
一、作者介紹,樂(lè)曲改編及創(chuàng)作背景
古箏曲《春到湘江》是一首由王中山先生親自操刀譜就的器樂(lè)改編作品,原作是同名竹笛曲《春到湘江》。在成為古箏演奏曲目之前,它就已經(jīng)是家喻戶(hù)曉的竹笛作品,寧保生先生作,并且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竹笛曲之一。春到湘江這首樂(lè)曲具有鮮明的湖湘音樂(lè)風(fēng)格,在由王中山改編之后,不僅保留了原作當(dāng)中精彩的段落,還加入了獨(dú)屬于古箏的技巧和音樂(lè)語(yǔ)言,并且將湖南花鼓戲這種題材的熱烈歡快盡情地展現(xiàn)釋放,可以說(shuō)是古箏改編曲當(dāng)中的集大成之作。
王中山先生作為古箏演奏家,其經(jīng)歷如同古箏的發(fā)展歷史一般,從民間音樂(lè)走向了院校和音樂(lè)殿堂,河南箏曲的深厚歷史和文化沉淀全部都在王中山身上體現(xiàn)出來(lái),不僅有扎實(shí)的演奏功力,比如在很多之后創(chuàng)作的箏曲中有“炫技”的華麗表現(xiàn),他還具有對(duì)音樂(lè)的敏銳洞察力,對(duì)樂(lè)器之間的深入了解,并且有嫻熟高超的作曲能力,使得春到湘江這部作品能夠成功移植改編,在不失原作精美的基礎(chǔ)上,使古箏這件樂(lè)器能大放異彩,使習(xí)箏者和觀(guān)眾感受到更多面的古箏魅力。
在王中山的古箏音樂(lè)創(chuàng)作中,體現(xiàn)了他扎實(shí)豐富的民族音樂(lè)閱歷和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厚重底蘊(yùn);其次,王中山的音樂(lè)中,有著老練的基本功,使得對(duì)任何作品的處理都能夠顯得游刃有余,尤其是在演奏快板甚至是急板的時(shí)候,快速激動(dòng)的彈奏使得樂(lè)曲扣人心弦,目不暇接。三者,在舞臺(tái)表現(xiàn)時(shí),王中山具有極強(qiáng)的舞臺(tái)表現(xiàn)力和調(diào)動(dòng)能力,不僅是音樂(lè)的微觀(guān)處理,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在彈奏不同的作品時(shí)體態(tài)和動(dòng)作都有一些程式化的演繹,可以說(shuō)是在古箏這一聽(tīng)覺(jué)藝術(shù)的基礎(chǔ)上,更增添了視覺(jué)觀(guān)賞的魅力。
在其器樂(lè)改編作品當(dāng)中,均富有濃郁的民族風(fēng)格,并且具有樸實(shí)的音樂(lè)色彩,因?yàn)槭敲耖g小戲題材,統(tǒng)統(tǒng)來(lái)源于民間和農(nóng)村生活,樂(lè)曲將這種風(fēng)格原汁原味地呈現(xiàn)了出來(lái)。再者,王中山的改編作品以深厚的理論知識(shí)和豐富的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作指導(dǎo),大膽地改革創(chuàng)新,在上面提到的作品中,他不僅對(duì)竹笛的音響效果和所傳達(dá)的音樂(lè)精神有著深刻理解,同時(shí)對(duì)古箏有著透徹的了解,在尊重原作的基礎(chǔ)上,充分發(fā)揮了古箏原有音樂(lè)語(yǔ)言的能力和魅力,對(duì)傳統(tǒng)的古箏指法進(jìn)行了革命性的改良和創(chuàng)新,不僅是在還突破性的將左手解放,使左手演奏同右手一樣,具有豐富多變的技巧,而不是單一的使用以往的按揉等簡(jiǎn)單方式,在加入了復(fù)雜甚至艱難的左右手演奏技巧,古箏演奏的難度和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提高。但同時(shí),作為古箏演奏家,教育家和作曲家,不僅有技術(shù)的華麗表現(xiàn),還遵循了古箏原有的音樂(lè)語(yǔ)言規(guī)律,“依箏行聲”、“依箏行韻”,在演奏曲目的同時(shí),重塑了古箏的音樂(lè)形象。
二、作品具體段落劃分,音樂(lè)要素構(gòu)成及演奏技巧的具體介紹
(一)段落的劃分,各個(gè)音樂(lè)要素構(gòu)成下的春到湘江
在引子當(dāng)中,整體的音樂(lè)風(fēng)格顯示出一種優(yōu)美如畫(huà)的意境,第一小節(jié)開(kāi)頭的3及左手的琶音,營(yíng)造出一種朦朧美感,仿佛薄霧籠罩下,撥開(kāi)樹(shù)枝展現(xiàn)出了美麗的湘江景色。在第一部分的散板當(dāng)中,雖然沒(méi)有固定的節(jié)奏節(jié)拍,但是在演奏時(shí),仍然要體現(xiàn)出湘江水連綿不斷的意境,以及積極陽(yáng)光的情緒。
在第二部分如歌的行板當(dāng)中,主要通過(guò)彈奏者左右手的配合完成演奏,主要聲部不單局限于右手,更加要突出左手的顆粒性與連貫性,為聽(tīng)眾營(yíng)造出一種湘江泛舟的輕快美好之感。
三搖和快速指序的許多特殊指法技巧,這些可以說(shuō)是王中山改編版本中十分重要且具有鮮明特點(diǎn)的地方,尤其是第106小節(jié)開(kāi)始的快速指序部分,保留了原作當(dāng)中的竹笛特有音色,同時(shí)將古箏指法做了系統(tǒng)規(guī)范的整理和確認(rèn),在演奏的時(shí)候,情緒熱烈歡快,并且十分穩(wěn)定快速。
在最后一部分的散板中,也就是尾聲部分,與開(kāi)頭的散板遙相呼應(yīng),體現(xiàn)了中國(guó)民族樂(lè)曲的傳統(tǒng)特色,給人以蕩氣回腸之感。前三小節(jié)舒暢自由,第177小節(jié)做了一個(gè)回原速的處理,并且將主旋律放在了左手上,在最后有一個(gè)強(qiáng)有力的收束,顯得整首樂(lè)曲干脆利落,可謂是一大亮點(diǎn)。
(二)具體演奏技巧的介紹
在演奏引子部分時(shí),最開(kāi)始的進(jìn)入要由弱漸強(qiáng),甚至要從無(wú)聲開(kāi)始,在前倚音35的時(shí)候要體現(xiàn)出一種清脆感,宛若湘江岸邊大樹(shù)枝頭的清脆鳥(niǎo)叫聲。之后的搖指1和6要逐漸增強(qiáng),有一定爆發(fā)力,為后面的整體樂(lè)曲情緒作鋪墊。第4小節(jié)的小撮3、6、1,要伸長(zhǎng),與琴弦足夠接觸,并且充分要體現(xiàn)琴弦對(duì)甲片的反彈,體現(xiàn)張力。值得一提的是,在第6小節(jié)當(dāng)中,有一個(gè)獨(dú)創(chuàng)性的勾搖技法,在搖指的同時(shí)使用勾指,增加了樂(lè)曲技法的豐富程度,同時(shí),#5也是本曲中極為體現(xiàn)湖湘音樂(lè)特色的代表性音符之一。
可以說(shuō),在引子當(dāng)中,包含有大量的前倚音,需要根據(jù)樂(lè)曲上下情緒作細(xì)微調(diào)整,但總體上要彈奏清楚,要有飽滿(mǎn)流暢的顆粒性。同時(shí),還有很多抹托的快速連續(xù)彈奏,不僅要入弦淺,更要運(yùn)用手腕的一定力量,使聲音更為靈動(dòng)有彈性。需要注意的是,在末尾的刮奏除了要按照譜例要求演奏,還要有強(qiáng)弱的變化,起初要朦朧輕巧,在后面的連續(xù)進(jìn)行時(shí),要漸強(qiáng),要體現(xiàn)出湘江水一浪緊接一浪的意境。

在如歌的行板當(dāng)中,前兩小節(jié)由左手彈奏,奠定整段的基調(diào)。在演奏時(shí),要注意“上行卡頭尾,下行彈貼同時(shí)”的技巧,由弱漸強(qiáng),也就是說(shuō),在進(jìn)行上行彈奏時(shí),小指和大指應(yīng)提前做好準(zhǔn)備,有助于下面的樂(lè)曲進(jìn)行;而在下行演奏時(shí),要彈完一個(gè)音再?gòu)椣乱粋€(gè)音,一指離弦,下一指馬上貼弦進(jìn)行彈奏,這樣可以使樂(lè)曲顆粒清晰,并且具有較好連貫性。在第20小節(jié)中,3和2的音有一個(gè)短小的輪指技巧,這樣的輪指技巧區(qū)別于長(zhǎng)篇幅的輪指,在王中山的作品中經(jīng)常會(huì)有這樣單音的一組短促輪指,增加了作品音樂(lè)的豐富性和靈動(dòng)感的同時(shí),并沒(méi)有帶給欣賞者過(guò)多的冗雜感。在左手按滑音的時(shí)候,要注意上滑及下滑音高的平均分配,4個(gè)音的音高要由弱漸強(qiáng),不能一概而論。
在23小節(jié)至39小節(jié),是一個(gè)俏皮曼妙的過(guò)門(mén),運(yùn)用了輪指、顫音、三指搖等豐富的技法,演奏時(shí)要銜接緊密,為之后的快板預(yù)留下了一個(gè)想象和呼吸的空間。

在第三部分,歡騰地快板當(dāng)中,速度和力度有了非常明顯的提高。這里是全曲最為精彩和奪目之處,一方面是湘江河水的歡快流淌,另一方面烘托和描繪出了湘江人民鼓足干勁、滿(mǎn)腔熱血建設(shè)家園的激動(dòng)景象。40小節(jié)到43小節(jié)的左手運(yùn)用了止音技巧,即彈即止。45、46兩小節(jié)的左手小撮一定要由弱漸強(qiáng),練習(xí)時(shí)要注意找弦的準(zhǔn)確性。62、63小節(jié)中,王中山創(chuàng)新性地將小撮指法一變而為勾指和抹指結(jié)合指法,輕巧且符合人體習(xí)慣。第67小節(jié),左手運(yùn)用了彈完后止的方法,與之前即彈即止的干脆利落不同,它增加了一種厚重感,與71小節(jié)輕盈的聲音形成了有趣的對(duì)比。
快板當(dāng)中的81小節(jié)開(kāi)始是十分具有特色的卡農(nóng)模仿,運(yùn)用了復(fù)調(diào)對(duì)位的方法,左右手相差一小節(jié)和一個(gè)八度,左手低八度演奏時(shí),音響特色要與右手相同,展現(xiàn)出一種歡欣熱烈、追逐嬉鬧的氛圍,快板的第105小節(jié)開(kāi)始,選自竹笛曲最著名的部分,在原曲4中,是由笛子吹出的接連不斷的長(zhǎng)音,在演奏時(shí)要嚴(yán)格遵守譜例上的指法標(biāo)記,左手的低音配合要有力堅(jiān)定,營(yíng)造出一種穩(wěn)健激動(dòng)的感覺(jué)。同時(shí),在練習(xí)和演奏時(shí),要將每一個(gè)音都扎實(shí)地彈出來(lái),顆粒要飽滿(mǎn)清晰,上下要足夠流暢連貫。

第四部分的散板,其實(shí)不是嚴(yán)格意義上的散板,在進(jìn)入176小節(jié)時(shí),又重新回到了原來(lái)的速度。在散板與引子相呼應(yīng)的同時(shí),左手成了主旋律,仍然使用快速指序的技巧,右手搖指要始終保持強(qiáng)搖,激動(dòng)有力。最后的刮奏、止音和右手彈奏均要保持,結(jié)尾是一個(gè)強(qiáng)有力的結(jié)束,使人意猶未盡、蕩氣回腸。
三、特殊技巧及指法練習(xí)需注意問(wèn)題
全曲為竹笛改編曲,在移植原有竹笛曲的同時(shí)具有極大的創(chuàng)新之處,很多段落及樂(lè)句采用了革新性的演奏方法。
輪指運(yùn)用的主要是右手的打勾抹托四指,在以往的彈奏中,主要運(yùn)用勾托抹三個(gè)指法,輪指不僅有創(chuàng)新性的音色,更是平均了四根手指的力量,演奏時(shí)要均勻發(fā)力,顆粒清晰飽滿(mǎn)均勻。
勾搖是在搖指的基礎(chǔ)上,運(yùn)用勾指,這樣既不影響搖指的連貫性,又添加了新的音色,增加了樂(lè)句的豐富程度。
三指搖,由大指搖發(fā)展而成,同時(shí)使用抹指和勾指,小臂帶動(dòng),三指固定好角度,同時(shí)彈奏,構(gòu)造出一種特殊的和聲效果,這在以往的箏曲中是絕無(wú)僅有的。
快速指序,彈奏時(shí)要注意與琴弦的接觸,指尖觸弦、平面觸弦,手指應(yīng)感受琴弦?guī)Ыo演奏者的對(duì)抗力,每一個(gè)音都要有清晰真實(shí)的發(fā)聲,不要提前貼好琴弦,而應(yīng)該快速、準(zhǔn)確的彈奏,并及時(shí)離開(kāi)琴弦,生動(dòng)有力。
小指勾弦,在古箏中,只有小指是沒(méi)有甲片佩戴的,因?yàn)樵谕踔猩降挠^(guān)念中,要有“肉聲”,也就是最原始、獨(dú)特的聲音,利用小指與琴弦的直接接觸,給人不同的感覺(jué),沉穩(wěn)有力。
無(wú)論是樂(lè)曲的演奏還是基本功的訓(xùn)練,都離不開(kāi)對(duì)力的使用,包括手腕、小臂以及手心在內(nèi)。
無(wú)論是右手的彈奏還是左手的按弦等技法,都需要手腕及小臂的能動(dòng)配合,對(duì)于練習(xí)時(shí)手臂起到穩(wěn)定及支撐的作用,演奏時(shí)不能過(guò)于僵直,以免造成重心轉(zhuǎn)換的不及時(shí)從而影響演奏效果。手腕要保持自然流暢的弧度,避免因角度過(guò)大或過(guò)小產(chǎn)生的屈曲或后伸,同時(shí)要保持松弛和靈活,不僵化和歪扭,始終將手臂和手腕保持在一種放松、能動(dòng)的穩(wěn)定狀態(tài)之中。
傳統(tǒng)的演奏運(yùn)用到的手心以八度演奏為主,手指間的間距較大,在演奏“勾托”和“大撮”等技法時(shí)往往需要手心有足夠的支撐,這樣的演奏在慢彈時(shí)聲音飽滿(mǎn)、穩(wěn)定并且十分清晰,但是在演奏達(dá)到一定的速度時(shí),卻多了張緊的力量而少了靈活性。在王中山的新指序技法當(dāng)中,手心的發(fā)力及力量訓(xùn)練不同于以往,手心除了擁有張力來(lái)控制平衡,需要減少其緊張性,更重要的是有伸縮性,在快速演奏中不但要采用傳統(tǒng)的“倒垂蓮式”演奏,更要使用半握拳的手形,充分利用好琴弦對(duì)手指及手掌心的反作用力,順勢(shì)而為,當(dāng)大撮銜接的是八度之內(nèi)的抹指或托指時(shí),利用琴弦的阻力順勢(shì)進(jìn)行手心的收縮,當(dāng)抹指銜接大撮時(shí),要使琴弦的阻力對(duì)手心產(chǎn)生張緊效果,以此循環(huán)往復(fù),使手掌的位置始終保持在一個(gè)穩(wěn)定的小范圍內(nèi),可以明顯感覺(jué)到演奏速度的提升。
四、肢體語(yǔ)言的特別呈現(xiàn)
動(dòng)作是語(yǔ)言的補(bǔ)充和延伸,同樣,在演奏當(dāng)中,有許多感情不足以單純通過(guò)音樂(lè)來(lái)準(zhǔn)確表達(dá)。尤其在聽(tīng)覺(jué)藝術(shù)逐漸向視聽(tīng)雙重藝術(shù)轉(zhuǎn)化的過(guò)程中,舞臺(tái)表現(xiàn)便成為與觀(guān)眾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演奏前,坐姿要挺拔,腰松背緊,左腳置于右腳之前,這樣在演奏時(shí),可以穩(wěn)定地轉(zhuǎn)換重心,協(xié)調(diào)連貫。左右手掌心相對(duì),分別置于琴碼和岳山兩側(cè)。
在結(jié)尾的刮奏時(shí),不能毫無(wú)章法,隨心所欲地刮奏,而要由弱漸強(qiáng),富有層次感,最后的琶音在彈奏結(jié)束之后,仍然要保持大臂對(duì)手的帶動(dòng),營(yíng)造出一種聲音連綿不斷的美好意境。
在行板中,左手描繪了湘江人民建設(shè)家園的歡騰景象,右手的搖指宛若連綿不斷的湘江水。彈奏時(shí)要如同泛舟湖中,身體仿佛隨船兒輕輕擺動(dòng),給人一種身臨其境之感。快板中的止音,要將手掌側(cè)面全數(shù)砸下,干脆利落,大有氣勢(shì)昂揚(yáng)、大干一場(chǎng)的畫(huà)面感。尾聲的結(jié)束依然是延續(xù)之前的快速演奏,氣勢(shì)浩大,用全身的力量收束,演奏最后的刮奏和大撮時(shí)要身體前傾,將重心調(diào)整到前側(cè),給人以酣暢淋漓之感。這樣方能結(jié)束全曲,達(dá)到完美的舞臺(tái)效果。
結(jié) 語(yǔ)
在古箏改編作品中,王中山的曲目是及大成之作,既保留了原作的精華和亮點(diǎn),又完美地表現(xiàn)出古箏的張力。在作品的演奏中,有各個(gè)因素影響,有演奏技巧的嫻熟、對(duì)音樂(lè)語(yǔ)言的把控、甚至是對(duì)現(xiàn)場(chǎng)的臨時(shí)掌控能力。要求所有演奏者具有專(zhuān)業(yè)、深厚的演奏技巧的同時(shí),更是要有足夠的人文素養(yǎng)和理論功底,如此才可以精準(zhǔn)領(lǐng)會(huì)創(chuàng)作者的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