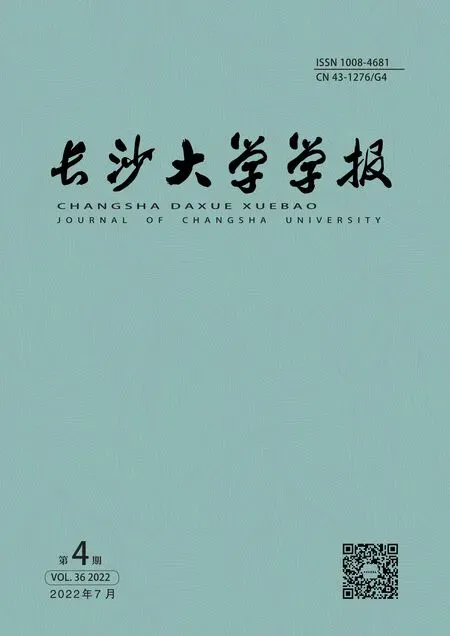基于感知習得理論的多媒體二語語音學習模式
周麗,胡偉,胡珍銘
(1.長沙學院外國語學院,湖南 長沙410022;2.長沙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南 長沙 410114)
基于行為主義的對比分析假設是二語習得研究的里程碑,但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生成音系理論被廣泛地用來構建中介語音系表征和解釋二語語音習得過程。近二十年來,現代音系學變得越來越包容,對現象的解釋越來越倚重感知、發音等功能—語音因素[1]。這種趨勢也體現在二語音系習得研究中:一些基于感知的二語語音習得模式對學習者發音的母語遷徙效益的解釋由抽象的音系層面回到了可觀測、可感知的聲學—聽覺層面,這種從形式主義向行為主義的范式轉換,可以看成沉寂多年的對比分析假設的某種回歸,只是此時的對比分析假設已經被賦予了新的內容與生機。我們將以學術史梳理的方式,闡述對比分析假設與基于感知的語音學習模型的理論淵源,并在多媒體語境下探討更合理的二語語音學習模式。
一 對比分析假設
Lado 的對比分析假設在語言學、行為主義哲學和外語教學之間搭建了橋梁。對比分析假設是指通過對比學習者母語和目標語各語法領域,找出它們之間有差異的結構特點,并憑此預測學習的過程中學習者將犯的產出錯誤。母語遷徙一直是二語習得研究的重點,對比分析假設對此的解釋是:母語和目標語相同(似)的結構有助于學習,相異的結構則有礙于學習,并導致學習者的產出錯誤。結構的差異首先是表征上的,如日本人往往將英語中的ride 讀成lide,因為日語的音段庫里沒有[r][2]。其次是因規則的不同引發的產出錯誤,如德國人很難學會加拿大英語的提升規則即[a?]在濁輔音前變成[??],是因為德語中的音節尾輔音清化規則的干擾。必須指出,在以行為主義為指導的對比分析假設中,無論是表征的差異還是規則的不同,都是可觀測的,是直觀的經驗總結。
二 中介語假設與形式主義二語習得研究范式的缺陷
(一)形式主義的中介語研究與語言教學實踐的分裂
行為主義的語言習得觀遭到了喬姆斯基的批判,他認為語言習得不是人與環境互動的產物,而是人類天賦的內在語言能力的外延。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學習者對目標語各階段性的認識都還不被認為是語言系統,但喬姆斯基1966 年在美國西北語言教師協會上發表講話后,中介語和學習者的心理表征成了二語習得研究的重心。Selinker 正式提出了中介語假設,指出二語學習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中介語和任何自然語言一樣是不斷演化的語法體系,演化的驅動力是獨立于母語、目標語之外的語言的內在機制[3]。
上述二語習得研究范式更替發生在美國形式語言學蓬勃發展的時期。形式主義的生成音系學中規則與表征是不可分的整體,規則是表征的一部分,所以在形式主義看來,一、二語的結構差異實質上都是表征的,因而也是抽象的、可形式化的,這是中介語假設產生的基礎,也使得隨后數十年的二語習得研究天然地傾向于形式主義。就音系習得而言,既然中介語音系是抽象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結構表征,可觀測到的學習者的語言表現就可以用來證實和證偽某一音系表征模型及其制約性原則。這種思想指導下的研究數十年來一直是二語音系習得研究的主流。相比之下,對學習者的語音表現(特別是錯誤)的研究被邊緣化,從對比分析到中介語理論的范式更替導致了二語研究與語言教學實踐的分裂。
(二)形式語言學理論體系中二語習得學科的不利地位
以形式主義為指導的中介語研究還導致該學科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二語習得在行為主義的對比分析盛行的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并不是一門真正獨立的學科,確實是形式主義的興起和介入使之成了一門獨立的語言學學科。但深受形式主義影響的二語習得學科并沒有因此獲得與音系學、句法學平等的地位,反而成了它們的附庸。很多二語研究只管描寫,實驗設計得再精妙,數據分析得再細致,也只是為了得到經驗證據,至于對經驗的解釋,都交給了音系學、句法學的各類理論假說。可以說,除了試圖探索二語學習者在習得各階段的表征體系和各階段聯系的中介語假說之外,二語習得自身沒有提供任何解釋性的理論模型。這種情況很像Lightbown et al.提到的語言習得研究發展的奇怪循環——研究從數據驅動型經過一個似是而非的理論導向時期后又回到了數據驅動的狀態[4],即便提出過一些假說,如表征缺陷假說[5],也僅是對數據歸納結論的表述。
(三)形式主義高度抽象的中介語表征的問題
盡管最初對比分析與中介語假設是根本對立的(前者以行為主義心理學和結構主義語言學為理論依據,后者以心智主義和形式主義語言學為指導),但二語習得研究近四十年的發展說明中介語假設并非專屬于形式主義,它是一項被各派學者廣泛接受的學說。中介語是客觀存在的、獨立的語言體系,也是不斷向著目標語法發展的,由各階段表征體系組成的動態過程,此乃各派之共識。各派的分歧在于,中介語的表征抽象程度和它與諸多外部因素的互動特點。形式主義者認為,中介語既然由抽象結構表征、普遍原則構成,那它本身就是演繹系統,具有推導和解釋的功能。這本與形式主義提出的理論模型應同時具備描寫和解釋功能的觀點不違背,但問題在于其高度抽象性和排外性,這種抽象性和排外性使其無力回答一些如豐富的個體差異等現實性問題,以及各中間階段表征體系之間如何過渡的問題,即過渡段可以是一個多種形式呈自由變體的階段等理論問題。此外,抽象、排外的中介語在對學習者產出錯誤的解釋上也易趨于簡單化。如用中介語缺乏“時態”的形態表征的假設來解釋中國學生為何常將動詞過去式讀成原形[5],這個觀點后來飽受質疑。顯然,更深刻的解釋必須依賴結構描寫或表征之外更深刻的機制——基于感知的二語語音習得模式。
三 基于感知的二語語音習得模式
(一)基于感知的二語語音習得模式的原理
現代語音學認為如某音段在不同的語音環境中擁有的音征數量(number of cues)和凸顯性(saliency)不一,可以比抽象音系表征(也包括規則)更好地解釋共時、歷時語音變化,語言習得等諸多語言現象。
二語語音習得研究越來越傾向用基于語音的模型來解釋學習者的產出錯誤,或概括階段性的中介語法。這些研究認為至少在學習初期,母語的音系對立嚴重影響著學習者對聽到的目標語語音信息的規整和范疇化,這種感知過濾往往帶來錯誤的音系規整,形成對目標音系的錯誤解讀進而影響學習者的語音產出[6]。顯然這些研究都直接繼承了對比分析假設,只是將學習者發音的母語遷徙效益的解釋機制從高級的抽象結構(表征)層面向低級的、可觀測的聲學—聽覺層面的轉移。目前影響最大的兩個理論是Flege 的語音學習模型 (Speech Learning Model,SLM)[7]和Best的感知同化模型 (Perceptual Assimilation Model,PAM)[8]。
(二)語音學習模型
SLM 為闡釋對比分析假設的遷徙效果提出了全新的概念——“等同歸類”[7]:導致學習的困難是母語和目標語的相似性而非差異。該理論認為,在音段學習中,目標語音的聲學參數以及其在母語語音聲學空間的統計分布決定聽音人對目標語語音的感知,由于母語中與目標語某元音在以第一、第二共振峰為軸建立的元音聲學圖上的空間位置非常接近,學習者錯誤地將該母語音段投射到該目標語音段,使其未能正確地設立新的音位范疇,而導致產出時的語音錯誤。如西班牙人將聽到的英語[?]歸為音位[i],故將[?]發成[i][9]。
但簡單的一、二語音段對照不能解釋很多經驗觀察。Katsura 讓日本學生和韓國學生聽辨英語[m,n,?]分別在音節首尾的對立,發現日本學生對音節尾[n,?]的辨別格外困難,這用音段相似度就解釋不通[10]。通過比較,他們排列出了三個鼻音彼此間的相似度:[m]與[n]之間的相似度最高,[m]與[?]其次,[n]與[?]最低。但根據SLM 的預測,相似度低的[n,?]應該最不會引起聽者的錯誤投射,也因而最好辨別。另外,SLM沒有考慮各類音征在感知中可能相互影響。Ingram et al.研究了日、韓學生學習澳大利亞英語的前元音的情況[11]。澳大利亞英語中松緊元音的區別主要是音質(一、二共振峰值),但時長也是重要語音參數,除[?]外,其他松元音都有相對應的緊元音,而緊元音明顯比松元音長。日語的長短元音有區別(音位)意義,韓語沒有長短元音的對立,因此日本聽者將會更容易察覺目標語中的松緊元音在時長上的語音或非音系的差異。如果按SLM 的預測,日本學生會將母語中與[?]在元音聲學—感知空間上位置最接近即音質上最相似的[e]來替換之。但產出試驗證明除[e]替換或同化[?]的格式外,日本學生更多地采用[a]同化[?]的格式。這顯然是日本學生同時運用共振峰值和時長兩個維度的感知信息的結果,因為在時長上[?]和[a]比[?]和[e]更為接近。
(三)感知同化模型及其與語音學習模型的區別
Best 的感知同化模型提出了三種音段感知同化格式[8]。第一,范疇對范疇的感知同化:母語有兩個不同的音位分別同化或替換目標語的某對音位時,聽者(即學習者)區分這對音段最容易。第二,非范疇對非范疇同化:當兩個目標語音位被同化為一個母語音位時,它們的可辨度最差。第三,非范疇對范疇同化:兩個目標語音段中一個同化為母語的某一音位而另一個同化為母語的某音位的一個變體時,學習者也不難區分它們。日語中[m]是范疇(音位),[n]或[?]是[N]的音位變體而非范疇,所以對日本學生來說,英語音節尾[m]vs.[n]和[m]vs.[?]的對立均屬非范疇對范疇同化,不難辨別。但音節尾[n]vs.[?]的對立屬于非范疇對非范疇同化,最難區分。Katsura 的試驗結果符合PAM 的預測[10]。
PAM 與SLM 的另一重要區別就是PAM 認為母語、目標語某音段感知上的異同與特定音姿(如圓唇或升降舌體等動態指令)一一對應,直接關聯,中間不需經過任何心理解讀。在對語音輸入的感知過程中,學習者(無論是成人還是兒童)逐漸將各類音征一一整合成與音姿耦合的知覺對象,即在認知中建立音姿和知覺對象的內在聯系。感知和產出共享一套有公約性的發音和聽覺參數(或特征)。因此在具體研究中,PAM 堅持產出試驗得到的聲學數據能夠直觀地反映出學習者在聽辨試驗中采用的感知特征。
從目前我們掌握的文獻看,PAM 比SLM 有優勢:首先,PAM 能更準確地預判對目標語音段的替換或同化格式;其次,PAM 堅持感知的發音基礎,音征和音姿的耦合,為在感知過濾中多個語音特征同時作用提供了可能。但我們必須指出,無論是音征和音姿的一體化,還是各特征交互作用的具體機制,都有待探究。
四 基于多媒體的語音教學模式
(一)多媒體語音教學模式的認知基礎
多媒體中的媒體指的是學習者和新信息交互的渠道。Mayer 的雙渠道假設認為人類的信息處理系統包括言語處理系統和圖像處理系統,這兩個子系統獨立地處理兩類信息[12]。Mayer 認為,在多媒體條件下,各種信息表征鄰近且連貫,學習者能更好地建立各表征間的聯系,這就是空間連貫原則。同時,多類媒體信息被同時而非斷續地呈現給學習者,使學習者在工作記憶中同時擁有多類表征,因而更容易建立和保持圖與文、視覺與聽覺的心理聯系,這就是時間連貫原則。
我們認為,多媒體學習的認知過程可以概括為理解、攝入和整合三個依次進行的環節:理解是指在工作記憶中對輸入材料進行初步加工,所形成的可理解的輸入和反饋再分別進入視覺和聽覺渠道,便開始了攝入過程;攝入的信息在工作記憶中形成文字、聲音、圖像的心理表征后,就需要在這些心理表征間建立互參的聯系,這就是整合;整合后的知識結構或表征已經進入長期記憶,成為學習者中介語法的構成部分。
因此,多媒體語音教學模式能結合聽覺和視覺兩個反饋渠道和建立視、聽的心理聯系,是提升語音學習效率的有效手段。
(二)多媒體語音教學新模式
圖1 是新的基于感知的多媒體語音學習模式,其工作原理如下。首先,各類輸入材料在工作記憶中初步加工后產生最初的語音產出。這類輸入材料包括:發音語音學、聲學語音學基本知識,比如對發音部位、發音方法的了解,對常用聲學參數的了解和英語音段在語圖上的識別等;對目標語(英語)音系的掌握,尤其是音位變體和音變規則(如閃音化、三音節松化)的了解,接下來是多媒體的認知過程,在這一環節,視、聽覺的反饋開始發揮關鍵作用。語圖上的相關聲學參數、標識和學生對標準音以及自己發音中相關音征的聽覺感知,能清晰地提醒學生注意自己的發音和標準音的差別,從而有力地推進感知與音姿的耦合過程。修正后的語音產出再次形成新的視、聽覺反饋,整個學習過程便開始下一個循環。例如湘方言區學習者受母語影響,在學習區分[l]和[n]時容易混淆,這兩個音聽感相近,學習者僅憑聽易產生困惑。通過圖1 所示的基于多媒體的訓練,[l]與[n]不同的音征在語圖上有清晰的體現,這樣的反饋可以幫助學習者認識自己的產出錯誤,使其更容易注意到[l]與[n]在聽感上的差異,把握這種差異的特點,同時不斷地調整發[n]或[l]時的音姿,并逐漸在認知中形成兩個有區別的、與不同音姿耦合的感知項。

圖1 新的多媒體語音學習模式
(三)多媒體語音教學新模式的開發與運用
目前,可視化語音教學穩步開展。基于感知的語音習得模式和多媒體學習的性質、特點吻合,加上聲學語音技術、平臺、程序也比較成熟,很多便攜商業軟件被開發推廣。比如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問世的CALL(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該軟件一直沿著感知精度與交際自然度最大化的方向發展,技術已相當成熟,可與手機應用程序兼容。此外,開發始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SpeechViewer 更側重超音段和口語整體表現的提高。這兩項技術在國外運用得比較廣泛,但在國內的推廣因產權等問題而受阻。在中國很多高校的語音教室里,安裝的多媒體教學系統中多帶有ASR(自動語音識別)技術,這主要是因為ASR 技術已無獨立產權。但該技術在各類高校中的運用情況還有待廣泛調查;如何盡快開發出適合我國國情的便攜軟件程序,來實施多媒體、可視化的二語語音學習,也是將來的重點工作。
綜上所述,通過持續地向學習者輸入可視語圖反饋(音征)和其他模式的知識,提醒其注意自己的發音與目標的偏差所在及偏差有多大,訓練其逐步調整發音—感知匹配,無疑是二語語音學習領域的不可逆趨向,也預示著對比分析假設將在新時代技術背景下持續彰顯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