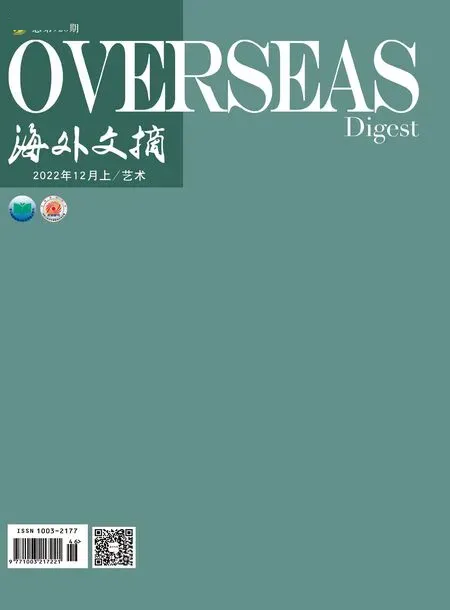箕子東渡與中原文化的傳播
□姚舜禹/文
箕子生活在商代末年,面對紂王的奢靡荒淫,他諫之無果,乃披發佯狂,隱而鼓琴以自悲。周武王滅商,造訪箕子,意欲請其歸服。箕子不予合作,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仆”,遠涉千山萬水逃往朝鮮,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也。殷商遺裔孔子尤為尊崇箕子,將之推崇為殷之“三仁”之一。《論語》有載: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以箕子自況,九夷之地如此落后蠻荒,箕子可安然居之,那么自己也可適之。又,孔子曾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春秋時代,須桴槎方可至之夷地,應特指朝鮮。孔子周游列國,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終不得實現,與當年箕子的處境何其相合,因此,他滿懷憤懣與遺憾,欲效法先賢箕子,離開華夏,遠適夷地,故出此言。箕子的東渡使得中原文化傳播至朝鮮半島,開啟此地深受華風熏染的序幕。
1 中原史書里的“箕子東渡”
《周易·明夷》有言:“箕子之明夷,利貞。”《尚書·微子》則記載,“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仆。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在之后的書籍中也可見箕子的事跡。
《尚書大傳·洪范》:“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也。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
《漢書·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后漢書·東夷傳贊》:“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
《三國志·魏書·東夷傳》:“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為盜。”
從上述按時間順序排列的記載中可以看到,對于箕子的敘述,最初的《周易》《尚書》本無對其品行的評價,僅有言行記載。最先為箕子冠上“仁賢”之美譽的是孔子,自孔子以后,對于箕子的稱贊之辭大量出現,不勝枚舉。后世的贊譽主要圍繞著三方面展開,概括而言,即柳宗元在《箕子碑》中提到的“正蒙難”“法授圣”“化及民”:
其一,箕子本人的道德品行——“正蒙難”。箕子雖身罹禍患,仍懷持仁心,為天下蒼生憂慮,“內難而能正其志”,韓愈還在孔子的褒揚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出了“非止商三仁也,蓋萬世之仁”。有今人考證,箕子的“子”是對作為“思想家”的箕子的敬稱[1]。
強調這方面的主要是儒家學者,多見于先秦經典的闡釋性著作中。不過,也有不同聲音,如成書于西漢的《戰國策·范雎說秦王》篇,范雎便直言,“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發而為狂,無益于殷、楚。”但此類負面評價非常少見,而且出現年代相對較早。越是到后世,對箕子越是清一色的正面、高度評價。孔子被后世儒家一步步尊封為圣人,箕子“榮膺”的“萬世之仁”的評價,也是相同的理路。
其二,箕子向周武王傳授“洪范九疇”。這是箕子提出的治理國家的政治理論,在此不贅述。
其三,箕子的東渡之舉——“化及民”。箕子遠赴蠻荒之地,為邊夷帶去了中原的先進文化和生產技術,立下了傳播禮樂、教化蠻夷的大功。這種說法大多是史書所記載的,不但中國史書如此,古代朝鮮半島政權所編纂的史書,也一致將箕子作為這片地域的文化的濫觴。
2 箕子“東渡”動機
關于“箕子東適”一事的闡釋,歷來大抵不外乎幾種說法:《尚書大傳》的說辭“不忍周之釋”,不愿臣事于周;《史記》的說辭“武王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也”,是受周之封;兩《漢書》的說辭“殷道衰、違衰殷之運”,為避紂王之暴政,續殷之祀。在此之外,當代研究者又指出了受到東北地區外族勢力發展的威脅因素。
還有一種解釋,即生于殷商末世的箕子深感“道”之不行,面臨國家滅亡,才走之朝鮮,建立政權,以實行其“道”,使國家大治,成為東方君子國[2]。箕子面臨的現實是武王克商、岸谷之變,箕子之“道”無法伸于中原,他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之政”,因而遠避海外,至蠻夷之地“教其民以禮義”,這在邏輯上確實是通順的。另外,《史記》記敘的箕子答周武王有關“常倫所序”的長篇大論,也可見箕子心懷宏遠的治國理念。在他身處的時代,紂王暴虐不恤民生,而周王朝之于他又隔著滅國之恨,于是,箕子希望在海外不受約束的地方開辟一個可供自己和族人棲身的地方,也是符合情理的。再結合后續記載,箕子確實在朝鮮進行了一系列移風易俗的舉措,遺惠后人,他本人也被尊為朝鮮之地的文明開化之祖。
誠然,箕子至朝鮮,帶來了中原王朝的禮樂教化,但是,這能夠說明箕子的本意確為“教其民以禮義”即實現自己的“道”嗎?
孔子所抒發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后人更多是從“孔子的隱逸思想”的角度來解釋,抑或評價其“進可推行主張,退可歸隱,可進可退”[3],而不是被單純地理解為“孔子希望去海外施行自己的‘道’”。箕子和孔子所面臨的處境有相似之處,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對照看待。以孔子的心態來類比箕子,便會覺得箕子僅僅是為了“實現大道”才遠渡海外的說法,有些許存疑之處。
從原始史料入手探究箕子東渡的原本動機,成書最早的《周易》和《尚書》中并沒有明確的表述。《周易》相關記載過于簡略,沒有前因后果;《尚書·微子》篇中太師的話語,應該是兩《漢書》所采的“違衰殷之運”即為避紂王之暴政之說的來源。此處,太師勸微子為自己的族人考慮,為延續殷商社稷而出逃,這個緣由更接近箕子的本意,國之將亡,無法挽救,出逃止為避禍而存延殷祀耳。而“實現大道”云云,或許箕子是有懷揣著這樣的想法,但不是主要的。將箕子東渡的動機全部歸于“實現大道”,未免失于偏頗。
據《史記·宋微子世家》,箕子對微子言:“天篤下災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史記》這一段箕子之語,其史料淵源很明顯是《尚書·微子》。但是,“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云云,于《尚書》并無依據。因此,日本儒學者中井積德指出,后面的這些話語“與上文不相肖,蓋太史公擇取書意而自言之也。[4]”在這里,司馬遷對箕子東渡的動機進行了第一次“制造”,箕子的人物形象中首度出現了“治國”這一關鍵詞。對于這個現象,學者認為,“司馬遷的補筆大多是為了使其傳文細節更為豐滿,人物形象更為突出,故雖于史無據,卻契合情理,是其文學想象力得以馳騁的重要空間。[5]”而兩《漢書》的記載已是漢武帝于朝鮮置四郡之后的事了,此地現在的民風教化為中原所知,自然會往上追溯,直至追溯到箕子時期,箕子朝鮮所推行的一系列舉措便被從“結果”反推成了“原因”。
3 箕子的歷史定位
有關箕子其人的歷史定位問題更主要體現在朝鮮的史書文集中。不僅中國史書強調箕子對于朝鮮的教化之功,朝鮮半島歷代王朝也津津樂道[6]。對于朝鮮半島政權而言,箕子所建立的箕子朝鮮政權的意義更為重要,他們認為,箕子到來之前的朝鮮半島雖已有生息,但尚未開化,完全算不上“文明”;直到箕子東渡,帶來中原禮樂,才是朝鮮文明之起始,所謂“本國之有箕子,猶中國之有帝堯[7]。”
箕子來自中國,且在中國的文化史與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儒家極為尊崇的“圣人”,他存在的意義,是使得朝鮮半島有一個可以與中國遠古圣人相提并論的“開國之君”,推崇箕子,自然就順理成章地提高了朝鮮自身的文化地位。奉行事大主義、世慕華風的朝鮮半島政權歷來仰中國為本位,自認為中國的分支即所謂“小中華”,因此,他們對箕子的崇拜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發濃重[8]。
高句麗時期,箕子已被冠以“朝鮮始祖”之稱,被當作神明來崇拜、祭祀。高麗年間,傳說的“箕子之墓”在平壤府被挖掘發現,高麗國王立刻“令平壤府求封箕子墳塋,立祠以祭,又建箕子祠于平壤”。沒過多久,忠肅王七年,“以箕子禮樂教化自平壤而行,令平壤府修祠致祭”,其重視程度可見一斑,箕子的形象已然被神化。高麗朝金富軾的《三國史記》記載“箕子受封于周室”,僧人一然在《三國遺事》也記載了“周虎[武]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鮮。”至李成桂推翻高麗王朝、建立新政權后,向當時的明朝請賜國號,備選項之一就是“朝鮮”。朱元璋擇此名賜之,從此,朝鮮王朝便將自己與明王朝的關系定義為“箕子朝鮮與周王朝”的關系:“今天子賜號之恩……與武王之封箕子、箕子之治朝鮮同一揆也。”想方設法將兩國關系比附作周與箕子朝鮮,以建立自己民族的認同感。
明清鼎革之際,朝鮮掀起了“尊周思明”的思潮,對于箕子的崇拜在這個時期發展到頂峰。儒學者柳麒錫言,“朝鮮始國于唐堯之世,有與于涂山之會。而及箕子來君,則以敘九疇之見,有設八條之教,為辟小中華。”他就將箕子東渡的目的直接定為“為辟小中華”。箕子在朝鮮半島的政治化色彩非常明顯,它脫胎于中國儒家學者對于箕子“圣人化”的形象制造,更強調它的政治性作用。“箕子崇拜使朝鮮在中華世界體系中找到一個特定的位置”,因此,箕子其人在朝鮮半島會如此受到重視。作為最典型的“中原文明”的代表符號之一,箕子是朝鮮王朝政權合法性的淵源,還是朝鮮以“小中華”身份自居的必要證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古代的朝鮮半島、尤其是朝鮮王朝被拔升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
箕子形象在后世的塑造中一步步豐富、完善,并且是通過我國與朝鮮的共同努力。除去客觀真實的歷史記載外,另一方面,也恐有后人想象的部分——史家文人根據現實需要,對箕子的形象做出自己的詮釋與定義。在這一過程中,箕子東傳華夏文明的功績一遍遍地被加以強調,形成了兩國共同的文化記憶。■
引用
[1] 陳浦清.論箕子的“子”不是爵位[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3(2):92-93.
[2] 張碧波.箕子論——兼論中國古代第一代文化人諸問題[J].北方論叢,2004(1):53-58.
[3] 王進鋒.海上交通與“乘桴浮于海”新證[J].中原文化研究,2021(5):99-105.
[4] 瀧川資言,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950.
[5] 程蘇東.失控的文本與失語的文學批評——以《史記》及其研究史為例[J].中國社會科學,2017(1):164-208.
[6] 孫衛國.傳說、歷史與認同——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之塑造與演變[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5):19-32.
[7] 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朝鮮太宗實錄卷23[M].漢城:韓國國史館,1961:638.
[8] 朱云影.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M].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