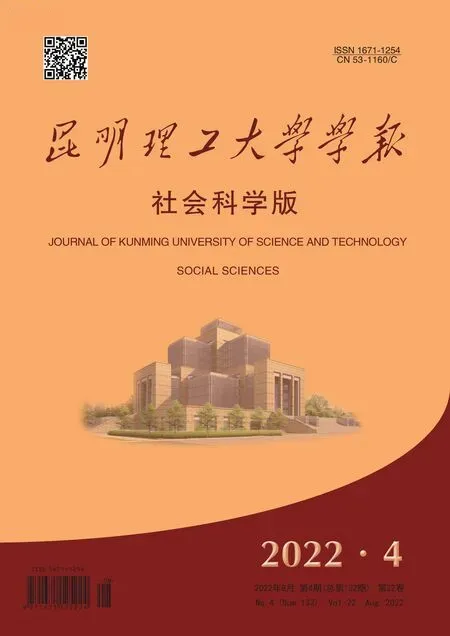政治性與民族性的有機統(tǒng)一: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辦學功能的歷史演進與形成依據(jù)
楊 柄,封海清,莊 玉
(云南師范大學 教育學部,云南 昆明 650500)
民族院校是黨的民族理論與政策的獨特產物,是我國高等教育不可缺少、獨具特色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族院校除了肩負普通院校的歷史使命外,還具有增進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tǒng)一、和諧民族關系、服務民族發(fā)展的特殊責任[1],并通過其作為高等院校的核心功能——人才培養(yǎng)來實現(xiàn),因而其人才培養(yǎng)也具有特殊性。但隨著歷史語境的變遷,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辦學功能遭遇了一定的質疑。如何正確延續(xù)與發(fā)揮民族院校在高層次民族人才培養(yǎng)方面的獨特地位,從而為民族院校在“雙一流”建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時代機遇中,在服務國家戰(zhàn)略、推動社會發(fā)展方面爭取更多話語權,是影響民族院校發(fā)展的重要因素。對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辦學功能的歷史演進與形成依據(jù)進行分析,是為了更好地發(fā)揮民族院校辦學功能,堅定民族院校辦學使命所做出的有益思考。
一、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辦學功能的歷史變遷
(一)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辦學功能的萌芽
滿蒙文高等學堂、蒙藏學校及延安民族學院是我國民族高等教育孕育階段中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學校。這些學校以專門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人才為其鮮明標志,為新中國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辦學功能的形成奠定了歷史基礎。
1.滿蒙文高等學堂:以造就滿、蒙、藏文專門人才為宗旨。成立于清末的滿蒙文高等學堂,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少數(shù)民族高等教育誕生的標志。1907年,為了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上層人士,清政府學部提議“仿照譯學館之例,另設清文專門高等學堂,以備中學堂升入此科,專心研究清文,務臻完備。”[2]次年,我國獨立設置的民族高等教育學校——滿蒙文高等學堂正式創(chuàng)立,其以“造就滿蒙文通才,以保國粹而裨要政為宗旨。”[3]14實際上就是一所造就滿、蒙、藏文專門人才的高等學堂。滿蒙文高等學堂培養(yǎng)了一批適應當時需要的少數(shù)民族人才,雖在內地辦學而未能向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發(fā)展,培養(yǎng)對象與方式也具有較多局限性,但它的建立為以后少數(shù)民族高等教育的發(fā)展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jù),具有重要的意義。
2.蒙藏學校:以開發(fā)、增進蒙藏青海人民之學識和文化為宗旨。1912年,負責全國少數(shù)民族教育事業(yè)的蒙藏事務局呈報大總統(tǒng):“請將前清所設景山、宗室、覺羅三學,及理藩部所設之蒙古學堂歸并改設蒙藏學校。”[4]北洋政府于次年設立蒙藏學堂,“以開發(fā)蒙藏青海人民學識、增進蒙藏青海人民文化”[5]2為其辦學宗旨,培養(yǎng)和訓練統(tǒng)治與管理少數(shù)民族的各種人員。其招生對象不分種族,但因西北閉塞而辦學,故重在多收蒙、藏、青海學生,名額分配為各蒙古占10/20,西藏占3/20,青海及其左近各回部占2/20,其余名額為漢滿兩族學生。蒙藏學校培養(yǎng)了管理民族事務的各類專門人才,成為民國政府對少數(shù)民族群眾進行國民身份塑造和民族國家意識統(tǒng)一的重要場所。
3.延安民族學院:以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干部為目的。延安民族學院是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辦的第一所少數(shù)民族干部學校。抗戰(zhàn)爆發(fā)后,為了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革命干部,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建立中華民族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1941年,中共中央在陜北公學民族部、中央黨校回民班、藏族班、彝族班的基礎上,并匯集延安其他高校少數(shù)民族學生,成立延安民族學院。延安民族學院創(chuàng)辦的目的鮮明,即在于進一步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干部,團結中華各民族,最終奪取抗戰(zhàn)的偉大勝利。它與滿蒙文高等學堂和蒙藏學校一樣,主要招收少數(shù)民族學生為主,分別招收漢、滿、蒙、回、藏、彝族、苗、東鄉(xiāng)8個民族的學生。在課程方面主要開設民族語文、民族歷史、民族理論與政策、民族經(jīng)濟等,體現(xiàn)了鮮明的民族特色[3]24。
(二)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辦學功能的發(fā)展
新中國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辦學功能雖在不同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表征方式,但其始終都以為少數(shù)民族與民族地區(qū)服務為旨歸,這也是民族院校的特色和優(yōu)勢。
1.以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政治干部為主導目的階段(1949—1978年)。新中國成立初期,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以及加強民族團結,需要大量的民族干部參與少數(shù)民族建設事業(yè),因而,此時民族院校以培養(yǎng)民族干部為主要任務。1950年印發(fā)的《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干部試行方案》,要求“為了國家建設、民族區(qū)域自治與實現(xiàn)共同綱領民族政策的需要,從中央到有關縣省,應根據(jù)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普遍而大量地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干部。”[5]1291951年,全國民族教育工作第一次會議強調,“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自己的干部是開展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各項事業(yè)的中心環(huán)節(jié),培養(yǎng)干部是現(xiàn)階段少數(shù)民族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務。”[6]此后,中央到地方各級民族學院先后建立,以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干部人才為其主要辦學目標。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近30年的時間里,民族院校的主要職責是開辦政治學校、開展干部培訓、培養(yǎng)民族干部,滿足民族平等團結事業(yè)建設的需要。
2.以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專業(yè)技術人才為主導目的階段(1979—1999年)。改革開放后,為滿足民族地區(qū)社會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的需求,民族院校逐漸轉變?yōu)榕囵B(yǎng)各類少數(shù)民族政治和專業(yè)技術人才的高等院校。1979年印發(fā)的《關于民族學院工作的基本總結和今后方針任務的報告》,要求民族院校要“大力培養(yǎng)四化所需要的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政治干部和專業(yè)技術人才,為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服務。”[5]159第一次把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專業(yè)技術人才擺在民族院校人才培養(yǎng)目標的突出位置。1983年,《關于民族學院干部輪訓轉向正規(guī)培訓的意見》[5]207及1993年《關于加快所屬民族學院改革和發(fā)展步伐的若干意見》再次重申并進一步提出民族院校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專門人才這一特定辦學定位[5]323。從政策文件的話語變遷中,可以看出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的重點逐漸轉移到了專業(yè)技術人才培養(yǎng)上,雖然民族院校人才培養(yǎng)目標的具體內涵發(fā)生了轉變,但其始終以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人才為宗旨。
3.以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高層次高質量人才為主導目的階段(2000—2011年)。進入新世紀,黨和國家越來越關注民族院校人才培養(yǎng)的質量與去向問題。為解決西部民族地區(qū)高層次人才稀缺的問題,自2004年開始,國家組織開展“少數(shù)民族高層次骨干人才計劃”,要求相關院校按照“定向招生、定向培養(yǎng)、定向就業(yè)”的原則,為西部民族地區(qū)培養(yǎng)具有較高科學人文素質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高層次骨干人才[5]422,至今已定向培養(yǎng)了數(shù)萬名碩、博研究生。此外,2005年印發(fā)的《關于進一步辦好民族院校的意見》,要求民族院校“以培養(yǎng)應用型專業(yè)技術人才為主,同時要高度重視培養(yǎng)復合型人才和民族類等特色學科的開發(fā)型和創(chuàng)新型人才。”[5]4732010年頒發(fā)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要求民族院校要提高辦學質量和管理水平,培養(yǎng)高素質民族人才[5]517。步入新世紀的民族院校人才培養(yǎng),在原有基礎上更講求人才培養(yǎng)的質量,以適應少數(shù)民族與民族地區(qū)發(fā)展的實際需要。
4.以立德樹人為根本的內涵式人才培養(yǎng)階段(2012— )。黨的十八大召開后,民族院校進入以立德樹人為根本的人才培養(yǎng)階段。2015年頒發(fā)的《關于加快發(fā)展民族教育的決定》,強調包括民族院校在內的民族教育要“以立德樹人為根本”“打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基礎”[7]。從高等教育人才培養(yǎng)的本質要求來說,立德樹人的根本要求是我國高等教育發(fā)展邏輯必須堅持的原則。民族院校作為我國高等教育重要的構成主體,概莫能外;從民族院校的特殊性來說,立德樹人的根本指向是民族地區(qū)維護社會穩(wěn)定和民族團結的現(xiàn)實需要,對于我國邊疆地區(qū)的長治久安具有深遠意義。進入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黨的民族工作主線,民族院校樹立“立德樹人”的人才培養(yǎng)目標,是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高度契合,是實現(xiàn)民族高等教育內涵式發(fā)展的重要舉措。
二、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辦學功能的變遷特征
(一)“為少數(shù)民族培養(yǎng)人才”的培養(yǎng)對象觀:培養(yǎng)規(guī)模不斷增大與民族學生比例不斷下降
民族院校是我國高層次民族人才培養(yǎng)的重要基地,從1950年時在校生僅489人,到2020年約達28萬人左右。自其創(chuàng)建至今,已為國家培養(yǎng)了近200萬名少數(shù)民族高層次人才(1)由各民族院校官網(wǎng)“學校簡介”“學校概括”統(tǒng)計。為方便統(tǒng)計并參考《中國民族統(tǒng)計年鑒》,本文所指的民族院校為直屬國家民委的6所民族院校以及7所省(區(qū))屬民族院校,即中央民族大學、中南民族大學、西南民族大學、西北民族大學、北方民族大學、大連民族大學,云南民族大學、廣西民族大學、內蒙古民族大學、貴州民族大學、湖北民族大學、青海民族大學、西藏民族大學。,有力支撐了少數(shù)民族事業(yè)的發(fā)展。2007年,13所民族院校只占當時全國本科院校數(shù)的1.76%,卻每年承擔了10%以上的少數(shù)民族大學生培養(yǎng)任務,并且每年全國有20%的少數(shù)民族干部由民族院校培養(yǎng)[8]。民族院校培養(yǎng)的大量高層次民族人才,為滿足少數(shù)民族和民族地區(qū)發(fā)展的迫切人才需要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為國家與民族培養(yǎng)了大量高層次民族人才的另一面,隨著民族院校的轉型,就培養(yǎng)對象而言,其獨特辦學功能也受到了一定削弱。相關數(shù)據(jù)顯示,民族院校少數(shù)民族在校本科生數(shù)由1999年的4萬多人,增長至2020年近14萬人,但民族院校中少數(shù)民族在校生的占比并未隨之增加,而是出現(xiàn)總體下降的趨勢。以中央民族大學為例,最初其少數(shù)民族在校生占比高達90%以上,2020年下降到48.4%;再如,中南民族大學與廣西民族大學1990年,這一數(shù)據(jù)分別為73%、84.2%,到2020年分別下降到60%、47%。2005年《關于進一步辦好民族院校的意見》要求各民族院校少數(shù)民族學生比例一般保持在65%~70%左右[5]573。顯然,目前大部分民族院校已達不到此要求。再看民族院校少數(shù)民族本科學生在全國少數(shù)民族本科生中的占比情況,1999年這一數(shù)據(jù)為18%,到2020年,僅約7.92%。從培養(yǎng)對象來看,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功能也被借“轉型”之意越來越“普通化”,如表1、表2所示。

表1 1990年以來部分民族院校少數(shù)民族在校生占比(%)(2)1990年、2000年、2010年數(shù)據(jù)參見付娜:《民族大學(學院)的特有功能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第75頁。 (3)2020年數(shù)據(jù)參見各民族院校官方網(wǎng)站。

表2 民族院校少數(shù)民族本科在校生占全國少數(shù)民族本科在校生的比例(4)1999年數(shù)據(jù)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發(fā)展規(guī)劃司編:《中國教育統(tǒng)計年鑒1999》,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8、146頁。 (5)2005年、2011年數(shù)據(jù)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發(fā)展規(guī)劃司編:《中國教育統(tǒng)計年鑒2005》 中,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發(fā)展規(guī)劃司編:《中國教育統(tǒng)計年鑒2011》,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頁;吳霓:《中國民族發(fā)展報告2013》,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90頁。 (6)以2020年為估算,數(shù)據(jù)參見教育部官網(wǎng):《2020年教育統(tǒng)計數(shù)據(jù)》,2021年8月31日、2022年6月27日訪問,參見各民族院校官網(wǎng)。
(二)“為民族地區(qū)培養(yǎng)人才”的培養(yǎng)去向觀:支援性的人才輸出與逃離式的就業(yè)選擇
民族院校是面向少數(shù)民族與民族地區(qū),服務少數(shù)民族與民族地區(qū)的高層次民族人才培養(yǎng)基地。一方面體現(xiàn)在嵌套式的人才培養(yǎng)去向觀。新中國成立初期,“受過高校正規(guī)培訓的民族干部,絕大部分出身于民族院校。”[9]10從民族自治地方的干部來看,大多也由地方民族院校培養(yǎng)。例如,當前云南省 29 個民族自治縣中的民族干部,大多畢業(yè)于云南民族大學[10];另一方面,體現(xiàn)在引導式的人才培養(yǎng)去向觀。在改革開放后相當一段時期內,民族地區(qū)是民族院校少數(shù)民族畢業(yè)生的主要就業(yè)目的地。例如,在廣西靖西縣(今靖西市),1985年以來考上高校的畢業(yè)生的返鄉(xiāng)率平均為61.4%,其中民族院校畢業(yè)生為74.5%,內地一般高校畢業(yè)生為48.9%,全國重點院校畢業(yè)生為2.8%[9]10。民族院校以支援式的人才培養(yǎng)為民族地區(qū)變革與發(fā)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但由于就業(yè)分配政策、民族地區(qū)就業(yè)環(huán)境等變遷的影響,部分民族院校少數(shù)民族畢業(yè)生服務民族地區(qū)的比例以及回鄉(xiāng)意愿出現(xiàn)不斷下降的現(xiàn)象。據(jù)相關研究,20世紀90年代初,南方某民族院校少數(shù)民族畢業(yè)生回鄉(xiāng)率在90%以上,此后逐年下降,到2000年左右,除個別省(區(qū))外,比例不足30%,個別年份、個別地區(qū),甚至不足5%[11]。有學者曾對民族院校少數(shù)民族學生畢業(yè)后的就業(yè)區(qū)域和地點進行調查,其中,59%的學生傾向到非民族地方就業(yè),41%的學生愿意回到民族地方,愿意回民族地方就業(yè)的學生中有74%的學生傾向于留在城市就業(yè),較少愿意到民族農村地區(qū)[12]。當前,民族院校畢業(yè)生回歸民族地區(qū)越來越少,民族院校為民族地區(qū)輸送人才的特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挑戰(zhàn)。
(三)“民族干部與專業(yè)人才”的人才培養(yǎng)類型觀:對口培養(yǎng)的優(yōu)勢彰顯與轉型后的特色弱化
民族院校承擔著其他高等院校所不具備也難以承載的特殊類型的人才培養(yǎng)任務。首先,培養(yǎng)民族干部是民族院校獨特的人才培養(yǎng)功能。新中國成立初期,民族院校通過招收轉業(yè)人員、先進分子、少數(shù)民族上層愛國人士進行政治培訓,培養(yǎng)了一大批民族干部。改革開放之后,盡管培養(yǎng)民族干部不再是民族院校的中心任務,但民族院校在培養(yǎng)民族干部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民族院校還是民族特色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的主陣地。正是由于民族院校所肩負的獨特使命及其多民族的生源結構、多民族文化的場域環(huán)境,使得民族院校成為開展人文社科研究、培養(yǎng)人文社科人才的得天獨厚之所,乃至民族院校所開設的部分民族類特色專業(yè),成為了“獨門絕學”。目前,在全國和各民族地區(qū)從事民族領域研究工作的專業(yè)人員中,大部分是民族院校的畢業(yè)生[13]。
跟隨高校擴大規(guī)模的浪潮,近年來民族院校急劇擴充其學科、專業(yè)設置數(shù)量。從1999年至2012年,民族院校本科專業(yè)設置中,理科專業(yè)設置的結構占比由35.62%上升至48.39%,改變了長期以來的文強理弱現(xiàn)象,民族院校向培養(yǎng)應用型人才的轉型得到了初步成效[14]。但民族院校在擴大辦學規(guī)模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出現(xiàn)了弱化人才培養(yǎng)質量的問題,也因此受到社會對其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功能的質疑。例如,部分民族院校開設的海洋學、船舶制造業(yè)等專業(yè)在民族地區(qū)的市場需求小,與民族地區(qū)的工作崗位匹配度不高,造成一定人才培養(yǎng)資源消耗而又難以適應民族地區(qū)需求的浪費。此外,隨著“獨門絕學”越來越“冷門”,民族院校通過培養(yǎng)特定民族人才傳承民族文化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削弱。
三、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辦學功能形成與變遷的依據(jù)
阿什比指出:“所以任何類型的大學都是遺傳和環(huán)境的產物”。其所謂的“遺傳”是指大學發(fā)展的內在邏輯,而“環(huán)境”主要指“資助和支持大學的社會體系和政治體系。”[15]7分析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功能形成與變遷的依據(jù),也就是對其背后的內外部動因進行全面的考察。
(一)外部動因:社會環(huán)境作用機制的變遷與影響
民族院校“從一開始就被置于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的主要領導之下,它充分說明民族學院的設立主要是基于國家的政治需要和解決民族問題的立場考慮的。”[16]只要造就民族院校的歷史環(huán)境未完全褪去,民族院校就會自然地延續(xù)這樣的功能,并隨社會環(huán)境的變遷而不斷地更替它的表現(xiàn)形式。
中國民族高等教育發(fā)端于近代民族危亡與政權危機之際。晚清政府希冀通過提振統(tǒng)治階級民族的教育來實現(xiàn)政權延續(xù)的政治理想,由此催生了滿蒙文高等學堂與同時代的其他高等學府。新中國成立初期,政權鞏固和民族團結成為當時國家面臨的首要問題。此時,干部培養(yǎng)顯得尤為急迫,教育為國家政治服務的呼聲占據(jù)上風,民族院校的“政府主導”模式也因之逐漸形成。隨著黨和國家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民族院校人才培養(yǎng)的定位也隨之由“以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干部為首要任務”轉變?yōu)椤芭囵B(yǎng)政治干部與專業(yè)技術人才并舉”。改革開放后,在經(jīng)濟改革話語下,市場機制也進入到高等教育領域。與此同時,作為民族院校存在的合理性依據(jù)——民族問題,也由關注民族關系的政治問題轉變?yōu)殛P注民族發(fā)展的建設問題,發(fā)生了根本變化。“高素質專業(yè)技術人才培養(yǎng)”成為這個時期民族院校人才培養(yǎng)的主導話語。以自主性、競爭性和開放性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改革,沖擊了國家權力在資源配置中的傳統(tǒng)權威作用,加之高等教育大眾化與就業(yè)政策的轉變,徹底更新了民族院校在政府主導之下形成的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辦學功能的認知。由單一服務于政治,到滿足民族地區(qū)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需要,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辦學功能開始走上了適應市場的轉型道路,民族院校人才培養(yǎng)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與傳統(tǒng)的告別并非瞬時可以完成,制度的慣性作用使其在既定方向得到延續(xù)并產生鎖定效應,形成制度的“路徑依賴”[17]。在計劃體制時代里,民族院校是執(zhí)行黨和國家解決民族問題的政策工具。但隨著市場機制的滲入,新舊傳統(tǒng)驟然交集,引發(fā)了民族院校在新歷史時段中的困惑。克拉克認為高等教育系統(tǒng)整合處在國家權力、市場、學術權威三種力量構成的“三角的協(xié)調模式之中”[18],社會體制的變革導致影響民族院校的各種力量重新組合。雖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市場機制也因其特性難免會出現(xiàn)失靈,為維護社會的穩(wěn)步發(fā)展,國家權力的干預仍不可或缺。對民族院校獨特性的關注與推動其朝向一般高等院校轉型的論爭是國家權力與市場關系的具體反映,這些論爭影響了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功能的價值取向。如前所言,造就民族院校的歷史環(huán)境還未遠去,那么,政府仍可以依據(jù)“誰付賬誰點唱”的合理原則,通過運用一系列行政舉措,限制市場的過度干預,要求民族院校對歷史中形成的“為少數(shù)民族和民族地區(qū)服務”的人才培養(yǎng)特定功能進行延續(xù),即使它已不如初創(chuàng)之期時表現(xiàn)得那么明顯。雖然社會機制的變遷為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的特定功能轉型開了一個缺口,但轉型并不意味著需要與過去完全割裂,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的特定功能需在國家權力、市場、民族院校自身的張力中尋找新的平衡。
(二)內部動因:民族院校內在邏輯的延續(xù)與應對
“內在邏輯對高等教育體系的作用猶如基因對生物體系的作用,它要保持這種體系的特性;它是這種體系的內在回轉儀。”[15]139民族院校是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中的一種獨特存在,其內在邏輯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作為黨和國家民族政策的產物,二是作為高等教育體系中的一環(huán)。
1.新中國民族院校真正的源頭是延安民族學院。延安民族學院開啟了我國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的特殊使命,今天的民族院校都在某種程度上賡續(xù)延安民族學院的“紅色血脈”。事實上,長期以招收少數(shù)民族及民族地區(qū)的學生為主,顯示出民族院校人才培養(yǎng)的補償性原則以及黨和國家民族政策的“幫扶”色彩。民族院校的政治屬性要求其相較于普通院校,在招生、就業(yè)等方面承擔著更多來自行政指令的特殊規(guī)定。這些規(guī)定在一定時期內,對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功能起到了良好的規(guī)約作用,但隨著社會發(fā)展與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其也在一定程度遭受了質疑。就業(yè)市場的變化對就業(yè)者的質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增加就業(yè)選擇機會的同時,就業(yè)機制也越來越成為人才流動的閥門,從而引發(fā)了民族院校究竟是少數(shù)民族與民族地區(qū)的人才培養(yǎng)基地還是人才流失中轉站的疑問;同時,伴隨高等教育走向大眾化,再到普及化的過程,高等教育系統(tǒng)內部也同樣存在著競爭。高等院校都試圖在時代變革之中博得上升的機會,而人才培養(yǎng)是衡量一所高校辦學質量的重要因素。民族院校也不可避免地卷入競爭之中,但肩負特殊政治使命的民族院校在競爭中時常顯出弱勢。是否忠實延續(xù)這一層面的內在邏輯,還是基于現(xiàn)實對其進行調試,從而為自身發(fā)展增加砝碼,成為民族院校在變革時代所面臨的抉擇。
2.民族院校本質上屬于高等教育,民族院校對國家和民族擔當?shù)呢熑未嬖谥欢ǖ慕缦蓿浣缦蘧褪敲褡逶盒W鳛楦叩冉逃裱陌l(fā)展規(guī)律與所能發(fā)揮的功能。布魯貝克提出大學遵循著兩種哲學邏輯,即認知論哲學與政治論哲學[19]7。二者之間實質上是純學術與實用目的、學術自由與社會責任、大學自治與政府干預的矛盾關系。高等教育緣起之時的主要職能是保存、傳遞和發(fā)展高深學問,并培養(yǎng)從事這一方向的高層次人才。隨著大學逐步從社會邊緣走向中心,其承擔起越來越多的社會職能。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功能所肩負的政治使命,是民族院校誕生時起就秉持的政治論哲學內在邏輯。從實際來看,民族院校履行社會責任常常處于較為被動的地位,過于強調服務政府最急切的任務,而忽視了民族院校作為高等院校主體對另一內在邏輯——認知論哲學的追求,從而導致民族院校在兩者的拉鋸中迷失了自我。雖然“為了生存并產生影響,大學的組織和職能必須適應周圍人們的需要”[19]16,通過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辦學功能對國家和民族負責是民族院校應長期堅守的責任,但如何兼顧并復歸民族院校作為高等教育的屬性。在認識論哲學與政治論哲學的博弈中尋找平衡,以高等教育規(guī)律為指引,充分發(fā)揮民族院校“身兼兩職”的作用,是決定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功能未來發(fā)展的重要問題。
四、結語
民族院校以其獨特的發(fā)展歷史與生存環(huán)境,形成了以培養(yǎng)民族人才為主的特定辦學功能,并以此堅韌地支持了民族事業(yè)的繁榮發(fā)展和國家的和諧穩(wěn)定。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辦學功能經(jīng)歷了政治話語主導到經(jīng)濟話語主導再到德才兼?zhèn)涞霓D變,在此過程中,這一功能的獨特性也漸為趨弱,以至出現(xiàn)是否仍應堅守的矛盾。但另一方面,這也印證了民族院校作為高等教育系統(tǒng)組成部分的根本屬性,昭示著辦好民族院校必須以高等教育規(guī)律為其根本依據(jù)。
探究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辦學功能的歷史演進是認清民族院校當前困境的重要方式,也是對民族院校人才培養(yǎng)規(guī)律的探索。對這一問題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民族院校在特殊與普通、維系與轉型之間抉擇難題的探討。對歷史的回顧與反思,正是為了對現(xiàn)實予以回應與關照。認識規(guī)律的目的不在于規(guī)律本身,而在于用規(guī)律去尋找問題解決的方法,這也是之后繼續(xù)開展民族院校培養(yǎng)民族人才特定辦學功能研究所應著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