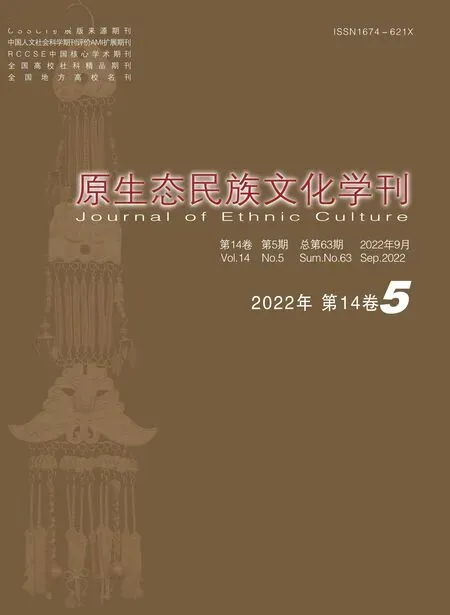“軍管集場”:清代湘西汛塘與鄉村集場的設置及運行
周 妮
本文所言湘西即清代湖南西部“三廳二縣”(乾州廳、鳳凰廳、永綏廳、永順縣、保靖縣)地域,范圍大致與今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相同。自康乾時期開始,清廷在湘西地區逐步進行改土歸流。為實現更全面的地方管理,開始建立、完善汛塘體系,并于乾隆時期全面完成汛塘在湘西基層的設置,完成以“(汛)塘”管“村(寨)”[1]的網絡建設,控制十分嚴密,筆者將這種軍事單位參與村寨管理的行為稱為“軍管村(苗)寨”[2]。受“軍管村(苗)寨”的影響,與村寨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集場亦被納入其中,與汛塘建立起緊密聯系。一方面,汛塘體系的選址與建設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鄉村集場業已構成的網絡;另一方面,在“軍管村(苗)寨”視域下,湘西各村寨民、苗均受汛塘控制,鄉村集場的開設、管理等亦在其管理之中。因此,湘西地區形成眾多的軍事政治類集場[3]55。
筆者在前人研究基礎上①鄧必海:《試論湘西民族集鎮的形成和發展》,《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3期;石邦彥:《清代湘西苗區的商業市場》,《民族論壇》1988年第6期;暨愛民、趙月耀:《“國家權力”的“地方”運作——以清代湘西“邊墻-墟場”結構為例》,《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張曉燕、暨愛民:《國家在場:地方治理視野下清代湘西之集場交易》,《貴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6期等,對湘西民族集鎮的歷史、交易情況,以及與“邊墻”關系等重要問題進行了探討。譚必友:《清代湘西多民族社區的近代重構》,民族出版社,2007年,亦言及湘西的民族貿易。但是,以上成果對于集場與汛塘之間的關系著重較少。秦樹才:《清代云南綠營兵研究:以汛塘為中心》(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 年)注意到綠營兵對清代云南農業、工礦業、商業的影響,認為綠營兵對云南城鎮的發展與繁榮起到了直接促進作用,也發現一些地方因汛兵的駐扎而建城,不少汛塘發展為云南各地區集市貿易場所,對本文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嘗試梳理文獻所載清代湘西汛塘與集場,分析兩者之間的時空關聯與互動關系,從歷史時期湘西集場的形成與變化及清代汛塘的建設與分布,探討湘西基層社會從“羈縻”到“軍管”的轉型過程,以及與近代社區(市場)建立之銜接,揭示清代湘西及其鄰近非漢族群聚居地區基層市場設置的歷史地理背景。
一、“乾嘉之亂”前湘西鄉村集場的設置與分布
湘西土司改土歸流前,歷史文獻關于區域內集場設置及交易往來的記載極少,但并不意味著其境不存在集場交易行為。如兩宋時期,區域內非漢族群與“省民”(漢族群)土地私自交易問題十分突出。嘉定七年(1214年),臣僚在上書中便提道:“夫溪峒之專條,山傜、峒丁田地,不許與省民交易,蓋慮其窮困,而無所顧藉,不為我用。今州郡謾不加恩,山傜、峒丁有田者,悉聽其與省民交易,但利牙契所得。而又省民得田輸稅,在版籍常賦之外,可以資郡帑泛用。而山傜、峒丁之米,掛籍自如,催督嚴峻,多不聊生,往往奔入生界溪峒受顧,以贍口腹,或為鄉導,或為徒伴,引惹生界,出沒省地,骎骎不已,為害甚大。”[4]9023又有言“宜明敇湖廣監司行下諸郡,凡屬溪峒山傜、峒丁田業,不得擅與省民交易,犯者以違制論。仍歸其田,庶山傜、峒丁有田可耕,不致妄生邊釁”[4]9023-9024。顯然,以田業為例,側面反映出當時湘西地域內不同群體之交易往來及基層集場的形成與維持,不僅由來已久,而且與當地不同群體之間的關系狀態密切相關,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地方官府的承認與管理。而禁止交易的目的,在于保障“山傜”“峒丁”基本生活,避免發生紛爭。
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于會溪(今古丈縣羅依溪鎮會溪坪)設立宣撫司,禁約省民、洞蠻,止于會溪交易。”[5]99所言會溪坪不僅是宣撫司治所,也是元代湘西民、“蠻”之間交易臨界點,應為歷史文獻所載最早的湘西集場。其所設宣撫司,在于控制“省民”“洞蠻”(即后之民、苗)交易與往來,折射出政治、軍事控制與湘西集場設置之間互相依賴與互動的關系。明洪武初年,設“高巖巡檢,以通交易”[1]233。高巖巡檢,位于明初所置崇山衛境內,說明明代湘西集場較之元代有進一步發展,開始在湘西內設置。然而,據《明實錄》記載,崇山衛,置于洪武十一年(1378 年)[6]1964,不久即以“孤懸苗地,轉運難艱,議撤”[7]122。因而高巖集場與崇山衛之命運極可能相同,所存時間不長。因此,無論宋代省民與峒溪苗、瑤之間的交易,還是元代會溪交易集場與明代高巖集場的置廢,都已明顯地反映出湘西地域范圍內族群關系、軍事設置與集場之間相互聯系的緊密性。
入清以后,伴隨改土歸流的進行與完成,清廷在湘西基層廣置汛塘,全面進入并控制湘西。組織嚴密,號稱“郡有鎮守,邑有分防,星羅棋布,如常山之勢”[8]658。汛塘系統建立后,湘西地區族群關系進入一個相對平穩的階段,鄉村集場系統也隨之較快地發展起來。經初步統計,改土歸流之后,雍正、乾隆時期湘西各府、廳、州、縣志所記載集場共有31 處。而集場的設置方位及地理分布,與汛塘等基層軍事建置相關性極強(見表1)。

表1 “乾嘉之亂”前湘西汛塘與鄉村集(市)場關聯示意簡表
顯然,鳳凰廳在乾隆時期置有西門江集、箭塘集、鳳凰集、永寧哨集、靖疆營集、新寨集、筸子哨集7 處集場。據文獻記載,前3 處集場因位置重要,地方官府特別“設立文武衙門彈壓”,而后四處集場“俱系乾隆十九年新設試開”,均為軍事駐防之地[9]34-35。永寧哨集、筸子哨集、箭塘集、靖疆營集,自明代即設有永寧哨、筸子哨、箭塘哨、靖江哨,均曾置兵駐守;西門江集、箭塘集、鳳凰集、靖疆營集、新寨集等,在乾隆時期亦置有營汛。如鳳凰集,在雍正時期即置鳳凰營,至乾隆時期,又設“廳標把總一員,帶領兵丁五十名”。新寨,雍正時已置汛,乾隆時期又“駐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千總一員,兵丁一百五十五名”[9]94。永綏廳,雍正時期已置有永綏城市、隆團市、花園市、排補美、米糯5 處集場,所在地均為雍正時期永綏廳重要關隘。永綏城市為駐城防守;隆團市置有隆團寨,設“守備、把總各一員,巡檢一員,兵一百一十名分防”;花園市置花園寨,設“千總一員,兵一百名分防”;排補美置排補寨,設“守備一員,巡檢一員,外委一名,兵九十九名分防”;米糯置米糯寨,設“千總一員,兵八十五名分防”[10]450-452。乾隆時期僅新增南門外場一處,亦為綠營兵駐城防守。保靖縣,雍正《保靖縣志》記有古銅溪、張家壩兩處集場,同治《永順府志》所載塔普與葫蘆寨亦為雍正時期設置,乾隆時期無新設集場。而古銅溪、張家壩等處均設有汛塘。古銅溪,雍正時設把總駐防,乾隆時仍置汛,“分駐把總一員,汛兵二十一名。”張家壩,設巡檢司駐扎;塔普、葫蘆寨在乾隆時期置汛塘,塔普塘“分設外委一員”,葫蘆寨汛“分防把總一員,汛兵二十二名”[11]124。清晰地呈現出集場與汛塘之間密切的依存關系。永順縣,乾隆時期置有王村市、舊司城、顆砂、西壩湖、列夕、十萬坪、杉木坪、勺哈、旦武營、古丈坪、田家洞、百棲關、店房、夾樹坪、李家坪等15處集(市)場,其中,除十萬坪、百棲關、店房3處外,其余在乾隆時期均置有汛塘。如王村市置有王村汛,設“分防千總一員,汛兵二十名”;舊司城有舊司治汛,設“分防把總一員,汛兵十六名”;旦武營有旦武營汛,設“分防把總一員,汛兵四十六名”;西(洗)壩湖置有洗壩湖汛,設“分駐外委一員,汛兵十名”[11]124。
綜上,湘西各廳縣在雍正、乾隆時期所置31 處集場,僅永順縣有3 處集場無軍事(汛塘)建置記載,其余28 處集場均有軍事建置,反映出湘西汛塘軍事體系建設與鄉村集場發展之間存在的必然、緊密聯系與高依存度。然而,因方志記載過于簡略,極少涉及各集場具體設置情形,導致集場是因汛塘而設,還是汛塘因集場而設的問題不明。筆者在全面閱讀湘西相關史籍后發現,《苗寨每逢市集交易日期責成文武官親往巡查》與《詳設集場》詳細記載了雍正時期古銅溪、張家壩、茶洞三處集場的設置過程與考慮,正可彌補地方志未詳細記載集場設置情形的不足,進一步揭示湘西軍事體系建置與鄉村集場建設的關系。
二、集場設置中汛塘環境的考量
如前文所言,改土歸流前,湘西所置與“外界”溝通交流之集場極少,明洪武初供以交易的高巖巡檢也因崇山衛的撤銷而荒廢。筆者認為,其癥結之一在于苗民與漢民之間的市場交易需求,缺乏對人身安全與公平交易等方面的基本保障。如《戒苗條約》言:“鹽、布二項是你苗急需,皆因你們性好劫殺,以致無人進來交易。即有轉賣進來的,其價又貴,是以你苗歷來常受寒冷淡食之苦,殊覺可憐。你若不劫殺,則漢人進來交易者多,將爾土產以換鹽、布,豈不兩得其利?再若爾果守法,可以自到乾州五寨司買去,其價更賤。”[12]即反映出民族集場衰落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當時苗民與漢民關系緊張,導致漢人進入湘西從事交易者極少。如無安全與公平交易的保障,則不會有穩定的交易行為,更無所謂長期存續的集場。但是,布帛、鹽、米又為苗民日常生活所急需,因此,伴隨改土歸流的進行與完成,解決苗民所需,設立集場成為勢在必行的選擇。而安全保障與公平交易問題,則是地方官員在設置集場時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
雍正時期,保靖縣設置古銅溪與張家壩兩場,地方官員王欽命上言《詳設集場》①雍正《保靖縣志》卷四有記載,但記載不全,因而此處所引全文出于同治《保靖縣志》卷一二(同治十年刻本)。,詳述兩場址選擇與設置過程。開篇即提出“為詳請設立苗界集場,以免民、苗出入滋事”之目的,表明保靖雖改土歸流,但其地與湘西腹地相連,對于苗民的管控仍為主要任務,因此,在其地設立集場尤須謹慎考量。又指出:“古銅溪在縣東南,張家壩在縣西南。古銅溪兼通水道,可行小舟,名曰小江,水源直通六里紅苗,民人常舟運貨物入內;至張家壩亦水陸皆通,民、苗相接,并連四川酉陽土司,四方貿易多聚于此,擬于此二處設立集場。”[13]911可見,古銅溪、張家壩為當地出入往來重要通道,是相鄰各省商路交匯之地,水陸交通便利,貿易興旺,商賈聚集,為設置集場的上乘之選。
選定合適地點后,如何避免“民、苗滋事”,成為當地官府考量的最主要問題,即“不欲使民、苗私相往來,以杜其勾引之漸,必別為之所,俾之易粟、易布,以通有無,則集場之在湘西更宜加之意矣。但開集設場,或稱經紀,或號牙行,大約均非善類。藏奸聚匪,啟爭致釁,恒出于此,選擇以慎初,稽察以善后,享其利,勿□其弊,是在官茲土者”[9]34。顯然,對于交易商賈群體的評價,并不公允,但是,維護市場交易公平,避免矛盾激化,卻是集場興旺最基本的保障。對此,王欽命提出:“場市既立,必須委員監察約束”。雍正七年(1729年)所置張家壩司巡檢[10]551與古銅溪(領兵)駐防把總[10]453,皆為其提供了保障。又張家壩“相隔一二里之里耶,設有把總一員”。因而至交易日期,以張家壩巡檢與里耶把總監察張家壩場;以古銅溪把總一員監察古銅溪場,同時派在城典史前往協司巡視[14]489-490。可見,地方官員在場市選址時,對考察地點周邊的防守力量有必然考量。而“惟各處集場原許民、苗按期趕趁,以有易無,應令汛屯員弁親為彈壓,無許市儈侵欺,一切公平互市,交易而散”[15]129。又說明派遣官員與兵弁駐扎集場的目的在于保證集場公平交易與安全進行,遏止市儈欺壓良善。這種情況下,集場與汛塘的位置需要盡量靠近,這也正是清代汛塘系統與湘西集場分布格局發生耦合與交集的關鍵所在。
與古銅溪、張家壩集場設置相較,茶洞場設置過程更加明顯地表現出集場設置與周邊汛塘環境的密切關系。首先,永綏廳改土歸流之初,“凡有往苗地貿易者,許令呈明本地方官給與印照,開明人數、物件、往回日期,汛塘驗明放行”[16]455。反映了民、苗貿易活動中,汛塘的基礎與關鍵作用。永綏地方官員張天如認為這種交易多有不便,因而提出在湘西分界之地設立集場。他借鑒前任地方官員設置南關集場的失敗教訓,提出于茶洞地方設立集場的意見。認為“河道之廣狹,民居之多寡,貨物之能否聚集,汛塘之能否彈壓”[16]457,為茶洞是否可置集場的決定因素。又指出茶場交通位置良好,且“茶洞土人四十余戶,客店二十余戶,民居比連,塘房在高坡之上,易于瞭望稽查”[16]457-458。同時,提出永綏所屬之花園、尖巖、本城、隆團俱有汛塘,同樣有軍事管控的保證。如若茶洞集場開設成功,那么,其他汛塘附近亦可設立集(市)場。
從張天如實地考察河道、居民、汛塘等狀況,到重新派員勘察周邊汛塘具體設置的過程,突出地顯示了地方汛塘在集場設置與維護中的關鍵性作用。非漢族群聚居地區集場的設置,并非輕而易舉之事。汛塘的設置,實質上是對于湘西集場的軍事管控與市場管理。因此,汛塘方位、兵力設置之更改,與集場設置及布局密切相關,若當時缺乏汛塘對集場交易秩序的維護與管理,集場的設置與長期持續是不可能的。
因此,筆者認為,從一定程度上講,湘西以汛塘為基礎“軍政兼理”,是湘西地區集場是否設置,以及置于何處的重要考量因素或決定性因素,也是維護集場交易秩序、促進集場和諧發展的重要保障。當然,也正是因為兩者之間密切的關系,湘西集場在“軍政兼理體制”下又存在著諸多不穩定性與不可預見的問題與矛盾,“軍政兼理體制”的弊端日益暴露。伴隨“乾嘉之亂”的發生,汛塘格局發生變化,鄉村集場環境與地理分布格局亦發生了不小變化。
三、“乾嘉之亂”后湘西集場的設置與分布
“乾嘉之亂”的發生,對湘西地方與清廷均造成了巨大沖擊,使清廷不得不再次慎重考量湘西安全與穩定問題,重新布置基層汛塘系統,以便進行更有效的防守與控制。嘉慶元年(1796 年),和琳在上奏中建議:“湘西營、汛應分別歸并,以聯聲勢。”又提出在平定“苗民起義”后,應于鳳凰、永綏、乾州三廳“擇其要隘處所,酌添兵丁及文武大員,以資彈壓”,又以湘西汛塘兵額不能管理或彈壓苗民為由,建議將“苗境內所有零星汛塘,全行撤出”[17]644。嘉慶二年(1797年),畢沅、姜晟、鄂輝等官員亦建議“將孤懸湘西零星汛塘撤回”[18]92-93,并上奏言“鳳凰、永綏、乾州等處兵力較單”,請“于事定后擇其要隘處所,酌添兵丁及文武大員以資彈壓”[19]578-579。清廷采納地方官員的建議,一方面“審時度勢”,根據形勢變化在原所設汛塘基礎上設營添兵或另設新營,撥兵駐守;另一方面,按和琳所奏,將苗境內散漫零星之汛塘全行撤出,湘西基層汛塘系統發生重大改變,鄉村集場之設置也隨之改變。筆者統計“乾嘉之亂”平定后湘西鄉村集場,可得其與汛塘建置關系如表2所示。

表2 “乾嘉之亂”后湘西汛塘與鄉村集(市)場關聯示意簡表

保靖縣強虎哨不詳普棲塘不詳水蔭場汛葫蘆寨汛鼻子寨塘夯沙汛阿稞塘不詳同治時期永順縣里耶汛馬老胡塘不詳同治時期龍鼻嘴汛河蓬塘不詳乾州廳 不詳鎮溪所河溪汛不詳大新寨平郎營不詳光緒時期強虎哨場江家坪場普濟場復興場水蔭場葫蘆寨場鼻子寨場夯沙坪場阿稞場茅溝寨場臥黨場卡棚場太平壩場拔茅寨場比耳場里耶場瑪瑙湖場巖板鋪三家田荊州街鹽井儲庫坪聳湖龍鼻觜河蓬坪扒蓑衣坡南門外場鎮溪所場河溪場馬頸 場大新寨場坪朗營場洽比場大河坪場弭諾場貓兒寨場龍潭場茶洞客場茶洞汛客場?永綏廳 不詳宣統時期茶洞汛茶洞汛

資料來源:道光《鳳凰廳志》、光緒《乾州志》、同治《保靖縣志》、同治《永順府志》、宣統《永綏廳志》。
顯然,鳳凰廳在道光時期共有集場14處,除新寨場、筸子坪(兩處里程稍有變化)為乾隆時期已置外,其余南門外場、廖家橋場、落濠場、雅拉營場、新廠場、杜望場、永新場、長凝哨場、得勝營場、水打田場、強虎哨場、江家坪場均為乾隆后新設。這些集場中,杜望場,明時曾設杜望巡檢;長凝哨,明隆慶時以長沖設哨;得勝營場、強虎哨場,乾隆時皆置有營汛;廖家橋場、落濠場、鴉拉營場,嘉慶時均置營汛,有重兵駐扎;新廠場、永新場、水打田場、江家坪場未見汛塘建置。可見,大部分集場仍建于曾經的重要軍事駐地。但這14處集場中的南門外場、廖家橋場、落濠場、雅拉營場、新廠場、杜望場、長凝哨場、得勝營場、筸子坪場、強虎哨場均處于“乾嘉之亂”后新劃“民、苗界限”地域,即新的汛塘兵力集中地帶。乾州廳,光緒《乾州志》載境內有集場8 處,南門外場為附城,為防守重地。鎮溪所場、河溪場、大新寨場、坪朗營場在乾隆時分別置有鎮溪所、河溪汛、大新寨、平郎營,且大新寨地方在明代原設高巖巡檢以通交易,河溪地方亦曾置河溪巡檢;馬頸坳場、恰比場、大河坪場未置汛塘,但馬頸坳場、大河坪場曾屬良章營[20]416-417,仍然多位于重要軍事駐地。其中南門外場、鎮溪所場、河溪場、馬頸坳場、恰比場均位于“乾嘉之亂”后新劃“民、苗界限”地域,即新的汛塘兵力集中地帶。而永綏廳在雍正、乾隆時期所置6處集場,原即處于“民、苗界限”地帶,并無明顯變化。可見,湘西汛塘撤出并重新集中于“民、苗界限”周邊,對湘西鄉村集場的設置產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使鄉村集場亦形成以“民、苗界限”為中心的分布格局。
從各廳縣內鄉村集場與汛塘設置的時間關系上看,自同治時期開始,在同一時期既設汛塘,又置鄉村集場的數量明顯減少。即同治及同治以后所置鄉村集場多分布于清代雍正、乾隆、嘉慶時期所置汛塘地,反映伴隨湘西社會的發展與轉型,鄉村集場與汛塘的依存關系在逐漸減弱。具體而言,同治時期,保靖縣境內集場增至15處,其中復興場即為原古銅溪場,后蕭條,于嘉慶時重設[21]112;普濟場、鼻子寨場、夯沙坪場、阿稞場、里耶場、瑪瑙湖場均為乾隆時期置汛塘;茅溝寨場,舊有防營駐扎[22]2621;拔茅寨場,置有防兵守拔茅寨塘;比耳場,同治時置有比耳塘,屬龍山縣;臥黨場、卡棚場、太平壩場等未詳汛塘建置。永順縣,同治時增置巖板鋪、三家田、荊州街、鹽井、儲庫坪、聳湖、龍鼻嘴、河蓬、坪扒、蓑衣坡等10處集場,僅龍鼻嘴、河蓬在嘉慶時曾置汛塘。永綏廳,宣統時置有集場12處,其中鴨保場、夯上場、排碧料場,雍正時已置兵駐守;茶洞客場、茶洞汛客場乾隆時置茶洞汛;排打扣,“向設小汛”,嘉慶時撤[23]484;弭諾場、貓兒寨場、龍潭場、排大魯場、衛城場未見汛塘設置。至宣統時期,汛塘名存實亡,多已無綠營兵駐守,鄉村集場與汛塘之間的關系幾不可見。說明湘西鄉村集場發展至清末,與基層汛塘系統之間已然沒有太多關聯,發生著從“軍政兼理”到“民治”的轉變。
四、余論
自德國學者沃爾特·克里斯塔勒出版《德國南部中心地原理》以來,基層商業交易市場的空間分布與相互關聯問題逐漸引起研究者的廣泛關注。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樣:“中心地體系是按一定中心規則圍繞一個中心地(即構成體系的中心地)的一定數量中心地組成的群體。這些規則可以取決于經濟規律,也可以取決于社會政治狀況,或兩者兼而有之。”[24]而施堅雅關于中國農村市場與社會結構理論的推出,更是引起了中國學者的熱烈響應。①任放、杜七紅:《施堅雅模式與中國傳統市鎮研究》,《浙江社會科學》2000年第5期;胡勇軍、徐茂明:《‘施堅雅模式’與近代江南市鎮的空間分布》,《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邢稞:《近代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及其構造模式——以施堅模的<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為例》,《貴陽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章立明:《在施堅雅模式啟示下的云南走廊研究》,《云南社會科學》2016年第1期等均對圍繞施堅雅關于中國農村市場與社會結構理論進行了不同視角的探討。然而,學者們也指出:“大量地采用公式化與標準化的模式,部分情況下難以符合現實。就集鎮規模上看,施堅雅的描述極為詳細,但在現實情況下能否實現仍然值得商榷。”[25]中國歷史悠久,地域廣闊,各地差異明顯,用統一模式進行詮釋與說明,顯然是不可能的。
中國基層市場都有著曲折與漫長的發展史,民族地區集(市)場更是如此,各類影響因素極為復雜,同樣影響到市場的空間格局。正如施堅雅所言:“區系空間的制度同時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透視點與相遇點……而且國家與社會不是對立的,而是在社會空間上互相兼容和密不可分的。”[26]113本文所言集場,主要指各族群交易之集場。湘西集場的設置最早可以追溯至兩宋時期的民間交易活動,元代則有了會溪地方集場交易的明確記載,明代則于土司管轄之地設置高巖巡檢開市交易。但是,這些早期交易活動均未形成規模,且受當時族群關系緊張,缺乏人身安全與公平交易保障等的影響,多被撤廢,具有很強的不穩定性。且直至改土歸流后,族群關系緩解,清廷才開始廣設集場,以供各族群交易。改土歸流之初,如何謹慎處理各族群關系,保證地方和諧穩定,是湘西地方官員的主要任務。在集場交易中,如何處理族群關系,又是能否保證公平交易,成為集場存續與否的關鍵。因此,在每一集場設置時,都必須有周密的考量,且“設立有案”。地方官府為了保障交易的安全與公平,“每逢集期,責成文武官親往巡查,不得視同內地某場,可查不可查也。”[16]478而要完成這一任務,基層軍事組織汛塘的設置變得尤為重要,成為集場選址重要考量因素。其中,茶洞場的設置最為典型——地方官員在設置過程中對周邊汛塘各相距里程、附近汛塘兵額調整、營房移建等,都有縝密的思考及妥當的安排,深刻反映出周邊汛塘環境對集場運行的重要作用。因此,雍正、乾隆、嘉慶時期湘西集場大多設在汛塘所在地或其附近,發生耦合與交集,呈現出湘西社會從“羈縻政體”到“軍政兼理政體”的轉型。
總之,隨著改土歸流的完成,族群之間關系的改善與汛塘系統的建立,為湘西集場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兩者在設置與方位上的交集,反映出特殊時期地域集場與軍事管控之間的互動關系。正如研究者所指出,在乾嘉苗民起義后,清廷在湘西大興“屯政”,而屯防職能之一就是“彈壓各處集場”[27]。而伴隨清廷的衰落與大量漢族移民的進入,民族交流與融合進一步加強,安全保障問題進一步淡化,湘西集場與汛塘系統依存關系明顯弱化,甚至發生完全脫離,也屬正常趨勢,更反映出新型體制下湘西集(市)場逐漸市場化(民治)的趨勢,是湘西“整合入大一統中國社會模式”[28]的一個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