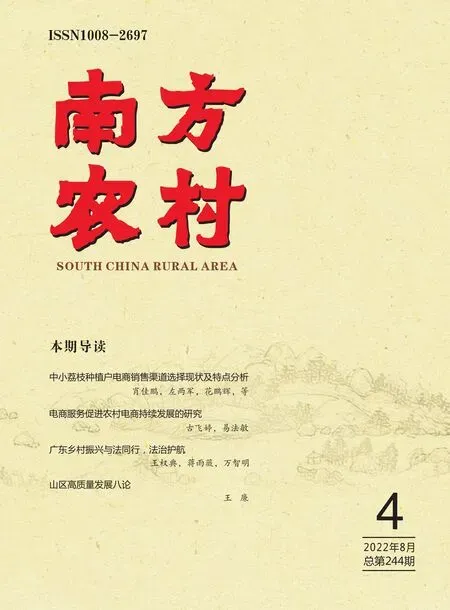就業能力、就業質量與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的實證分析
——來自廣州的數據
余秀江,黃 穎,張嘉琳,王麗萍
(1.華南農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642;2.仲愷農業工程學院 管理學院,廣東 廣州 510225;3.廣東省蕉嶺縣蕉城鎮農業服務中心,廣東 梅州 514115)
一、引言
我國城鎮化發展有著起點低、速度快的特點。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城鎮常住人口從1978年的1.72億人增加到2020年的9億人,城鎮化率從17.92%提升到60%,年均提高1.04個百分點。城市的急劇擴張迅速席卷了緊鄰城市的村莊而形成諸多“城中村”,其中的原住民被稱為“城中村村民”(城中村是由村莊演變而來的,目前城中村的居住人口來源復雜,為了突出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城中村的住民,沿用社會普遍稱呼,將其稱為“城中村村民”,不代表本文對研究對象身份的主觀認知)。他們是經濟發達地區的失地農民,在制度層面的被動市民化雖已基本完成,但是觀念和意識層面的轉變比較緩慢,對自身身份的認識是模糊的[1,2],城中村村民仍然沒有完成從村民到市民的蛻變。原有鄉村濃厚的小農觀念與生活方式,使城中村村民市民化具有強烈的被動特征和心理抗拒現象,帶來城市基層治理上的一些矛盾。如何讓城中村村民在生產生活、行為方式、思想觀念、身份意識等方面盡快實現市民化?如何才能使城中村村民盡快認同自己新市民的身份?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完成城中村村民的市民化,不能僅依靠政府從制度方面改變進行外部賦能,更要調動村民自身增能的主動改變的動力[3]。那么城中村村民應該從哪個方向去努力,通過自我增能來實現市民化呢?城中村村民缺乏專業技能、綜合素質不高,導致就業較困難、就業質量不高,加上擁有出租房屋收入和集體分紅,目前城中村村民主動失業現象普遍,更嚴重的是產生了部分閑散人員滋鬧生事,擾亂社會治安。就業作為城市個體生命歷程中的一個重要生活事件,對失地農民融入城市生活有重要影響[4]。農民的生產和生活靈活性大、自主性強,而市民的工作和生活自由度相對受約束較多。就業不僅是城中村村民在城市生存與發展的保障,更是改變思維習慣和生活方式融入城市的重要手段。因而提升城中村村民的就業能力,提高就業質量,是實現市民化的內在動力。本文研究城中村村民就業能力對市民化的影響,找到提升就業能力的途徑,尋找加快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解決基層治理問題的有效措施。
二、模型構建與變量解釋
(一)模型構建
借鑒已有研究成果、理論分析,構建城中村村民就業能力對市民化直接影響效應和就業質量的中介效應的理論模型(圖1)。本文認為就業能力可分解為五個維度,即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職業認同、適應能力、學習能力,對城中村村民市民化具有直接影響效應;同時,就業能力通過就業質量進而影響城中村村民的市民化程度。

圖1 就業能力、就業質量與市民化三者關系理論模型
(二)變量解釋
1.因變量:村民的市民化
戶籍意義上市民化和職業上的非農化是融入城市的物質形態表象特征;社會地位認同、權益保障、思想行為融合、生活質量提升是市民化進程的結果;作為角色主體的農業轉移人口在意識上主動融入城市是市民化進程的開端[5]。王桂新等[6]從居住條件、經濟生活、社會適應、政治參與和心理認同五個維度測算上海市農民工市民化程度,江靜等[7]把居住條件、生活質量、人口素質、基本權利、心理態度五個層面作為市民化的評價指標,辛寶英[8]通過對全國十省農民工從文化融合、經濟地位、社會適應、心理認同四個維度測算市民化程度,楊風、燕浩揚[9]從經濟適應、身份認同、文化適應、行為適應四個方面描述失地農民城市融入情況。綜上,借鑒前人的研究、結合城中村村民的實際情況,本文衡量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程度的指標為生活質量、社會交往、社會地位、身份認同。
2.自變量:村民的就業能力
國內學者普遍根據Fugate[10]劃分的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職業認同、適應能力四個維度對就業能力進行研究。由于城中村村民缺少城市中工作的就業能力,但如果學習能力越強,越容易重新學習非農生產的勞動技能。于是,本文在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職業認同、適應能力四個維度的基礎上,增加“學習能力”維度構建量表,主要參照肖峰[11]開發的就業能力量表,結合城中村村民的具體情況進行設計。采用李克特5點量表法進行打分,即“完全不認同”“比較不認同”“一般”“比較認同”和“完全認同”分別給予“1、2、3、4、5”分。

表1 變量說明(a)

表2 變量說明(b)
3.中介變量:村民的就業質量
本文將從勞動者的微觀角度出發,將城中村村民在工作收入、工作安全性、工作時間、工作與家庭和諧、晉升機會、社會地位方面的滿意度作為就業質量的評價指標[12],分五個等級,依次是“非常不滿意”為1分、“比較不滿意”為2分、“一般”為3分、“比較滿意”為4分、“非常滿意”為5分。
4.控制變量
本文把個體特征(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婚姻狀態、工作情況、月工資、家庭收入情況)、守護型經濟占比(集體分紅與房屋出租占家庭總收入比例)作為控制變量。
三、數據來源與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與描述性分析
本文采取集中方式開展了兩次正式調查,第一次是與相關街道訪談村社干部,了解城中村村民目前的生活生產情況,并到村民居住社區進行實地走訪。第二次是選取有代表性街道進行問卷調查,隨機抽選一些城中村村民到社區服務中心進行問卷調查,調查集中在周末進行。共發放問卷400份,回收問卷354份,回收率為88.5%,排除暫無工作、回答不完整、前后邏輯矛盾的無效問卷,最終共獲取有效問卷276份,有效問卷率為69%。
在被調查的村民中,以男性為主,年齡主要集中在26~45歲;文化程度主要在高中及以上學歷;婚姻狀況以已婚為主,占87.5%;自覺健康狀況以好和一般為主,分別占45.6%和31.7%;村民大部分有穩定工作,占93.5%,只有少數村民靠打零工獲取工作收入;大部分村民的月工資集中在3000~6000元,占75%,6000~10000元占14.9%,月工資10000元以上占4%;家庭年收入在5萬元以下的有26戶,占樣本的9.4%,年收入5萬到10萬的占17%,年收入10萬到15萬的占36.2%,年收入15萬到20萬的占12%,20萬到25萬的占14.1%,25萬及以上的占11.3%,最低家庭年收入為1萬元,最高家庭年收入為50萬元,平均家庭年收入為13.72萬元,由此可以看出家庭年收入有較大的差距。樣本基本情況如表3所示。

表3 樣本情況(N=276)
(二)信度與效度分析
本文將問卷分為人力資本(RL)、社會資本(SH)、職業認同(ZR)、適應能力(SY)和學習能力(XX)五個維度。采用Cronhach's α系數評價量表的內部一致性,>0.7表示量表內部一致性好;同時結合條目對總體的相關系數和刪除該項后Cronhach's α系數對問卷進行信度分析。結果顯示:全部條目的Cronhach's α系數為0.965,且問卷各維度的Cronbach's α系數基本在0.85以上,且所有條目的item-total correlation>0.6,說明本問卷信度較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一般,可靠程度較好,可用于本次研究的調查。
(三)線性回歸分析
本文借助SPSS22.0軟件,采用線性回歸模型估計個體特征變量與就業能力、就業質量、市民化之間的關系,表4為線性回歸結果。

表4 線性回歸結果
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礎上加入了就業能力,就業能力的回歸系數為正(P<0.001),就業能力對城中村村民市民化存在顯著正向影響,表明就業能力能夠促進市民化水平的提高。此時守護型經濟占比對市民化程度的影響在5%的統計水平顯著,系數為-0.136,說明守護型經濟占比越高,反而制約了市民化水平的提高,與目前學者分析的結論一致。本文認為守護型經濟是城中村的獨特區位條件、政治經濟條件決定的,集體分紅依靠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利潤,房屋出租收入依靠的是城中村內的自建房。這兩種收入來源,一是強化了城中村村民對集體經濟組織依賴,二是城中村成為村民的利益共同體,城中村內的社會關系的重要性超過了村外的社會關系,并且在村民追求利益的情況下,城中村的改造也難以推進,村內村外環境的差異,也會影響村民對自身角色的認知,從而制約了市民化水平的提升。
模型四在模型三的基礎上引進了就業質量后,雖然R平方得到提升,但是就業能力對市民化不具有顯著影響,就業質量對市民化具有正向影響,回歸系數為0.191,在5%的統計水平下顯著。新加入的就業質量削弱了就業能力對市民化的影響,就業質量也能影響市民化,說明就業質量在就業能力與市民化之間存在中介作用。
(四)結構方程分析
1.結構方程模型構建
在獲知就業能力對市民化存在顯著正向影響和就業質量在就業能力與市民化之間存在中介作用的前提下,利用結構方程的路徑分析驗證就業質量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AMOS21.0進行結構方程模型的構建,基于專家意見、文獻梳理和理論依據進行模型的構建,然后結合模型擬合度、模型參數估計結果及模型修正指數對模型進行修正,形成模型。
理論模型中共包括1個二階潛變量、7個一階潛變量和30個顯變量,具體為:二階潛變量——就業能力,一階潛變量——人力資本、社會網絡、職業認同、適應能力、學習能力、就業質量和市民化;其中就業能力的相關顯變量在前文已做說明,就業質量通過以下6個方面的滿意度(6個顯變量)來衡量:工作收入、工作安全性、工作時間、工作與家庭和諧、工作的晉升機會和工作的社會地位;市民化也通過4個方面(4個顯變量)來反映:生活質量、社會交往、社會地位、身份認同。
2.模型擬合情況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CMIN/DF=2.308<3,RMR=0.040<0.05,GFI=0.821,IFI=0.927,TLI=0.918,CFI=0.926,PGFI、PAFI均大于0.5,以上大部分指標均達到模型擬合較好的標準,少數指標為可接受,說明模型達到擬合標準,具體見表5。模型及標準化系數見圖2。

表5 模型擬合結果

圖2 就業能力和就業質量對市民化的標準化系數結果
3.模型路徑系數解釋
模型的路徑系數的結果包含路徑系數估計、標準誤、臨界值、顯著性(P值)及標準化路徑系數,路徑系數的正負號表示路徑之間相關性的正負向,標準化路徑系數的大小可反映關系強弱的統計學意義由臨界值和P值反映,P≤0.05認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模型分析結果顯示,大部分模型中的路徑系數有統計學意義,就業能力對就業質量和市民化均存在正向直接影響(P<0.05),標準化路徑系數分別為0.710和0.276;就業質量對市民化存在直接正向影響(β=0.270,P=0.017<0.05)。說明就業能力對就業質量的影響較大,就業能力除了直接影響市民化之外,還能通過就業質量間接影響市民化,就業質量在就業能力和市民化的關系中起起到中介作用。具體見表6。

表6 模型路徑系數結果(N=276)
分析結果顯示,就業能力對市民化既有直接影響也有間接影響,直接效應為0.276,間接效應為0.197,總效應為0.468,間接效應占比41%,說明就業質量在就業能力影響市民化的過程中起到了相當一部分的中介作用。具體見表7。

表7 就業能力和就業質量對市民化的效應分析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本文基于就業理論、社會認同理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構建理論分析模型,分析城中村村民就業能力、就業質量與市民化之間的邏輯關系,并基于廣州市城中村村民的問卷調查數據,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多元線性回歸、結構方程等實證方法,分析了城中村村民就業能力、就業質量、市民化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
城中村村民就業能力包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職業認同、適應能力、學習能力五個維度,其中職業認同對就業能力的影響作用最大,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影響效果較小。可能是因為城中村村民的人力資本水平普遍較低,特別是文化程度,原本在村莊中擁有的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社會網絡不能夠提供獲取城市就業機會的社會資本,失去土地讓他們轉變了就業方向,較高的職業認同可以幫助其有目的地進行自我增能、提升就業能力。
個體特征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與現有部分文獻的研究結論一致。在本研究結論中,城中村村民的年齡與就業能力之間存在倒“U”型,健康狀況越好,就業能力水平和市民化程度越高;性別對城中村村民的就業能力沒有顯著影響,但是性別對市民化有顯著負向影響,男性的市民化程度低于女性;守護型經濟占比增大能夠提升就業能力水平,但是對市民化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可見守護型經濟對城中村村民來說有利也有弊,并不是守護型經濟收入占比越大越好,而是要將守護型經濟收入利用得當,家庭收入不能過分依賴于某一來源。
就業能力對城中村村民的市民化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就業能力中的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職業認同、適應能力、學習能力對其市民化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其中,職業認同對市民化的影響最大,社會資本對市民化的影響最小。
就業質量在就業能力與城中村村民市民化之間存在顯著的中介作用。城中村村民的就業能力對市民化有顯著促進作用,并且通過就業質量作為中介發生傳導;就業能力水平提升會提高城中村村民獲得高質量就業崗位的機會,從而獲得就業中附帶社會地位等隱含價值,以促進市民化水平的提高。
(二)政策建議
為了真正促進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發展,不僅需要提升就業能力,而且需要實現高質量的就業,獲得就業附帶的經濟收入、社會地位、社會網絡等。提高城中村村民的就業能力,增強其對城市工作崗位的職業認同,豐富其在城市生活圈的社會資本,對于促進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的推進有積極作用。通過數據分析結果,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轉變守護型經濟收入的用途,促進物業升級。研究發現,守護型經濟收入能提升城中村村民的就業能力,但是也會阻礙市民化進程。守護型經濟會抑制村民外出就業的積極性,一方面集體經濟組織需弱化集體分紅的金錢價值,轉變為村民增添福利待遇,可為城中村村民提供無償的就業培訓、就業咨詢、創業幫扶等,幫助村民提升就業能力,提高就業質量,消除坐享其成、不思進取的懶惰作風;另一方面,在與村公司領導的訪談中了解到,由于村缺乏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2000年后,村集體經濟逐漸退出工業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改為以物業出租為主。房屋出租,即物業出租已成為了城中村村民的主要收入來源。雖然房屋出租對市民化的負面作用確實存在,但是現代城市并不排斥物業經濟,作為外來人口大省廣東的一線城市更是需要物業經濟,政府應對村公司和村民進行正向引導,提升村民發展市場經濟的意識和能力,促進物業升級,亦可能有利于其市民化。
第二,著力提升城中村村民的職業認同。研究發現職業認同對城中村村民就業能力的影響最大,就業能力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提高,50歲左右開始隨之下降。以40歲以下青壯年為重點對象,特別是暫無工作的年輕人,重視對其進行職業教育,引導其轉變就業觀念,明晰其對職業發展方向的感知,有目的性的提高其崗位所需的勞動技能,喚起城中村村民發揮自身能力的成就感,從而提升城中村村民對其能夠從事職業認同意識,就業能力也得以提高,進而就業質量提升,城中村村民在“業緣”的社會網絡隨之壯大,打破城中村目前封閉的社交網絡,城中村村民對自身與市民的社會認同差距拉近,對自我市民身份的認同度提升,進而促進了市民化進程。
第三,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人力資本不足是城中村村民就業的重要障礙。隨著時代的快速發展,就業崗位對文化水平的要求越來越高,城中村村民要將目光放長遠,不能只局限于眼前的利益,不能安逸于當下的生活,要重視對子女的教育投資,讓其掌握更多的知識去創造價值。社區應該營造崇文重教的良好氛圍,集體經濟組織可對優秀學子給予獎勵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