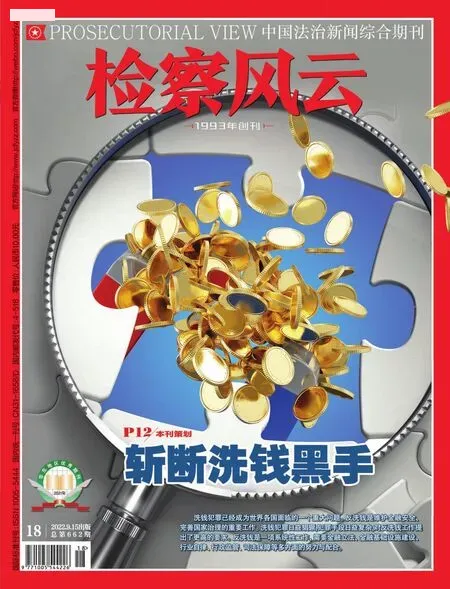完刑人困境與社會集體無意識
文·圖/林樸

在“多倫多電影節”首映、屢獲各類獎項的日本影片《美好的世界》,講述前黑社會分子三上正夫(役所廣司飾演),因殺人罪被判入獄,服刑13年后重返社會,努力融入社會但處處碰壁、找不到出路的故事。
這是一部頗具觀賞性的作品。攝影、敘事、表演都有獨到之處,細細觀賞,當然是一部“傳統意義”上的好電影。但回到電影的主題上,不免令人覺得,好的電影技巧浪費在了一個自我禁錮的范式內。這里所謂自我禁錮的范式是:社會大眾對有前科的社會人員,太過嚴苛,不論是就業還是融入社會,都過于排斥,使他們在回歸社會的過程中,受到了較為難堪的境遇。有些人走投無路再次犯罪;有些極端者,甚至選擇一死了之。三上正夫的結局正是后者。當只有一部電影講述這樣的故事,在認知上它是獨特的;但當一大堆電影講述同類的故事,我們便稱之為“范式”。在數量龐大的同類作品中,《美好的世界》沒有創新的表達,沒有打破范式,這算是筆者對新作品特有的苛責。
英語世界里有這樣一句名言,“Everybody deserves a second chance”(每個人都應該有重來的機會)。這句話也常被用于服完刑回歸社會的人。他們應該有回到社會被平等對待的權利。但現實不是這樣,甚至人們很難做到這一點。不論東方還是西方社會,對有前科的人,人們大多持警惕、排斥的態度,他們回歸社會可謂困難重重。這個應然和實然的沖突,構成了這類電影的表達范式。
刑罰是法律體系對犯罪事實應受懲罰定性定量的判定和執行。那么,服刑人員刑滿釋放后,他就洗清了所有犯過的罪孽,變成一個和沒有前科的人一樣的社會人了嗎?在法律體系看來,的確如此。然而,現實生活中,社會大眾很大程度上似乎并不認同這一點。層出不窮、不論拍多少不同個體的完刑人回歸社會的電影故事,全都像在同一個范式中不斷重復,并且指向同一個困境。
社會大眾是由各行各業、年齡和身份極為離散的人構成的。世俗社會中,他們往往不約而同地對完刑人予以集體無意識地排斥。翻拍同類故事的制作人或創作者意識到了這種沖突,抓住了曾經的罪犯在這種集體無意識面前孱弱的一面,在藝術上形成了近乎流水線作業的悲劇滿足感反差;甚至,無一例外地將悲劇性結果歸咎于社會大眾的冷漠與偏見。
筆者以為,這差不多是謬論。當幾乎沒有鏡頭和故事對準受害者遭受苦難后的境遇,無視社會大眾對犯罪的擔憂,似乎只能讓觀眾隨著編劇和導演們一起陷于無法突破的社會困境,尋求烏托邦式的解決路徑。人們依舊在不停地追問(難道大眾沒有權利責問),犯罪的后果被完全糾正了嗎?完刑人再犯的風險被降低到了最低嗎?他們真心懺悔,跟過去(犯罪)完全切割了嗎?如此種種,卻往往忽略了出獄者成為累犯,還有一部分原因恰恰源自社會大眾對他們的歧視和排斥。
當然,社會大眾的反應是真實的,他們在以群體無意識的方式,通過暴力機構的威懾某種意義上把罪犯的刑期變長,令罪罰變得超出法律體系的認定。這不是冷漠和偏見,而是社會大眾對犯罪行為的深層抑制本能。
藝術工作者正在嘗試的,是用作品告訴觀眾:世界并非那么美好,犯罪行為除了受法律體系懲罰之外,還會在更長時間內受到來自社會大眾的軟性懲罰。這是一個客觀現象,并非僅僅出于冷漠與偏見,甚至并非只針對完刑人,而是整個社會大眾的一種自我惕厲——不要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