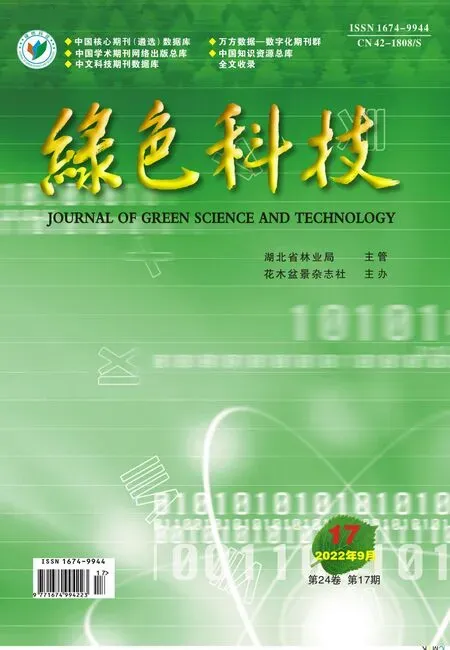江西省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耦合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模式探究
王 剛,楊一帆
(江西理工大學(xué) 商學(xué)院,江西 南昌 330013)
1 引言
城鎮(zhèn)化是指人口向城市流動(dòng)并聚集,人口結(jié)構(gòu)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逐步發(fā)生轉(zhuǎn)變。農(nóng)村人口隨著向城市聚集逐漸轉(zhuǎn)為城市人口,第一產(chǎn)業(yè)為主的發(fā)展模式隨著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逐漸轉(zhuǎn)變?yōu)橐缘诙⒌谌a(chǎn)業(yè)為主的過程。我國城鎮(zhèn)化進(jìn)程具有規(guī)模大、速度快的特征,主要可分為緩慢起步階段、爆發(fā)增長階段和穩(wěn)進(jìn)發(fā)展階段。在早期快速城鎮(zhèn)化的階段中,是以損耗部分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為代價(jià)的,城鎮(zhèn)化的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使生態(tài)環(huán)境遭受影響,產(chǎn)生一種交互脅迫的耦合關(guān)系[1]。之后黨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鎮(zhèn)化建設(shè)方針,指出新型城鎮(zhèn)化是一種以人為核心,體現(xiàn)生態(tài)文明和諧發(fā)展理念的高質(zhì)量的城鎮(zhèn)化。指出了新型城鎮(zhèn)化發(fā)展是需要協(xié)調(diào)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一種城鎮(zhèn)化發(fā)展模式。
對于新型城鎮(zhèn)化與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耦合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眾多學(xué)者都進(jìn)行了深入研究。胡祥福等[2]建立了雙重復(fù)合系統(tǒng),并使用熵權(quán)法和耦合協(xié)調(diào)度模型對江西省兩者的協(xié)調(diào)關(guān)系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發(fā)現(xiàn)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發(fā)展進(jìn)程的不同步。鄧宗兵等[3]在耦合協(xié)調(diào)度模型的基礎(chǔ)上,增加了相對發(fā)展模型和固定效應(yīng)模型進(jìn)行研究,發(fā)現(xiàn)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發(fā)展不足。呂潔華等[4]采用灰色關(guān)聯(lián)度模型分析了兩者耦合的主要因素并發(fā)現(xiàn)黑龍江省城鎮(zhèn)化發(fā)展超過生態(tài)環(huán)境發(fā)展。梁龍武等[5]則是站在城市群城市化的角度對京津翼地區(qū)兩者協(xié)同關(guān)系進(jìn)行研究,也同樣發(fā)現(xiàn)生態(tài)環(huán)境發(fā)展開始落后于城市化發(fā)展。柯小玲等[6]則是以湖北省為例,采用空間自相關(guān)分析對兩者耦合協(xié)調(diào)度的空間關(guān)系,發(fā)現(xiàn)周圍地區(qū)會(huì)對兩者的協(xié)調(diào)度產(chǎn)生影響。趙建吉等[7]則是以黃河流域?yàn)檠芯繀^(qū)域,對兩者耦合的時(shí)空格局進(jìn)行了探究,發(fā)現(xiàn)了在推進(jìn)新型城鎮(zhèn)化發(fā)展的情況下,推動(dòng)生態(tài)環(huán)境發(fā)展壓力逐漸顯現(xiàn)。
2 研究區(qū)域、數(shù)據(jù)來源和指標(biāo)體系
2.1 研究區(qū)域概況
江西省地處我國東南部,位于北緯24°29′~30°04′,東經(jīng)113°34′~118°28′之間,地屬華東地區(qū),氣候溫暖,屬于亞熱帶濕潤氣候。全省面積167064 km2,下轄地級(jí)行政區(qū)11個(gè),省會(huì)為南昌市。地理環(huán)境和區(qū)域位置優(yōu)越,地下礦產(chǎn)資源分豐富,享稱“稀土王國”“有色金屬之鄉(xiāng)”。
根據(jù)江西省第三次國土調(diào)查數(shù)據(jù)顯示,常住人口城鎮(zhèn)化率從2009年的43.18%,至2019年已經(jīng)提高到了57.42%。城鎮(zhèn)化率于2014年底突破50%,城鎮(zhèn)化穩(wěn)步發(fā)展。但據(jù)2020年統(tǒng)計(jì)年鑒數(shù)據(jù)顯示,2019年末,南昌市城鎮(zhèn)化率高達(dá)75.16%,而全省城鎮(zhèn)化率最低的宜春市為51.22%。表明江西省城鎮(zhèn)化發(fā)展速度較快,但區(qū)域間的差距較大,城鎮(zhèn)化區(qū)域發(fā)展不平衡。
根據(jù)第九次森林清查報(bào)告顯示,江西省森林面積為1.53億畝,畝森林覆蓋率為61.16%,森林覆蓋率在全國排名第2。濕地保有量為1365萬畝,在2016~2019年期間,濕地保護(hù)率為61.99%,在全國生態(tài)環(huán)境建設(shè)中,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處于前列水平。
2.2 數(shù)據(jù)來源
本文研究江西省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耦合協(xié)調(diào)情況, 研究數(shù)據(jù)來源于2006~2020年的《江西省統(tǒng)計(jì)年鑒》《中國城市統(tǒng)計(jì)年鑒》。
2.3 指標(biāo)體系構(gòu)建過程
為了更好研究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耦合協(xié)調(diào)情況,將指標(biāo)體系分為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兩個(gè)系統(tǒng)層,在客觀性的前提下,本著科學(xué)的系統(tǒng)觀念,為實(shí)現(xiàn)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原則,參考了劉耀彬[8]、畢國華[9]、王國惠[10]等研究成果,將新型城鎮(zhèn)化從人口、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和空間維度分成4個(gè)子系統(tǒng)層,在生態(tài)環(huán)境系統(tǒng)下,使用聯(lián)合國用于研究環(huán)境問題的模型框架,即“PSR”模型——“壓力-狀態(tài)-響應(yīng)”模型,將生態(tài)環(huán)境從狀態(tài)、壓力和響應(yīng)維度分成3個(gè)子系統(tǒng)層。接著采用文獻(xiàn)分析法和統(tǒng)計(jì)分析法對歷年相關(guān)文獻(xiàn)中的指標(biāo)進(jìn)行聚類和識(shí)別,篩選出頻次出現(xiàn)高的指標(biāo),再依據(jù)國家新型城鎮(zhèn)化發(fā)展戰(zhàn)略和江西省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建設(shè)的特征,最后選取了18個(gè)新型城鎮(zhèn)化指標(biāo)和11個(gè)生態(tài)環(huán)境指標(biāo),構(gòu)建了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指標(biāo)體系,如表1所示。

表1 新城鎮(zhèn)化與生態(tài)環(huán)境指標(biāo)體系

續(xù)表1
3 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耦合協(xié)調(diào)關(guān)系
本文共選取了城鎮(zhèn)化指標(biāo)18個(gè),生態(tài)環(huán)境指標(biāo)11個(gè),按時(shí)間序列進(jìn)行分析,使用熵權(quán)法和線性權(quán)重法確定各指標(biāo)權(quán)重和兩個(gè)系統(tǒng)每年綜合評(píng)價(jià)指數(shù),采用耦合協(xié)調(diào)度模型對兩者耦合協(xié)調(diào)關(guān)系進(jìn)行分析。
3.1 數(shù)據(jù)的標(biāo)準(zhǔn)化
由于所選取的指標(biāo)數(shù)據(jù)量較多并且指標(biāo)間的單位各異,直接運(yùn)用熵權(quán)法計(jì)算得出的結(jié)果有效度和可靠度不足,其權(quán)重結(jié)果不能客觀準(zhǔn)確反映指標(biāo)的真實(shí)權(quán)重,所以,要先對具體指標(biāo)數(shù)據(jù)進(jìn)行無綱量化處理,本文采取的是極值標(biāo)準(zhǔn)化法將指標(biāo)數(shù)據(jù)統(tǒng)一標(biāo)準(zhǔn)化,公式如下:
Xij為正向指標(biāo):
(1)
Xij為負(fù)向指標(biāo):
(2)
式(1)、(2)中:Xij是原始指標(biāo)數(shù)據(jù),Zij是標(biāo)準(zhǔn)化后的指標(biāo)數(shù)據(jù),i(i=1,2,…,n)指的是所選取指標(biāo)的年份,j(j=1,2,…,n)指的是所選取指標(biāo)第年的項(xiàng)數(shù)。
3.2 指標(biāo)權(quán)重的計(jì)算
指標(biāo)權(quán)重的確定方法多種多樣,主要分為主觀賦權(quán)法和客觀賦權(quán)法,基于權(quán)重計(jì)算的客觀性和可靠性原則,本文使用Excel工具,采用熵值法,通過原始指標(biāo)數(shù)據(jù)間的數(shù)學(xué)關(guān)系來確定權(quán)重,首先計(jì)算所選取的39個(gè)指標(biāo)具體數(shù)據(jù)的熵值,接著計(jì)算差異系數(shù),最后算出指標(biāo)數(shù)據(jù)的熵權(quán)來確定權(quán)重。具體步驟如下所示。
首先,計(jì)算相對熵所用到的概率,即第年第項(xiàng)指
標(biāo)的數(shù)據(jù)所占的比重,公式如下:
(3)
其次,計(jì)算第j項(xiàng)指標(biāo)熵值,為了避免數(shù)據(jù)值無意義,當(dāng)Pij=0時(shí),令ln(Pij)的值為0公式如下:
(4)
接著,計(jì)算第項(xiàng)指標(biāo)的差異系數(shù),公式如下:
gj=1-sj
(5)
最后,計(jì)算得出第項(xiàng)指標(biāo)權(quán)重,公式如下:
(6)
式(3)~式(6)中,計(jì)算所得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各指標(biāo)體系權(quán)重如表1所示。
由表1各個(gè)指標(biāo)權(quán)重?cái)?shù)據(jù)可知,在新型城鎮(zhèn)化系統(tǒng)中,第三產(chǎn)業(yè)GDP比重和第三產(chǎn)業(yè)就業(yè)人數(shù)占比所占權(quán)重相較其他指標(biāo)更大,對新型城鎮(zhèn)化的作用力和影響力更大。在生態(tài)環(huán)境系統(tǒng)中,工業(yè)廢氣排放總量、工業(yè)固體廢物產(chǎn)生量和工業(yè)污染治理投資額指標(biāo)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作用力和影響力更大。
3.3 綜合評(píng)價(jià)指數(shù)
綜合評(píng)價(jià)指數(shù)是以指標(biāo)的重要程度作為權(quán)數(shù),綜合不同的指標(biāo)并轉(zhuǎn)換為相同度量尺度的個(gè)體指數(shù),通過比較指數(shù)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能反映出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綜合發(fā)展?fàn)顩r,公式如下:
(7)
式(7)中:Wj表示為第項(xiàng)指標(biāo)在系統(tǒng)中所占的權(quán)重,zij表示為標(biāo)準(zhǔn)化后的原始數(shù)據(jù),F(xiàn)j表示為綜合評(píng)價(jià)指數(shù),其數(shù)值越接近于1,代表系統(tǒng)綜合發(fā)展情況越好。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綜合評(píng)價(jià)指數(shù)如圖1所示。

年份
從圖1可以看出,在新型城鎮(zhèn)化系統(tǒng)中,江西省2005~2019年的綜合評(píng)價(jià)指數(shù)呈直線上升趨勢,說明江西省的新型城鎮(zhèn)化發(fā)展保持著持續(xù)穩(wěn)步增長態(tài)勢。在2005年時(shí),新型城鎮(zhèn)化發(fā)展水平低,直到2011年時(shí),綜合評(píng)價(jià)指數(shù)都低于0.3,屬于較低的發(fā)展水平。而在2012~2015年,綜合評(píng)價(jià)指數(shù)大致在0.3~0.6之間,處于中等發(fā)展水平。到2016年后,開始達(dá)到較高的發(fā)展水平,并且新型城鎮(zhèn)化發(fā)展也愈加迅速。這與黨的“十八大”所提出新型城鎮(zhèn)化建設(shè)戰(zhàn)略下所制定的《江西省新型城鎮(zhèn)化規(guī)劃(2014~2020)》的宏觀政策支持有關(guān),并且和經(jīng)濟(jì)的快速發(fā)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升息息相關(guān)。
在生態(tài)環(huán)境系統(tǒng)中,綜合評(píng)價(jià)指數(shù)處于波動(dòng)式上升趨勢,其整體發(fā)展態(tài)勢比較穩(wěn)定。2005~2008年綜合評(píng)價(jià)指數(shù)在0.3左右波動(dòng),于2007年到達(dá)峰值0.442后開始回落趨于穩(wěn)定,大致處于由低發(fā)展水平向中等發(fā)展水平的過渡階段。2009~2017年則穩(wěn)定在0.5~0.6波動(dòng),長期處于一個(gè)中等發(fā)展水平,這是與江西生態(tài)環(huán)境優(yōu)勢和保護(hù)政策有關(guān)。而在2018~2019年開始達(dá)到較高的發(fā)展水平,這與《“十三五“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規(guī)劃》有關(guān),尤其是在2018年江西省開展的污染防治攻堅(jiān)戰(zhàn)中,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和建設(shè)取得了優(yōu)異成績。
3.4 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耦合協(xié)調(diào)度
耦合起初是源自物理學(xué)中的概念,是指多個(gè)系統(tǒng)在各種不同的相互作用力下,對各自系統(tǒng)產(chǎn)生影響以至聯(lián)合的現(xiàn)象。在此概念推廣得出的耦合度則是度量系統(tǒng)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程度,是可以通過量化的數(shù)值反映出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兩個(gè)系統(tǒng)之間地相互作用力的大小或程度。兩個(gè)系統(tǒng)的耦合度模型可表示為:
(8)
式(8)中,F(xiàn)1和F2分為表示為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這兩個(gè)系統(tǒng),C則表示為兩個(gè)系統(tǒng)的耦合度,其數(shù)值大小處于[0,1],耦合度越接近于1,表示兩個(gè)系統(tǒng)的相互作用程度越大、相互聯(lián)合影響程度越深。
由于耦合度只能反映出系統(tǒng)間相互作用強(qiáng)度,不能反映出系統(tǒng)間的綜合水平,所以在耦合度模型基礎(chǔ)上引入?yún)f(xié)調(diào)發(fā)展指數(shù)構(gòu)建出耦合協(xié)調(diào)度模型[11],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指數(shù)公式如下:
T=αF1+βF2
(9)
式(9)中,T表示為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指數(shù),待定參數(shù)α和β的數(shù)值大小是由兩個(gè)系統(tǒng)的在綜合發(fā)展中的重要程度和影響程度所決定,參考已有文獻(xiàn)和考慮江西省實(shí)際綜合發(fā)展情況,認(rèn)為兩個(gè)系統(tǒng)在江西省的綜合發(fā)展中處于同等重要地位,因此參數(shù)α和β都設(shè)置為0.5。
耦合協(xié)調(diào)度模型表示為:
(10)
式(10)中:D表示為耦合協(xié)調(diào)度,其數(shù)值大小處于[0,1],耦合協(xié)調(diào)度越接近于1,表示兩個(gè)系統(tǒng)綜合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程度越高,兩個(gè)系統(tǒng)的發(fā)展關(guān)系越接近于良性發(fā)展。參考王國惠[10]和同類型文獻(xiàn)研究,可將耦合協(xié)調(diào)度劃分成五個(gè)階段,階段劃分如表2所示。

表2 耦合協(xié)調(diào)度階段劃分
根據(jù)上述步驟計(jì)算可以得出2005~2019年江西省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耦合度,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指數(shù)和耦合協(xié)調(diào)度以及所對應(yīng)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階段,如表3所示。

表3 2005~2019年江西省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耦合協(xié)調(diào)關(guān)系
4 評(píng)價(jià)和討論
4.1 評(píng)價(jià)
2005~2006年,兩個(gè)系統(tǒng)處于輕度失調(diào)的耦合協(xié)調(diào)階段。此時(shí)江西省新型城鎮(zhèn)化發(fā)展還處于起步初始階段,整體城鎮(zhèn)化水平都非常低。生態(tài)環(huán)境建設(shè)發(fā)展情況相較于城鎮(zhèn)化發(fā)展要更優(yōu),但也處于較低的水平,新型城鎮(zhèn)化發(fā)展水平遠(yuǎn)落后于生態(tài)環(huán)境發(fā)展。
2007~2009年,兩個(gè)系統(tǒng)處于勉強(qiáng)協(xié)調(diào)的耦合協(xié)調(diào)階段。江西省期間開始著力發(fā)展城市建設(shè),以中心城市和鄉(xiāng)鎮(zhèn)作為建設(shè)重點(diǎn)和發(fā)展中心,增強(qiáng)城市功能和居住生態(tài)環(huán)境。此時(shí)新型城鎮(zhèn)化處于增速發(fā)展的初始階段,城鎮(zhèn)化發(fā)展水平開始爬升,生態(tài)環(huán)境建設(shè)發(fā)展水平也出現(xiàn)了短暫的升高,兩者都在穩(wěn)步發(fā)展。
2010~2016年,兩個(gè)系統(tǒng)處于良好協(xié)調(diào)的耦合協(xié)調(diào)階段。此時(shí),江西省新型城鎮(zhèn)化發(fā)展處在爆發(fā)增長階段,生態(tài)環(huán)境發(fā)展較平穩(wěn)且發(fā)展依舊優(yōu)于前者,但兩者差距正在逐年縮小。在2012年,兩者短暫處在同一水平上后繼續(xù)保持著生態(tài)環(huán)境建設(shè)的領(lǐng)先性,直至2015年起,新型城鎮(zhèn)化發(fā)展開始超過生態(tài)環(huán)境,由過去的新型城鎮(zhèn)化滯后發(fā)展轉(zhuǎn)變?yōu)樯鷳B(tài)環(huán)境滯后發(fā)展。
2017~2019年,兩個(gè)系統(tǒng)處于優(yōu)質(zhì)協(xié)調(diào)的耦合協(xié)調(diào)階段,江西省積極響應(yīng)國家關(guān)于新型城鎮(zhèn)化高質(zhì)量發(fā)展戰(zhàn)略政策,多體系協(xié)同發(fā)展,盡管生態(tài)環(huán)境發(fā)展依舊落后于新型城鎮(zhèn)化約一個(gè)階段水平,但兩者發(fā)展步調(diào)同步,在發(fā)展同時(shí)保持差距穩(wěn)定。
整體來看,江西省在2005年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耦合度為0.586,處于中等耦合水平。在2006~2019年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相互作用程度強(qiáng),耦合水平在期間內(nèi)出現(xiàn)過輕微波動(dòng),整體都維持在比較高的耦合狀態(tài)。在耦合協(xié)調(diào)方面,在整個(gè)期間耦合協(xié)調(diào)度都處于持續(xù)增速的上升狀態(tài)。2005~2009年耦合協(xié)調(diào)水平處在良好偏下的水平上,2010~2016年發(fā)展成良好協(xié)調(diào),在2017~2019年達(dá)到了優(yōu)質(zhì)的耦合協(xié)調(diào)階段。
這說明,盡管江西省兩個(gè)系統(tǒng)之間持續(xù)存在著穩(wěn)定的強(qiáng)作用力,但在早期和中期都沒能很好地協(xié)調(diào)好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地建設(shè)工作,沒有利用好兩者在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發(fā)展中相互關(guān)聯(lián)、相互影響的關(guān)系。直至中后期,隨著“十三五”戰(zhàn)略布局下,開始對兩個(gè)系統(tǒng)進(jìn)行協(xié)同調(diào)整。在發(fā)展新型城鎮(zhèn)化的過程中兼顧生態(tài)環(huán)境并且形成相互促進(jìn)的良性發(fā)展的耦合協(xié)調(diào)體系,使兩者的耦合協(xié)調(diào)狀態(tài)越來越佳。
4.2 討論
江西省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耦合協(xié)調(diào)發(fā)展主要經(jīng)歷了由單系統(tǒng)發(fā)展模式轉(zhuǎn)變?yōu)槎嘞到y(tǒng)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模式。具體由兩者相互制約脅迫關(guān)系轉(zhuǎn)為相互良性影響的促進(jìn)關(guān)系,最后發(fā)展成有機(jī)統(tǒng)一的協(xié)同發(fā)展模式。表現(xiàn)形式從新型城鎮(zhèn)化滯后發(fā)展轉(zhuǎn)變?yōu)樯鷳B(tài)環(huán)境滯后發(fā)展。其目標(biāo)是在保持兩者優(yōu)質(zhì)高水平發(fā)展的基礎(chǔ)上實(shí)現(xiàn)同步協(xié)調(diào)發(fā)展,讓兩者發(fā)展處在同一水平層面上,最終實(shí)現(xiàn)全省綜合實(shí)力和發(fā)展水平的提升。在此目標(biāo)基礎(chǔ)上對江西省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耦合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模式的建設(shè)途徑進(jìn)行探討,其關(guān)鍵的影響因素在于協(xié)調(diào)性,具體為實(shí)現(xiàn)系統(tǒng)層面的協(xié)調(diào)和實(shí)現(xiàn)各具體要素間的協(xié)調(diào)。本文據(jù)此提出合理的耦合協(xié)調(diào)發(fā)展模式的建設(shè)路徑建議:
(1)在宏觀的系統(tǒng)層面進(jìn)行耦合協(xié)調(diào)路徑建設(shè)。堅(jiān)持發(fā)展以人為核心的生態(tài)城鎮(zhèn)化建設(shè),在保持新型城鎮(zhèn)化發(fā)展的基礎(chǔ)上,著力協(xié)調(diào)建設(shè)好生態(tài)環(huán)境,建設(shè)生以態(tài)環(huán)境為重心之一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體系。經(jīng)濟(jì)是發(fā)展的基礎(chǔ),大力發(fā)展生態(tài)市場建設(shè),引領(lǐng)低碳經(jīng)濟(jì)發(fā)展,在生態(tài)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推力下建設(shè)生態(tài)環(huán)境,在綜合水平上擺脫滯后于新型城鎮(zhèn)化發(fā)展?fàn)顩r,先實(shí)現(xiàn)綜合水平的協(xié)調(diào),再進(jìn)一步打造農(nóng)業(yè)生態(tài)建設(shè)模式、工業(yè)生態(tài)建設(shè)模式以及服務(wù)業(yè)生態(tài)建設(shè)模式,對第一、第二和第三產(chǎn)業(yè)進(jìn)行生態(tài)優(yōu)化升級(jí),深化與新型城鎮(zhèn)化的耦合協(xié)調(diào)發(fā)展。
(2)以城市為單位進(jìn)行耦合協(xié)調(diào)路徑建設(shè)。從整體來看,江西省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建設(shè)發(fā)展協(xié)調(diào)水平較好,但城市之間的協(xié)調(diào)性不足。城市之間的城鎮(zhèn)化水平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建設(shè)都有著比較大的差異,具體表現(xiàn)為南昌市城鎮(zhèn)化水平遠(yuǎn)高于宜春市,且南昌市屬于生態(tài)滯后,而宜春市處于城鎮(zhèn)化滯后[2]。因此,可以以城市為單位進(jìn)行差異化戰(zhàn)略發(fā)展,從互補(bǔ)性原則上出發(fā),先協(xié)調(diào)好城市內(nèi)部的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建設(shè)發(fā)展。由于周圍地區(qū)的發(fā)展會(huì)影響到兩者的耦合協(xié)調(diào)關(guān)系[6],所以堅(jiān)持以中心城市南昌為重點(diǎn)向周圍輻射,將各個(gè)城市鏈接,建設(shè)網(wǎng)狀生態(tài)城市群。繼以城市為基點(diǎn),向內(nèi)部繼續(xù)深化協(xié)調(diào),加速推動(dòng)城鄉(xiāng)融合,消除城市二元矛盾,構(gòu)建城鄉(xiāng)一體化發(fā)展。最后構(gòu)建出協(xié)同以深化城市內(nèi)部的縱向一體化發(fā)展模式和城市與城市之間的橫向一體化發(fā)展模式的生態(tài)城市群,以達(dá)成新型城鎮(zhèn)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耦合協(xié)調(diào)發(fā)展。
(3)在要素層面進(jìn)行耦合協(xié)調(diào)路徑建設(shè)。在城鎮(zhèn)化方面,由于空間城鎮(zhèn)化發(fā)展相較于人口、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城鎮(zhèn)化更落后,所以可以加快空間城鎮(zhèn)化發(fā)展,加大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的投入力度。對已建設(shè)好的城市空間布局進(jìn)行重新調(diào)整,以適應(yīng)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需求,而對于開發(fā)程度低的地區(qū)以發(fā)展的眼光進(jìn)行提前合理規(guī)劃,避免浪費(fèi)。在生態(tài)環(huán)境方面,堅(jiān)持垃圾分類,提高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加大工業(yè)污染治理投資和提高工業(yè)廢棄物回收利用率,并加強(qiáng)城市污染防治,減少生態(tài)環(huán)境壓力,為協(xié)調(diào)新型城鎮(zhèn)化發(fā)展提供良好環(huán)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