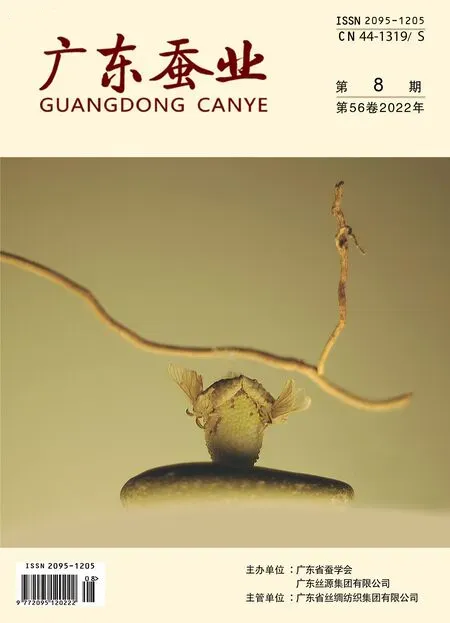貴州民族村寨旅游效應比較研究
——以秀水村、寨沙侗寨、云舍村為例
劉 鋒 劉 韜 劉 慧
(1.貴州師范學院旅游文化學院 貴州貴陽 550018;2.安順學院旅游學院 貴州安順 561000;3.衡陽市氣象局 湖南衡陽 421009)
鄉村旅游在帶動村寨經濟發展、提高農民就業和收入、改善基礎設施、優化生態環境等各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貴州是少數民族居多的省份,民族村寨數量眾多且有著豐富的民族文化色彩,這使得貴州民族村寨的鄉村旅游得到了長足發展。前期通過調研、專家討論,選出貴州安順秀水村、江口縣寨沙侗寨及云舍村作為民族村寨典型旅游目的地,三個村寨各具不同特征,為貴州民族村寨旅游效應比較研究提供了實證基礎。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總結借鑒相關學者在旅游效應方面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實地考察、個人訪談、問卷調查,以及行業領域專家和學者的專題研討和咨詢,構建了以旅游效應為目標層,經濟效應、社會效應、環境效應、文化效應為準則層,居民人均年收入等20個標的為指標層的旅游效應體系(見表1)。對準則層及其對應的指標層進行評判的標度取值采用1~9標度法進行指標的重要性評判,按照AHP計算方法求出各指標的權重值,并通過一次性檢驗[1]。指標評價采納5級制,分別為1、2、3、4、5,評價尺度:4.20~5.00為極高水平,3.50~4.20為較高水平,3.00~3.50為一般水平,2.00~3.00為較低水平,2.00以下為極低水平。

表1 民族村寨旅游效應體系表
研究數據通過深度訪談、問卷調查等形式收集。問卷數據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數進行信度檢驗,alpha系數愈高,代表量表的內部一致性愈佳。通常認為,alpha系數在0.8以上,則信度甚佳;alpha系數在0.7以上,該變量可信[2]。采用KMO值和Bartlett's test進行效度檢驗,KMO值越大,越有利于因子分析。KMO值在0.7以上,適合進行因子分析;Bartlett's test顯著性水平sig值低于0.05的標準,則問卷有效[3]。運用SPSS 24.0對問卷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對案例地旅游效應指標層、準則層及目標層進行比較分析,以期找出影響旅游效應的主要因素及存在的共性問題,進而提出相應建議,助推民族村寨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
2 案例地基本情況及比較
秀水村位于貴州安順普定縣中部,面積9.2 km2,森林覆蓋率95%,全村878戶3 247人,民族主要為漢族、苗族、布依族,村民人均純收入13 000余元/年。2015年,興偉集團幫扶秀水村開發鄉村旅游,建設了波玉河漂流、龍灘露營基地、秀水湖、水上樂園等56個旅游景點。秀水村現游客接待量100余萬人次/年,旅游收入1 000余萬元/年。秀水村成立村級公司對旅游進行經營管理,村支兩委經營管理公司,景區效益為村民所共享,獨創了“秀水五股”利益分配模式,即人頭股(占10%)、土地股(占30%,每畝土地每年1 000元)、笑益股(占30%)、孝親股(占5%,65歲以上老人每人每月500元)、發展股(占25%)。
寨沙侗寨位于貴州銅仁江口縣太平河畔,世界自然遺產梵凈山腳下,距梵凈山大門1.5 km,面積0.08 km2,森林覆蓋率82%,全村75戶304人,其中侗族占比85%,村民人均純收入30 000余元/年[4]。2008年,在縣政府統一規劃、縣直部門幫扶、村里能人帶領下,整合各類專項資金5 000多萬修建基礎設施、公共景觀,給予參與旅游開發的農戶建設補貼和經營扶持[5]。目前,全寨有農家樂74戶,其中村民自己經營有11戶,外來租賃經營有63戶,每戶租金8萬元~10萬元/年,游客接待量54余萬人次/年,旅游收入900余萬元/年,村民旅游行業參與度非常高。寨沙實行村民自主經營、管理自治原則,成立了組委會和鄉村旅館合作社,負責調解村民糾紛、衛生打理、安全防范、公共設施及集體資產管理等。
云舍村位于貴州銅仁江口縣太平河畔,距世界自然遺產梵凈山南山門23 km,全村面積4 km2,森林覆蓋率91%,全村529戶2 235人,其中楊姓土家族占比高達93.7%,有著600年悠久歷史,是“中國土家第一村”,村民人均純收入11 000余元/年。2013年年底,蘇州重點支持江口縣文化旅游和云舍歷史文化名村建設,投入幫扶資金9 000萬元,其中超六成用于支持當地建設美麗鄉村、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等項目[6]。縣政府成立的公司負責景區的經營管理、項目開發等事項,村民則以農家樂經營為主,現有餐飲33家、民宿26家(租賃價格每年3萬元~5萬元),旅游業從業人員280余人,游客接待量30余萬人次/年,旅游收入500余萬元/年。
3個案例地對比,文化背景差異明顯,秀水村是多民族聚居村落,寨沙侗寨和云舍村分別是侗族、土家族聚居地。在景區核心力量導向上,秀水村采取村委會成立村級公司,負責景區開發、經營與管理的“公司核心力量導向”模式;寨沙侗寨是由寨組委會、合作社負責公共事務,社區居民自主經營管理的“居民核心力量導向”模式;云舍村采取地方政府組建公司負責景區開發、經營與管理,社區居民參與旅游業的“政府核心力量導向”模式。在經濟特征上,秀水村以集體經濟為主,寨沙侗寨以個體經濟為主,云舍村以集體經濟為主、個體經濟為輔。
3 案例地問卷調查情況
秀水村發放旅游效應調查問卷86份,最終收回有效問卷82份,問卷有效率95.35%。問卷信度檢驗結果Cronbach′s alpha系數為0.802,問卷效度檢驗結果KMO值為0.821,Bartlett's test的顯著性水平sig值為0.000,說明村民問卷內部的一致性較為理想,問卷的設計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調查對象人口學特征:女性36位,占比43.9%,男性46位,占比56.1%;年齡51歲~65歲人數最多,占比42.7%,其次為65歲以上,占比29.2%,中老年人居多;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最多,占比93.9%,高中及以上占比6.1%,文化水平偏低;職業上以從事農業居多,占比58.4%,從事旅游相關行業占比18.3%,旅游參與度一般;家庭年收入20 001元~40 000元占比29.3%,40 001元~60 000元占比28%,60 001元以上占比19.5%,10 001元~20 000元占比17.1%,10 000元以下占比6.1%,以中低收入為主。
寨沙侗寨發放旅游效應調查問卷47份,最終收回有效問卷43份,問卷有效率91.49%。問卷的信度檢驗結果Cronbach′s alpha系數為0.814,效度檢驗結果KMO值為0.835,Bartlett's test的顯著性水平sig值為0.000,說明村民問卷內部的一致性較為理想,問卷的設計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調查對象人口學特征:女性24位,占比55.8%,男性19位,占比44.2%;年齡36歲~50歲人數居多,占比32.7%,其次為23歲~35歲,占比27.9%,51歲~65歲占比25.6%,中青年人居多;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最多,占比76.8%,高中占比11.6%,文化水平偏低;職業上以從事旅游相關行業最多,占比79.1%,外出務工占比6.9%,旅游參與度非常高;家庭年收入60 001元以上最多,占比59.5%,40 001元~60 000元占比24.3%,20 001元~40 000元占比10.8%,10 001元~20 000元占比5.4%,10 000元以下沒有,整體收入可觀。
云舍村發放旅游效應調查問卷83份,最終收回有效問卷78份,問卷有效率93.97%。問卷的信度檢驗結果Cronbach′s alpha系數為0.797,效度檢驗結果KMO值為0.814,Bartlett's test的顯著性水平sig值為0.000,說明村民問卷內部的一致性較為理想,問卷的設計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調查對象人口學特征:女性48位,占比61.5%,男性30位,占比38.5%;年齡36歲~50歲占比30.7%,51歲~65歲占比30.7%,65歲以上占比19.2%,其次為23歲~35歲,占比15.4%,年齡段相對均衡;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最多,占比96.1%,高中占比3.9%,文化水平較低;職業上從事農業的占比40%,旅游相關行業占比35%,外出務工占比15%,其他占比10%;家庭年收入20 001元~40 000元居多,占比40.9%,10 001元~20 000元占比31.8%,10 000元以下占比18.2%,40 001元~60 000元占比9.1%,60 001元以上占比為0,中低收入為主。
4 案例地旅游效應比較分析
4.1 經濟效應比較分析
經濟效應5個指標權重值為 =[0.228,0.187,0.263,0.196,0.126],各指標的分值乘以其權重值之和得到經濟效應的分值(后文同理,不再贅述)。如表2所示,寨沙侗寨經濟效應分值4.46,達到極高水平;秀水村與云舍村經濟效應分值分別為3.33、3.09,均屬一般水平。從指標層來看,在物價水平指標上,三地均值分別為2.52、2.27、2.24,均屬較低水平。三地差異較大的指標為居民人均年收入、居民旅游參與率、旅游收入占總收入比重與景區游客接待量,其中寨沙侗寨在居民人均年收入、居民旅游參與率、旅游收入占總收入比重指標上達到了極高水平,在景區游客接待量指標上達到較高水平;秀水村在景區游客接待量指標上達到極高水平,在居民人均年收入、居民旅游參與率、旅游收入占總收入比重指標上評價水平均為一般;云舍村在居民旅游參與率指標上達到較高水平,在居民人均年收入、旅游收入占總收入比重、景區游客接待量指標上均為一般水平。

表2 案例地旅游經濟效應比較
寨沙侗寨是以社區居民核心力量為導向,全寨75戶有74戶直接或間接從事旅游業,居民旅游參與率非常高,相應地旅游漏損很小,旅游收入占總收入比重很高;加上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得寨沙侗寨相比位置稍遠的云舍村獲得了更多高消費游客。秀水村與云舍村的居民旅游參與率相對較低,旅游收入占總收入比重、居民人均年收入均一般。鄉村旅游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物價的上漲,屬于正常的經濟現象,三地在該指標上趨于一致。從單一指標來看,居民人均年收入是最重要的指標,與三地經濟效應具有較為明顯的正相關性。
4.2 社會效應比較分析
社會效應6個指標權重值=[0.191,0.22,0.188,0.128,0.141,0.132]。如表3所示,秀水村、寨沙侗寨、云舍村的社會效應分值分別為3.36、3.29、3.25,均達到了一般的評價水平,且三地之間基本無差異。從指標層來看,在旅游提升居民素質上,三地均達到了較高的評價水平,相互之間均值差異較小。在改善交通基礎設施上,三地均達到了極高的評價水平,其中云舍村均值最高。在鄉村社會治安狀況上,秀水村與寨沙侗寨均值分別為4.06與4,均達到較高水平;云舍村均值4.26,達到極高水平,存在明顯差異。在居民參與旅游規劃、居民代表組織等指標上,三地評價水平均較低。在污染、噪聲控制上,秀水村均值3.77,屬較高水平;云舍村均值3.36,屬一般水平;寨沙侗寨均值2.76,屬較低水平,存在顯著差異。

表3 案例地旅游社會效應比較
旅游的發展確實給鄉村社會帶來了明顯提升。三地共同的不足是在居民參與旅游規劃、居民代表組織上評價均較低,這也是鄉村旅游普遍存在的問題。其原因一是公司、政府、村民等在旅游利益分配上的博弈中,居民往往是處于弱勢的;二是景區經營主體與村民溝通協商交易成本大,難以達成一致意見;三是村民普遍文化水平偏低,維護自身權益意識不強。在控制污染、噪聲指標上,寨沙侗寨評價水平較為明顯低于秀水村和云舍村,這與寨沙侗寨面積小、游客接待量大不無關系。云舍村是中國歷史文化名村,投入了大量的資源改善交通基礎設施與加強社會治安,因此在這兩個指標上,云舍村獲得的評價水平更高。
4.3 環境效應比較分析
環境效應5個指標權重值=[0.137,0.142,0.292,0.217,0.212]。如表4所示,秀水村、云舍村的環境效應分值分別為4.31、4.46,均屬于極高水平。寨沙侗寨的環境效應均值為4.09,屬于較高水平。從指標層來看,在改善生態環境質量、居民環境保護意識上三地均取得了較高的評價,且相互之間均值差異較小。在森林覆蓋率、增加生物多樣性上,秀水村、云舍村均達到極高水平,寨沙侗寨達到較高水平,指標均值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在村寨衛生狀況上,云舍村4.72,達到極高水平;秀水村4.28,達到極高水平;寨沙侗寨4.16,達到較高水平,指標均值存在顯著差異。

表4 案例地旅游環境效應比較
美麗的生態環境是村寨發展鄉村旅游的一大優勢,秀水村、寨沙侗寨、云舍村都擁有山清水秀、空氣新鮮的良好環境,三地都達到了較高的環境效應水平。秀水村、云舍村面積大,環境稟賦相對寨沙侗寨更為優越,在森林覆蓋率和生物多樣性上,評價水平自然較寨沙侗寨更高。同時,云舍村與秀水村分別是中國最美村寨和中國美麗休閑鄉村,在村寨衛生上投入更多,保持得更干凈,評價水平較寨沙侗寨更高。
4.4 文化效應比較分析
文化效應4個指標權重值=[0.105,0.054,0.538,0.303]。如表5所示,云舍村的文化效應均值為3.63,達到較高水平,寨沙侗寨與秀水村的文化效應均值分別為3.32和3.15,均屬一般水平,寨沙侗寨評分稍高一點。從指標層來看,在文化遺產重視與保護上,三地均達到了較高評價水平。在促進與外界文化交流上,三地均達到較高水平,但三地均值存在一定差異。在民族文化開發狀況上,云舍村均值3.7,屬于較高水平,寨沙侗寨與秀水村均屬于一般水平,存在顯著差異。在旅游對傳統文化沖擊上,云舍村達到較高水平,寨沙侗寨評價水平一般,秀水村評價水平較低。

表5 案例地旅游文化效應比較
云舍村與寨沙侗寨分別是土家族與侗族的聚居地,民族文化底蘊深厚;秀水村是漢族、苗族、布依族等民族聚居地,民族文化雖多,但較為分散。通過三地之間的文化效應比較,不難發現,云舍村與寨沙侗寨作為純粹的單一民族村寨,在文化效應上評價水平比秀水村更高,民族文化開發狀況更好,同時在應對外來文化沖擊時,保持自身文化獨立性的能力更強,其中作為歷史文化名村的云舍村,在這兩點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4.5 旅游總效應比較
旅游總效應4個準則層權重值=[0.309,0.286,0.134,0.271]。如表6所示,在目標層旅游效應上,寨沙侗寨均值3.77,取得較高水平評價;秀水村均值3.42,云舍村均值3.52,均屬一般水平,兩者相差無幾。從準則層上來看,三地在社會效應上都取得一般的評價,基本無差異。在環境效應上,云舍村、秀水村均值更高,寨沙侗寨也取得了較高評價。在文化效應上,云舍村達到較高水平;其次是寨沙侗寨與秀水村,均屬一般水平,其中寨沙侗寨稍好一點。在經濟效應上,三地存在明顯差異,寨沙侗寨達到了比秀水村和云舍村更高的評價水平,秀水村與云舍村評價基本一致。

表6 案例地旅游總效應比較
秀水村、寨沙侗寨、云舍村在經濟效應、環境效應、文化效應上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其中,寨沙侗寨在經濟效應上評價水平明顯更高,環境效應均值則明顯低于云舍村和秀水村,云舍村在環境效應與文化效應上評價更高,秀水村在環境效應上評價水平極高。通過對比發現,旅游效應與經濟效應具有很強的正相關性,經濟效應在旅游效應中起主導作用,旅游開發大大地改善了村寨基礎設施且美化了生態環境。多數民族村寨出于對商業利益的追求,往往忽視對當地民族民俗文化的開發與保護,使得鄉村旅游的文化內涵呈現不夠,進而影響民族村寨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
5 結論與建議
從測算三個民族村寨旅游案例地的旅游效應指標評價值來看,旅游效應最佳的為寨沙侗寨,其次是秀水村、云舍村。經濟效應相差不大的村寨,旅游效應評價相差也不大。旅游效應大小與民族村寨旅游發展時間沒有明顯關系,單一民族占比高的村寨文化效應評價相對更高,其受到的文化沖擊相對也更小。寨沙侗寨以個體經濟為主,個體經營戶中社區居民占有很大的比重,這使得當地居民普遍享受到了旅游發展的紅利;秀水村是以集體經濟為主的村寨,居民旅游參與度較低,旅游利益分配均衡性差,旅游現狀滿意度、旅游效應相應也較低;云舍村作為歷史文化名村,在民族村寨特色民族文化開發上,達到了較高的評價水平,而秀水村與寨沙侗寨民族文化開發都在一般水平以下,不利于旅游差異化競爭和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現就本文所得出的結論,提出一些建議。第一,完善鄉村旅游制度,健全公開透明機制。當地居民與村集體作為旅游資源的擁有者,理應有權參與、知情并實施監督,旅游運營主體應適時公開經營情況及旅游規劃,當地政府、村委會及村民代表應積極介入,維護居民正當權益。第二,完善旅游利益分配機制,提高當地居民旅游參與度。當地政府、村集體應積極鼓勵村寨居民從事旅游業,扶持居民個體經營,提升經營效率與經濟活力,讓更多居民享受到旅游發展的紅利。第三,著眼長遠發展,加強民族文化開發,實現文旅融合發展。文化是民族村寨的靈魂,是吸引游客、留住游客的重要旅游元素,應加強民族文化開發,挖掘文化內涵,形成村寨特色,促進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