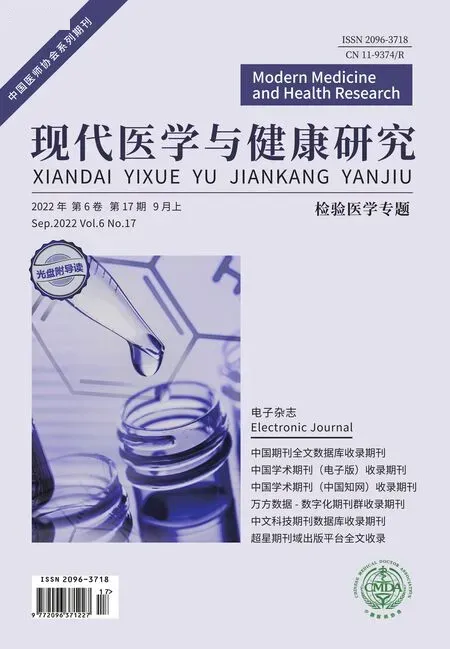血清炎癥因子及T 淋巴細胞亞群與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的相關性分析
林劍煉,彭雁忠
(1.深圳市福田區慢性病防治院全科醫療科,廣東 深圳 518048;2.廣州醫科大學,廣東 廣州 510182;3.北京大學深圳醫院感染性疾病科,廣東 深圳 518036)
病毒性肝炎是以多種肝炎病毒導致患者肝臟發生病變為主要特征的一種傳染病,其中甲型病毒性肝炎與戊型病毒性肝炎已成為全球各國傳播較為廣泛的腸道傳染病,一般表現為急性感染癥狀且能自愈[1]。據統計,我國2004 年至2018 年報告戊型病毒性肝炎患者358 122 例,每年的平均發病率是1.78/10 萬[2]。而乙型病毒性肝炎與丙型病毒性肝炎是腸道外傳染性疾病。據WHO 公開數據[3]顯示,2015 年全球各國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的感染人數達3.25億人次,有134 萬人死于因病毒性肝炎病毒感染引起相關疾病,該類致死人數遠超瘧疾、肺結核和艾滋病等重大疾病的致死人數,嚴重威脅世界各國人民的健康。若不及時治療,病毒性肝炎可能會引起危及患者生命的并發癥,如肝癌、肝硬化、肝硬化腹水等。而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是指因病毒性肝炎間接或直接誘發的肝硬化腹水,其發生與病毒性肝炎患者的感染有關。研究發現,輔助型T 細胞1(Th1)可分泌出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干擾素γ(IFN-γ)、白細胞介素-2(IL-2),能參與機體內的細胞免疫應答,殺死細胞內的病毒及細菌;而輔助型T 細胞2(Th2)能分泌出白細胞介素-4(IL-4)、白細胞介素-6(IL-6)及白細胞介素-10(IL-10),可參與機體內的抗體介導的免疫應答[4]。研究發現,T 細胞為細胞免疫作用的重要效應細胞,按T 細胞表面抗體表達及功能分為T 抑制類型細胞CD8+細胞和T 輔助類型細胞CD4+細胞[5]。本研究探究IL-2、IL-6、TNF-α、IFN-γ、CD3+CD4+、CD4+/CD8+與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發生的相關性,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取2019 年1 月至2021 年6 月深圳市福田區慢性病防治院收治的100 例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患者作為研究組,并選取同期就診的100 例病毒性肝炎患者作為對照組,進行回顧性分析。兩組患者的一般資料,具體見表1。本研究經深圳市福田區慢性病防治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納入標準:①被確診為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疾病;②患者年齡在18 歲以上;③患者智力、精神正常,意識清醒,對事物有較清晰的表達能力。排除標準:①合并原發性肝癌者;②合并感染巨細胞病毒或Epstein-Barr 病毒(EBV)感染者;③合并造血系統、內分泌系統、泌尿系統、呼吸系統、嚴重心腦血管相關疾病者;④曾行經頸靜脈肝肝內分流術者或脾切除術者;⑤合并嚴重免疫缺陷疾病者。
1.2 標本采集與檢測方法入院后次日清晨的兩組患者空腹采集4 mL 外周血,均置于抗凝試管,再經離心處理(離心速度為3 500 r/min,離心時間為10 min,離心半徑為12 cm),并分離出上清液,置于-20 ℃的環境中備用。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進行檢測,選用美國BD 公司提供的試劑,依照試劑盒上說明書檢測IL-2、IL-4、TNF-α、IL-6、IFN-γ、IL-10 指標水平及CD3+、CD3+CD4+、CD4+/CD8+水平。
1.3 觀察指標①單因素分析。收集患者的全部臨床資料,包括患者的性別、年齡、民族、吸煙史、飲酒史、肝病家族史、身體鍛煉情況、勞動情況、對自身疾病的理解程度、對自身疾病的治療情況,是否長期抗病毒治療等,并進行單因素分析。②多因素Logistic 分析。將單因素分析中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數據納入多因素Logistic 回歸模型中進行分析,并篩選影響因素。
1.4 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 24.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以[ 例(%)]表示,行χ2檢驗;計量資料以(±s)表示,行t檢驗;使用Logistic 回歸模型分析影響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發生的因素。P<0.05 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影響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發生的單因素分析單因素分析顯示,兩組患者在長期抗病毒治療、長期吸煙、鍛煉身體、IL-2、IL-6、TNF-α、IFN-γ、CD3+CD4+、CD4+/CD8+等方面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1。

表1 影響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發生的單因素分析
2.2 影響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發生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以病毒性肝炎患者發生肝硬化腹水為因變量,以單因素分析的結果中有統計學意義的項目為自變量,Logistic 回歸分析的結果為,長期抗病毒治療是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發生的保護因素,IL-2、IL-6、TNF-α、TNF-γ、CD3+CD4+、CD4+/CD8+水平高是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發生的危險因素(均P<0.05),見表2。

表2 影響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發生的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
3 討論
腹水為病毒性肝硬化腹水患者癥狀最突出的臨床疾病,也是一種較為常見的病毒性肝硬化患者并發癥,研究發現[6],病毒性肝硬化患者在失代償期出現腹水的概率在75%以上。腹水患者常表現為腹下垂、蛙腹、腹部膨隆、腹脹等,影像學檢查可提示有腹水的存在。導致腹水的主要原因是鈉水潴留,而病毒性肝硬化腹水發病可能與肝淋巴液分泌過多、抗利尿激素及繼發性的醛固酮增多、門靜脈壓力升高、低白蛋白血癥及循環血量不足等因素相關聯[7]。病情輕重程度不同的肝硬化腹水均表現出免疫力低下,極易引起感染[8]。探討血清中的炎癥因子及T 淋巴細胞亞群與病毒性肝炎相關性肝硬化腹水的相關性具有重要意義。
本研究結果顯示,長期抗病毒治療是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發生的保護因素,且長期抗病毒治療與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發生有較高的相關性,說明長期抗病毒治療能延緩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的發生,積極進行保肝抗病毒治療能明顯降低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及其他并發癥的發生,此結果與既往研究[9]結果相一致。人體內存在兩種不同T 細胞亞群,其中Th1 細胞能分泌出IFN-γ、IL-2、TNF-α,而Th2 可分泌出IL-4、L-6、IL-5、IL-10 及IL-13 等。機體在正常的情況下,Th1/Th2 細胞處于平衡狀態,若機體功能出現異常時,兩種細胞的平衡被打破,常表現為偏向一方,即為“Th1/Th2 平衡漂移”,若Th1/Th2 細胞間的平衡被打破,會導致機體細胞因子間的動態平衡打破,從而導致疾病的發生及發展[10]。本研究結果顯示,IL-2、IL-6、TNF-α、TNF-γ是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發生的危險因素,與劉鎮平等[11]研究結果有相似之處,表明細胞因子在肝硬化患者中不僅能介導肝臟器官中肝細胞損傷,還會隨著機體內血清水平的增加而加重其肝臟損傷程度,加速肝硬化患者疾病發展,增加肝硬化腹水的發生風險,IL-2、IL-6、TNF-α、TNF-γ 與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發生有較高的關系。
T淋巴細胞亞群中的CD4+表示T輔助細胞,CD8+表示T 殺傷細胞和T 抑制細胞,在患者機體免疫反應時常表現為CD4+T 淋巴細胞,而在免疫反應中的起效應細胞主要為CD8+T 細胞[12]。本研究結果顯示,CD3+CD4+、CD4+/CD8+是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發生的危險因素(P<0.05),且CD3+CD4+、CD4+/CD8+與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發生有較高的相關性,與李娜[13]研究的結果有相似之處,肝硬化腹水的發生會引起免疫反應,作為輔助性的CD3+CD4+T 細胞會參與免疫反應,從而引起其濃度的改變。王昀等[14]認為乙肝相關性肝硬化患者隨著病情的惡化,其機體免疫系統發生紊亂,并逐漸加重,此結論證明肝硬化腹水的發生與機體免疫的降低有關。
綜上所述,病毒性肝炎肝硬化腹水的發生會使患者體內的細胞因子(IL-2、IL-6、TNF-α、TNF-γ)和T 淋巴細胞亞群(CD3+CD4+、CD4+/CD8+)呈現異常高表達狀態,應加強對病毒性肝炎患者的血清中細胞因子及T 淋巴細胞亞群的監測,發現異常并及時干預,延緩病毒性肝炎患者疾病發生的進程,提高其生存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