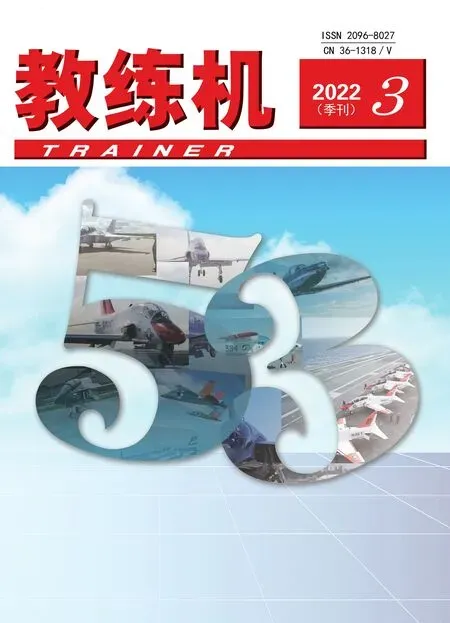“兩機”訓練體制下的飛行員培養探析
閆會明,張大尉,何 飛,劉 濱
(航空工業洪都,江西 南昌,330024)
0 引言
軍事飛行訓練體制是各國進行飛行員培養的實體及其運行機制,是隨著不同時期國情、訓練需求以及裝備技術而發展和變化的。科學的飛行訓練體制,對合理配置訓練資源、有機組合訓練要素、規范訓練行為,實現飛行員培養高成才率、低訓練成本、短培養周期和高水平技能養成,進而促進部隊戰斗力生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1 國際軍事飛行訓練體制發展
軍事飛行員培養的發展歷史可以追溯到20 世紀初,1909 年世界上第一架軍用教練機——雙座萊特A 型飛機交付部隊用于飛行學員訓練,1910 年美軍正式成立軍事航空學校,開始有組織的飛行訓練。由于體制不健全,飛行學員培養的目標較為單一——培養飛行學員具備單飛能力,核心是保證飛行員可以安全地駕駛飛機。
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加速推動了飛行訓練體制的發展,為適應作戰需要,批量培養飛行員成為核心矛盾,美國等國家先后構建起了 “初級-基礎-高級”三級訓練體制。由于戰爭對飛行員數量的迫切需求,該階段訓練體制主要側重于快速大批量培養飛行員,對于各級教練機資源幾乎“能用盡用”,但成才率低、訓練成本高、飛行員技能水平總體偏低。
經過百余年的發展,國際上主流軍事飛行訓練階段主要分為初級、基礎和高級訓練階段,對應的訓練體制主要有兩大類型: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北約國家,多配置兩型教練機,形成“初級/基礎教練機(初級/基礎訓練)—高級教練機(高級訓練)”或“初級教練機(初級訓練)—高級教練機(基礎/高級訓練)”的“三級兩機”訓練體制;二是以俄羅斯為代表等國家,多配置三型教練機,形成“初級教練機(初級訓練)—基礎教練機(基礎訓練)—高級教練機(高級訓練)”的“三級三機”體制。
各國在不同的發展時期,基于當時的訓練需求和可用資源的匹配情況,飛行訓練體制調整的側重點和關注點也隨之變化。
1.1 美軍“三級兩機”訓練體制發展
美國“三級兩機”體制的構建源自20 世紀60 年代,1952 年,美軍為提高初始學員的質量,降低淘汰率,發布了“全新飛行員訓練計劃”,引入“輕型篩選飛機”。1958 年,根據朝鮮戰爭的空戰經驗和大量裝備噴氣式戰斗機的現狀,美軍為縮短飛行員培養周期,減少由螺旋槳飛機向噴氣式飛機改裝時間,提高噴氣式作戰飛機操控技能,開始執行 “全噴氣機訓練計劃”,引入T-37 作為基礎教練機,從而與高級教練機T-33 構成了簡潔的“兩機”培養體制,正式進入“三級兩機”制時代。20 世紀80 年代,由于軍費的持續壓縮,美軍啟動聯合初級飛機訓練系統(JPATS)項目,并采用T-6A 渦槳教練機承擔初級/基礎訓練,為彌補螺旋槳飛機與噴氣式飛機的差異,進而保持其“三級兩機”訓練體制,美軍在T-6A 飛機上采用了發動機數字控制系統和螺旋槳自動糾偏裝置,并引入訓練系統的概念,在降低訓練成本的同時,實現了與淘汰率、訓練周期以及訓練水平的綜合平衡。目前,美國空軍戰斗機飛行員培養采用“T-6A(初級/基礎訓練)—T-38(高級訓練)”的“三級兩機”訓練體制,T-6A 訓練時間約6 個月/86 飛行小時,T-38 訓練時間約6 個月/114 飛行小時。未來,隨著以T-7A 新型高級教練機為核心的綜合訓練系統的服役,美軍將形成更加有效的新“三級兩機”體制[1]。
1.2 前蘇聯/俄羅斯“三級三機”體制發展
前蘇聯飛行員訓練始于1910 年——在加特契納市開辦空軍飛行軍官學校的飛行員訓練部,與美軍基本同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前蘇聯開始創建專業飛行學校并迅速發展。20 世紀60 年代前,前蘇聯空軍教練裝備體系層級多、機種雜,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訓練體制。進入20 世紀60 年代,逐漸形成“雅克-18(篩選/初級訓練)—L-29(基礎訓練)—烏米格-15(高級訓練)”的“三級三機”訓練體制。20 世紀60 年代后期,為解決雅克-18、L-29 等訓練效能不足且逐漸到壽的問題,1968 年發展L-39 基礎/高級教練機替代L-29,1978 年發展雅克-52 雙座教練機替代雅克-18,并引入烏米格-21 承擔高級訓練,形成“雅克-52(篩選/初級訓練)—L-39(基礎訓練)—烏米格-21(高級訓練)”的“三級三機”訓練體制。雅克-52 飛機飛行訓練時間約30 小時,L-39 飛機飛行訓練時間約200 小時,烏米格-21 飛行訓練時間約120 小時。
俄羅斯空軍飛行訓練體制繼承自蘇聯時期,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空軍在經費、裝備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難。由于烏米格-21 停產,L-39 提價且備件保障困難,戰斗機在訓練中大量消耗,飛行學員的訓練無法保障。因此,俄羅斯空軍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采用雅克-130 新型高級教練機替換老舊的L-39 等教練機,裝備雅克-152 初級教練機逐步取代雅克-52 教練機,同時正在發展SR-10 渦扇基礎教練機。預計后續將形成“雅克-152(篩選/初級訓練)—SR-10(基礎訓練)—雅克-130(高級訓練)”的新“三級三機”訓練體制。
1.3 國際軍事飛行訓練體制發展特點
從美、俄等空軍強國飛行員培養發展看,軍事飛行訓練體制主要有以下發展特點:
一是動態調整,適應新要求。飛行訓練體制并非一成不變,尤其是教練裝備更是隨著不同時期訓練需求的變化而動態調整。為有效解決飛行員和作戰平臺的“能力適配”問題,在二代機、三代機以及四代機的不同時期,都發展與之相配套的教練裝備及訓練系統、完善優化訓練體制來培養飛行員。二代機強調的是飛行員的飛機操縱駕駛技術,飛行員具備一定飛行經驗后在二代機同型教練機上進行改裝訓練,可短期培養出二代機飛行員。二代機過渡到三代機過程中,由于外部作戰環境和三代機作戰能力革新,飛行員核心能力培養由“駕駛”技能向“駕馭”能力轉變,著重強調三代機飛行員適應高機動和多任務能力的培養,相應地構建了以新一代高級教練機為核心的三代機飛行員訓練體制。與三代機飛行員相比,面臨復雜多變的作戰環境和高度綜合的第四代戰斗機飛行員的核心能力已出現明顯躍升,就美軍而言,其通過發展“卓越”訓練,并正在發展新型高級教練機T-7A 及綜合訓練系統,來構建滿足四代機飛行員訓練需求的訓練體制。
二是注重結果,突出目標。采用“三級兩機”訓練體制和“三級三機”訓練體制的根本并不在于體制本身的形態,而是適應不同條件下的飛行員培養需求,最大限度實現高成才率、低訓練成本、短培養周期和高水平技能養成這一目標。但由于不同時期的目標側重點不同,訓練體制的變革需要根據其所想得到的結果對其培養目標所占權重進行調配。如作戰時期某一階段教練機數量不足以支撐訓練時,則采用其他階段教練機或者作戰飛機進行臨時補充,此時的目標側重點是實現短周期培養出高水平技能的飛行員,成才率和訓練成本已經不是首要制約條件。而在和平年代,追求飛行員培養的規模、可持續性、高成才率和低訓練成本成為了目標側重點,如何構建簡約的訓練體制成為變革的直接動力。如美軍發展新一代高級教練機時明確提出了其“下載”和“卸載”能力,目的就是為了降低訓練成本。
三是技術驅動,綜合提升。技術的發展和裝備的支撐是實現訓練體制變革的重要保障。飛行學員技能的成長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各個訓練環節需要不同的教練能力進行支撐。增加或省去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都必須由其他裝備的教練能力進行補充。初-中-高三級訓練是國際上探索總結出來的飛行學員培養的三個必然階段,正常來說應該配裝三種類型教練裝備以實現其教練能力的銜接。國際上“兩機”訓練體制的主流做法是采用一型教練能力基于初級和基礎級之間的教練機,承擔初級/基礎訓練,為彌補缺乏的教練能力,一方面需要提升高級教練機向下訓練能力,一方面使用模擬訓練等新訓練技術進行補充和提升,進而支撐訓練體制的改革。如美軍采用T-6A 飛機承擔初級/基礎訓練時,同步配備了訓練系統。
2 “兩機”制飛行學員培養的優劣分析
“兩機”訓練體制與“三機”訓練體制相比,從根本上來說是對于傳統的一種突破和尋優,是為降低訓練成本、縮短培養周期、提升訓練效率而進行的體制變革,這種變革要取得成功,還要系統性考慮變革帶來的成才率、飛行員技能水平成長以及裝備發展等問題。目前國際主流“兩機”訓練體制與“三機”訓練體制相比,主要有以下差異:
“兩機”訓練體制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從訓練角度有利于降低訓練成本、縮短訓練周期。通過兩機的合理搭配,減少一型機型,可有效避免飛行學員機型轉換多、改裝周期長,優化空中訓練時間,釋放保障資源,經驗表明:培養同等數量的三代機飛行員,采用“兩機”訓練體制可節省訓練成本15%左右,縮短訓練周期30%左右。二是從作戰使用角度有利于延長飛行員服役年限,更大限度發揮飛行員作戰效能,使其在該訓練的時期進行訓練,該作戰的時期承擔作戰任務,避免因前期訓練時間過長而錯過最佳服役時間。三是從體制本身的構建角度,“兩機”訓練體制后期調整將更加靈活,參數組合的減少更容易挖掘出體制本身存在的問題,有利于體制的精準優化和改進,以及教練裝備的精細發展和使用。
“兩機”訓練體制的限制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空中飛行訓練時間過少容易導致飛行員空中受訓不足,空中作戰潛能挖掘不充分,不利于空中作戰能力的培養和生理心理習慣的養成[2];二是訓練周期的劇烈壓縮使得飛行學員技能增長率被人為拔高,一方面使飛行學員因不適應而產生較大的淘汰率,影響成才率,另一方面也可能因“拔苗助長”而留下“后遺癥”,使飛行員“基礎不牢、后勁不足”。三是“兩機”訓練體制的實現對生源質量和教練裝備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其他配套資源的同步實施。
因此,要真正實行“兩機”訓練體制并從中受益,需要基于自身國情、訓練需求以及技術基礎統籌考慮。美軍實行“三級兩機”體制,一方面得益于其濃厚的航空文化,飛行學員未進入軍事訓練前就已經具備較強的飛行理解能力,有利于其技能的增長和習慣的養成;另一方面美軍為保障“三級兩機”體制的順利實施,在教練裝備發展過程中不僅發展配套訓練系統,更是不斷應用VR、AI、LVC 等新技術,進一步彌補其訓練不足,提升整體訓練能力。而俄羅斯在其未具備開展“三級兩機”變革時機前,仍是采用“三級三機”體制,雖然培養成本較高、周期較長,但也實現了高作戰水平飛行員的培養。
3 啟示
從國際發展趨勢來看,采用“三級三機”訓練體制和“三級兩機”訓練體制均能保證飛行員培養的正常實施,但從可持續、高質量、高效率運行的角度來看,“三級兩機” 體制仍是我國走實大國空軍之路的必然選擇。
一是新形勢下飛行人才高效、快速、規模化培養對“兩機”體制改革提出了需求。按照“空天一體、攻防兼備”戰略要求,未來空軍航空兵力量結構將發生較大變化。進攻作戰力量將獲得較大發展,三代機、四代機以及多用途戰斗機比重逐年增大,預警指揮、偵察干擾、空中加油、運輸投送、搜索保障等支援保障力量比重將明顯提高,對飛行員培養的數量和質量提出了新的要求,飛行訓練體制改革必須適應這種變化。
二是通用航空的大力發展和航空文化的不斷普及為“兩機”訓練體制的實施奠定了人才基礎。在新的發展形勢下,民用飛行員數量需求將逐步提升,民間飛行院校、飛行俱樂部的效能發揮將更加明顯。同時,隨著空海軍青少年航空學校和青少年班等早期培養策略的推行,對于早期飛行人才的發展和儲備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是新一代高級教練機訓練能力的提升,為“兩機”訓練體制的構建提供了裝備基礎。新一代高級教練機是為適用三/四代作戰飛機而發展的專用教練機,具備高安全性、高適應性和高效費比,可同時適應飛行學員技能增長要求和作戰飛機作戰能力要求,向上能下載作戰飛機訓練內容,向下能適當兼顧基礎訓練內容。
四是新訓練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應用為“兩機”體制提供了強大的技術基礎。以教練機為核心的綜合訓練系統的不斷應用和發展,顯著增強了綜合訓練能力,可有效彌補和提升“兩機”體制帶來的缺陷。同時,隨著VR、AR、AI 等新技術的成熟,也為“兩機”訓練體制的發展提供了“定心丸”。
4 結語
通過對國際飛行訓練體制的發展進行剖析,結合我國飛行訓練體制發展需求及特點,現階段“三機”訓練體制仍可以很好地滿足飛行員培養需求。但從長遠發展角度看,采用“兩機”訓練體制是最佳選擇,現階段已具備相關條件,通過提升高級教練機及其配套訓練系統的使用效率,發展具備承擔初級/基礎訓練能力的教練機,可形成科學有效、搭配合理的“兩機”訓練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