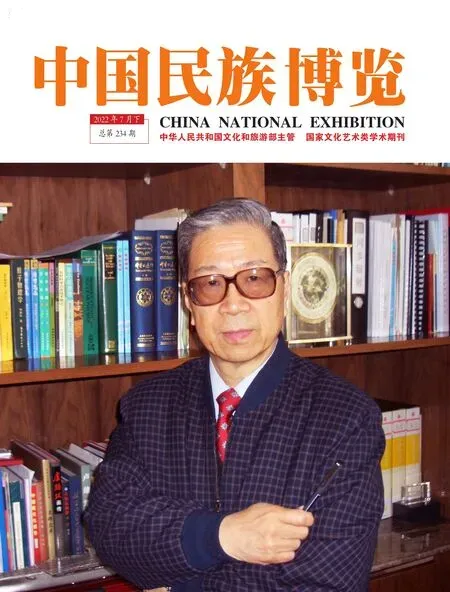楊福家:點燃每個人心中的“火種”
本刊編輯部整理
改革開放40年,可以是一個關乎民族、關乎時代的宏大主題,也可以是一個個具體而微的人物和故事。40年來的奮斗悲喜交集,40年來的夢想感同身受,本文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寧波諾丁漢大學校長楊福家在2018“書香中國”閱讀論壇暨解放日報第74屆文化講壇上發表的演講。
我是新中國第一批去西方深造的學者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今天我很榮幸在這個場合向大家介紹一下我過去40多年來的體會。
我的題目是“我有一個夢想”。這句話不是我發明的,是馬丁·路德·金說的話。在上個世紀快結束的時候,曾經評選過去100年里最有名的10句話,第一句話就是馬丁·路德·金講的“我有一個夢想”。
在我的理解,夢想就是追求。
1962年,鄧小平同志提出了“往西方派留學生”,這句話在今天看來很平常,但在我們那個年代是讓人很難想象的一句話。因為在那時候,我們腦子里崇拜的是蘇聯老大哥,西方國家好像都是我們的敵人。

2001年2月17日,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舉行歡迎儀式,熱烈歡迎中國著名學者楊福家到諾丁漢大學擔任校長。新華社記者 侯少華 攝
當1962年中蘇關系破裂時,鄧小平果斷地做出了一個決定— —往西方派留學生,這在當時是一大創舉。對我來說,這也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我很榮幸被選中去了丹麥。
詳細說來,你要去西方留學,就必須先要通過語言關。我們從全國各地初步被挑選出來的幾十位同志,一起到北京去集中學習英語。到北京后的第一堂課,由當時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的許國璋老師對我們進行考核。他讓我們每個人讀一段英語,再問兩句話讓我們回答。考核完以后,他當面不講,背后就說了:你們想半年就通過考試?兩年能通過就已經不錯了!
怎么辦呢?我和后來當北大校長的陳佳洱一起散步時說:我們的英文不見得像他講得那么差,我們已經翻譯過很多英文資料了。從現在開始,我們每天早上散步就不講中文了,只講英文。就這樣堅持了半年,最后由英國人來對我們進行考試。很幸運,我們兩個都通過了。我去了丹麥,他去了英國。
所以,我第一次出國,就是作為新中國第一批去西方深造的學者到丹麥玻爾研究所進修。

1963年,楊福家在丹麥玻爾研究所。
改革開放以后,我才有了第二次出國
丹麥玻爾研究所是哥本哈根大學的一個獨立的研究所,被許多物理學家譽為“物理學界的朝拜圣地”,當時由后來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小玻爾主持。那里的房子不怎么樣,沒有漂亮的大樓,房子看上去舊舊的,但是人才輩出,是當時全世界最有名的研究所之一。
我1963年第一次訪問丹麥玻爾研究所,說好進修時間為一年。結果,一年快結束的時候,由于我做出了一些成果,玻爾教授提出讓我再工作一年,所以我在玻爾研究所待了兩年。
有一張我在玻爾研究所里做實驗的照片,是丹麥同事給我照的。但大家不知道的是,這張照片是凌晨兩點半的時候拍的,我們當時真是日夜奮斗,經常48小時不睡覺地拼命干活。為什么這樣?因為我有一種使命感,我是新中國第一批派到西方來深造和進修的,我絕對不能丟祖國的臉,我要努力地工作,努力地學習,所以兩年下來獲得了比較好的成績。
回國以后,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這段時期對我們科研工作者來說簡直沒有夢想可言。1978年,改革開放的大幕拉開,又是鄧小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們又可以開始做“夢”了。
從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時間,可以講是滄桑巨變。有這樣的巨變,才有了今天的中國,在座的年輕人應該說是很幸福的。
從那以后,我們到國外去訪問成了一件習以為常的事情。第二次訪問丹麥是在改革開放的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去了以后,玻爾教授問我:我邀請你和夫人一起來,你怎么只有一個人來了?說實話,當時我們出國怎么敢把夫人一起帶去?沒想到,玻爾教授非常認真,通過大使館再次向我和夫人發出邀請,因此我很榮幸,第三次去丹麥,是和我夫人一起去的。這在當時都是破天荒的事情!
改革開放以后,我去丹麥玻爾研究所的次數非常多,1979年、1980年、1995年、1998年、1999年、2005年……我與丹麥玻爾研究所結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誼。2005年以后,由于我導師的身體不好,他不希望被我看到一個有病的人,因此丹麥之行才告一段落。
總而言之,中國的大門從封閉到打開,我從中收獲很多,大開眼界。

1979年,楊福家和玻爾在哥本哈根。
我走進了美國武器實驗室
在玻爾研究所工作的第一年,我和一位丹麥同事合作搞研究,做出了一些成果。當時研究所一共有80位研究員,其中60位都來自國外。第二年,有一個美國人希望加入我們的研究小組,我請示大使館,大使館說沒有問題,可以讓他加入。但后來寫論文,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勸我,那個時候中美關系非常不好,和美國人一起署名寫論文是很糟糕的。于是,雖然這項研究主要是我做的,但我表示我不署名。這個美國人感到很驚訝,也很感動,從此以后我們成了好朋友。
后來我才知道,他在美國武器實驗室工作。很多年以后,他向我發出邀請,訪問美國武器實驗室,我就帶了6個人一起去了。
有人也許會問:我們去美國武器實驗室干什么?這個時候美國的核武器研究確實比較先進,但我們去并不是為了打探核武器的秘密,而是為了了解基礎研究對武器研究的作用。
走進美國武器實驗室,我才知道武器實驗室里竟然有一個基礎研究部。這個基礎研究部請來了這個領域的一批頂尖專家。請來干什么呢?你可以在這里搞你的基礎研究,與武器實驗沒有任何關系;但是你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出席討論武器的會議,雖然你不是搞武器的,但你可以從另外的角度來發表你的見解,而往往這些搞基礎研究的科學家提出的意見,是從事武器研究的人所提不出來的。所以,這個基礎研究部的設置,對于武器的創新和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回國后,我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作《武器研究與基礎研究》,對國內的武器研究工作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楊福家與美國前國防部長佩里等。
李道豫說:“你的民間外交做得很好”
除了我們走出去以外,我們也請進來,把美國武器實驗室的科學家請過來,讓他們也了解一下中國的情況。當時陪同美國科學家一起參觀的,有陳能寬、王淦昌等人,他們都對我們國家的武器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大家一定認為,我國研究尖端武器的科學家們生活條件應該很好,但事實上,他們當時的條件非常艱苦。我曾經去過他們工作的大西北核試驗場,給我住的房子是他們那里最好的房子,面積很小,里面只能放一張床,屋外零下30攝氏度,最要命的是,早晨上廁所要跑很遠的路。今天我們國家在國際上有越來越高的地位,全世界都對我們另眼相看,其實就是這一批人的艱苦奮斗換來的。
在我的心目中,中國最偉大的科學家是中國“氫彈之父”于敏,這個名字可能很多人都沒有聽說過。我1958年從復旦大學物理系畢業,1959年他在成都講學,我去聽課,同時講學的還有一位英國回來的教授。雖然于敏的名氣并不響,但是他的精彩講學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我一生中最欽佩的人,是非常偉大、了不起的科學家。習近平主席曾經親自授予他國家最高科技獎。他當年也和我們一起去了解,武器研究如何從基礎研究中獲益。
我順便再講一下,從1994年開始,因為我的外國朋友多,所以邀請我參加美國一年一度的總統早餐會。被邀請參加總統早餐會,是一件很榮幸的事情,那一天美國總統會接見與會者,還會做即興演講。
1997年,在華盛頓的總統早餐會上,我見到了克林頓和他的夫人希拉里。我從他那里學到了什么呢?克林頓總統在演講中提到了“知識經濟”這個詞,我當時是第一次聽到,聽了之后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回國之后,我找了很多這方面的材料,寫了《關于知識經濟》這篇文章,刊登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等報刊上,后來被幾十家報紙轉載。這是我一生中被引用次數最多的一篇文章。
在總統早餐會上,我還有幸認識了美國眾議院議長,他后來以我的名字做了一面旗幟,在美國國會大廈上空飄揚,這是對我所做的貢獻的認可。當時的中國外交部駐美國大使館大使李道豫對我說:“你做的事情是很多人做不了的,你的民間外交做得很好。”

楊福家訪問美國與楊振寧會面。
點燃了他們心里的火種,他們就會騰飛
因為在英國諾丁漢大學擔任校長的緣故,這些年我走訪了世界上的很多大學,對教育有了一些思考。
在美國,大學被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像哈佛大學、復旦大學這樣的學校,屬于研究型大學,它在美國的大學中只占3%;第二類是普通的大學;還有第三類,占美國大學的60%,那就是高等職業學校。
在我們國家,如果你的孩子考取了職業學校,會被認為是很丟臉的事,但我告訴你們一件真實的事情:我姐姐的外孫女成績優秀,在美國可以考進哈佛大學,但是她卻想進一所烹飪學校,也就是我們中國人認為學做飯的學校。當時她的外婆已經在美國待了一段時間,當我姐姐得知外孫女的決定時就說:你陪我去那所學校看看。我姐姐去看了以后才知道,這所學校是世界上排名第一的烹飪學校,這個學校的學費比哈佛大學高多了,我姐姐最終同意了外孫女的決定。后來那個女孩畢業以后,在一家五星級酒店專門制作藝術雕刻蛋糕,做得很漂亮,非常有成就感。她的薪水也比一般人高多了,但她主要不是為了錢,而是她真心喜歡這個工作。
人和人的不同,并不在于分數高低,而在于心中的“火種”。如果你找到了孩子心里的火種,并把它點燃了,那么他的人生就會活得精彩。
我可以再舉幾個例子。我有一位同學非常優秀,畢業以后進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他研究的方向是夸克。夸克是什么?夸克是一個物理名詞,也是構成物質的基本單元。夸克有什么用?我到現在也不知道。他的畢業論文就是有關夸克的研究。但是誰也沒想到,他并沒有沿著這個軌跡研究下去,而是出于個人的愛好,用夸克原理研究股票,并最終創建了一門新的學科——經濟物理學。
我還有一位在復旦大學的同班同學,他的愛好是磨玻璃,他來復旦大學報到的時候還隨身帶著一套磨玻璃的工具。當時學校里的老師沒有對他另眼相看,有一位教授對他說:你喜歡磨玻璃,復旦大學有一家玻璃工廠,其中有個蔡祖泉非常有名,就讓他帶你一起磨。后來畢業分配的時候,他被分配到南京天文臺,參與國際水平的天文望遠鏡的制作,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所以,如果你們有孩子,不一定非要讓孩子上北大清華、復旦交大,而是要幫助他們找到自己的火種,一旦點燃了他們心里的火種,他們就會騰飛。因為時間的關系,我就講這些,謝謝大家!

1993年1月,楊福家任復旦大學校長。

2001年,英國諾丁漢大學隆重的就職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