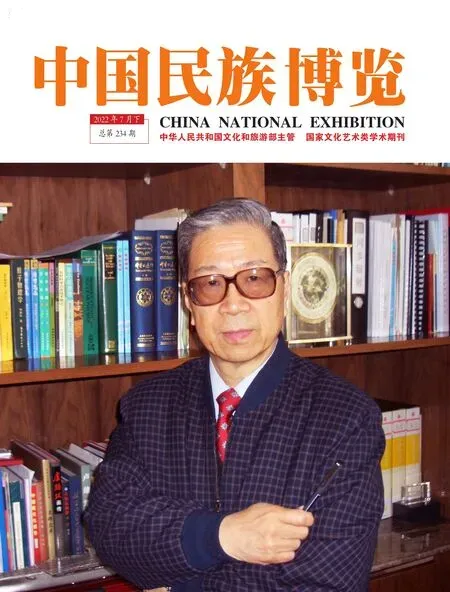呂坤與《近溪隱君家訓》碑
李 丹
(太原市文物保護研究院,山西 太原 030045)
我國自古講究門風,注重家訓家教,基于明朝“為治之要,教化為先”的治國理念,明代出現(xiàn)了數(shù)量眾多、形式各異、內(nèi)容豐富的家訓,其中關(guān)于端正家風和社會風尚、倡導節(jié)儉、倡導薄葬、女子家訓的內(nèi)容大量增加,家訓的發(fā)展歷史在明朝達到了鼎盛時期。
在太原市永祚寺內(nèi)就珍藏有一通明代大儒呂坤所鐫刻的《近溪隱君家訓》碑,其家訓內(nèi)容極富哲理,細細品味寓意深遠,對修身立命、處事應(yīng)物、培養(yǎng)品行等均不無裨益。
呂坤(1536—1618),字叔簡,號抱獨居土,人稱“沙隨夫子”,河南寧陵人,是一位眼光敏銳、胸襟博大、言行一致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哲學家。呂坤言為人師,行為人法,居官有實政,在鄉(xiāng)黨有惠澤教化,深受百姓們的愛戴,與沈鯉、郭正域被譽為明萬歷年間天下“三大賢”。呂坤著書累百萬言,篤實切近,講求實學,注重文化教育,其所著述多出新意,主要作品有《去偽齋集》《呻吟語》《實政錄》《四禮翼》《四禮疑》《閨范圖說》等,內(nèi)容涉及政治、經(jīng)濟、刑法、軍事、水利、教育、音韻、醫(yī)學等各個方面,對后世有很大的影響。
呂坤鐫刻的《近溪隱君家訓》中近溪隱君為呂坤的父親呂得勝,字壽官,號近溪,又號漁隱閑翁。呂得勝一生熱心于兒童的教育工作,其撰寫的《小兒語》《女小兒語》蒙學讀物,以四言、六言、雜言的韻文方式,宣揚如何做人做事,倡導傳統(tǒng)美德,影響廣泛。在其父呂得勝的影響下,呂坤為政清廉、愛民重民,極為注重德性教育,明萬歷二十一年(1591),呂坤將其父呂得勝對他的諄諄教誨與本身的思想整理成《近溪隱君家訓》,并刻于石上。
一、《近溪隱君家訓》中呂坤的思想
《近溪隱君家訓》碑高2.3米,寬0.79米,厚0.25米,沒有碑額,也沒有紋飾,是一通非常樸素的刻石。
“存陰隲心,幹公道事,做老成人,說實在話,把天理先放在頭直上。處人只要箇謙□,居家只要箇和平,教子只要箇學好,喫穿只要箇飽暖,房舍家火只要箇堅牢,有□冠婚喪祭只要箇合禮。纔開口便想這話中說不中說,纔動身便想這事該做不□做,纔接人便想這人可交不可交,纔見利便想這物該取不該取,纔動怒便想□□該忍不該忍。處身要儉,與人要豐。見善就行,有過便認。尤可戒者,奢侈一節(jié)。今人□作無益,只圖看相強。似費了財帛誇俗人眼目,不如那些錢糧救窮漢性命。錦上添花何用?彼冬無破絮者皆天地生靈。案前積肉何為?彼日無飽糠者皆同胞赤子。看那慳吝儹錢之人,生驕奢破家之子。天道甚明,愚夫不悟,爾曹切記吾言!
萬歷辛卯山西按察使仲男呂坤刻石
(注:“□”為殘缺字)
《近溪隱君家訓》碑短短251個字,包含了立身處世原則、治國理政之道,體現(xiàn)了儒家倫理道德,通篇圍繞一個“仁”字,形成了個人倫理、家庭倫理、國家倫理,乃至宇宙?zhèn)惱淼牡赖乱?guī)范,其中更是將呂坤以人為本、愛民、重民、恤民的思想,貫穿于《近溪隱君家訓》整篇內(nèi)容中。
呂坤晚年注釋《陰符經(jīng)》時,曾說自己的思想是“不儒不道不禪,亦儒亦道亦禪”。“人問:君是道學否?曰:我不是道學。是仙學否?曰:我不是仙學。是釋學否?曰:我不是釋學。是老莊申韓學否?曰:我不是老莊申韓學。畢竟是誰家門戶?曰:我只是我。”呂坤以孔孟儒家思想為主體,又兼采百家,具有求真求實的態(tài)度和鑄融百家的精神,“我只是我”突出了呂坤的個性特點,也是他治學獨立性的宣言。
(一)仁者愛人
“陰騭心”指對人寬厚,惻隱之心(同情心)是為“仁”也。“仁”是中華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在各個歷史時期和
各種道德中居于首位,在世俗道德生活中也是最普遍的德行標準。
呂坤講學只主六個字,叫作“天地萬物一體”。有人問他:“你這樣不是另立門戶嗎?”呂坤說:“不,我只是講孔門的一個‘仁’字”。他十分贊賞北宋大儒張載的“民胞物與”思想,張載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張載把天地看作父母,把百姓看作兄弟,把萬物看作朋友,把人倫的觀念,貫徹到天地萬物中,人作為天地大家庭的一員,應(yīng)當擔當起自己的責任。呂坤稱:“子厚胸中合下有這般著痛著癢心,方說出此等語。”“仁者,人也。”(《禮記·中庸》)凡是人都有仁性,天生就有惻隱之心,能對別人的痛苦與歡樂產(chǎn)生共鳴。有仁德的人會用愛心去對待人,既自愛又愛人,既自尊又尊人。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滿六合是運惻隱之心處。君子于六合飛潛、動植、纖細毫末之物,見其得所,則油然而喜,與自家得所一般;見其失所,則惘然而戚,和自家失所一般。位育念頭,如何一刻放得下。”明萬歷十六年(1588),呂坤任山東濟南道右參政。因此,連續(xù)兩年旱災(zāi),造成山東大饑荒,災(zāi)民食盡草根樹皮,又吃各種野草,有些草含有劇毒,災(zāi)民食后備受折磨直至死亡。呂坤得知此情深為痛惜,遂作《毒草歌》以悼死者,遍查藥書、農(nóng)書,細心了解各類植物的特性,一一注明各類藥物是否可食,以誡生者。呂坤始終“以仁為己任,死而后已,此是大擔當;老者依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此是大快樂。”由此可見,其愛民、重民、恤民之心躍然紙上。
(二)克己奉公
“生來不敢拂吾發(fā),義到何妨斷此發(fā)。”呂坤曾任山西按察使,主管一個省范圍內(nèi)的刑獄和官吏考核之事,作為一名執(zhí)法者,他始終秉持著“王法上承天道,下順人情,要個大中至正,不容有一毫偏重偏輕之制。行法者要個大公無我,不容有一毫故出故入之心,則是天也。君臣以天刑法,而后下民以天相安”的原則,視“徇情而不廢法,執(zhí)法而不病情,居官之妙語也。”
“政者,正也。”呂坤為政期間剛介耿直,以公道正派為做官之本分,以徇私舞弊、誹謗、背離原則、追求個人的名聲為第一等恥辱的事。正人必先正己、正心。中國倫理道德歷來強調(diào)公私之辨,把“公義勝私欲”作為道德的根本要求。呂坤批評指責一些官員為政期間把天地間真實的道理當虛套子干,把世間虛套子作實事干,富貴是圖,巧恣漁奪,負國負民。呂坤告誡說:“六合都是情世界,惟朝堂官府為法世界,若也只徇情,世間更無處覓公道。”“公正二字是撐持世界底,沒了這二字,便塌了天。”他認為很多不法的行為都是一個“私”字造成的,就是這樣一個“私”字,卻擾攘得不成世界。倘若上至朝廷官吏,下至市井黎民,人有人品,官有官德,人人都能做到秉公辦事、堅持公心,天下自然便會太平安寧,政治自然便會清明,獄訟自然能平息。
(三)篤實寬厚、謹言慎行
自古以來,中華傳統(tǒng)在待人接物上,一向以寬厚為美德、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將心比心”、“以心換心”作為原則和原理,推己及人,設(shè)身處地地為他人著想。
為政者要有寬廣的胸懷和宏大的氣度,以寬容待人,對有過之人如果采取激烈的態(tài)度,只會加劇他的錯誤并導致激化矛盾。呂坤任大同守令時,見縣丞到任便拱手作揖,結(jié)果縣丞顧其他未看到呂坤作揖。于是呂坤就當面斥責薄吏說:“為什么不把禮節(jié)告訴新官?”縣丞很是羞愧地向他謝罪,后來一直到公宴結(jié)束那名縣丞臉色依舊不是很自然。對此事呂坤甚悔之。后呂坤任山西按察使期間,每當升堂時,首領(lǐng)官有四個人,先向堂官作揖,然后再分班作揖。退堂時,呂坤拱手作揖,四人鞠躬后再退。有一天,有三人因公外出,只余一首領(lǐng)官在堂上,忘記對班無人依然作揖行禮,禮畢后覺得羞愧無言,其他人也在旁邊掩口竊笑。呂坤拱手作揖說:“有事不妨先退。”那人退下時臉色變得平和多了。“急言遽色、厲聲怒氣,原無用處。萬事萬物只以心平氣和處之,自有妙應(yīng)。余褊,每坐此失,書以自警。”呂坤將此事記載下來,作為培養(yǎng)忠厚品德的開始。
“予平生做事發(fā)言,有一大病痛,只是個‘盡’字,是以無涵蓄,不渾厚,為終身制大戒。”他認為一個人的心術(shù)最主要的是光明篤實,風貌最主要的是正大老成,說話最主要的是簡重真切。“從容而不后事,急遽而不失容,脫略而不疏忽,簡靜而不涼薄,真率而不鄙俚,溫潤而不脂韋,光明而不淺浮,沉靜而不陰險,嚴毅而不苛刻,周匝而不煩碎,權(quán)變而不譎詐,精明而不猜察,亦可以為成人亦。”呂坤認為這樣的人便是德才兼?zhèn)涞某墒熘恕?/p>
(四)能辨是非、以義取利
孟子提出:“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明辨是非、知者不惑、文理密察是“智”的開端。儒家認為,“智”是人必備的一種重要品德,也是實現(xiàn)仁、義的重要手段。
“為政之道,以不擾為安,以不取為與,以不害為利,以行所無事為興廢起弊。”明朝統(tǒng)治者的過分貪婪,過分聚斂財富,導致人民貧困流離失所。對此,呂坤公開上書斥責萬歷皇帝貪財愛貨:“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數(shù),君欲富則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今民生憔悴極矣,乃采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姓之怨氣于一言,結(jié)九重之仇于四海,臣竊痛之。”
作為從政執(zhí)法者,面對明朝世風大壞、亂象萌發(fā),呂坤揭露明代官吏,“事有便官吏之私者,百世常行,天下通行,”以至“日盛月新”,“彌漫而不可救”。同時,他還指斥一些官吏“人事日精而民務(wù)疏”,一官到手便志得意驕,筵設(shè)庭陳,心不念民,口不談?wù)T趨卫さ男哪恐校倮舻穆氊煈?yīng)該是:“民生憔悴,愁苦困窮。付我生養(yǎng),付我輯寧。”“才見利便想這物該取不該取。”能明辨是非、以義取利是廉明,能自我約束而不貪求是廉儉。廉的根本是在取予之間,取道義、去邪心,嚴格自我約束,才能養(yǎng)成廉正的美德,才能受到百姓的稱頌和尊敬。
(五)綱常倫理、萬物本意
“天理”是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倫理道德本體。“人倫者,天理也。”(二程《外書》卷七)“理者,五常而已。”(朱熹《晦庵文集》卷七十四)
呂坤要求自己時時體悉人情,念念持循天理,將為人辨冤白謗,作為第一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者也。”呂坤非常重視心性道德的修養(yǎng),如謂“吾儒學問,只講‘心’之一字。”他認為七情都是欲望,但只要欲望是正當?shù)模褪翘炖恚逍裕偟恼f都是仁心,只要不仁了,就都是人欲。即便是天理,也要知道反省檢查是偏面之見還是自然法則。
“萬事都要有個本意,宮室之設(shè)只為安居,衣之設(shè)只為蔽體,食之設(shè)只為充饑,器之設(shè)只為利用,妻之設(shè)只為有后。推此類不可盡窮。茍知其本意,只在本意上求,分外底都是多了”。“人生在天地間,無日不動念,就有個動念底道理;無日不說話,就有個說話底道理;無日不處事,就有個處事底道理;無日不接人,就有個接人底道理;無日不理物,就有個理物底道理。”呂坤認為細小的事務(wù)尚且要求合乎自然的道理,何況天地人的常道這樣的大節(jié),哪能超越法度呢?如果每個人都恣情縱欲地實現(xiàn)自己的欲望,那就稱不上萬物之靈了。
(六)謙和之德
中國人自古就懂得“滿遭損,謙受益”的道理。“和”體現(xiàn)在待人接物中為和氣,在人際關(guān)系中為和睦,在價值取向上為和諧。孔子曰:“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禮之運作,包含有謙和之德,謙者,謙虛也,謙讓也,根源于人的恭敬之心、辭讓之心。
“方嚴是處人大病痛,圣賢處世離一溫厚不得,故曰:‘泛愛眾’,曰‘和而不同’,曰‘和而不流’,曰‘群而不黨’,曰‘周而不比’,曰‘愛人’,曰‘慈祥’,曰‘豈弟’,曰‘樂只’,曰‘親民’,曰‘容眾’,曰‘萬物一體’,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只恁踽踽涼涼,冷落難親,便是世上一個礙物,即使持正守方,獨立不茍,亦非用世之才,只是一節(jié)狷介之士耳。”中國傳統(tǒng)文化十分重視宇宙自然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
“才開口便想這話中說不中說。”所謂道不可執(zhí)一,必有經(jīng)有權(quán);理不可片面,過猶不及,應(yīng)求中正。呂坤認為“‘中’之一字,不但道理當然,雖氣數(shù),離了中,亦成不得。寒暑災(zāi)祥失中,則萬物殃;飲食起居失中,則一身病。故四時各順其序,五臟各得其職,此之謂中。差分毫便有分毫驗應(yīng)。是以圣人執(zhí)中以立天地萬物之極。”
“才動怒便想□□該忍不該忍”。呂坤說,“仁者之家,父子愉愉如也,夫婦雍雍如也,兄弟怡怡如也,僮仆欣欣如也,一家之氣象融融如也。義者之家,父子凜凜如也,夫婦嗃嗃如也,兄弟翼翼如也,僮仆肅肅如也,一家之氣象栗栗如也。仁者以恩勝,其流也知和而和;義者以嚴勝,其流也疏而寡恩。故圣人之居家,仁以主之,義以輔之,洽其太和之情,但不潰其防斯已亦。其井井然,嚴城深塹,則男女之辨也,雖圣人不敢于家人相忘”。圣人處理家庭事務(wù)時,以仁為主,以義為輔,使人的自然之情融洽和諧。“仁”者愛人以孝悌為根本,“為仁由己”,只要克己修身,篤實躬行,便可成為“仁人”。
(七)勤儉戒奢
明人顧炎武說:“國初,民無他嗜,崇尚簡質(zhì),中產(chǎn)之家,猶躬薪水之役……后則靡然向奢,以儉為鄙……而奢靡之風,乃比于東南。”
呂坤在《近溪隱君家訓》碑中認為:立身處世,對待自身要簡約樸素,對待他人要慷慨大方;見到善言善行就去實行,有了過錯就應(yīng)該立即改正。最應(yīng)該戒掉的就是奢侈一事。“余參政東藩日,與年友張督糧臨碧在座,余以朱判封,筆濃字大,臨碧曰:‘可惜!可惜!’余擎筆舉手曰:‘年兄此一念,天下受其福矣。’判筆一字,所費絲毫朱耳,積日積歲,省費不知幾萬倍。充用朱之心,萬事皆然。天下各衙門積日積歲,省費又不知幾萬倍。且心不侈然自放,足以養(yǎng)德;財不侈然浪費,足以養(yǎng)福。不但天物不宜暴殄,民膏不宜慢棄而已。夫事有重于費者,過費不為奢;省有不廢事者,過省不為吝。余在撫院日,不檢于紙而戒示吏書片紙皆使有用。比見富貴家子弟用財貨如泥沙,長余之惠既不及人,有用之物皆棄于地,胸中無不忍一念,口中無可惜二字。人或勸之,則曰:‘所值幾何?’余嘗號為溝壑之鬼,而彼方侈然自快,以為大手段不小家勢,痛哉!兒曹志之。”
明萬歷中期,世人奢靡之風甚重,有些人物質(zhì)方面稍不及人,便覺得是一種恥辱,認為是低人一等。呂坤告誡兒子說:“你看那老成君子,宮室不如人,車馬不如人,衣服飲食不如人,仆僮器用不如人,他卻學問強似人,才識強似人,存心制行強似人,功業(yè)文章強似人。較量起來,那個該愧恥!”衡量一個人、一個家庭或家族的標準不是物質(zhì)享受,人要“攀比”的也并不是衣著美食、隨從扈傭,而應(yīng)是學問、才識、心氣和文章。在呂坤看來,這些方面不如人,才是真正應(yīng)該羞愧的。
二、《近溪隱君家訓》碑的教化作用
據(jù)道光《陽曲縣志》所載:“城隍廟山門東墻,嵌近溪隱君家訓石刻。高六尺,寬二尺,楷書字方二寸。”可見,原先《近溪隱君家訓》碑并不在太原市永祚寺,而是嵌在太原城隍廟墻中。
“崇墉為城,環(huán)水為隍”。太原城隍廟始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明萬歷二十七年(1599)重修,占地面積1萬多平方米。位于太原市杏花嶺區(qū)的城隍廟曾經(jīng)是太原最富盛名的祭祀護城之神的廟宇,其所處街巷也曾經(jīng)是明、清以來最繁華熱鬧的商貿(mào)街。每年農(nóng)歷三月十五,為大祭城隍之日,由當時府城知府率文武官員,親臨廟內(nèi)祭祀,貢品豐富,儀式隆重。官家祭祀儀式結(jié)束后,百姓就可隨意入廟拜祭和游覽了。《近溪隱君家訓》碑嵌于城隍廟山門東墻,對官吏、百姓都是一種教育的引導,可以起到讓世人的德行回歸純厚,達到風俗淳厚、家室和平、移風易俗而有利于正道的目的。
呂坤對民間疾苦有著深刻的洞徹,有著深厚的同情與拯救的實施措施,任山西按察使期間呂坤在太原展開了一場“移風易俗”的活動,明萬歷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592—1593)間,呂坤頒布《禁約風俗》,他提出:“照得風俗儉奢,系小民生死。”意思是說風俗的儉樸與奢侈,關(guān)乎老百姓的生死。他專門編撰了《實政錄》,要求屬吏照此辦理以正民風,婚喪簡辦,政務(wù)簡從,以身作則,以教化官吏百姓,引導淳厚民風,以期達到教化世人之目的。
《禮記·學記》:“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呂坤極為重視道德教育和德性培養(yǎng),尤其重視對時代風習和世道風俗的教化和引導。“化民成俗之道,除卻身教再無巧術(shù),除卻久道再無頓法。”“言教不如身教之行也,事化不如意化之極也。事化信,信則不勞而教成;意化神,則神不知而俗變。”呂坤認為用事實來教化百姓,使人相信,相信了不費勁就能教化成功;用意志來教化更為神奇,不知不覺中習俗就發(fā)生了改變。
他規(guī)定,官吏上任時的公宴,只用鼓樂一次,以后不用。至于小唱、戲子,公庭中要絕去蹤跡,縉紳知理守法,自然要節(jié)儉。呂坤還反對大建寺廟、大搞祭祀、大辦節(jié)會。他認為,祈雨謝雨,只在各廟燒香即可,修建寺廟、搭建高臺、鑄塑神像上,只是耗費財物,尤其無益。
“今人□作無益,只圖看相強。似費了財帛誇俗人眼目,不如那些錢糧救窮漢性命。錦上添花何用?彼冬無破絮者皆天地生靈。案前積肉何為?彼日無飽糠者皆同胞赤子。”在《近溪隱君家訓》中,呂坤提出奢靡之風是不正確的人生觀,質(zhì)問奢侈浪費的那些行為,不如積存些布匹糧食賑濟災(zāi)民,為子孫留一些陰德,勤儉節(jié)約是美好的習俗,而吝嗇奢侈則是邪惡的心性。
呂坤極為重視道德教化的作用,尤其重視對時代風習和世道風俗的教化和引導,以《近溪隱君家訓》碑作為其施行“移風易俗”的思想教化,在“移風易俗”中破舊立新,弘正能量,倡樹新風,以便達到《移風易俗》有利于正道的目的。
三、結(jié)語
《近溪隱君家訓》讓人受益匪淺,讀之令人驚醒,動人性情,推堪人情物理,研辨內(nèi)外公私,痛切之至,令人當下猛省,奚啻砭骨之神針,苦口之良劑。
《近溪隱君家訓》碑不僅是一通家訓碑,它還是呂坤為政期間施行《鄉(xiāng)甲約》《禁約風俗》,開展“移風易俗”活動、倡導淳厚民風的一通教化碑,其所蘊含的是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寶庫中極具特色的部分,體現(xiàn)了我國傳統(tǒng)道德文明的精華及歷史發(fā)展,是我們繼承發(fā)揚我國傳統(tǒng)美德的重要實物,也是我們研究中國傳統(tǒng)倫理道德、探究當時風俗教化活動、社會狀況的歷史史料,具有極高的教化作用與文化研究價值。
1《呻吟語正宗》卷一談道
2北宋張載《西銘》
3《呻吟語正宗》卷一談道
4《呻吟語正宗》卷三應(yīng)務(wù)
5《呻吟語正宗》卷五治道
6《呻吟語正宗》卷四品藻
7《呻吟語正宗》卷五治道
8《明史·傳十九·呂坤》
9《呻吟語正宗》卷二修身
10《呻吟語正宗》卷一存心
11《呻吟語正宗》卷三應(yīng)務(wù)
12《呻吟語正宗》卷一談道
13《呻吟語正宗》卷一倫理
14明代顧炎武《肇域志·山西》
15《呻吟語正宗》卷二修身
16《呻吟語正宗》卷五治道
17《呻吟語正宗》卷六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