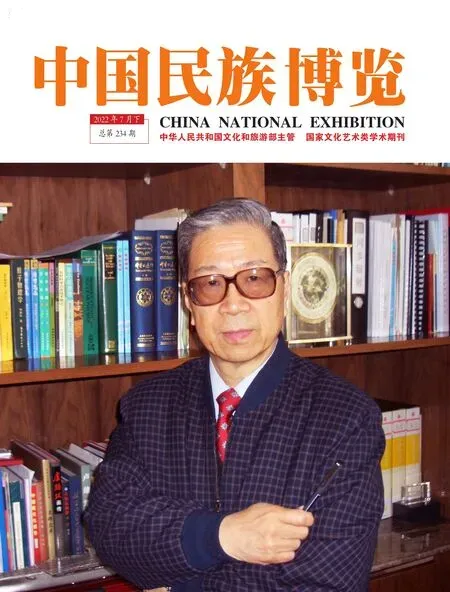淺析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知識產權保護
呼 艷
(山西博物院,太原 山西 030021)
近年來,我國經濟不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人們對精神文化的追求愈加強烈。博物館,作為文化資源的守護者和傳播者,是普羅大眾接受歷史文化熏陶,實現自我精神價值的重要場所。尤其是博物館中豐富的館藏文物,可以讓瀏覽者重新見證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深切感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隨著社會的發展,博物館不再止步于館藏文物的常規展示,我國各個博物館都拓展思維,開始充分利用自己的館藏文物資源開發各類文物衍生品,使冰冷的館藏文物“活”了起來,讓高冷的館藏文物融入大眾生活之中,不僅可以為博物館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還能真正發揮博物館傳播文化的重要使命。然而,隨著館藏文物衍生品行業的快速發展,對館藏文物衍生品知識產權的保護卻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基于這一點,本文從館藏文物衍生品的自身性質出發,總結國內外對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知識產權立法現狀,探討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知識產權相關爭議,提出對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知識產權保護建議。
一、館藏文物衍生品概述
(一)館藏文物衍生品的定義
館藏文物衍生品,是指依據館藏文物本體可從外在觀察到的形制以及內在所蘊含的歷史文化、知識信息等價值,通過各類載體,物化出的體現館藏文物文化的產品。
(二)館藏文物衍生品的分類
館藏文物衍生品大致分為館藏文物復刻品、館藏文物展示品和館藏文物文化創意產品三種門類。
其一,館藏文物復刻品。館藏文物復刻品是最具博物館特色的一類館藏文物衍生品,它從館藏文物本體的形態、顏色、特征出發,借助仿古工藝或現代科技手段,完整復刻館藏文物,或是同比例放大與縮小。館藏文物復刻品要求的是對館藏文物本體的最大限度還原,其追求通過對館藏文物外在形態的復刻來反映館藏文物本身的文化內涵。
其二,館藏文物展示品。館藏文物展示品是最常見的一類館藏文物衍生品,不同于復刻品的三維立體形式,展示品主要依托書籍、音像錄制品等媒介形式,以館藏文物資源為基礎,通過整理、標注館藏文物信息及研究成果,起到向社會大眾進行宣傳教育的作用。隨著電子科技的發展,館藏文物展示品不再局限于紙質及光盤等形式,各類相關電子程序也不斷被開發出來,民眾得以突破物理空間的限制,即使不進入博物館,也可以隨時隨地運用App接受博物館的文化知識傳播。
其三,館藏文物文化創意產品。館藏文物文化創意產品是基于館藏文物本體的二次創作成果,是開發者通過對館藏文物的藝術外觀和歷史內涵進行分析研究,并進一步總結升華,同時注入開發者自己的獨特創意,最終制得的一類館藏文物衍生品。相較于復刻品和展示品,館藏文物文化創意產品的產品形態更加多元,既包括具備一定紀念性和實用性的實用藝術品,也包括基于館藏文物的背后故事而再創作出的小說、動畫或電子游戲軟件等出版物,還包括強調現場體驗感,以參觀者親手制作出的相關產品為主的文化體驗品。
(三)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發展現狀
西方歐美國家博物館在館藏文物衍生品方面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創、產、銷”產業鏈,其以自身館藏文物資源進行開發,創造出獨具特色的館藏文物衍生品,實現宣傳與獲利的雙豐收。以著名的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為例,其館藏文物衍生品的收入已約占其整體收入的80%,遠超常規的門票收入。
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國大陸的博物館大多數屬于國有博物館,收入來源主要為財政補貼,而且基于其公益文化事業的特殊定位,大多數國有博物館都在盡量避免與謀利行為產生關聯。近年來,隨著文化創意行業的蓬勃發展,國有博物館從業人員也突破了傳統思維的束縛,積極探索館藏文物衍生品的開發路徑。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推出“朕知道了”系列膠帶紙后,北京故宮博物院也發散思維,開發出各類符合時代潮流的館藏文物衍生品。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館藏文物衍生品的年銷售額已超15億元,是門票收入的2倍。
二、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知識產權爭議
(一)博物館是否是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知識產權主體
探討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知識產權保護,首先需要明確其權利主體。作為主導開發館藏文物衍生品的主體,博物館首先會被考慮是否可以作為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知識產權主體。博物館一般可分為國有博物館和私有博物館,由于在我國大陸的博物館中,尤其是收藏文物的博物館,絕大多數都屬于國有博物館,因此本文在對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知識產權進行探討分析時,主要是針對國有博物館這一主體來進行的。
對博物館是否是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知識產權主體這一問題,司法實踐并未予以明確,學術界也一直存在爭議。
一方面,有的學者認為博物館的公益事業定位與知識產權的私權性質相矛盾。博物館基于其公益文化事業的特殊定位,其成立的目的是研究并保護文物,同時向社會大眾宣傳文化知識。在現代社會中,博物館的職能趨向于社會性,很多博物館都免費向社會開放,這也符合其所承擔的滿足國民精神文化需求的社會責任,而知識產權則屬于民事法律關系的范疇。作為一種具備專有性和排他性的私權,知識產權是對知識財富的私有化。博物館的公益性質與知識產權的私權性質產生了強烈的矛盾,故博物館不宜作為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知識產權主體。
另一方面,有學者提出博物館中館藏文物的所有權屬性與知識產權主體對知識產權的獨占性要求相矛盾。根據我國《文物保護法》第五條第四款第二項規定,國有博物館作為國有文物收藏單位,其收藏、保管的文物屬于國家所有。博物館作為國有文物的保管單位,其代替國家行使對國有文物的權力。因此,博物館基于館藏文物開發出來的衍生品也是屬于國家所有,衍生品的知識產權也就隨之當然屬于國家所有,在全民所有制的情形下,這些知識產權應為全體人民所平等共有。但知識產權作為私權,強調的是權利主體的獨占性。館藏文物及其衍生品的共有性與知識產權主體的獨占性相矛盾,因此博物館不宜成為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知識產權主體。
博物館是否是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知識產權主體的問題如果不能解決,將導致在司法實踐中無法妥善處理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知識產權糾紛,進而將阻礙館藏文物衍生品行業的發展。對上述兩種爭議,筆者提出如下看法。
其一,對博物館的公益性質和知識產權的私權性質之間產生的矛盾。筆者認為,雖然一般看來博物館的公益性質與知識產權的私權性質是相背離的,但當博物館處于館藏文物衍生品開發者這一角色時,就需要從博物館的行為而非其主體性質來看待博物館的主體身份。此種情況下,博物館以普通民事主體的身份,參與市場經濟活動,其與其他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民事主體地位相同。因此,博物館開發館藏文物衍生品時,就理應受到知識產權法律的保護,即博物館享有對其開發產品的知識產權。此外,博物館開發出來的館藏文物衍生品,有助于向社會大眾宣傳文化知識,更易于滿足民眾的精神文化需求,這與博物館的公益文化事業定位也相符合。博物館在開發并銷售館藏文物衍生品獲利后,也可為自身正常運作提供資金,在減輕國家負擔的同時,還能將多余資金投入創新發展中,有利于更好地發揮其自身價值。由此可見,知識產權的私權性質不僅與博物館的公益性質不會產生矛盾,反而還有助于博物館公益功能的實現。
其二,對館藏文物及其衍生品的共有性與知識產權主體的獨占性之間的矛盾。筆者認為,我國國有博物館對館藏文物行使的是一種管理權,這種管理權其實是一種在國家所有之物上設立的物權,這種物權產生于國家享有的所有權但又與之相分離,博物館作為管理人享有的這種物權是類似于用益物權的權利。也就是說,博物館所開發的館藏文物衍生品,其權利其實應歸于博物館這一管理人,這與國家對館藏文物擁有的所有權并不矛盾。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知識產權獨立于館藏文物本體之外,不屬于國家所有,也就并非歸全民所共有。由此可見,館藏文物的共有性并不及于其衍生品,館藏文物衍生品屬于博物館所專有,這也與知識產權主體的獨占性相一致。
綜上所述,博物館及其開發的館藏文物衍生品的權利性質與知識產權的私權性質并不矛盾,博物館要成為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知識產權主體在學理上并不會產生阻礙。
(二)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獨創性認定
館藏文物作為古人的作品,根據《著作權法》對權利保護期的相關規定,館藏文物的復制、匯編、改編等權利早已超出了法律保護期限,從而使社會大眾可以在不經許可的情況下便能免費使用。因此,館藏文物本體的諸多權利不會被《著作權法》所保護,此時館藏文物衍生品想成為被《著作權法》所保護的作品,實質上只需要具備獨創性即可。
獨創性強調新作品與原有作品的差異性,包括“獨自完成”和“最低程度的創造性”兩層含義。對館藏文物衍生品來說,獨創性需要開發者在館藏文物本體的基礎上,加入自己的獨立構思,運用新思維或新技術,開發出與館藏文物本體在作用、形式等方面產生一定程度上區分的新作品,使之得以體現開發者的思想與個性。
對前文總結的館藏文物復刻品、館藏文物展示品和館藏文物文化創意產品三類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獨創性,筆者將逐一進行分析。
一是館藏文物復刻品。一般來說,館藏文物復刻品的開發并不要求開發者具備自己的獨特創意,因而學術界對館藏文物復刻品是否應納入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有一定的爭議。筆者認為,館藏文物復刻品是開發者對館藏文物本體的精準復刻,具備較高的收藏意義和審美意義,但對開發者來說,雖然傾注了大量心血,但無法加入自己的獨特構思,因此館藏文物復刻品并無獨創性,不屬于知識產權法律所保護的對象。
很多博物館為了更好地保護文物,選擇將館藏文物精美復刻用于對外展示,不少復刻品投入了制作者大量的精力,成品也展示出制作者高超的技藝,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但只是由于其缺乏獨創性,就無法被知識產權法律所保護。當然,開發者在制作館藏文物復刻品時發明出新的工藝技術或新的工具,在符合《專利法》規定的前提下,是可以被知識產權法律所保護的。
二是館藏文物展示品。無論是書籍、音像錄制品,還是電子程序,館藏文物展示品一類的衍生品都是屬于匯編類作品,一般以出版物的形式展示成果。根據著作權法律理論中“思想與表達二分法”的基本原則,法律不會保護“思想”,只會保護更易辨別的“表達”。對匯編類作品,判斷其是否具備獨創性時,無須關注其匯編的內容是否具備獨創性,而應對其表達方式是否具備獨創性進行分析。能被知識產權法律所保護的匯編類作品,其表達方式不是將收集的材料進行簡單的組合,而是根據匯編人獨有思想將材料進行系統性的整理。具體到館藏文物展示品,具備獨創性的匯編類作品,應是博物館根據自己館藏文物資源的特色,有判斷力地進行獨創性的系統整理并予以出版的作品。
以故宮博物院的《故宮日歷》為例,該作品由故宮出版社連續十二年出版,旨在倡導讀者每天都能感受一件國寶的魅力。最新版的《故宮日歷2022年》,以生肖虎為主體,每日展示一件由專家選取的與虎相關的故宮館藏文物。此外《故宮日歷》還會按月選取符合當月月份特點的主題對文物進行系統整理,如二月的“吉虎迎瑞”、九月的“皇家圍獵”、十二月的“冬運冰嬉”。《故宮日歷》向讀者展示了西周的青銅虎、宋代的陶獅子、清代的青玉刻御制《射虎行》馬鞭等各種珍貴文物。由此可見,故宮博物院對虎年的相關文物并不是機械式的選擇,而是賦予其深厚的文化內涵,是具有獨創性的甄選和匯編,這樣的館藏文物展示品當然會受到知識產權法律的保護。
三是館藏文物文化創意產品。對館藏文物文化創意產品是否具備獨創性的問題并不能一概而論,而是需要根據具體產品進行具體分析。
第一類館藏文物文化創意產品是實用藝術品。對實用藝術品來說,除了要判斷其是否具備獨創性以外,還需判斷其是否屬于“作品”。若將實用藝術品認定為作品,則其受《著作權法》的保護,但若將其認定為外觀設計,則其應受《專利法》的保護。對這一問題,有學者提出實用藝術品本質上應滿足以下三點要求:首先,實用藝術品的實用功能與藝術設計無須依存;其次,實用藝術品的藝術設計部分具有獨創性;最后,實用藝術品必須達到一定藝術設計水準。滿足以上三點要求的產品才屬于實用藝術品,同時會被《著作權法》認定為作品,從而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筆者贊同這一觀點,實用藝術品作為館藏文物的衍生品,由博物館主導開發,其藝術性是要大于實用性的,這也是實用藝術品區別于工業產品之所在。因此,實用藝術品應屬于作品,而非外觀設計。在將實用藝術品認定為作品的基礎上,判斷其是否具備獨創性,就只需判定該實用藝術品與館藏文物本體相比在藝術設計上是否具有獨特性即可。
第二類館藏文物文化創意產品是出版物。這一類產品的獨創性判斷與館藏文物展示品相類似,區別在于展示品是匯編類作品,而這里的出版物為改編類作品,只要改編人在作品中表達出自己的獨特創意,則該作品是擁有獨創性的。
第三類館藏文物文化創意產品是文化體驗品。由于其主要是基于傳統手工藝的個體創作,創作者主要是游客,而非專業設計人員,所以筆者認為對其進行獨創性判斷時應采用較高標準,即作品需要滿足較高的藝術設計感,可以表達出創作者獨特的創作意識,才可判斷為具備獨創性。
三、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知識產權保護建議
(一)提升博物館對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
面對當前文化產業市場廣闊和國家產業政策扶持的雙重利好,博物館應牢牢把握機遇,提升館藏文物衍生品開發水平的同時,還要強化自身對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
一方面,博物館需要落實對館藏文物衍生品的著作權登記。我國實行的是著作權自愿登記制度,創作者的著作權基于其創作行為的完成就可自動獲得。但在實踐中,一旦發生關于著作權的權屬糾紛,如果沒有進行著作權的登記,就會在一定程度上為創作者證明自己的權利帶來不便。因此,博物館應積極落實館藏文物衍生品的著作權登記,在保障產品后續交易的同時,還能為自己在處理權屬糾紛時帶來便利。
另一方面,博物館要加強對館藏文物衍生品知識產權的維權意識。很多博物館在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知識產權被侵犯時,出于舉證困難、資金和時間成本較高的顧慮,往往會放棄維權,這種情況不僅助長了知識產權侵權者的囂張氣焰,還損害了館藏文物衍生品的良好創作環境,阻礙了館藏文物衍生品行業的健康發展。所以,必須加強博物館對館藏文物衍生品知識產權的維權意識,司法部門和文物行政部門也應為博物館維權提供相關渠道和便利。
(二)規范博物館對館藏文物衍生品的品牌授權運營
在開發館藏文物衍生品的過程中,博物館的優勢在于其豐富的館藏文物資源,但缺乏提出創意和成熟運營的能力。在此種情形下,博物館可以將自己的品牌授權給成熟的文化創意公司來運營。需要注意的是,博物館應謹慎選擇合作的文化創意公司,要保證館藏文物衍生品的產品質量,確保其能體現文化內涵,形成良好的品牌效應,這也有利于產生良幣驅逐劣幣的效果,從而形成對館藏文物衍生品知識產權的保護。
(三)加大對館藏文物衍生品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打擊力度
對館藏文物衍生品知識產權的侵權行為,一方面,需要國家完善立法、加強執法,對侵權行為加大懲處力度,為館藏文物衍生品行業的發展保駕護航;另一方面,需要加強對消費者知識產權相關知識的宣傳,鼓勵消費者拒絕盜版產品,并加入打擊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行列,形成打擊侵權行為的全民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