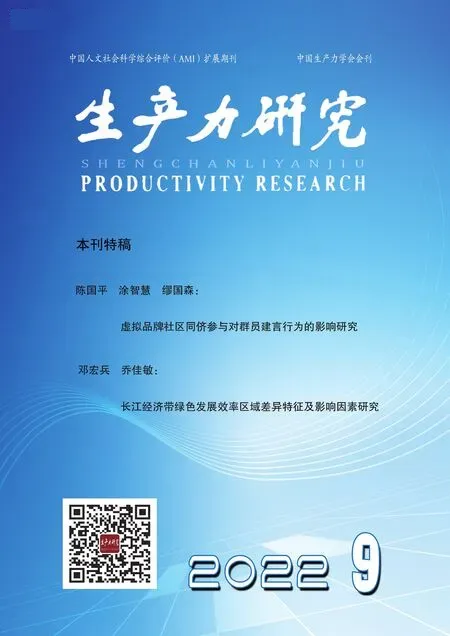上市公司控股股東股權質押研究綜述
彭 英,葛蒙妤,閆昕蕾
(1.南京郵電大學 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03;2.南京郵電大學 國際電聯經濟和政策問題研究中心,江蘇 南京 210003)
一、引言
黨的十九大以來,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成為經濟改革一大重心,如何發揮資本市場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作用、提高企業融資效率、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成為各部門和眾多企業深思與探究的問題。中國現處在前途無限光明卻仍面臨嚴峻挑戰的重大戰略機遇期,資本市場的各種問題和挑戰值得我們思考與探究。
2008 年對于中國資本市場來說是特別的一年,除了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開始對中國經濟產生影響外,股權質押業務也開始存在于中國資本市場。而股權質押業務在國內的流行則是從2013 年起,此年上交所發布《股票質押式回購交易及登記結算業務辦法》系列規定,相比其他融資渠道,股權質押不僅融資成本低,審批放款速度快,且對企業約束小的同時還不易稀釋股權,成為越來越多上市公司融通資金的主要渠道之一。東方財富Choice 數據表明,截至2021 年末,登記在中國滬深股市A 股的所有上市公司中,具有股權質押行為的公司有2 517 家,質押總股數達4 198.27 億股。然而股權質押并非萬無一失的融資方式,具有一定市場風險。監管部門為了更好地監管市場、控制風險,于2018 年1 月12 日頒布了相關規定的修訂版本。如今國內相關領域雖研究成果頗豐,但仍缺乏系統深入地理解。因此,本文立足上市公司的股權質押問題,從實際意義出發,構建邏輯分析框架,涵蓋動機、影響因素與經濟后果等方面,在現有理論成果與實證研究基礎上梳理總結,以期系統展現我國股權質押領域的研究成果與未來方向,具體研究框架如圖1 所示。

圖1 研究框架
二、概念界定及股權質押理論視角
(一)概念界定
股權質押,又稱股權質權,是指金融中介機構對出質部分股權評估后向出質人提供資金的行為。我國的質押擔保制度的實施始于1995 年10 月1 日頒布的《擔保法》中有關股權質押的相關內容:上市公司選擇進行股權質押后,控股股東并不會直接喪失其權利,僅被質押部分股權的財產權利,如分紅權等歸于質權人,而決策、控制權等非財產權利仍由出質人享有,且股權質押與否無需董事會或股東大會參與抉擇。在股權質押研究領域中,學者們常從以下三個視角進行研究。
(二)代理理論視角
股權質押行為常涉及第二類代理問題,控股股東在進行股權質押后仍可以用較小的現金流權維持其原有控制權。控股股東隧道挖掘行為的產生與兩權分離程度成正比,控股股東完全可以在只承擔自身行為產生的部分后果情況下,惡意侵占中小股東利益。如若股權集中度提升,兩權分離程度就隨之加大,控股股東能夠惡意控制股價的提升,第二類代理問題由此被激化,一系列后果隨之產生:企業內控質量下降,企業價值降低等等(鄭國堅等,2014)[1]。如果企業在財務窘迫的同時還面臨股價下跌風險,控股股東大概率會選擇掏空來追加擔保以獲取資金、穩定股價,掏空情況下代理問題將異常嚴峻(黃志忠和韓湘云,2014)[2]。
(三)控制權轉移風險權衡視角
為了防范股權質押業務中種種會引發股市動蕩的風險,監管部門于2004 年頒布了《證券公司股票質押貸款管理辦法》,規定股權質押期間應設立警戒線和平倉線,股價與本金的比例應高于兩者。當比例降低至警戒線時,質權人有權要求出質人進行補充質押,當跌破平倉線時,質權人有權賣出質押品,不足部分由出質人清償。此外,在實際環境中,無論是什么因素導致質押品本身的質量下降,金融機構都有權終止質押,要求企業提前償還債務,控制權轉移風險由此增加。控股股東為了降低控制權轉移的風險,甚至會在股權質押情境下,采用慈善捐贈行為來穩定股價(胡珺等,2020)[3]。
(四)信息不對稱理論視角
股權質押時,企業為了提高貸款成功率和貸款額度會采取盈余操縱行為,使傳遞的信息與企業實際信息不對稱,增大了質權人的信貸風險,使其處于信息劣勢地位。因此,質權人在質押談判時,會格外關注出質企業是否采用了相關手段操縱盈余,或是與關聯方進行交易等等一系列會導致價值偏離的行為,會通過限制折扣率來降低自身經受的信貸風險。對出質人而言,除了承擔股票本身無法消除的系統風險外,還有市場上頻繁爆倉帶來的對質押企業的負面影響,信息不對稱更使得市場對質押企業的信息反應激烈。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東股權質押的動機
股權質押動機可以分為兩個方面,學者們將控股股東的融資需求、控制權需求等稱為善意動機,將侵占中小股東利益稱為惡意動機。
(一)善意動機
股權質押的伊始是一種市場融資行為,一定程度上能緩解中小企業融資困境、拓寬融資渠道。王斌等(2013)[4]指出企業的股權質押行為能夠很大程度上就表明了控股股東資金高度緊缺,財務困境十分嚴峻。從股票市場和信貸市場的雙重擇時動機出發,發現當股價被高估及信貸成本較低時,利用高比例股權質押方式融通資金,解決融資困境是控股股東的首選(徐壽福等,2016)[5]。
(二)惡意動機
由于股權質押會使企業現金流權和控制權的分離進一步加大,從而降低了控股股東的掏空成本,其采用關聯方交易、非公開發行股票等隧道挖掘行為而惡意侵占中小股東利益。有學者研究發現股權質押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與控股股東的占款情況成正比(陳澤藝等,2018)[6]。更有部分學者認為,股權質押行為本身就可視為一種掏空方式。通過研究質押資金投向,張陶勇和陳焰華(2014)[7]發現當質押資金用于控股股東自身時,較大的控制權轉移風險促使其掏空公司。鄭國堅等(2014)[1]認為,股權質押融資說明控股股東處于財務困境,此時侵占上市公司利益成為“上策”,控股股東與公司的利益沖突效益被強化。并且如果資金短缺過于嚴重,股權質押也無濟于事,則占款動機增強(陳澤藝等,2018)[6]。
四、上市公司控股股東股權質押的影響因素
(一)法律制度因素
融資市場的一舉一動都受法律制度約束,我國對于股權質押的約束最早出自擔保法,相關規定對質押雙方都有保障作用。質押率、警戒線和平倉線的規定,不但能夠控制出質人的以控制權轉移風險為代表的種種風險,還可以保障質權人債權的實現。然而,由于股價“崩盤”事件的頻繁發生,對股權質押附加了負面影響,控股股東選擇股權質押融資會面臨著重大風險,現有制度雖含有一定風險防范機制,但并不完善。因此推動股權質押業務科學發展的重中之重是完善相關法律制度。
(二)市場環境因素
1.股票市場。股權質押的本質是權利質押,股權是其主要質物,股票的市場價值決定了擔保價值,因此決定了質押貸款的金額的大小,可見股票市場是影響股權質押的重要市場環境因素。股票錯誤定價程度與控股股東的質押意愿及比例呈正相關關系,股價高估將推動其選擇股權質押(徐壽福等,2016)[5]。同樣,對質權人而言,股票價值及擔保物價值的實時變化決定了其出資意愿和規模。出質人的融資規模與股票價值成正比。因此,股價的漲幅會對質押雙方產生影響。
2.信貸市場。由于《擔保法》規定了質押期滿后,出質人需按約定還本付息,因此控股股東選擇質押融資首要考慮的就是信貸的成本。一方面,當控股股東進行股權質押后,現金流權收益轉向質權人,減少的此部分收益就是股權質押的機會成本;另一方面,緊縮型貨幣政策或是高額信貸利率會增加公司融資成本,抑制其資金需求(徐壽福等,2016)[5]。緊縮的貨幣政策和較高的信貸利率對控股股東的股權質押行為起到抑制作用。
五、上市公司控股股東股權質押的經濟后果
(一)股權質押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現有文獻研究股權質押對上市公司的影響主要集中于股權質押與公司價值、市值管理及創新投入等方面。
1.股權質押與公司價值。基于代理理論視角,謝露和王超恩(2017)[8]認為控股股東的股權質押行為會使其與中小股東間的利益沖突增大,并且由于產品市場的競爭激烈性會誘使控股股東過度投資,最終可能對公司價值產生負面影響。相反,也有學者質疑上述影響路徑。王斌等(2013)[4]發現存在一種情形:只有一級控股鏈條,此時控股權與現金流權一致,不存在兩權分離度加大的問題。在不對控股股東性質(國有和民營)加以區分的情況下一概而論,無助于探究控股股東股權質押是否基于代理理論的對于上市公司的掏空行為。結合兩方學者的觀點,基于代理理論視角,利用兩權分離度來解釋控股股東掏空行為的觀點是否明確還有待商討。
基于控制權轉移風險權衡視角,控股股東為了最大程度上避免控制權轉移,在股權質押后會更加重視公司的市值管理活動,實施短期性會計盈余質量操縱行為,最終導致公司會計政策受到影響(黃志忠和韓湘云,2014)[2]。同時也有小部分學者持相反意見,認為股權質押對公司價值具有正向積極作用。民營性質下的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后,為了最大程度避免控制權轉移,積極正面地進行公司管理的動機增強,使得公司業績不斷攀升。
對于股權質押對公司價值影響,學者們的觀點還有諸多分歧,且具體影響機理和路徑研究還有待深入。現有文獻基本都只基于公司內部治理視角展開研究,尚未結合外部治理環境進行分析檢驗。
2.股權質押與市值管理。控股股東為降低股價崩盤風險會重點關注公司股價并進行市值管理,而非實際改善公司經營狀況。廖珂等(2018)[9]指出,上市公司經營和財務決策權由控股股東所有,控股股東市值管理的措施主要為盈余管理、股利政策及信息披露。
(1)盈余管理。股權質押使得金融機構參與到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中,而上市公司會通過操作盈余的手段以達成通過評估獲得融資的目的。謝德仁和廖珂(2018)[10]認為股權質押公司的操縱盈余管理行為會比未質押公司的程度更高。任思文(2021)[11]認為控股股東股權質押次數越多,其真實盈余管理行為就越多,兩者存在正向關系。
(2)股利政策。控股股東為了達成市值管理的目的,通常會采用公司股利政策操控手段向基本市場傳遞有利信息以穩定或提高股價。李旎和鄭國堅(2015)[12]認為股權質押特有的追加保證金風險、平倉風險及控制權轉移風險會使得控股股東具有強烈動機去操控股價。關于如何使用股利政策達成控制目的,現有學者的觀點主要有兩種:一種觀點是增派現金股利,基于代理理論,控股股東的股權質押行為加劇了兩權分離(宋迪和楊超,2018)[13];另一種觀點進行“高送轉”,降低現金股利發放,控股股東“高轉送”概率,降低現金股利發放傾向與股權質押比例成正比(黃登仕等,2018)[14]。
(3)會計信息披露。股權質押后,控股股東存在機會主義行為,通過信息披露向資本市場傳遞利好消息以穩定股價規避控制權轉移風險。李常青等(2018)[15]發現控股股東的常規操作是在交易日披露利好消息,在非交易日披露負面消息,這樣可以有效控制股價的波動;張晨宇和武劍鋒(2020)[16]將信息披露視為控股股東穩定股價的重要渠道,信息披露違規比經營違規更有助于滿足穩定股價的需求。
3.股權質押與創新投入。學者們大多認為股權質押會抑制企業的創新投入。羅婷等(2009)[17]發現企業創新需要大量資金投入,而股權質押實際是一種融資手段,控股股東股權質押暗示其財務困境,資金不足的情況下勢必就會減少研發投入;張瑞君和徐鑫(2017)[18]提出,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后更傾向于保守型財務決策,包括降低研發投入;李常青等(2018)[19]發現兩職合一的上市公司股權質押后,控股股東抑制創新投入的意愿更加明顯,并且在企業質押率較高和接近平倉線時抑制作用最為顯著。
(二)股權質押對利益相關者的影響
股權質押業務產生的經濟后果除了影響上市公司自身外,對上市公司的利益相關者同樣也有不小的影響,具體的利益相關者有投資者、審計師等。債務投資者作為債權人,對于不對稱的風險與收益格外關注。控股股東在股權質押后會通過盈余管理等手段穩定公司股價進而抵御控制權轉移風險。審計師面臨的是由業務風險和審計風險構成的審計總體風險。考慮到放松賣空管制的外部治理效應和大股東逆向選擇,王靖懿等(2019)[20]認為一定程度上,放松賣空管制的外部治理作用對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后的掏空行為具有抑制作用,抑制其向審計師支付高額審計費用達到利益最大化;而徐會超等(2019)[21]認為控股股東股權質押后更傾向于選擇低質量的審計師,以規避公司受到外部高質量的監督。
(三)股權質押的治理效應
目前學者主要從兩個角度對股權質押的治理效應進行研究。一方面,由于股權質押引入質權人這一外部治理角色,其對于質押品的質量關注需求強化上市公司外部監管,對控股股東的操控行為起到抑制作用。王斌和宋春霞(2015)[22]發現金融機構對出質人的評估設定會抑制控股股東盈余管理動機;另一方面,由于質押品質量的治理效用,譚燕和吳靜(2013)[23]發現質押品質量既對出質人行為起抑制作用還對質權人的債務代理成本起降低作用,且金融機構對質押品的質量控制效用與金融發展水平成正比;而呂曉亮(2017)[24]認為質權人對股權質押公司起到外部治理作用,能夠有效監督上市公司的股權質量,減少了上市公司的違規動機與行為。
六、述評與展望
目前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質押行為已十分普遍,隨著股權質押的廣泛采用,其影響力也日漸擴大,越來越多的學者從不同視角,對股權質押的相關問題展開大量研究。在文獻梳理后,本文認為未來股利質押研究領域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尋求突破。
第一,重視外部制度約束對上市公司股權質押的影響。不同時期控股股東股權質押所受的外部制度約束不同,不能簡單視為一種無約束差異的融資行為,制度變化對質押雙方的影響及后續差異值得被分析探究。關于制度規范對控制權轉移風險、代理成本問題及信息披露的影響研究還尚待開發,制度規范研究的完善能夠使學者們的研究更具實際參考價值與現實說服力。
第二,統一股權質押對公司價值影響的結論,深入研究其影響機理和路徑。基于公司內部治理視角展開的研究較為充分,而結合公司外部治理環境進行的分析檢驗還有待補充。
第三,區分控股股東的性質(國有和民營),不能一概而論。細致的區分有助于探究控股股東股權質押是否是基于代理理論的對于上市公司的掏空行為。基于代理理論視角的利用兩權分離度來解釋控股股東掏空行為的觀點還有待更多學者的商討。
第四,對于出質人的詳細定義。目前的研究多是以大股東的控股地位出發,以“控股股東”作為研究角度,亦或是以“最終控制人”的研究角度,然而現實中,上市公司進行股權質押的控股股東并非一定是企業的最終控制者,因此目前研究對于出質人的概念界定還存在模糊性,清晰有效的界定更有利于研究結論的明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