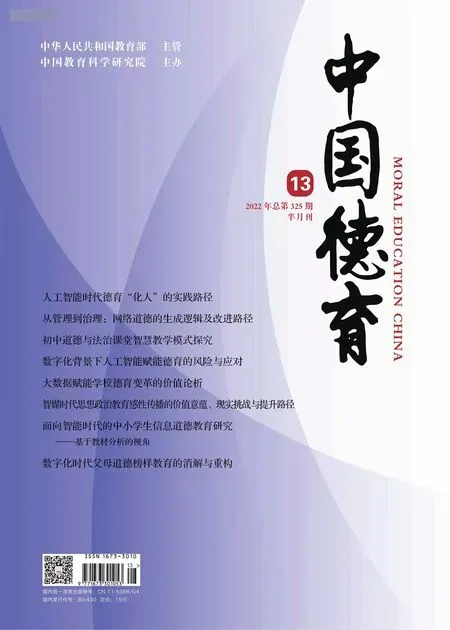數字化時代父母道德榜樣教育的消解與重構
■ 賀園園
榜樣教育是德育領域常談常新的話題。榜樣教育的可貴之處在于,其所彰顯的具有正面價值的榜樣具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價值。社會對道德榜樣教育的提倡就意在突出榜樣的道德價值。當下對道德榜樣教育的探討大多圍繞著青少年群體展開,少有對父母道德榜樣教育的探討。從古至今父母道德榜樣教育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蘇霍姆林斯基指出,一個人自身的道德會發展成什么樣,要看他的母親在這方面如何,也要認識自己父親身上的那些道德財富,這是任何東西都無法替代的榮譽課。但是,與傳統社會相比,在數字化時代,父母實行道德榜樣的時空形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從宏觀的社會背景來看,我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科學技術加速迭代、智能媒體不斷涌現、移動終端迅速普及,一個尼古拉·尼葛洛龐帝在20世紀90年代所預言的人類“數字化生存”狀態已然到來。家庭道德生活的時代背景正經歷著由非數字化社會向數字化社會的轉變,家庭場域中的道德生活圖景也因此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涂爾干認為,人類道德感的萌芽源于個體對他人的依戀,孩子最初的依賴感就源自家庭。數字化時代家庭德育氛圍的革新對父母道德榜樣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戰。從微觀的數據分析來看,2021年7月共青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與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了《2020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該報告顯示,57.5%的家長表示自己對互聯網懂得不多,上網主要是看新聞或短視頻,還有4.1%的家長表示自己不會上網,可能導致其在子女上網管理與引導方面“簡單粗暴”或“有心無力”。由此可見,對大多數家庭來說,父母對孩子的道德榜樣教育面臨著數字化時代的考驗。直面數字化時代的挑戰,亟須深入探討父母道德榜樣教育緣何消解,又何以重構。
一、數字化時代父母道德榜樣教育緣何消解
數字化時代以其固有的特性,影響著家庭德育中的時空、文化以及道德氛圍,從而對父母道德榜樣教育提出了諸多挑戰。這主要體現在數字化社會改變著父母進行道德榜樣教育的家庭德育環境。也就是說,父母進行道德榜樣教育的環境已經由家庭傳統德育環境轉向家庭網絡德育環境,進而消解父母道德榜樣教育的權威地位和主體優勢。
(一)家庭網絡德育環境的“出場”
家庭網絡德育環境的“出場”,是指數字化時代家庭場域中的德育環境已變為家庭網絡德育環境。家庭網絡德育是網絡德育的子概念。目前學術界和理論界對網絡德育與家庭網絡德育的概念有著多樣的理解,但研究者都旨在突出當下家庭德育環境受到數字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庫利在“鏡中我”理論中強調社會環境極大地影響著個體的自我認同。數字化時代家庭德育環境的變革深刻影響著個體道德品性的培育。
數字化時代家庭網絡德育環境的“出場”使得父母進行道德榜樣教育的時空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父母進行道德榜樣教育的時間上來說,相比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孩子,21世紀的孩子是在新媒介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馬歇爾·麥克盧漢在其《理解媒介》一書中論及新媒介時說到,新媒介在19世紀80年代是電報;在20世紀20年代是廣播;在20世紀50年代是電視,直到20世紀90年代后是移動互聯網。在數字科學技術加速迭代的影響下,媒介環境勢必會不斷更新。當下,“00后”的孩子被稱為數字化時代的“原住民”,他們從一出生就生活在一個數字化的世界,數字生活對于他們來說是一種原初生活、日常生活。從父母進行道德榜樣教育的空間上來說,第4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我國未成年網民的互聯網普及率為 94.9%且未成年人“觸網”低齡化的趨勢明顯;未成年網民擁有屬于自己的上網設備的比例已達82.9%。可見在數字化時代,普遍的數字參與已漸趨成為未成年人的顯著標簽。與此同時,家庭無疑是未成年人接觸數字生活的主要場所。家庭網絡德育環境的“出場”,推動了文化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所描繪的年長一輩向年輕一輩學習的后喻文化的加速發展,進而增強了孩子在家庭中的話語權與優勢地位,同時也拓寬了父母道德榜樣教育的空間,由此使得傳統的父母道德榜樣教育面臨著嚴峻的現實考驗。
(二)父母道德榜樣教育的權威“褪色”
家庭網絡德育環境的“出場”,改變著父母進行道德榜樣教育的家庭時空環境,進而引發了父母道德榜樣教育的權威“褪色”。父母道德榜樣教育的權威“褪色”,是指相對于家庭傳統德育來說,父母在家庭網絡德育中的權威地位在不斷弱化。在傳統社會的家庭生活中,長輩會制定出自己家庭中適用的規矩來約束后輩,并將其作為使家庭成員社會化的手段與保證家庭功能實現的制度條件。包括父母在內的長輩在家規的制定與執行中有著絕對的權威。基于生理成長需要及家庭倫理制度,父母在孩子各方面的成長中都扮演著權威的守護者角色。“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就是傳統社會對父母權威角色的生動描繪。
數字化時代父母在孩子道德榜樣教育中的權威角色正在逐漸“褪色”,表現為在家庭網絡德育中父母的道德認知、道德情感以及道德行為方面的權威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具體來說,父母道德認知的權威“褪色”表現為通過數字媒介產品,孩子可以更快速地獲取需要的信息,而不再是僅僅局限于從父母的言傳身教中獲取信息。比起向父母詢問某些困惑或者等待父母的教育引導,孩子通過手機、平板電腦、智能機器人等媒介,可以快捷地獲取豐富的信息資源。父母道德情感的權威“褪色”表現為數字化時代信息數字技術與多元文化環境交相輝映,孩子不可避免地會接觸到眾多的電子媒介產品。多樣的數字媒介產品帶給孩子海量信息的同時也向孩子傳達著多元的價值觀,這些都沖擊著父母比起孩子在道德情感上的優勢地位。父母在道德認知與道德情感方面優勢地位的下降,影響父母進行道德榜樣教育時道德行為示范的實效。父母道德榜樣權威的“褪色”,促使父母道德榜樣教育需要在家庭網絡德育中“轉向”。
(三)父母道德榜樣教育的主體“失色”
家庭網絡德育環境的“出場”,在引發父母道德榜樣權威“褪色”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父母道德榜樣教育的主體“失色”。父母道德榜樣教育的主體“失色”指的是,父母不再是對孩子進行道德榜樣教育的單一主體,父母在孩子德性養成中也不再是唯一的主導力量。數字化時代雖然父母作為天然的榜樣范本仍舊發揮著重要作用,但父母對孩子進行道德榜樣教育時已有的主體優勢有所下降。父母道德榜樣教育的主體“失色”,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從父母自身這一道德榜樣教育主體來說,父母自身道德榜樣教育的力量有所式微。數字化時代“互聯網+教育”深入發展,“翻轉課堂”“慕課”等新的教學形式相繼涌現,加之近年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圍內的肆虐,都使得孩子的線上與線下生活緊密相關、融為一體。孩子通過電子媒介產品進行學習與生活的現象越來越普遍與必要。在家庭網絡德育中,數字媒介產品的便利性為家庭生活中父母道德榜樣教育的“不在場”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除此之外,現實中很多家庭,父母因外出打工或上班等原因,將電子媒介作為陪伴孩子的工具,使之扮演著“電子保姆”的角色。這使得在真實的家庭環境中,孩子對父母的道德依賴感也會有所降低。從父母之外的其他道德榜樣教育主體來說,父母道德榜樣教育的優勢受到了其他榜樣力量的沖擊。按照道德榜樣教育主體的不同,道德榜樣教育可以是父母道德榜樣教育、同輩群體道德榜樣教育、教師道德榜樣教育,以至包括時代英雄、行業專家、網絡明星等在內的社會人士的道德榜樣教育。數字時代除父母之外的其他道德榜樣教育主體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對孩子的德性養成產生深刻影響,從而沖擊著父母道德榜樣教育的主體優勢。
二、數字化時代父母道德榜樣教育何以重構
數字化時代隨著家庭網絡德育環境的“出場”,父母道德榜樣教育的權威地位與主體優勢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面對家庭網絡德育環境的挑戰,父母對孩子進行道德榜樣教育的理念、內容、方法等都需要作出適應數字化時代的調整。具體來說,父母在進行道德榜樣教育時需要不斷提升自身的網絡素養,并在家庭網絡德育中“轉向”,即從道德榜樣教育中的道德權威者轉向道德共識的促進者,從在道德榜樣教育中的主體地位轉向利他地位。
(一)父母需提升自身數字素養
家庭網絡德育環境“出場”的同時,家庭傳統德育環境逐漸“退場”,需要父母在家庭網絡德育中不斷提高自身的數字素養能力,也即父母需要提高自身在工作、就業、學習、休閑以及社會參與中,自信、批判和創新性使用信息技術的能力。家庭整體的道德觀念以及家長自身的道德觀念長期以來對孩子的道德發展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因此,父母需要有意識地提高自身的數字素養與能力,才能更好地對孩子的數字化生活進行引導,進而推動家庭網絡德育建設。
數字化時代信息科學技術正如一把雙刃劍。數字技術一方面為家庭成員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另一方面也可能使還未完全具備自我管理能力的孩子形成對數字科技的深度依賴。除此之外,未成年人對于良莠不齊的網絡信息資源也缺乏必要的辨別能力,很容易造成對網絡信息的聽之信之,更有甚者會在數字游戲中成癮。因此,父母在對孩子進行道德榜樣教育時,需要提高自身的數字素養,并努力打破與孩子之間的媒介隔閡,嘗試與孩子共同建構“媒介融合型家庭”。針對家庭網絡德育中的問題,父母需要加強對孩子網絡生活的過程性監管,打通家庭網絡生活與現實生活的鴻溝,從根本上提高孩子的網絡道德素養。面對家庭網絡德育環境,父母借助數字技術手段為家庭道德教育賦能應漸趨成為新時代家庭德育的必然選擇。
(二)從榜樣權威轉向促進共識
在家庭網絡德育中,要應對父母道德榜樣教育權威“褪色”的挑戰,就需要父母在家庭德育中由傳統的道德榜樣權威者轉向道德底線的共識促進者。也就是說,父母在對孩子進行道德榜樣教育時需要在與孩子的雙向溝通中,從真理與權威的化身轉變為道德底線的共識促進者。傳統的父母榜樣權威的“褪色”是對現代社會親子間民主平等觀念的回應,也順應了數字化時代后喻文化的發展特征。但是父母的道德榜樣權威的“褪色”并不是說傳統社會中父母榜樣權威的完全失效。沃特·桑德斯通過綜述四個關于榜樣角色的調查指出,比起其他道德榜樣角色,父母及其家庭成員仍是多數孩子所認為的最重要的榜樣角色。父母對于孩子的榜樣權威,不僅僅是長輩對于后輩傳統家族意義上的權威,更多的來自父母相比于孩子更多的經歷以及父母成長中的經驗性積淀。因此,數字化時代需要對父母傳統道德權威進行再審視。
一方面,父母應該承認數字化時代帶來了親子之間的隔閡,并應努力地通過平等對話了解孩子的感受和想法,以矯正不同時代看待問題的視差。另一方面,父母也應該意識到,道德權威的淡化意味著自身作為道德榜樣的過往經歷或經驗已經難以完全適應數字化時代孩子生活中所面對的新問題、新情境。因為經驗的有效性建立在生活的重復性上,重復性建立在社會發展的緩慢性上。當下,數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整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加速轉型。父母作為道德榜樣雖然道德權威淡化,但是孩子也未曾有經驗,父母自身卻有歷史經驗的思維方式。總之,數字化時代父母作為孩子的道德榜樣既不應擺老資格,也不應妄自菲薄。父母應在家庭網絡德育環境中實現身份轉向,轉向孩子的視角,轉向有意識地提高自身的數字素養能力,才能為孩子德性的養成提供良好的氛圍。
(三)從主體優勢轉向利他優勢
在家庭網絡德育中,應對父母道德榜樣教育主體地位“失色”的挑戰,需要父母在家庭網絡德育中,攜手其他道德榜樣教育主體的力量,共同培育孩子的道德素養。父母道德榜樣教育主體地位的“失色”,為多種道德榜樣力量形成合力提供了契機。在家庭網絡德育環境下,孩子可以更便利地了解網絡流行文化,更方便地聚集到同輩群體的網絡話語中。如北京的一項研究表明,13至l5歲的青少年將心里話告訴他人的首選對象是同性的同齡的伙伴。可見,同輩群體也具有影響個體德性成長的潛在力量。與此同時,偶像明星在孩子的眼中顯得更形象、生動、親切,類型也更加多樣,可以滿足孩子的主體需要和價值追求。因此,父母要善于利用青少年偶像崇拜心理,因勢利導,達到榜樣教育的目的。
總之,父母在對孩子進行道德榜樣教育中要注重凝聚多種道德榜樣的力量,使之形成合力,這就需要父母對家庭網絡環境進行疏通而不是堵塞。父母只有對孩子信賴的同輩群體榜樣或偶像明星榜樣給予充分的了解與尊重,才有可能引導孩子對不良的數字信息以及消極的榜樣進行批判性思考。與此同時,面對急劇變遷的數字化時代,孩子比父母具有更高的信息敏感性和吸收能力,父母作為孩子的道德榜樣也應該放低姿態,汲取孩子身上新的道德養分,更應從傳統家庭環境中在孩子道德榜樣教育中的主場優勢,轉向為同輩群體榜樣和積極的偶像明星榜樣發揮良性作用創造條件。
家是社會的承載體,社會的任何一點變動都會直接作用在每一個家庭。數字化社會之于家庭的作用在于,一方面消解著傳統社會中父母道德榜樣教育的權威與地位,另一方面又為父母道德榜樣教育更好地實施提供了新的思路。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數字信息技術無疑改變了父母與孩子之間相互關系的形態,但無可置疑,在未來社會父母仍舊是孩子德行養成乃至德性培育的重要主體。因此,父母道德榜樣教育的傳統角色要在家庭網絡德育中實現轉向。要從對孩子道德榜樣教育時的權威者轉向能夠與孩子平等對話的共識促進者;從在孩子道德教育中一家獨大,到重視同輩群體、社會組織以至孩子個體自身的道德教育力量。惟其如此,才會使父母道德榜樣教育助力孩子的德性成長與家庭德育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