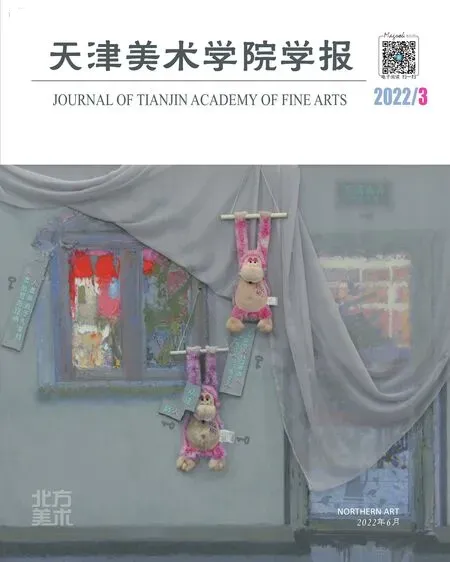“‘中國(guó)歷代繪畫(huà)大系’先秦漢唐、宋、元畫(huà)特展”展評(píng)
紀(jì)雙雙
紀(jì)雙雙:中國(guó)美術(shù)學(xué)院博士在讀
編者按:2005年,由浙江大學(xué)、浙江省文物局負(fù)責(zé)編撰的“中國(guó)歷代繪畫(huà)大系”項(xiàng)目獲批。這是一項(xiàng)規(guī)模浩大、縱貫歷史、橫跨中外的國(guó)家級(jí)重大文化工程。“盛世修典——‘中國(guó)歷代繪畫(huà)大系’先秦漢唐、宋、元畫(huà)特展”展現(xiàn)了該項(xiàng)目17年來(lái)的主要工作成果,觀眾可以將其看作是對(duì)項(xiàng)目一個(gè)的導(dǎo)引,為深入了解項(xiàng)目提供的一扇窗口。本文的作者曾親身參與到項(xiàng)目的具體工作中,對(duì)項(xiàng)目的組織結(jié)構(gòu)脈絡(luò)有更深的體會(huì),在文中作者不僅介紹了展覽的大致面貌,還對(duì)部分重要展品的研究?jī)r(jià)值、所涉及的研究領(lǐng)域和研究現(xiàn)狀做了說(shuō)明,其中表現(xiàn)出的國(guó)際視野尤為值得稱(chēng)贊。
展覽鏈接:
盛世修典——“中國(guó)歷代繪畫(huà)大系”先秦漢唐、宋、元畫(huà)特展
主辦單位: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浙江大學(xué)、中國(guó)美術(shù)學(xué)院
承辦單位:浙江大學(xué)藝術(shù)與考古學(xué)院、浙江美術(shù)館、中國(guó)美術(shù)學(xué)院視覺(jué)中國(guó)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
時(shí)間:2022年3月10日—4月20日(巡展下一站為浙江嘉興)
地點(diǎn):浙江美術(shù)館1、4、5、6、7、8、9、10、11、12號(hào)廳及天光長(zhǎng)廳、藏品陳列展廳
“中國(guó)歷代繪畫(huà)大系”共收錄海內(nèi)外260余家文博機(jī)構(gòu)的紙、絹(含帛、綾)、麻等材質(zhì)的中國(guó)繪畫(huà)藏品12479件(套)。涵蓋了絕大部分傳世的國(guó)寶級(jí)繪畫(huà)珍品。先后編纂出版《先秦漢唐畫(huà)全集》《宋畫(huà)全集》《元畫(huà)全集》《明畫(huà)全集》《清畫(huà)全集》共計(jì)66卷240余冊(cè)。這是迄今為止同類(lèi)出版物中藏品收錄最全、圖像記錄最真、印刷質(zhì)量最精、出版規(guī)模最大的中國(guó)繪畫(huà)圖像文獻(xiàn)。①2022年3月10日至4月20日,“盛世修典——‘中國(guó)歷代繪畫(huà)大系’成果展”在浙江美術(shù)館展出。
4、5、6號(hào)展廳分“久久為功”“漢唐奇跡”“無(wú)界之境”三個(gè)主題,其中“久久為功”根據(jù)不同主題將繪畫(huà)并列展出,如將鈐有金內(nèi)府收藏印章的《摹張萱搗練圖》《張萱虢國(guó)夫人游春圖》《步輦圖》《歷代帝王圖》等圖并列展出,并將圖中印章挖出放大,如《芙蓉錦雞圖》中的“奎章閣寶”、《江行初雪圖》中的“天歷之寶”、《摹張萱搗練圖》中的“群玉”“明昌御覽”、《虢國(guó)夫人游春圖》中的“明昌”“明昌寶玩”“御府寶繪”等印章,這些印章不僅昭明了其鈐印之畫(huà)的鑒藏歷程,通過(guò)印章與繪畫(huà)的對(duì)比研究,還可以尋繹出繪畫(huà)在流傳過(guò)程中重新裁割裝裱的痕跡,將這些鈐蓋金內(nèi)府收藏印的繪畫(huà)合并觀看,更可以探尋出“明昌七璽”的形成過(guò)程和使用方式。“明昌七璽”為金章宗仿宋徽宗“宣和七璽”而制,在使用時(shí)分鈐于畫(huà)卷的前隔水、題簽上、下,以及畫(huà)心后上、下角和后隔水并拖尾上。依序?yàn)椤懊馗保êJ印)、“明昌”(圓頂長(zhǎng)印)、“明昌寶玩”、“御府寶繪”、“內(nèi)府珍玩”、“群玉中秘”、“明昌御鑒”。②鑒別偽印是鑒定歷代繪畫(huà)的重要手段,徐邦達(dá)曾言“宋摹閻立本《步輦圖》上‘明昌’諸印,多半是或完全是作偽者后添的”③,通過(guò)對(duì)展覽中展示圖片的重新觀察,研究者或許對(duì)此一問(wèn)題有重新思考(圖1)。
此外,還將不同版本的《洛神賦圖》(圖2)、《瀟湘圖》、《五牛圖》、《搗練圖》并列展出,以便觀覽研究。
“漢唐奇跡”主要展出先秦漢唐繪畫(huà),如1949年出土于湖南省長(zhǎng)沙市陳家大山的《人物龍鳳圖》,這也是迄今我國(guó)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繪畫(huà),以及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長(zhǎng)沙市子彈庫(kù)1號(hào)墓的《人物御龍圖》,這兩幅繪畫(huà)在中國(guó)美術(shù)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饒宗頤先生曾評(píng)《人物龍鳳圖》:“此幀全用線(xiàn)條勾勒,人物與動(dòng)物,韶秀清勁,此時(shí)期線(xiàn)條所表現(xiàn)的骨法用筆,有高度造詣,生動(dòng)之筆觸成為畫(huà)面主要元素。具見(jiàn)繪畫(huà)者如何工于控制毛筆,大有后世所稱(chēng)‘高古游絲描’之手法,流露出輕蒨雅麗之快感。”④金維諾評(píng)《人物御龍圖》道:“畫(huà)家已經(jīng)注意到描繪不同的部位,運(yùn)用不同的線(xiàn)來(lái)體現(xiàn)形與質(zhì)。面部的線(xiàn)是精微的,若隱若現(xiàn),呈現(xiàn)的是嚴(yán)峻的容貌與須眉;表現(xiàn)服飾的線(xiàn)是綿延舒暢的,如行云流水,如春蠶吐絲,呈現(xiàn)的是舒緩行進(jìn)中的廣袖長(zhǎng)袂。”⑤除了用于研究當(dāng)時(shí)的繪畫(huà)水平,這兩幅畫(huà)還為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空間,如畫(huà)中龍、鳳所承載的崇拜觀念即象征意義,其繪畫(huà)主題與當(dāng)時(shí)楚國(guó)社會(huì)民眾對(duì)生命、靈魂的信念的關(guān)系等。其偏于現(xiàn)實(shí)的畫(huà)風(fēng)及細(xì)致的描繪,也為學(xué)者研究先秦時(shí)期的服飾制度提供了寶貴的圖像資料。
展廳中央陳列的《十王經(jīng)》圖卷(圖3、圖4),原件現(xiàn)藏于大英圖書(shū)館。其本出于《佛說(shuō)十王經(jīng)》《地藏十王經(jīng)》,二經(jīng)為唐末五代時(shí)中國(guó)本土所造偽經(jīng),其中“出現(xiàn)了地獄十王,分別為:秦廣王、初江王、宋帝王、五官王、閻羅王、變成王、太山王、平正王、都市王、五道轉(zhuǎn)輪王”⑥。《佛說(shuō)十王經(jīng)》“在五代以后因?yàn)樾麄鞯牧垒喕厮枷胗狭酥袊?guó)百姓,而十王信仰與我國(guó)喪葬禮儀的七七忌、百日忌、一周年忌、三周年忌等相結(jié)合,加上許多民間神話(huà)傳說(shuō),成為超度亡靈的水陸法會(huì),是為亡者祈福的一種重要民間活動(dòng),流傳甚廣”⑦。
兩宋時(shí)期,僧人將“十王信仰”由寧波通過(guò)海上傳入日本,其中一些作品也東傳至日本,現(xiàn)藏于日本的各大寺院和博物館。目前學(xué)界對(duì)《十王經(jīng)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寧波《十王經(jīng)》圖卷[是展“宋韻無(wú)盡”(五代宋遼金繪畫(huà))主題中展出了奈良國(guó)立博物館所藏陸信忠《十王圖》的高清圖像,是作即屬寧波《十王經(jīng)》圖卷],如日本學(xué)者鈴木敬、田中一松、中野照男、宮次男、梶谷亮治、井手誠(chéng)之輔,德國(guó)學(xué)者雷德侯,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石守謙等均曾研究過(guò)寧波《十王圖》。⑧
此次展出的《十王圖》與寧波《十王圖》相較,學(xué)界對(duì)此本的研究尚顯不足,“十王圖像源于古神話(huà),內(nèi)容大都是根據(jù)民間神話(huà)故事改編的,并隨著時(shí)代變遷而不斷地發(fā)生變化,經(jīng)歷唐宋時(shí)代的演變,直到明代其內(nèi)容才相對(duì)固定下來(lái)”⑨。將是本與寧波《十王圖》相結(jié)合進(jìn)行研究,不僅可以梳理出《十王圖》在不同時(shí)期的演變脈絡(luò),還有可能發(fā)現(xiàn)不同地域《十王圖》描繪特點(diǎn)及其背后的觀念差異。
“無(wú)界之境”采用3D技術(shù)復(fù)制敦煌典型洞窟,如敦煌莫高窟第45窟、57窟,龍門(mén)石窟古陽(yáng)洞四大北魏龕、云岡石窟第6窟南壁“文殊問(wèn)疾”屋形龕、佛光寺雕塑壁畫(huà),創(chuàng)造出融建筑、雕塑、書(shū)法、繪畫(huà)于一體的綜合公共美術(shù)空間,給觀者帶來(lái)身臨其境的體驗(yàn)(圖5、圖6、圖7)。
黑水城遺址位于今中國(guó)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阿拉善盟額濟(jì)納旗政府所在地達(dá)來(lái)庫(kù)布鎮(zhèn)東南12.5千米處,蒙古語(yǔ)Khara Khoto,意為黑城;黑水城始建于公元11世紀(jì)初,西夏曾在此設(shè)十二監(jiān)軍司之“黑水鎮(zhèn)燕軍司”,黨項(xiàng)語(yǔ)“亦集乃”語(yǔ)義為黑水,漢語(yǔ)作額濟(jì)納。是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關(guān)隘,14世紀(jì),因戰(zhàn)亂、黑水河改道等原因,其城沒(méi)于沙漠。1908—1909年,俄國(guó)探險(xiǎn)家柯茲洛夫兩次進(jìn)入黑水城,攫取了大量出土文物。這些文物被運(yùn)至俄羅斯,分別藏于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和俄羅斯科學(xué)院東方研究所,其中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所藏出土文物總共有3500件;柯茲洛夫所獲大部分的文書(shū)和版畫(huà)藏于東方研究所,大約有8000件。“這些稱(chēng)傲于世的西夏文物成為俄蘇西夏學(xué)研究的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開(kāi)創(chuàng)了以聶歷山為代表的西夏學(xué)派。在20世紀(jì)80年代以前,對(duì)黑水城唐卡的介紹和研究,主要是由俄蘇學(xué)者進(jìn)行的。”⑩“直到20世紀(jì)70年代末歐美學(xué)者開(kāi)始關(guān)注西藏藝術(shù)品以后,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的一些著名藏品才開(kāi)始出現(xiàn)在西方出版的西藏繪畫(huà)圖錄中。”從黑水城文物的發(fā)掘至今,隨著各國(guó)學(xué)者的整理、研究,逐漸形成“西夏學(xué)”這一世界性的學(xué)問(wèn)。西夏為黨項(xiàng)羌族政權(quán),與周邊吐蕃、回鶻、宋、遼、金、蒙古交往頻繁,其文化呈兼容、多元的特點(diǎn),這些出土文物包括宋、西夏、元的藝術(shù)品,涉及文化、宗教、民族交流等方面的信息,雖然向達(dá)等人很早就對(duì)柯茲洛夫及斯坦因等人在黑水城所獲文物進(jìn)行了介紹和分析,但國(guó)內(nèi)學(xué)者對(duì)黑水城出土繪畫(huà)的研究起步很晚,直至20世紀(jì)90年代我國(guó)學(xué)者才有機(jī)會(huì)介入到這批文物的研究之中。
目前學(xué)界對(duì)黑水城出土的繪畫(huà)文物的研究,主要分為分類(lèi)研究和個(gè)案研究。前者“如奧登堡以自身印度學(xué)學(xué)養(yǎng)對(duì)受印度佛教繪畫(huà)影響的黑水城繪畫(huà)的研究,聶歷山、柯切托娃對(duì)星神圖像的研究,魯多娃對(duì)木刻版畫(huà)的研究。克列謝托娃是首位以黑水城‘中國(guó)’繪畫(huà)為題的研究者”;后者如魯多娃對(duì)阿彌陀佛繪畫(huà)的研究,王艷云對(duì)文殊菩薩圖像的研究,席鑫洋對(duì)大勢(shì)至菩薩的研究,何旭佳、鄭怡楠、金鵬等人對(duì)黑水城出土水月觀音圖像的研究,黃士珊《西夏佛經(jīng)版畫(huà)再探》中對(duì)《妙法蓮華經(jīng)》《華嚴(yán)經(jīng)》《心經(jīng)》等佛經(jīng)版畫(huà)的詳細(xì)圖像分析和對(duì)比等,這些研究對(duì)于“中原風(fēng)格的佛畫(huà)卷軸部分題材的研究較為充分和深入,但相比于數(shù)量龐大的繪畫(huà)遺存,現(xiàn)有研究仍有亟待填補(bǔ)的空白”,我國(guó)的學(xué)術(shù)界和藝術(shù)史界由這些繪畫(huà)遺存為切入點(diǎn),研究佛教文化與藏傳密宗、西北邊疆民族藝術(shù)傳統(tǒng)、宮廷藏傳佛教藝術(shù)和西夏藏傳佛教藝術(shù)之間的關(guān)系,無(wú)論從研究視野還是從研究方法上,將會(huì)迎來(lái)黑水城繪畫(huà)研究新格局。這些研究的前提是研究者能夠目睹這些出土文物的圖像資料,這次展覽展出的黑水城出土的大量佛教文獻(xiàn)和唐卡,為研究者提供了清晰準(zhǔn)確的資料信息,對(duì)推進(jìn)這一領(lǐng)域的研究亦有所裨益(圖8)。
7、8、9、10號(hào)展廳所展主題為“宋韻無(wú)盡”,這一主題集中而全面地展示了五代、宋、遼、金的繪畫(huà),不同作品或按作者,或依主題集中展出(圖9、圖10)。如展廳入口即為貫休等人所畫(huà)的羅漢圖,為觀者了解這一繪畫(huà)母題提供了便利。李成、范寬、郭熙等人的山水作品按時(shí)代次序陳列,為觀者勾勒出五代、北宋山水畫(huà)發(fā)展的基本脈絡(luò)。北宋院體繪畫(huà)的集中展出,呈現(xiàn)出由黃筌到崔白,北宋院體繪畫(huà)風(fēng)格發(fā)展的演變歷程。楊補(bǔ)之、趙令穰等文人畫(huà)與北宋院體繪畫(huà)的對(duì)比陳列,也頗有意趣。此外還展出了五代、宋、遼、金的大量佚名畫(huà)作,佚名畫(huà)作被如此集中、大量地展示極為難得,或許可以引起學(xué)界對(duì)這一繪畫(huà)領(lǐng)域的關(guān)注。
馬和之所作《詩(shī)經(jīng)》《唐風(fēng)圖》《陳風(fēng)圖》《詩(shī)經(jīng)小雅鴻雁之什六篇圖》《詩(shī)經(jīng)陳風(fēng)十篇圖》《魯頌三篇圖》《周頌清廟之什圖》《小雅節(jié)南山之什圖》《唐風(fēng)》均被集中展示。關(guān)于馬和之《毛詩(shī)圖》較為全面的研究有黎晟的博士論文《馬和之〈毛詩(shī)圖〉研究》,文中統(tǒng)計(jì)現(xiàn)各博物館和收藏機(jī)構(gòu)所藏“歸于馬和之名下的各類(lèi)《毛詩(shī)圖》共一十八種,三十卷(冊(cè)、幅),另加三卷不同篇章雜合圖卷,共三十三卷(冊(cè)、幅)。這些作品大多保持著相同的形式與畫(huà)風(fēng)”,徐邦達(dá)《傳宋高宗趙構(gòu)孝宗趙昚書(shū)馬和之畫(huà)〈毛詩(shī)卷〉考辨》《趙構(gòu)書(shū)馬和之畫(huà)〈毛詩(shī)〉新考》對(duì)馬和之名下的《毛詩(shī)圖》進(jìn)行考證辨?zhèn)巍P(yáng)之水《馬和之詩(shī)經(jīng)圖》一文稱(chēng)“《詩(shī)》有圖,大約是很早的”,“至南宋,詩(shī)經(jīng)圖忽如一樹(shù)花朵因風(fēng)吹開(kāi),據(jù)稱(chēng)圖成‘毛詩(shī)三百篇’,此即高宗和孝宗書(shū)詩(shī)、馬和之寫(xiě)畫(huà)的詩(shī)經(jīng)圖。就數(shù)量而言,洵可謂‘前無(wú)古人,后無(wú)來(lái)者’”,揭示了《詩(shī)經(jīng)圖》這一繪畫(huà)母題在南宋盛行的狀況,揚(yáng)之水并未深究現(xiàn)存馬和之名下的《詩(shī)經(jīng)圖》是否定為其所作,而是認(rèn)同楊仁凱《國(guó)寶沉浮錄——故宮散佚書(shū)畫(huà)考論》將這些作品多定為“院本”的觀點(diǎn),“視為馬和之及畫(huà)院中人的遵命之作,似大抵近實(shí)”。揚(yáng)之水此文還以考古知識(shí)審視馬和之畫(huà)作,通過(guò)考察《唐風(fēng)圖》中所畫(huà)馬車(chē)的系駕方式,《周頌·賚》所畫(huà)“斧文”,《周頌·昊天有成命》圖中導(dǎo)從所持傘蓋、牙旗、障扇、幡、旌等制度,認(rèn)為馬和之所畫(huà)古代器物制度多依據(jù)當(dāng)時(shí)的考古成果,并結(jié)合宋代的現(xiàn)實(shí)制度。對(duì)此揚(yáng)之水稱(chēng)“我們以今天的知識(shí)而能夠?yàn)椤对?shī)經(jīng)》的時(shí)代勾勒出一個(gè)接近真實(shí)的場(chǎng)景,讀詩(shī)經(jīng)圖,自可見(jiàn)出宋人畫(huà)筆下所融入的宋人之當(dāng)代經(jīng)驗(yàn)”。揚(yáng)之水此論,是觀者欣賞馬和之這一系列畫(huà)作的絕佳導(dǎo)語(yǔ)。
11、12號(hào)展廳展示主題為“桃源春曉”,是展并非致力于展示傳世名作,而是將元代名家較為罕見(jiàn)的畫(huà)作呈現(xiàn)在觀眾面前。走入展廳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中有許多繪畫(huà)以馬為主題,如任賢佐的《人馬圖》、任仁發(fā)的《飾馬圖》、趙雍《臨李公麟人馬圖》、錢(qián)選《武陵挾彈圖》等,面對(duì)這么多以馬為主題的繪畫(huà)作品,可以窺見(jiàn)元代畫(huà)家學(xué)習(xí)李公麟所畫(huà)的馬,與其所處的游牧民族統(tǒng)治下的社會(huì)文化環(huán)境之間的關(guān)系。其中錢(qián)選所畫(huà)《武陵挾彈圖》,據(jù)圖中錢(qián)選題跋,知此畫(huà)源于趙孟頫,趙孟頫之子趙雍也曾作過(guò)這一主題的畫(huà)作。可以推測(cè),從錢(qián)選到趙雍對(duì)這一母題的描繪,均是受趙孟頫的影響。趙孟頫描繪這一母題,若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生活圖景的再現(xiàn),其中所展露的社會(huì)生活風(fēng)貌及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情境下文人士夫的個(gè)人活動(dòng),尚待學(xué)者挖掘。
提到元代畫(huà)家,人們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元四家及趙孟頫等人,與之相較李郭畫(huà)派的畫(huà)家則暗淡許多,這一狀況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與董其昌的“南北宗”論有關(guān),當(dāng)美術(shù)史學(xué)者帶著“南北宗”的固定觀念去看元代畫(huà)家,趙孟頫、黃公望、王蒙、倪瓚等人與唐棣、曹知白、朱德潤(rùn)等人在繪畫(huà)風(fēng)格上的界限也立即變得清晰。此展所展出的唐棣《輞川圖》《王維詩(shī)意圖》提醒觀眾轉(zhuǎn)變視角,站在“南北宗”論提出之前的觀念下,考慮這些畫(huà)家彼此之間在繪畫(huà)與觀念上可能存在的交錯(cuò)的關(guān)系。
最后要提及的是,這場(chǎng)展覽所展示的作品均為“中國(guó)歷代繪畫(huà)大系”項(xiàng)目組根據(jù)圖像資料復(fù)制而成。古代藝術(shù)的傳播要依靠藝術(shù)品原件的流通及畫(huà)家對(duì)藝術(shù)原作的臨繪勾摹,這其中為贗品提供了足夠充分的生存空間,這在無(wú)形中也塑造了古代美術(shù)史學(xué)者的研究方法和鑒定藝術(shù)品的傳統(tǒng)。如今隨著照相術(shù)、數(shù)字印刷和數(shù)字媒介的發(fā)展,在為藝術(shù)在當(dāng)今的傳播帶來(lái)便利的同時(shí),如巫鴻先生言,“實(shí)際上,我們可以認(rèn)為攝影從本質(zhì)上改變了美術(shù)史的運(yùn)作”。
注釋?zhuān)?/p>
①《盛世修典“中國(guó)歷代繪畫(huà)大系”——先秦漢唐、宋、元畫(huà)特展展覽手冊(cè)》。
②丁羲元,《再論〈步輦圖〉為閻立本真跡》,《故宮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4期,第118頁(yè)。
③徐邦達(dá),《古書(shū)畫(huà)鑒定概論》,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39頁(yè)。
④饒宗頤,《澄心論萃》,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第274頁(yè)。
⑤金維諾,《中國(guó)美術(shù)史論集(上)》,黑龍江美術(shù)出版社,2004年,第19頁(yè)。
⑥王航,《敦煌密教鬼神信仰研究》,陜西師范大學(xué)博士論文,2018年,第127頁(yè)。
⑦參見(jiàn)蔡元平《水陸畫(huà)十王地獄圖像的神話(huà)性》,《神話(huà)研究集刊》,2020年第1期,第231—248頁(yè);王航《敦煌密教鬼神信仰研究》,第123頁(yè)。
⑧東傳日本的宋代寧波佛畫(huà)《十王圖》之研究以奈良博物館藏陸信忠筆《十王圖》為中心。
⑨同⑦。
⑩謝繼勝,《黑水城出土唐卡研究述略》,《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第83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