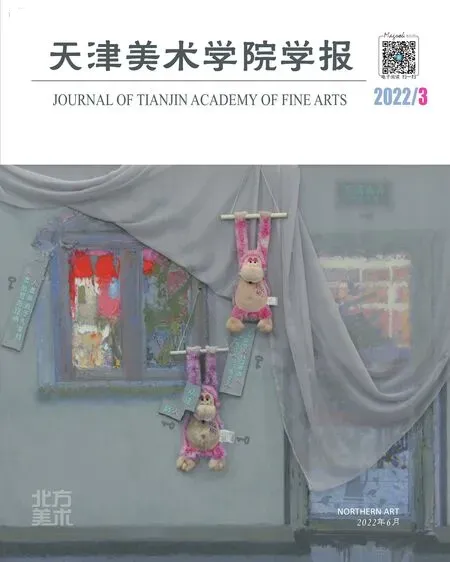作為當代藝術(shù)的照片:針對線性時間觀的遭遇
張容瑋
張容瑋: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視覺中國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博士后研究員
攝影誕生至今已接近180年。然而,直到20世紀最初10年,“攝影究竟是不是一種藝術(shù)”仍然是一個在攝影界內(nèi)部被廣泛爭論的問題。①時至今日,雖然從宏觀角度來講,攝影作為一種藝術(shù)的身份已經(jīng)不會再受到太多的質(zhì)疑,可即便是在其發(fā)源地歐洲,將攝影納入具體的當代藝術(shù)領(lǐng)域仍然是一種近三四十年才興起的相對較新的主張,②而關(guān)于攝影究竟是不是當代藝術(shù)的爭論也一直延續(xù)至今。③本文以西蒙·奧蘇立文教授(Simon O’Sullivan)所提出的藝術(shù)中的“遭遇”理論(Encounter Theory)為判定當代藝術(shù)的標準,以法國后結(jié)構(gòu)主義哲學(xué)家吉爾·德勒茲(Gi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所創(chuàng)立的塊莖哲學(xué)(Rhizome Philosophy)為視角,分析攝影成為當代藝術(shù)的屏障,并指出,由于其先天帶有質(zhì)疑和拓展線性時間觀的潛力,攝影是一個正當?shù)漠敶囆g(shù)門類。
一、當代藝術(shù)的“遭遇”特質(zhì)
在討論“攝影”或者“照片”這種具體的藝術(shù)形式之前,首先需要強調(diào)的是,本文中的“照片”所指的是那種不曾被軟件或其他手段二度處理過的攝影作品,而文中所指的“當代藝術(shù)”并非一切創(chuàng)作時間意義上的“當下”的作品。本文中所說的藝術(shù)作品的“當代性”特指那種能夠為觀眾帶來“遭遇型”觀看體驗的作品。“遭遇型”觀看體驗以及與其相對應(yīng)的“識別型”觀看體驗是倫敦大學(xué)金史密斯學(xué)院(Goldsmiths,University of London)的西蒙·奧蘇立文(Simon O’Sullivan)教授在其所著的《藝術(shù)遭遇德勒茲與加塔利:超越再現(xiàn)主義的思考》(Art Encounters Deleuze and Guattari: Thoughts Beyond Representation)一書中所指出的一種理論。奧蘇立文教授在書中指出,世界上有些東西“強迫我們思考”,這樣的東西是“遭遇型物體”(Object of Encounter)。而與它們相對的是“識別型物體”(Object of Recognition)。這兩者有著本質(zhì)的不同。按照他的講解,“識別型物體”所指的是那種能夠讓我們鞏固、確認自己已有的知識、信仰或價值觀的物體。④米開朗琪羅繪制的西斯廷天頂壁畫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識別型物體。通過將天主教的世界觀視覺化,米開朗琪羅鞏固強化了教徒已有的信仰。甚至到了五百年后的今天,無論是不是基督徒,也無論對美術(shù)史有多少了解,絕大多數(shù)觀眾哪怕是在畫冊中看到這件作品時也能或多或少地領(lǐng)會到這件作品背后的天主教信仰和價值觀。
這種通過創(chuàng)作一件作品來傳達甚至強化某種已存的觀念比如知識、信仰或價值觀的行為也就是奧蘇立文所說的“再現(xiàn)”(Represent)。英文中,“present”作為一個動詞的含義為“展現(xiàn)”或者“顯示”。而詞頭“re-”有“再次”的意思。因此,represent一詞的意義就是“再次展現(xiàn)”,而再次展現(xiàn)的就是那個已存的觀點或事實。而用represent一詞的形容詞形式representational(再現(xiàn)的)來形容某件作品則大致上有兩種可能:一是這件作品“再現(xiàn)”了某個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事物或場景。絕大多數(shù)寫實繪畫和雕塑都可以被歸在這種情況之下。而另一種可以被稱為representational的作品“再現(xiàn)”的則是作者某個已經(jīng)確定的知識、信仰或價值觀。除了西斯廷天頂壁畫,這類“再現(xiàn)式”藝術(shù)作品包括向我們不斷再現(xiàn)法西斯納粹暴行的《格爾尼卡》(Guernica)以及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為我們再現(xiàn)“大消費時代之下明星如商品一般被以機械方式不斷印刷消費”這一現(xiàn)象的《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
盡管再現(xiàn)式藝術(shù)作品在鞏固社會價值觀方面可以發(fā)揮一定的作用,可是奧蘇立文從一個純學(xué)術(shù)角度指出,再現(xiàn)式的藝術(shù)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阻礙觀眾的思維的。⑤由于這一類作品再現(xiàn)的是“已知”,觀眾很可能在觀看它們的時候并不需要運用思維或想象力去理解什么新的觀念。而藝術(shù)家在創(chuàng)作再現(xiàn)式作品時所達到的美或震撼的效果也只是為了強化那個要被“再現(xiàn)”的觀念。換言之,無論是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作還是觀眾的觀看,在涉及再現(xiàn)式藝術(shù)作品時,要在觀念上達到“新”是比較困難的。
與“識別型物體”相對的,是“遭遇型物體”。按照奧蘇立文的說法,所謂“遭遇型物體”大概是這樣一個事件或物體,某人在經(jīng)歷了該事件或物體后,她/他所習(xí)慣的思維或觀點會受到刺激和破壞,促使她/他對自己所習(xí)慣的想法、觀點、信仰或價值觀進行反思,進而產(chǎn)生新的觀念。換句話說,“遭遇型的經(jīng)歷”對經(jīng)歷者而言是一次先破后立的體驗。⑥同樣以一件藝術(shù)作品為例,馬塞爾·杜尚(Marcel Duchamp)創(chuàng)作的《泉》(Fountain)就是一件“遭遇型物體”。對于抱有“藝術(shù)是需要被嚴肅對待甚至是被仰視的”這一觀點的人來說,杜尚將小便池作為藝術(shù)品這一行為對他們的藝術(shù)觀絕對是有破壞力的。比利時美術(shù)史學(xué)家蒂埃利·德·迪弗(Thierry de Duve)在《杜尚之后的康德》(Kant After Duchamp)一書中就講述了1917年杜尚初次試圖將那個簽了名的小便池送進大中心宮藝術(shù)展覽時在兩位策展人之間引發(fā)的“究竟應(yīng)不應(yīng)該讓這件污穢下流之物成為展品”的爭論。策展人策劃那次展覽的目的就是要舉辦一次“沒有委員會的展覽”。在他們的構(gòu)想之中,那次展覽是絕對自由的,定義藝術(shù)的權(quán)力完全在大眾手中。任何人只要交6法郎,就可以交兩件作品參展,無須委員會的開恩批準。然而,面對杜尚送來參展的簽名小便池,兩位策展人還是爆發(fā)了激烈的爭吵。甲策展人認為,既然已經(jīng)為展覽定下了“自由”的基調(diào),那么即使是小便池也應(yīng)該讓它參展,畢竟作者認為這東西是藝術(shù)。而乙策展人則堅持認為,無論多么自由,藝術(shù)也有其底線,小便池這種下流之物無論如何也不能成為一件藝術(shù)品。⑦
從事情后來的發(fā)展來看,兩位策展人的那場爭論顯得有些無關(guān)緊要。因為《泉》已經(jīng)成為西方美術(shù)史上不可磨滅的一筆,而它的意義也已經(jīng)遠遠地超出了在那次展覽上制造的麻煩和玩笑。如今距離《泉》的誕生已經(jīng)百年,可是這件作品依然保有對觀眾的刺激和破壞力。對于為數(shù)不少仍堅信著“藝術(shù)必須是美的”或者“藝術(shù)必須是高尚的”的觀眾來說,要“理解為什么這個簽了名的小便池是一件極其重要的藝術(shù)作品”要求他們?nèi)ベ|(zhì)疑甚至摒棄自己原本對于藝術(shù)的理解,這種質(zhì)疑和摒棄之后所帶來的必然是一種思維的掙扎和混亂,但是當這些觀眾成功地在這種混亂中重新構(gòu)建起一個能夠容納《泉》的藝術(shù)觀的時候,他們就完成了“拓展藝術(shù)的理解”這一行為。這樣的經(jīng)歷也就是一次奧蘇立文所說的“遭遇型物體”為觀眾帶來的思維上的先破后立的拓展。
然而,需要提醒的是,一旦某一件“遭遇型作品”對現(xiàn)行的創(chuàng)作方式或規(guī)則進行了先破后立的突破,那么這件作品將很可能吸引很多的后續(xù)作品來模仿或重復(fù)它為觀眾和創(chuàng)作方式帶來的遭遇式拓展。這樣的例子包括,在《泉》之后,美國攝影師安德烈斯·塞拉諾(Andres Serrano)于1987年拍攝的作品《尿中基督》(Piss Christ)和英國藝術(shù)家特蕾西·埃敏(Tracey Emin)于1998年創(chuàng)作的《我的床》(My Bed)。雖然這兩件作品在形式上與《泉》差別很大,但其創(chuàng)作邏輯卻并未走出杜尚所創(chuàng)立的“將生活中污穢的現(xiàn)成品用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范圍。這些例子說明,由于“藝術(shù)品”和“創(chuàng)作”等概念的定義是處于不斷的發(fā)展之中的,藝術(shù)中的“常態(tài)”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從觀眾的角度來說,什么樣的作品是“遭遇型”的取決于這位觀眾的觀念和知識結(jié)構(gòu)。然而,從藝術(shù)自身的角度來說,“遭遇型作品”永遠是未知的,這樣的作品正處于被藝術(shù)家創(chuàng)作出來的過程中。這也就是為什么“藝術(shù)創(chuàng)作”本質(zhì)上是一種創(chuàng)新,不僅是因為被創(chuàng)作出來的作品是之前并不存在于世上的物品,更是因為藝術(shù)創(chuàng)作這一行為正在通過“遭遇”不斷地拓展著自身的范圍。
二、被綁定的“真實”以及被漠視的主觀性
奧蘇立文的這種“識別”和“遭遇”的劃分很大程度上可以作為衡量一件作品是否能夠被視為當代藝術(shù)作品的標準。這也就意味著,一件作品是否“當代”不光取決于它是否在時間意義上的“當下”被創(chuàng)作出來,更重要的是要看它是否能對觀眾固有的觀點或思維造成“遭遇型”的拓展。正是在這層意義上,照片(再次強調(diào),本文特指未經(jīng)軟件后期處理過的照片)要成為當代藝術(shù)作品似乎就有了一道先天的屏障。而這道屏障,就是照片和被攝之物的不可分割性。正如法國哲學(xué)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明室》(Camera Lucida)一書中所說:“某一張照片永遠不可能和所拍攝的對象相區(qū)別(和照片所再現(xiàn)之物相區(qū)別),或者說,至少不能一下子就和所拍攝的對象區(qū)別開來,或者說這種區(qū)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得出來的……照片屬于那類成層的物品,你無法把兩層?xùn)|西分開而不使物品損壞。”⑧沒有被拍攝之物就沒有照片,至少在被拍攝的那個瞬間,這兩個是無分割的。
這也就意味著,照片的產(chǎn)生方法就是“識別型”的或者說是“再現(xiàn)型”的。除非在后期通過某些圖像處理軟件的二度調(diào)試,最原汁原味的照片無論如何都只是在“再現(xiàn)”世上的某個事物或風(fēng)景而已。我們所處的是一個資訊高速流通的時代,當代人已經(jīng)不再需要通過親身經(jīng)歷來了解某個人、事、物或地方。因此,照片單單通過“再現(xiàn)地球上某個事實”很難對觀眾的觀點或思維進行先破后立的“遭遇型”拓展。英國肯特大學(xué)(University of Kent)的格雷厄姆·克拉克教授(Graham Clarke)在其1997年所著的《照片》(The Photograph)一書中提到,直到20世紀初,攝影究竟“是不是藝術(shù)”仍然是攝影師們爭論的一個主要話題。⑨如今,攝影作為一個藝術(shù)門類的身份是無可爭議的。然而,這種藝術(shù)門類似乎更適合以“識別”的方式鞏固觀眾的已知。比如,某個南方人也許熟讀“北國風(fēng)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卻沒有親自見過北方的雪景,那么,通過一張哈爾濱冬季大雪紛飛的照片,她/他背熟的詩句很可能會更生動和深刻地印在那個人的腦中。
也正因如此,即便是在“前衛(wèi)藝術(shù)”(Avant-Garde)的發(fā)源之地歐洲,攝影作為藝術(shù)學(xué)院中的一個學(xué)科也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被排斥在“當代藝術(shù)”教育的大門之外。直至1982年才由托馬斯·約書亞·庫珀教授(Thomas Joshua Cooper)在蘇格蘭的格拉斯哥藝術(shù)學(xué)院(The Glasgow School of Art)創(chuàng)立了歐洲首個致力于通過攝影來創(chuàng)作當代藝術(shù)作品的“攝影藝術(shù)”專業(yè)(Fine Art Photography)。⑩目前,這所學(xué)校中仍然有兩個攝影專業(yè),一個是隸屬于該校美術(shù)學(xué)院的攝影藝術(shù)專業(yè),而另一個是隸屬于該校設(shè)計學(xué)院。
換言之,即便是在以“前衛(wèi)”為己任的歐洲的藝術(shù)教育界,接納攝影成為一種可以產(chǎn)生“遭遇型”當代藝術(shù)作品的方法也僅僅是最近四十多年的事情而已。而目前在歐洲廣受贊譽的以攝影作為創(chuàng)作手段的當代藝術(shù)家比如烏塔·巴特(Uta Barth)和約翰·斯蒂扎克(John Stezaker)也普遍是通過拍攝后對圖像的二度處理或剪裁拼貼來完成作品的。不經(jīng)過二度處理的話,最原始意義上的“照片”似乎很難擺脫“再現(xiàn)世界”這個將它擋在當代藝術(shù)大門之外的阻礙。而既然是一種只能“再現(xiàn)這個世界”的形式,照片可以是藝術(shù),但只能是“識別型”的傳統(tǒng)藝術(shù),它無法進入通過“遭遇”讓觀眾拓展范圍的當代藝術(shù)的行列。
這種觀點的核心是假定了照片無法擺脫“再現(xiàn)真實”的限制。而確實也有相當一部分藝術(shù)家和學(xué)者將照片和“真實”綁在一起。比如,法國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André Bazin)曾在《攝影圖像的本質(zhì)》(The Ontology of the Photographic Image)一文中表示,雖然繪畫和攝影同樣都是人造圖像,可是由于繪畫作品是由畫家本人通過操弄顏料而完成,它總是籠罩在畫家本人主觀性的陰影之下。相較之下,拍攝照片則更像是制作一具木乃伊。被拍攝的對象就像是一具“尸體”,攝影師透過鏡頭將它保存下來,它從此保持住了那一瞬間的“真實”,不會繼續(xù)腐爛或消逝。德國當代繪畫大師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也曾在他1964到1965年的筆記中寫道:“攝影改變了我們觀看和思考的方法。照片被認為是真實的,而繪畫被認為是人造的。繪制的圖像已不再可信,由于繪畫被視為捏造而成的圖像而非對事實的真實記錄,它‘再現(xiàn)事實’的能力已經(jīng)被徹底凍結(jié)。”
不可否認的是,從圖像的呈現(xiàn)這個角度上看,攝影的“客觀性”是繪畫無法比擬的。正如我們可以單從筆觸這一點上就很清晰地在倫勃朗和哈爾斯的作品之間做出區(qū)分,即便是在攝影誕生之前,也就是繪畫的第一任務(wù)仍然是“再現(xiàn)這個世界”的年代,一個畫家無論在技法上多么純熟也很難在創(chuàng)作中掩飾住自己的主觀性。而攝影則是另一種情況。除非經(jīng)過軟件或其他手段的后期處理,攝影師的主觀意志除了通過對角度和光線等因素進行選擇之外,似乎很難再找到其他切入點來直接影響被拍攝之物的視覺效果。更關(guān)鍵的是,一位畫家即使是在沒有實際的模特、風(fēng)景或靜物作為參照的情況下仍然可以創(chuàng)作出一幅寫實作品,而一位攝影師如果沒有具體的對象則無論如何都無法拍攝一張照片。因此,照片必須從“真實”中來,沒有“真實”就沒有照片。照片也就只能成為“識別型”的藝術(shù)作品。
然而,這是否意味著,照片就離“真實”更近呢?專攻街頭人像攝影的美國攝影師加里·威諾格蘭德(Garry Winogrand)顯然并不這么認為。他曾公開表示,盡管攝影師不可能脫離“事實”進行拍攝,但是當一個人用一個四角邊框?qū)λ?他所見的“事實”進行提取或篩選的時候,她/他也就對所見的“事實”做出了改動。英國波普畫家大衛(wèi)·霍克尼(David Hockney)也曾指出,攝影的問題是:它是一個人用一只眼睛通過一個孔所看到的東西,而這樣的圖像又有幾分“真實”可言呢?這些觀點強調(diào)了攝影師的主觀性在照片產(chǎn)生中發(fā)揮的作用。確實,世界一個最本質(zhì)的“真實”是,無論是人的相貌還是事物的狀態(tài),一切都在不停頓的變動之中。但是,攝影師的主觀性卻可以讓一個嬰孩的笑臉、一棵樹投下的影子,或是云和山的某種轉(zhuǎn)瞬即逝的組合長久地保存下來。這是對“不斷改變”這一真實的一種劇烈的改變。只是,不同于具象繪畫中那種標簽一般的主觀性,比如梵高濃烈的色彩和奔放的筆觸,或者倫勃朗和卡拉瓦喬戲劇化的強光影對比,攝影師的主觀性在照片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常常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影響或改變著被攝之物在作品中的視覺呈現(xiàn)。這種影響非常微妙,連巴贊和里希特都沒有對它的重要性給予足夠的承認。
攝影師對通過拍攝這一行為對被攝之物施以的這種“暗度陳倉”式的影響和改變,與前文中分析過的杜尚的作品《泉》有異曲同工之妙。事實上,《泉》在問世之初,并沒有立刻就造成什么影響。甚至,如今收藏于法國國立現(xiàn)代藝術(shù)美術(shù)館的《泉》是1964年的復(fù)制品,因為1917年的原作早已遺失。可以說,杜尚通過《泉》為觀眾帶去的“遭遇型”拓展低調(diào)又微妙,并不像如今一些所謂“當代藝術(shù)作品”那樣大張旗鼓地把“挑釁”或者“反叛”寫在自己的臉上。既然《泉》為觀眾帶來的“遭遇型拓展”是低調(diào)微妙的,那么,同樣以低調(diào)微妙的方式玩弄著主觀和客觀的邊界的照片,是否也能從某個容易被人忽視的角度為觀眾帶來“遭遇型拓展”,從而取得成為“當代藝術(shù)作品”的資格呢?
三、通過觀看挑戰(zhàn)線性時間觀
前文的討論說明了,將照片視為“對現(xiàn)實的再現(xiàn)”是一種片面的理解。照片是在攝影師的主觀性和客觀存在的被攝之物的組合之中產(chǎn)生的。這兩者在照片的產(chǎn)生中缺一不可,而且任何一方都無法被認定是比另外一方更加重要的。因此,要在“對現(xiàn)實的再現(xiàn)”之外重新為照片尋找一個身份,就需要從一個能夠考慮到攝影師主觀性的新角度出發(fā)。正是在這一點上,德勒茲和加塔利所創(chuàng)立的“塊莖”哲學(xué)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新思路。這種哲學(xué)概念建立于德勒茲和加塔利在1972到1980年間合作的“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研究項目(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塊莖”原指的是一種植物組織,比如生姜和土豆。德勒茲和加塔利用這種植物組織來代指一種哲學(xué)概念,或者說是看待事物的一種角度和方法。以這種角度看來,一切事物都是以一種多重且不可預(yù)知的方式聯(lián)系在一起。世界因此也就是這些異質(zhì)的事物所聯(lián)結(jié)而成的巨大的、平面的,且無中心的拼接物。這種哲學(xué)超越統(tǒng)治西方思維上千年的以因果關(guān)系、等級體系、二元對立結(jié)構(gòu)如男/女、我們/他們?yōu)樘卣鞯臉錉罱Y(jié)構(gòu)思維。它將一切都置于一種不斷變化的聯(lián)系之中,一切的身份和存在因此都是暫時的,唯一不變的只有混亂的生成。
從這個角度來說,每一個物體自身都是一個正在發(fā)展變化的事件。也正是在這層意義上,理論物理學(xué)家李·斯莫林(Lee Smolin)指出:“人類是通過感知變化來感知時間的。”從攝影師摁下快門到她/他拿到照片總是需要一定的時間的(即便是拍立得也需要幾秒鐘)。換言之,從“看到想拍攝的東西”到“看到拍攝的照片”,與這張照片相關(guān)的一切都已演變到了一個新的狀態(tài)。攝影師本人看照片時的思緒和情感狀態(tài)與透過鏡頭觀看被拍攝之物時必然不同。而被拍攝的,無論是人是物還是風(fēng)景,在那張照片問世的那一刻,也必然處于一個不同的狀態(tài),無論那種不同是多么的細微。所以,從塊莖哲學(xué)的角度來看,自問世的那一刻起,照片就只是它自己,是攝影師和被攝之物這兩種異質(zhì)的東西結(jié)合而生成的新的存在,而不是某個“事實”的視覺表象,因為世上已不存在照片里記錄下的“本體”或者“真實”。這也就意味著,照片不可能是在“再現(xiàn)”,不可能是在re-present,因為它背后的那個“真實的本體”早已不在。因此,與認定“照片等于真實”相似,認為“照片作為一種藝術(shù)品只能為觀眾提供‘識別型’的體驗”同樣是片面的。
那么,觀眾在看到一張照片時看到的是什么呢?一個簡單的答案是,被攝之物的某個存在過的狀態(tài)。但是,正如威諾格蘭德所說,當一個人用一個四角邊框?qū)λ?他所見的“事實”進行提取或篩選的時候,他也就對所見的“事實”做出了改動。拍攝這種行為是將鏡頭對準的對象從一個廣大的語境中提取出來。鏡頭確實誠實地記錄下了被攝之物那一瞬間的某種狀態(tài)。然而,通過被拍攝,這個被記錄下來的狀態(tài)也就從某個事件的一部分轉(zhuǎn)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完整個體。比如,在某位攝影師的主觀選擇之下,公園里某片毫不起眼的落葉也許會變成一張照片中絕對的中心。那么相應(yīng)的,在觀看這張照片時,觀眾所面對的也就不是那個公園,而僅僅是一片落葉。更重要的是,由于人的知識結(jié)構(gòu)和情緒狀態(tài)也是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即便面對的是同一張照片,觀看者的每一次觀看體驗所產(chǎn)生的情緒體驗和各種想法也一定是不同的。換言之,觀看者也許會認為她/他在還原照片中的那個場景,可是這卻很可能只是一個錯覺。盡管照片是從過去的事實中產(chǎn)生的,觀看者卻無法預(yù)知她/他觀看的體驗。即便是當某個人觀看她/他自己拍攝的作品,她/他能得出怎樣的觀看體驗仍然是不可預(yù)知的,因為她/他在觀看之時的狀態(tài)已經(jīng)與拍攝之時不同。
前文提到,物理學(xué)家斯莫林認為,對人類而言,時間是以改變的形式被我們感知的。即使某人呆坐在房間里什么都不干,她/他也能從窗外陽光的變化中感到時間正在流逝。因此,我們習(xí)慣了以“過去、現(xiàn)在、未來”的結(jié)構(gòu)來看待時間,仿佛時間是一條不可逆之線。然而,在觀看照片的那個“現(xiàn)在”,被記錄下來的某個過去的碎片(照片)卻能刺激觀看者的感情和思緒進入一個無法預(yù)知的新狀態(tài)(未來)。換言之,過去、現(xiàn)在、未來在觀看一張照片時融合了。“觀看照片”這一行為挑戰(zhàn)了我們所習(xí)慣的線性時間觀。“時間”在這一行為之中從一條不可逆之線變成了一個混沌的整體。而這種混沌的時間觀又可能會為觀看者的思維或行為提供一些不可預(yù)知的可能性,比如逆線性時間的行為[例如,一張他人拍攝的照片也許會激起觀看者的懷舊情緒,使她/他接下來的一段生活(未來)的中心是重復(fù)過去的某段經(jīng)歷],或者在某幾個跨時間、跨文化的地區(qū)間做出聯(lián)結(jié)(比如,一張20世紀拍攝于某北方城市的照片也許會感動一位生長在南方的青年人,而這次觀看經(jīng)歷,也就使得這位觀看者通過重塑自己在本世紀的南方的生活經(jīng)歷,為照片中的北方城市提供一個角度獨特的解讀,兩個不同時代的不同地點也就有了一個獨特的聯(lián)結(jié))。
前文的討論中指出,一件藝術(shù)作品能否被視為“當代作品”,需要考慮它能否為觀眾帶來“遭遇型體驗”。作為一個物體,照片與杜尚在《泉》中所使用的小便池一樣,也已經(jīng)在我們的概念中有了一個相對確定的身份(照片就是“再現(xiàn)事實”的圖像,小便池就是承載排泄物的臟東西)。同樣的,與杜尚的小便池一樣,照片也可以通過質(zhì)疑這種確定身份來取得為觀眾提供“遭遇型體驗”的潛力。只要我們一天堅持著“藝術(shù)一定是高尚的、藝術(shù)一定是美的”這種觀念,諸如前文中提到的安德烈斯·塞拉諾的《尿中基督》和特蕾西·埃敏的《我的床》以及皮耶羅·曼佐尼(Piero Manzoni)的《藝術(shù)家的糞便》(Artist’s Shit)等刻意在創(chuàng)作中使用污穢骯臟之物的當代藝術(shù)作品就不會消失。同樣的道理,只要我們一天堅持認為“時間是一條不可逆轉(zhuǎn)之線”,照片就因其能夠通過觀看將時間轉(zhuǎn)為一團混沌而保留其提供“遭遇”的能力。正如《泉》質(zhì)問它的觀眾:“藝術(shù)一定是高尚的嗎?藝術(shù)一定是美的嗎?”照片同樣在質(zhì)問它的觀眾:“時間一定是一條線嗎?時間一定不可逆嗎?”而正視并回答這些問題正是當代藝術(shù)所追求的“遭遇”的起點。也正因如此,攝影從其誕生之初就具有了后世藝術(shù)家所追求的“當代性”,而作為作品的照片當然也是正當?shù)漠敶囆g(shù)作品。
注釋:
①Clarke,G.The Photograph,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67.
②https://www.list.co.uk/article/65504-preview-of-thomasjoshua-cooper-scattered-waters-sources-streams-rivers/.
③https://www.fotomuseum.ch/en/explore/sill-searching/articles/27000_photography_versus_contemporary_art_whats_next和https://petapixel.com/2017/03/04/photographers-dont-get-modern-art/.
④O’Sullivan,S.Art Encounters Deleuze and Guattari:Thoughts Beyond Representation,Palgrave MacMillan,2006,p.1.
⑤同上。
⑥同上,pp.1-2.
⑦de Duve,T.Kant After Duchamp,The MIT Press,1996,pp.90-91.
⑧Barthes,R.Camera Lucinda: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New York: Hill &Wang,1999,pp.5-6.
⑨同①。
⑩https://www.list.co.uk/article/65504-preview-of-thomasjoshua-cooper-scattered-waters-sources-streams-riv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