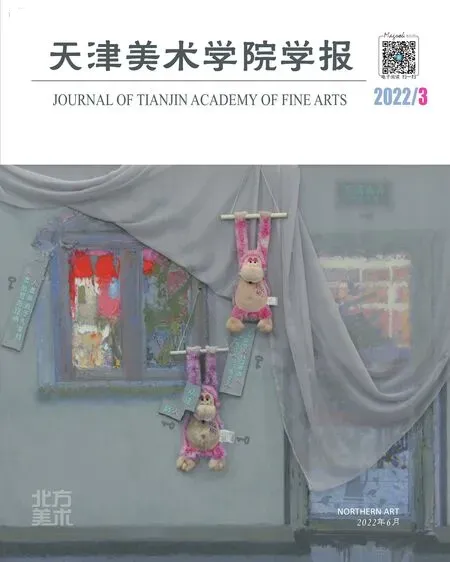一個海外華人藝術家的視覺藝術經驗
——劉曉民的藝術創作
王偉毅
王偉毅:天津美術學院美術館常務副館長
一
2019年底開始的新冠病毒的肆虐,使大多數人處于社交隔離狀態下,原有的生活、工作方式被改變。觀眾被迫“缺席”,使以往熱鬧的藝術界變得沉靜,物——展品與人——觀眾的消失讓所有的人重新認識藝術。對于從事視覺創作與生產的藝術家來說,網絡提供了不斷切換、變幻的場景,這些快速變換的場景傳遞著不斷刷屏的思潮,給藝術家帶來最直觀的感受。分分秒秒被影響的人生態度,或改變與被改變的視覺經驗,無疑影響著藝術家的思考與創作方式。當然,這也許是絕佳的反觀自身(藝術和藝術家)的良機——閉門謝客的獨處為藝術家提供了反思自我的機會。這種反思涉及對藝術的認識和理解,以及藝術家對自身的認識。我們如何認識自己?我們如何面對自身的視覺經驗?我們如何理解藝術?我們如何應對當下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
二
旅居漢堡的華人藝術家劉曉民,本科畢業后到漢堡美術學院學習自由藝術。畢業后定居漢堡,去國三十余年。20世紀90年代的漢堡美術學院比今天的它顯得“前衛”,“觀念藝術”先驅克索斯(Joseph Kosuth)、行為藝術家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都在此任教,架上藝術被學生視為敝屣,成為“落后”的代名詞。今天在國際藝術界風頭正健的日本裔藝術家鹽田千春和德國藝術家梅森(Jonathan Meese)90年代初在此學習藝術,曾經為劉曉民的同窗。在國內受過正統學院油畫訓練的劉曉民面對這樣的局面,如何看待以前的經驗,不是簡單的繪畫技術問題,而是對藝術本質的認識受到了沖擊。20世紀80年代在國內成長起來的藝術學子,資訊比較封閉,獲得域外藝術信息的途徑無非是學院圖書館外文閱覽室中翻爛了的英文版《藝術新聞》《美國藝術》,“對前衛藝術”的認識大多止于抽象表現主義或波普藝術,在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記得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人H.H.阿納森(H.H.Arnason)的《西方現代藝術史》中文版在國內面世給藝術學子在觀念上帶來的強烈沖擊。
任教于漢堡美術學院的克索斯認為:“實際的藝術品不是后來配上框子掛在墻上的東西,而是藝術家在創作時所從事的活動。”“一件物體用藝術眼光看待時才算是藝術。”①在這樣的語境下,初入漢堡美術學院學習的劉曉民不知做何感受,是認識新藝術的“啟示”,還是“頓悟”?是澆滅了對架上繪畫的“熱情”,還是發現了架上繪畫在當代藝術語境下新的可能?不管怎樣,對于劉曉民來講,漢堡美術學院的經歷積累了與以往不同的理解當代藝術的視覺經驗。曾經的同窗、藝術家梅森談到所受的學院教育時講過:“自由是無法被教授的。藝術是對技能的徹底超越。藝術也是無法被教授的,人們不可能通過學習掌握藝術創作的秘密。誰要以為經過思考就能找到藝術創作的方法,那么他就是一個庸才,這種人最多也只能在藝術問題上指手畫腳,卻沒有任何實際貢獻……而對藝術來說,學院不啻為囚籠,學生們在這里被迫接受洗腦,他們就像流水線上的產品,被訓練成整齊劃一的列兵,成為藝術的盲從者。”②處在這樣的環境下,敏感的劉曉民不會游離在外,他迅速、主動地投入其間,在20世紀90年代,創作了大量的作品(圖1、圖2)。這些作品涉及架上繪畫、影像和行為藝術。現在看20世紀90年代劉曉民的作品,絕非是視覺沖擊后的簡單“反響”,或是媒介和形式的變化,德國藝術中強烈的情感表達、對社會問題的關注深刻地影響了他的創作。
在德國藝術中,源自中世紀宗教藝術的德國表現主義繪畫傳統從來就沒有“離開”。當然,表現主義也絕非是筆觸飛動的外在形式,表現主義不是一種風格。“但決不是說,表現主義沒有共同的基礎。表現主義藝術家將他們的創作基礎建立在大量的個人情感表達上,而不是拘泥于千篇一律的風格設計上。”③德國藝術史學者保爾·福格特(Paul Vogt)認為:“藝術家們通過個人表達所展現的個性比共同愿望所表現的特征要鮮明得多,更具代表性。”④這種不拘外在形式、風格,更重情感表達的藝術至今仍然影響著劉曉民的藝術創作。
劉曉民1992年創作的一組作品(圖3),以中國楊柳青年畫中的形象為畫面主題,加上象征意義的流行文化符號(電視機、耐克運動鞋、萬寶路香煙、麥當勞漢堡、電子琴)后重新組合,傳達了他到歐洲后所面臨的文化沖擊,映射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中國重新融入世界,經濟、文化所面臨的處境。劉曉民將個人經歷、國家現狀、國際環境,以及對新的國際秩序的態度投射于作品之上。在此,可以視德國表現主義藝術為劉曉民藝術創作的一個重要基礎。藝術是困苦危難時期或是經歷內心煎熬時的反映——藝術家的境況,與自然、社會的關系,以及變化不定的內心世界,愛恨情仇的激情與憂郁。因此,“內容”從來就沒有離開他的藝術創作,他的經歷和對藝術的判斷不會完全地陷入純粹的藝術形式“游戲”中去,他要用藝術表達“意義”,他以自己的藝術實踐說明:“一件藝術品從根本上來說是藝術家的思想,而不是有形的實物——繪畫或雕塑”⑤。
20世紀90年代,劉曉民從事架上藝術創作的同時,受在漢堡美術學院任教的行為藝術家阿布拉莫維奇和“激浪”(Fluxus)藝術家亨寧·克里斯汀森(Henning Christiansen)的影響,也從事過行為藝術創作(圖4、圖5)。他從事行為藝術的時間很短,作品也不多,但是行為藝術開放的思維方式對他的藝術創作有深刻的影響。1994年與漢堡美術學院同窗共同實施的行為藝術作品《我愛博伊斯,博伊斯愛我》是對“激浪”藝術家博伊斯(Joseph Beuys)的行為藝術作品《我愛美國,美國愛我》的回應。在《我愛美國,美國愛我》這件作品中,博伊斯使用了對其生命有重要意義的毛氈、《華爾街日報》和美洲傳統習俗中認為的神圣動物狼,試驗人與動物之間的溝通和交融,這件作品的另一個含義是對現代化生活價值、消費社會中人的物質化墮落的批判。當然《我愛博伊斯,博伊斯愛我》絕不是對博伊斯作品的簡單回應,面對“總是喜歡做一個意見的引導者、教育家、巫師去干擾、引導別人”(朱青生語)的博伊斯,后來者往往會陷入另一種博伊斯設定的定式中,博伊斯所倡導的“人人都是藝術家”和將一切賦予意義成為新的悖論。劉曉民等人的《我愛博伊斯,博伊斯愛我》是對這種新定式的反諷。將《我愛美國,美國愛我》的意義消解,在這個過程中完成新的“社會雕塑”⑥。
消解意義本身也是傳達了意義,通過作品消解了“經典”的意義,完成了一次自我的覺醒。
表現主義、激浪派、新表現主義等德國藝術有一條貫穿的線索,在各種概念的否定中、在形式媒介的變化中力求傳達意義。成年后旅居海外的劉曉民有著其難以抹去的“詩以言志,文以載道”的中國文化背景,兩者的結合,使其旅德三十年來的藝術創作呈現出“混雜”的面貌與復雜的意義。
三
2019年突發的疫情改變了我們既往的生活方式與生產方式,世界瞬息萬變、日夜更迭的場景被賦予全新的效能和使命,也提供了構造生活的另一種思路與格局。悲觀者認為,因疫情引起的隔離狀態結束后,一些正常狀態下“不正常”的現象會變得“正常”起來。譬如:關閉學校上網課,一勞永逸地中止一切政治和文化議題的聚會討論,只用數字訊息交流,用智能設備取代人際的一切接觸……今天我們不是在慢慢地接受這個現實嗎?疫情之下,如同“這個世界會好嗎”一樣,這個世界還需要藝術嗎,或者是這個世界需要怎樣的藝術等一系列有關藝術的疑問也浮現出來。
當這些有關藝術的疑問擺在旅居海外的劉曉民面前,獨特的生活、藝術經歷讓其藝術創作呈現出更為獨特的面貌。宣紙水墨繪畫材料被重新拾起,作品所反映的內容由網絡打開的視野獲得,思維方式變得開闊。無辜的白兔被戴著面具的持槍者槍殺(圖6、圖7),如手無寸鐵的普通百姓面對兇險的恐怖分子,持槍者如游戲般射殺小白兔;碧波蕩漾的一池清水,孤獨的游泳人在水中獲得一時的自由,卻似漂在扁舟之上(圖8);當他與眾人一起“同舟共濟”時卻落入了怪獸的口中,不單是失去了自由,生命也變得岌岌可危(圖9)。一個人只能在“船上的水面”這個矛盾的場所中游泳,船似乎航行于宇宙之中,人如若離開這個水面將會墜入虛空中,載舟的水面成為吞噬舟船的“黑洞”,猶如未知的宇宙。沒有人會告訴你應該怎么“游泳”,只有潛在的危險,對每個“游泳者”來說,不管是水面還是深淵,只有自己面對……當人和社會脫離既往的規律工作、生活、運轉時,以往可遵循的規律變得不可信,一切都可能失控(圖10),如噩夢一般墜入大腦——這個產生思想的“場所”所形成的深淵(圖11)。自由意志與控制,控制欲與人與生俱來的反控制,以及博伊斯的藝術觀念對后繼者的影響,個人自覺的喪失,被別人控制……劉曉民2020年創作的水墨畫延續了1994年的行為藝術《我愛博伊斯,博伊斯愛我》傳達的藝術觀念。當然,他也要隨時警惕自己,不要使自己落入自我設定的“深淵“,大腦可以產生自由的思想,也會成為自由的牢籠。要隨時突破自己,更要突破理性的控制。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一百余年前,前清官員梁濟自沉前問自己的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樂觀主義者的兒子給了父親積極的回答。但是,樂觀主義者絕非犬儒,積極地面對生活不是佯裝智慧的瀟灑。應如梁漱溟那樣的樂觀主義者一樣,用一生去影響、改造社會和世界。知足常樂的生活態度影響了中國人的價值判斷。在豬的世界中有食物就是快樂、快活,是生活的一切,笑變成了信仰,變成了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江湖”。在劉曉民的作品《笑是一種信仰(江湖)》(圖12)、《笑是一種進化》(圖13)中,窗格似乎是一種象征,墻上掛著中國山水畫,這些符號點綴在快活的、享樂的豬的周圍,一派祥和……作品中對犬儒主義價值觀的批判,對享樂主義的厭惡,繼承了德國藝術中對現實批判、關懷的特質,這正是我們藝術傳統中缺少并應補足的養分。當我們將無聊看作祥和,將懶散看作天人和諧,我們如何面對這個飛速發展變化的世界;當將“思考者”看作異類,當我們不再思考如何實現對自我的超越,如此,我們的“這個世界將不會好”……
“細讀”劉曉民2020年創作的這批水墨畫,可以發現,年齡的增長,在他的藝術創作上呈現為直接和力量,不需用太多復雜的媒介,簡單的宣紙、水墨完全可以傳達出要表達的意義。如同博伊斯在作品中使用毛氈、油脂一樣,⑦對媒介自身的反思可以提出更為深刻的問題——難道我們的繪畫材料僅僅滿足“聊寫胸中逸氣”嗎?
四
以“人人都是藝術家”的理念為支撐,博伊斯在20世紀60年代曾經提出建立一所“自由大學”,在這所大學中,他要爭取的是“以其他方式結業與國家考試結業具有同等效力”,博伊斯從根本上顛覆了藝術學院。⑧如果不拘泥于以上事件本身,則會啟發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必須要做當代藝術嗎?我們必須遵循某種媒介或理念的限制嗎?乃至疑問:我們需要藝術嗎?
不管有無答案,反思歷史、反思自己不應停止。當我們面對這個世界時應有自己的態度。劉曉民的藝術創作正走在這樣反思的路上……反思的目的抑或結果應使一切包括人自身變得更加有意義。
一切人的問題,只是塑造的問題。難道藝術不是自我塑造嗎?
注釋:
①[美]H.H.阿納森:《西方現代藝術史》,鄒德儂、巴竹師、劉珽譯,沈玉麟校,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第699頁。
②[德]彼得·施內曼:《學會像個未受教育的孩子:作為標簽設定和身份建構的美術教育機構》,載朱青生主編《美術學院的歷史與問題》,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98—99頁。
③[德]保爾·福格特:《20世紀德國藝術》,劉玉民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頁。
④同上。
⑤同①,第697頁。
⑥博伊斯的“社會雕塑”藝術觀念是反傳統藝術觀念的,這種“反”和杜尚的“反藝術概念”并不一樣,杜尚的“反藝術概念”是美術史意義上的,而其本身就是西方傳統藝術概念上的一環。博伊斯所謂的“反”,恰恰與杜尚的“反藝術概念”相反,是反對因襲至今的所有藝術概念,他的這一觀念顯然已超出藝術史,面向整個社會,進入更高的境界。
⑦油脂和毛氈是博伊斯在藝術創作上經常使用的物質。研究者認為這與他“二戰”后期在納粹空軍擔任飛行員時的經歷有關。在一次飛行中,博伊斯的戰機被擊落,韃靼人將他救起,為了保暖,在他的身上涂滿油脂并為他裹上毛氈。當然,也有論者認為,博伊斯不是隨便以油脂、毛氈作為作品的材料,而是想借此說明其理論,即“總體化的藝術觀念”(totalisierten Kunstbegriff)。在博伊斯看來,“一切人的問題,只是塑造的問題”,在此又回到了“社會雕塑”這個概念中。
⑧1961年,博伊斯受聘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在教學中博伊斯提出建立一所“自由大學”,其辦學理念為:是否參加并通過國家考試由學生自己決定,并且無限放寬入學考試。這與其“人人都是藝術家”的藝術主張不無關系,但是卻成為一個引起社會關注的“事件”。1972年,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拒絕為五十多名博伊斯的學生注冊,博伊斯帶領學生占領教務處,使這所有兩百年歷史的藝術學院被迫關閉幾天……最后博伊斯不得不在警察的“夾道歡送”之下離開學院。幾十年后的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博伊斯的精神仍在影響著學院的辦學理念,在招生手冊上印有“藝術是不可教授的”(Kunst ist Nicht Lehrbar),這句話來自20世紀初包豪斯的創辦者格羅皮烏斯,但是卻洋溢著博伊斯所提倡的對精神自由的追求和對理想主義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