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孩子一樣畫畫”
——基于兒童本位論的跨界滲透與兒童模式畫的興起
李蔚 | 溫州大學教育學院
“兒童模式畫”指:一種不承襲學院模式,出自畫家本能,類似于兒童畫的風格模式。“兒童模式”既不是“兒童形象”,也不是“兒童題材”。真正的從兒童之眼看世界,這種內部視角的創作觀的出現是到了晚近(19世紀中葉)才有的現象,并在19世紀末的藝術史取得自身的位置。沿著曲折發展的道路,“兒童模式”的藝術風格逐漸形成一套不容小覷的系統。本文討論兒童本位論的跨界滲透與兒童模式畫的興起,及其背后觀念交替、形成原因與合法化歷程。

一、兒童本位論的出現和對文藝作品的滲入
1.兒童本位論的空缺與顯現
生活在羅馬的古希臘學者普魯塔克在《論兒童教育》中提出,讓兒童接受德育、智育和體育,以便兒童將來成長為羅馬的優秀公民。這是一種“社會本位論”的兒童觀。可以說,在16世紀以前的歐洲大陸,“兒童”都只是一個附屬性概念,即被視為家長的依附品或成年之前的過渡階段,其本身并不被視為具有獨立性。反映在藝術史中,兒童的形象在造型藝術或文學故事中都是缺失的,在11世紀甚至都完全沒有出現兒童的形象,直至12世紀前后的中世紀藝術,其中還未涉及兒童與其專屬的童裝或飾品。直到13世紀才有了對嬰兒的關注。13世紀出現了天使、圣嬰、裸嬰的少兒形象:少年的天使多見于意大利14至15世紀安吉利科(Fra Angelico, 1395—1455)、波提切利(Botticelli,1445—1510)、基爾蘭達約(Ghirlandajo, 1449—1494)等人所畫的天使;圣嬰,即童年耶穌,依托于圣經故事,與圣母的母愛聯系在一起;裸嬰多見于哥特藝術時代,通過死者和靈魂的隱喻,將裸體兒童的形象引入造型藝術中,例如被希律王所屠殺的無辜嬰孩和所羅門王為兩位母親爭搶兒子做裁決時的那個死嬰。
13至17世紀,雖然當時的人們還不是十分重視嬰孩的培育,但已經開始意識到兒童的獨立人格。這表現為美術史中出現了越來越多關注兒童的作品——兒童形象不僅僅出現在圣經故事中的“圣母子”和神話中的“丘比特”,還體現在諸多世俗題材中,如出現于16世紀的圖式——“皮托”,17世紀的畫家魯本斯的全家福《魯本斯、妻子海倫富爾曼和他們的兒子》(1639)、委拉斯貴支的《宮娥》(1656)等。《宮娥》可能是西方油畫歷史上最早一幅用兒童(小公主瑪格麗特·特蕾莎)作主角的作品。這一情況在18世紀更為普遍,有格勒茲的《被寵壞的孩子》(1765)、夏爾丹的《午餐前的祈禱》(1740)、莫里索的《搖籃》(1874)等,這一現象直至攝影術被發明出來后才告一段落。
進入18世紀,“童年”和“兒童”的發現成為近代教育與現代教育的標志,兒童本位論隨之在教育學領域崛起。盧梭《愛彌兒》(1762)回應了洛克《教育漫話》(1693),他批判洛克“用成人的標準來要求孩子”的教育觀念。人們扭轉了原來將兒童被視為父母私有財產和家族依附品的觀念,但把兒童看作是成人的雛形的觀點仍占統治地位。兒童本位論往后越來越成為一種主流的觀點,兒童越來越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被重視。教育思想在洛克、盧梭以及泛愛派的推動,以及裴斯泰洛齊、赫爾巴特、福祿貝爾的開拓與深化之下,“兒童年齡分期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兒童所具有的特性和發展潛能也被進一步挖掘。19世紀,市場上涌現出大量的作為兒童教育產品的文藝作品(如兒童文學、兒童繪本),兒童產品的門類被進一步細化。這一情況也對藝術史帶來了深刻影響,主要體現在19世紀下半葉,兒童模式繪畫的集體涌現并走向合法化進程。
2.兒童本位論滲入文學領域與對民眾觀念的開拓
“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應當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其實正如盧梭在《愛彌兒》所寫的,孩子和成人不應該用同一套標準來對待,“童年”有其自身的地位,并非“成年”的附屬品。《愛彌兒》展示出作者在各個階段倡導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并首次將目光關注在“兒童”身上。除了教育學領域中“兒童”概念的先導,兒童模式繪畫的合法化進程還離不開兒童文學對市場的開拓。17世紀的歐洲,“兒童”作為一個獨立概念被人們重視起來,兒童形象可以脫離家庭生活獨立表現。1697年《鵝媽媽的故事》(又稱“貝洛童話”)出版,被認為是歐洲文學史上第一部明確為兒童創作的自覺的兒童文學作品。

午餐前的祈禱 夏爾丹 1740

宮娥 1656 委拉斯貴支 西班牙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
兒童本位論逐漸成為一種主流思潮,并在18世紀逐步滲入文學領域與民眾觀念,結合浪漫主義所強調的內心感受與幻想,由此催生出兒童文學。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浪漫主義文學和幻想文學興起,作家們喜歡歌詠童心。英國藝術家威廉·布萊克的詩集《天真與經驗之歌》(,1794)包含“天真之歌”與“經驗之歌”兩部分:前部分是童趣的;后部分是苦澀的,反映了詩人的思想和創作從孩子般的天真狀態走向成人經驗的艱苦歷程。布萊克將詩歌與插畫結合起來,創造性地發展了圖畫書的藝術形式,德國畫家海因里希·霍夫曼用類似的形式制作了《蓬頭男孩》(Struwwelpeter),這成為現代兒童圖畫書的雛形。繪本后來成為一種專門面向兒童的教育商品。
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在出版商人艾德蒙·埃文斯(Edmund Evans, 1826-1905)的帶領下,英國率先進入兒童文學黃金時代。埃文斯掌握了更先進的色譜木刻印刷術(chromoxylography),可以用低成本的工藝批量制作出精美的圖像書籍,讓兒童圖畫書迅速被大眾市場接納,圖畫書也就成為兒童文學中的一個體裁門類。進入19世紀60年兒童雜志大為流行,作家紛紛開始為兒童寫作。卡洛爾1865年出版的《艾麗絲漫游奇境》、巴利在1911年出版的《彼得·潘》、王爾德在1888年出版的《快樂王子》、吉卜林在1894年出版的《叢林故事》和斯蒂文森在1881至1883年的《金銀島》等,打開了兒童文學的新天地。兒童文學在市場上取得的成功拓展了民眾的觀念:“兒童”的東西不再只是低級趣味的象征。放眼至今,童趣商品的受眾群體的構成并非只有小孩子,大人們也可以作為受眾的一部分。

狂歡節之夜 116.8cm×89.5cm 1885—1886 亨利·盧梭 費城藝術博物館
3.兒童本位論與“稚拙畫派”
兒童本位論的創作觀先被推行于兒童文學領域,而后進入繪畫。在繪畫中,兒童本位論化身為“稚拙畫派”(Na?ve Painting)以及同時代相類似的藝術畫派,代表人物是亨利·盧梭(Henri Rousseau,1844—1910)。他的創作生涯從1871到1910年持續了40個年頭,完整地經歷了“兒童模式”繪畫逐漸被主流輿論接受的道路。在嚴肅的藝術評價體系中,兒童模式繪畫早期是受到輕蔑的,后來的評價雖然一度有所好轉,爭議卻持續不斷。偏見的扭轉要歸功于西涅克、高更、德加、畢加索、畢沙羅等文化名流的大力辯護。他們不約而同地表示,要將發掘創造力的眼光轉向兒童,稱要向兒童學習。畢加索不止一次公開表達,每個孩子都是天生的藝術家。他曾說:“兒童筆下的東西往往令人感到意外……總可以讓我學到一些東西……”20世紀以后,整個社會的觀念都開始重視兒童起來,這導致業界對盧梭與其“稚拙畫派”的評價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人們的看法完全發生了轉變。盧梭與“稚拙畫派”贏得了文化學者的普遍認同,并被載入藝術史序列之中。《西方藝術史》將盧梭列入“后印象派和19世紀后期”章節的陣列,最終冠以“稚拙畫派(Na?ve Painting)”的風格名稱。
遺憾的是,“稚拙畫派”的藝術家們并沒有形成一個綱領明確的團體,因此藝術史學家難以對這批人進行專門的命名,便粗泛地將他們稱為“20世紀早期畫家”或“20世紀民眾畫家”。這個群體不像其他現代主義中那些顯赫的藝術流派具備完整的動宗旨和行動綱領,他們只是一群業余畫家。他們像兒童那樣,以最原始、最樸素的方式去作畫,不以顯豁的姿態公開露面。這批畫家有:塞拉芬(Séraphine Louis,1864—1942)、波希安(André Bauchant, 1873—1958)、路易·維凡(Louis Vivin, 1861—1936)、凱米爾·邦波瓦(Camille Bombois,1883—1970)、多明尼克·培洛涅(Dominique Peyronnet, 1872—1943)、伊 凡·拉 布 辛(Ivan Rabuzin, 1921—2008)、伊凡·吉納里克(Ivan Generalic, 1914—1992)、阿德夫·德特利希(Adolph Dietrich,1877—1926)、愛德華·希克斯(Edward Hicks,1780—1849)等等。盡管他們現在還無法被歸于最著名的藝術家行列,但是他們在歷史中留下來的別具一格的審美形態已成為一項開拓性的事業。
二、“像孩子一樣畫畫”:20世紀的繪畫新視角
1.“童真”作為一種藝術價值
亨利·盧梭的經歷可以被看作是繪畫“兒童模式”合法化道路的縮影。盧梭多次被官方沙龍拒絕之后,命運將他推入獨立藝術家協會沙龍展(Salon des Indépendants)。1885年,盧 梭 的 作 品 第一次公開參加官方性質的香·埃呂西沙龍(Salon des Champs-Elyee'es)。在展覽會上,盧梭的兩幅作品(已遺失)遭到了侮辱性的對待。盧梭完全拋開了學院繪畫的固定程式,畫面中的事物都來自于他的主觀印象,元素搭配間的隨意性產生了另類于學院派的情趣。大多數情況,觀眾會嘲笑畫家表現手法的笨拙、業余。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盧梭并沒有受到當時文化名流的嘲笑。雷東、雷諾阿、勞特累克、羅丹,還有評論家古爾蒙(Remy de Gourmont, 1858—1915),他們都將盧梭作品中的“真摯”和“淳樸”看作是難能可貴的優點。
印象派畫家西涅克(Paul Signac, 1863—1935)推薦盧梭參加1886年的獨立藝術家協會(Societe des Artistes Indépendants)舉辦的“獨立美展”,屆時亮相的《狂歡節之夜》被推為稚拙畫派的奠基之作。1908 年,年輕的畢加索在街頭偶然看見盧梭的畫作,被深深吸引,便買下了他的畫作。接著,畢加索在自己位于蒙馬特浣衣舫的工作室舉辦了盧梭晚宴(Le Banquet Rousseau),這場聚會被視作20世紀藝術界關鍵事件之一。這次晚宴大約有30多位巴黎的各界精英出席,其中著名的詩人兼藝評人阿波利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1918),盛贊盧梭的畫有種難得的品質——“純真”(Na?ve),并用贊美的文章積極地宣傳,“稚拙畫派”的說法由此傳播開來。
美國美術史學者喬納森·費恩伯格(Jonathan Fineberg)表示:“這種對兒童畫的藝術審美隨著藝術領域內現代主義的擴張在20世紀,這些現代派的藝術家甚至搜集和研究兒童的繪畫作品來激發自己的創作靈感……”舉例而言,抽象主義大師康定斯基想要建立基于心理感受的色彩學(不僅限于視覺,還包括聽覺和精神上的色彩體系),他曾指出孩子在感知上的敏銳:“世界給一個孩子帶來的感受就是這樣,對他來說,任何一個對象都是新鮮的。”另外一位現代派大師馬蒂斯(Henri Matisse, 1869—1954)在1954年《藝術新聞與評論》上發表了《用兒童的眼光看生活》,認為藝術家要像第一眼看事物時的眼光那樣去重新感受每一個事物;應該像孩子那樣去看待生活,否則,他就不可能用獨創的方式去表現自我。其實,馬蒂斯“用兒童的眼光看生活”的這一觀點在20世紀中葉算不上新鮮的提法,在世界范圍內就有一批藝術家不約而同地開始用兒童畫的模式來創作。
美國畫家米爾頓·艾弗里(Milton Avery,1885—1965)簡化處理的藝術風格深受馬蒂斯晚年觀念的影響。他的繪畫趨向平面,構圖十分簡潔,物體的描繪基本上由輪廓和色彩決定。艾弗里的繪畫中的形體稱不上描繪得精確,卻非常具有抒情特質,就像兒童天真爛漫的表達。西班牙畫家胡安·米羅(Joan Miró,1893—1983)天生具有兒童般敏銳的觀察能力。他深受兒童繪畫的影響,并認為“兒童時期的天賦”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其作品風格與兒童畫相似,常用明亮、鮮艷的顏色來表達他對童年生活的追憶。他畫畫不強調構圖意識,所有的物體似乎都是隨意擺放,造型上也看不到專業繪畫中的透視,只用一系列兒童般稚拙的幾何圖形構成畫面。巴黎畫派代表人物馬克·夏加爾(Marc Chagall,1887—1985)作品童真且夢幻,用兒童畫的語言形式將自己過往的經歷夢幻化。劉易斯教授稱:“夏加爾的視覺圖像寶庫永遠不會離開他童年的風景,那里有積雪的街道、木屋和無處不在的小提琴手……童年場景的記憶在一個人的腦海中不可磨滅,并賦予它們如此強烈的情感負擔,只有通過不懈地重復表現那些相同的神秘符號和表意文字,才能將其隱晦地表達出來……”米爾頓·艾弗里、胡安·米羅、夏加爾都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嶄露頭角的一批畫家。與其說是美術史中涌現出一批兒童模式畫的藝術家,不如說是“童真”作為一種藝術價值被普遍認同和接受。這種盛景不是一蹴而就,也是由多種因素構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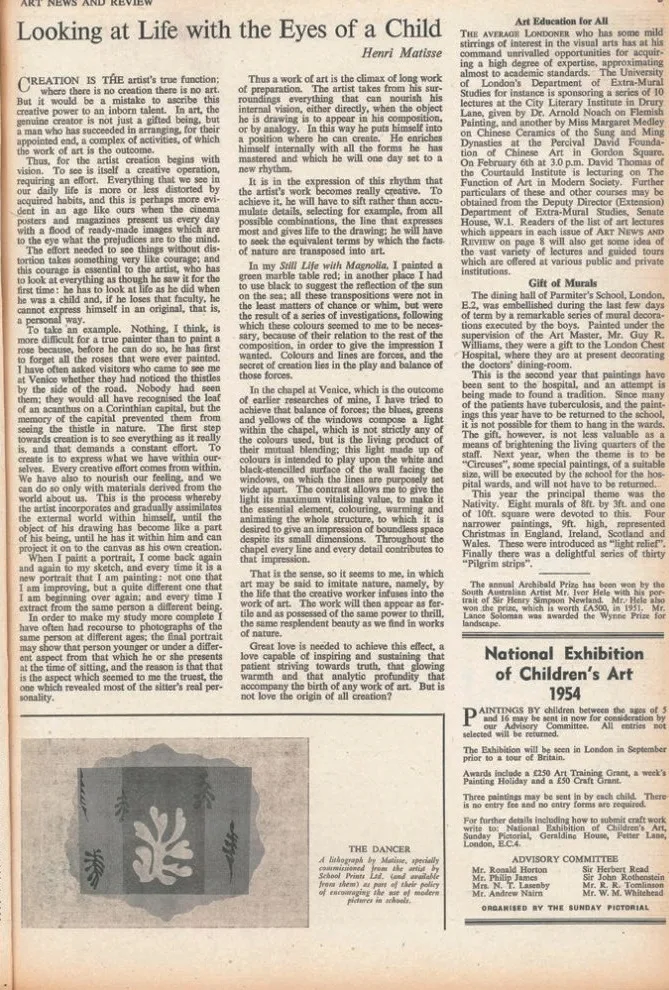
1954年2月《藝術新聞與評論》亨利·馬蒂斯(Henri Matisse) 《用兒童的眼光看生活》
2. 兒童模式畫合法化的多重因素
(1)“兒童”概念深入人心,“童真”被視作一種美學價值
1632年,教育學家夸美紐斯出版《母育學校》,開篇提到“兒童是無價之寶——上帝的靈魂”《母育學校》被譽為西方教育史上第一部學前教育專著,“兒童”概念在教育學當中被強調出來,但仍未擺脫強烈的宗教意識形態。進入18世紀啟蒙運動,盧梭作為一名反基督教斗士,反對基督教壓抑兒童的“原罪論”,極力主張自然教育和兒童天性的釋放。盧梭指出:“兒童是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如果想用我們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們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簡直是最愚蠢的事情……”。他認為用成人的要求和理性的方式來教育孩子是錯誤的觀念。如果我們是站在兒童的視角上,則應該對其施行感性教育。這種主張是基于兒童的個人愛好和興趣,強調兒童自身在探索中習得經驗,而非通過成年人的經驗進行灌輸教育。再到19世紀,蒙臺梭利的《童年的秘密》,作者細致地觀察出兒童在智力、秩序感、節奏感、觀察力等方面的發育特征。蒙臺梭利稱:“童年構成了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她再次強調了童年在人生成長階段的重要意義。從17世紀到19世紀,“兒童”概念逐步為大眾接受,人們對兒童的態度從最初的忽視到現在的倍加呵護,可謂發生了翻轉式的變化。瑞典作家愛倫·凱(Ellen Key, 1849—1926)曾在1909年出版《兒童的世紀》,此書名蘊涵了作者對新世紀教育的期待——20世紀成為“兒童的世紀”——朝著兒童中心主義的新教育運動發展。
比較起來,中國在明代雖有思想家李贄提出“童心說”,但從整體上看,中國仍未構建起系統性的“兒童本位論”。西方隨著17世紀教育思潮的遞變,西方民間兒童文學被納入學術視野,便出現了系統性的兒童文學觀念。“兒童”概念越來越深入人心,這一情況表現為19世紀蓬勃發展的兒童文學,各種專門面向兒童的服飾商品也在市場上取得了良好反響。相應地,19世紀末的藝術史,以盧梭為代表“稚拙畫派”便應時而生。稚拙畫派能夠取得成功,不僅源于盧梭及其身后那批業余畫家們的努力,深層次上,更是源于“童真”作為一種藝術價值在人們心中獲得了認可。人們發現,古典藝術固然具備一些美好的品質(其中的嚴謹性、復雜性、技巧性、寓言性),但這些品質的反面,例如現代藝術中的可愛、天真、簡單、直率……這些品質也并不遜于古典審美的內涵要求,它們甚至在19世紀觀念史的轉變中被重新認可為藝術創作中最可貴的品質。
(2) “感性”“直觀”“直覺”等概念的地位提升
啟蒙時代哲學強調“理性”,但理性不是人類意識的全部。現代哲學認識到這一點,表現為一種對抗古典哲學的“反理性”運動。哲學家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在20世紀初對現代性做了一個著名的判斷:本能沖動反邏各斯。另外,由克爾凱郭爾、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爾到福柯、德里達等人的思想鏈接成新的一條“解釋學譜系”,正日益顯示出對傳統形而上學思想制度的強解構取向。他們所解構的便是昔日對人們矯枉過正的理性哲學。哲學家胡塞爾1913年起陸續出版的《純粹現象學與現象學哲學的觀念》是總結現象學基本觀點的系統性著作。他提出,對意識整體結構層次或奠基順序的把握可以大致分為五步,其中感知構成最底層的具有意向能力的意識行為,并稱直觀概念是現象學“一切原則的原則”,而這種“本質”與“直觀”的非對立化設定就是現象學對德國古典哲學最大的挑戰。現象學采用“懸置”(epoche)的方法,即讓主體隔絕于任何關于時空事實性存在的判斷,也不以任何命題作為判斷的依據。“懸置”就是舍棄先入為主的成見,排除各種既定的文化審美形態的規定,排除約定俗成的技術延承,留下活生生的現場感知。放在繪畫上就是讓觀察之眼回到原始的目光,拋卻空間透視法、人體解剖學等場外的知識,這就呈現為兒童畫的形態。斯坦利·霍爾(Granville Stanley Hall, 1844—1924)從1890至1905年 期間的研究表明,兒童所經歷的一系列發展階段與從野蠻到文明的人類進化所經歷的階段是一致的,進而推斷兒童藝術與原始部落藝術相類似。可以說,兒童畫就是采用原始人的觀看模式,即使用“懸置”(epoche)的眼光和方法。
另外對抗理性的學說還有20世紀初柏格森的“直覺論”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論”等,他們提出的“直覺”和“前意識”“潛意識”是更隱蔽的反映感性的一種意識形態。柏格森之于未來主義,精神分析論之于超現實主義,這些觀念深刻地影響了現代藝術的發展。兒童模式畫的出現也應該被歸為這次運動的案例之一。未來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因為有專人撰文“運動宣言”(《未來主義宣言》和《超現實主義宣言》)和“運動紀事”,整個過程中的一系列事件得以被后人梳理、記載和傳承。而稚拙畫派由于缺乏專業人士的運作,很少有遺留下來的論述表明它們藝術與觀念之間確切的聯系,但這并不能說明稚拙畫派沒有受到20世紀新觀念的啟發。
無論是現象學的“懸置”“本質直觀”,還是柏格森的“直覺”,抑或弗洛伊德的“前意識”“潛意識”,現代哲學將“感性”“直觀”“直覺”這種曾經在古典哲學處于低等地位的概念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實際上,幼孩在創作藝術時,他們就是沒有工具理性的,他們對色塊節奏、線條韻律、肌理變化這些畫面的形式語言是沒有儲備的,也是沒有興趣的。因此,他們更關注創作行為的主題內容,而非形式、風格。很多兒童在早期便開始無意識創作。這便表明,兒童無需等到后天知識的習得,就能自己發動創作行為。野獸派藝術家馬蒂斯曾倡議藝術家們向兒童學習,他說:“希望不帶偏見地觀察事物……像自己是孩子時那樣去看生活……”。馬蒂斯所欣賞的就是兒童那種永遠保持好奇,永遠保持敏感的狀態。倘若藝術家缺失了兒童這種看待世界的眼光,那么他就不可能用獨創的方式去表現自我。觀念史進入20世紀,現代美學范式跟著轉變——從客觀認識論的美學轉向對主體心理感受的描述與研究。作畫邏輯從注重解剖學、透視學,轉向主觀感受上的心理學。兒童模式畫也伴隨著這次觀念的遞變步入合法化進程。
(3)藝術史中學院派消解,現代藝術多元化發展
1863年的落選者沙龍(Salon des Refusés)是后起之秀對當時學院派主導的官方藝術審美形態的一次對抗。最終,印象派的年青人們占得上風,這場運動消解了當時由學院派掌舵的話語權,為之后的后印象派、現代主義的發展騰出空間。印象派運動落幕后的半個世紀,藝術評論的論調完全扭轉了,學院派已然成為“庸俗文化”的代表。現代藝術批評家克萊門特·格林伯格在《前衛與庸俗》中對學院派藝術定義:“一切庸俗藝術都是學院藝術;反之,一切學院藝術都是庸俗藝術。”學院派的審美權威凋零,其他的審美形態便可競相生長,藝術史形成多元發展的格局。
20世紀初,諸類“主義”風起潮涌,稚拙畫派成為現代主義的分支之一,和其他現代主義藝術流派一樣,它們并不關心繪畫的技巧,而關注于各種追求的表現理念。稚拙畫派主張返回原始藝術的風格中去,舍棄作畫技法(工具理性),而追求那種自然天成的表現形式。稚拙畫派的創作原則從根本上挑戰了文藝復興時期以來學院派所形成的諸多基本的慣性定律:
a. 空間上,可以不遵循三維縱深的透視原則;
b. 形體上,可以不遵循人體解剖學規定的比例和結構;
c. 色彩上,可以直接使用高飽和度的顏色涂色而無需調配;
d. 畫面關系上,不需要對背景作出虛化的處理,也不需對主體與配適作出繁簡對比。
可以說,現代藝術運動成為了一場全面清算“古典學統”的藝術運動。這倒不是說,現代要與傳統徹底地決裂,而是現代性要立足于當下,更好地向未來出發。進入20世紀,世界政治格局、經濟生活、科學技術都在發生劇變。種種情況表明,過去的經驗已不能為我們提供一勞永逸的指導。現代藝術家經常呼吁人們要從全新的視角去重新認識世界。他們在兒童身上找到新的靈感,畢加索曾說,他畢生努力追求的,就是要把作品畫成兒童畫般的純真。如此擁護兒童畫的情況在美術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罕見現象。
圖像史中,古代不乏有兒童形象的圖式出現,但歸根結底,這些作品出發的視角是成年人的視角,而非真正從孩子的視角來觀察和表達世界。現代藝術的多元化發展也體現在題材的包容度上,即去魅性(disenchantment)題材的興起。無論是題材上的去魅性,還是手法上的去技巧性,19世紀美術史的顛覆意義是祛除創作上的“繁文縟節”,而轉向稚樸的,直接的,面向內涵本體的表達。由此看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對原始主義的再發現和再評價,便是一種必然的趨向。兒童模式繪畫呈現為這樣一種力量:它不是要在客觀認知上與科技高速發展的現代文明背道而馳,而是要在主觀意愿上用新的眼光探視世界。藝術在沿著人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上,傳統的禁忌被一步步瓦解,兒童模式繪畫或許只是一個對抗禁錮的道德標識,但令人無法忽視的是,這股敢于打破陳規的“無知者無畏”的勇氣,正是源于“童真”的力量。
三、現代教育與現代藝術的雙邊交互
“像孩子一樣畫畫”,這句話可能是20世紀以來最廣為流傳的觀點之一。但在此之前,從未聽說過哪個時代的畫家將孩子的行為模式推崇至如此高的地位,這一轉變與近現代兒童地位的提高密不可分。在古代,兒童不被看作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只被視為家庭和家族的隸屬品;到了近代,在學者的呼吁下,兒童的天性得到釋放,人們開始肯定兒童的權利和要求,但把兒童看作是成人的雛形的觀點仍占統治地位;現代的兒童觀普遍認為,兒童應當被視作一個獨立的個體被對待,人們應該了解兒童成長的特性和發展潛能。在近現代教育觀的演進下,人們越來越關注兒童的感受。18到19世紀,兒童本位論與兒童中心主義(Paidocentricism)應運而生。這股思潮很快進入了文藝界,繼而推動了兒童文學和兒童模式畫的興起。彼時的“兒童本位論”不僅成為教育界當中的主流思想,也成為文藝創作的理念之一。用歷史的眼光看,“像孩子一樣畫畫”,并非一句空洞的口號,其背后所隱射的是時代的轉變。
在我國的語境中,關于兒童的話題一直很少被提及。直到20世紀初,在教育界知識分子的呼吁下,“兒童”從此成為一個被人們不斷提及的概念。1912年,蔡元培曾在“臨時教育會議”上提出教育不應存成人之成見,要“立于兒童之地位”,并在《美育實施的方法》(1922)中提出:“兒童滿了六歲,就進小學校……專屬美育的課程,是音樂、圖畫、運動、文學等”。1919年至1921年,杜威來中國作了200多場演講,遍布14個省,他的兒童中心主義深刻地啟迪了當時的教育界。陶行知遵循杜威的兒童中心主義,提出兒童創造教育理論。與其同時,還有周作人“以兒童趣味為本位”(1914),俞子夷“學童之地位”為“學校之中心”(1915),志厚“兒童中心主義”(1914)、 耕辛“兒童本位”(1916)等等。而在藝術教育上,豐子愷1926年于開明出版社出版《子愷漫畫》,取材多是來自兒童,以古詩文意境入畫。“兒童本位論”這時已經深入教育界、兒童文學創作與研究領域了。也是從這時算起,中國才真正出現一批兒童體系的學說和文藝作品,大概已經晚于西方近兩百年。
年幼的孩子在認知和思維上相對簡單,難以接受復雜的事物。他們喜歡畫面中具象的,輪廓線清晰的,色彩區分度大的事物,喜歡明確的故事情節。兒童本位的藝術作品不僅是附屬于兒童審美的存在,其本身也應該被視作具有獨立審美價值的存在,而其中的核心價值——“童真”——也不止是專屬于兒童的審美形態。豐子愷的漫畫造型簡練,帶有詼諧幽默的敘事情節,受孩子喜歡,但漫畫也蘊含哲理,同樣可以得到大人們的喜愛。20世紀現代美術風云際會,其中以稚拙畫派為先導的諸種兒童模式畫的興起,其背后離不開兒童本位論的跨界滲透,離不開“兒童”觀念的確立和發展。“像孩子一樣畫畫”,這句稀松平常的觀點,卻是現代教育與現代藝術雙邊交互的經典體現。
① 皮托(putto):文藝復興藝術中裸體兒童(尤指小天使或丘比特)的畫像,被認為是希臘化時代愛神厄洛斯的復現。
②《愛彌兒》第一卷注重對2歲以前的孩子進行體育教育,幫助兒童自然發展;第二卷認為2-12歲兒童的智力水平尚且處于休眠時期,主張進行感官教育;第三卷12-15歲的少年智力喚醒,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可進入智育教育;第四卷15-20歲青年步入社會,主張德育教育;第五卷20歲以后的男女青年應接受愛情教育。
③ 1845年,他被朋友們說服以匿名方式出版了這本書,名為“有趣的故事和奇幻的圖片,15張精美彩圖,適用于3至6歲的兒童”。這是兒童書中最早使用色譜法的案例之一。在1858年第三次出版將標題更改為“Struwwelpeter”,也是故事中角色的名稱。這本書在整個歐洲深受兒童歡迎。
④ 亨利·馬蒂斯,《用孩子的眼睛看生活》(Looking at Life with the Eyes of a Child),1954年2月6日,《藝術新聞與評論》(Art News and Review ),后改刊名為《藝術評論》(ArtReview)。中文文章收編于《馬蒂斯論藝術》(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馬蒂斯藝術全集》(金城出版社,2013年)等。
⑤ M.J.劉易斯(Michael John Lewis),威廉姆斯學院藝術史專業教授,授課現代建筑和美國藝術,《華爾街日報》的建筑專欄評論家 。
⑥《大教學論》寫道:“基督教的兒童不能像叢林一樣生長,而是需要照料的……”。夸美紐斯. 大教學論[M]. 傅任敢譯. 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9:33。
⑦ 中國唐宋時期,圖像藝術中不乏有佛教阿彌陀佛身邊象征多子多福的孩子;同一時期的西方,以圣子耶穌為代表的幼嬰形象也是“圣母子題材”畫作中的主要人物。文藝復興之后,還有對“愛神丘比特”嬰孩天使形象的開發。這些嬰孩形象在當時之所以能夠入畫,大多是因為宗教神話的賦魅。文藝復興以后人文主義復蘇,嬰孩形象漸漸出現在世俗題材中。
⑧ 1914年,周作人在《玩具研究一》一文中提出了“以兒童趣味為本位,而又求不背于美之標準”。
⑨ 俞子夷1914年回國著手展開“兒童中心”的“關聯課程”,1915年將 “學童之地位如何”列為“現今教育上應急研究之根本問題”之一,他說:“學校內學童之地位若何?曰當為學校之中心也。”
⑩ 1914年,志厚在《兒童研究》等文章中介紹蒙臺梭利的教育思想與方法。
? 1916年,耕辛在《學習法之刷新》中討論了“教師本位與兒童本位”、“教科書本位與兒童本位”及“教授法與學習法”等不同種類的學習法,并對當時的小學教育提出了強烈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