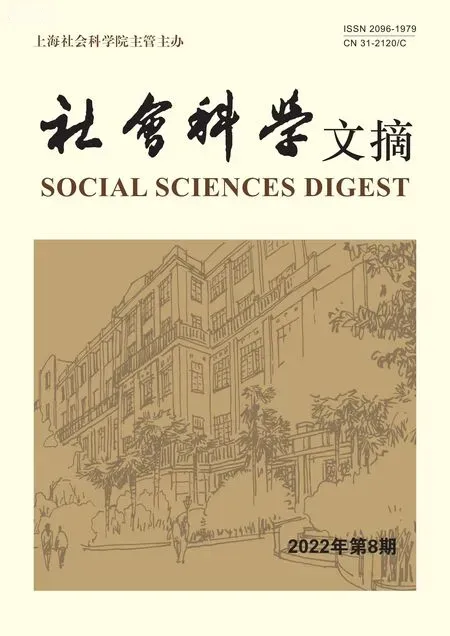界域建構(gòu)中的困境及其反思
——立足于近代華北區(qū)域史研究的考察
文/王先明
改革開放以前,并不存在特定學(xué)科或?qū)W理意義上的華北區(qū)域史,相關(guān)研究多體現(xiàn)為地方史或地方性歷史研究,且主要表現(xiàn)為以抵抗列強(qiáng)侵略和政治運(yùn)動研究為中心的地方史,實際上是研究者配合黨史和革命史等政治史的需要開展的學(xué)術(shù)活動。20世紀(jì)80年代以后,受學(xué)術(shù)研究領(lǐng)域開放活躍的內(nèi)在驅(qū)動和地方社會經(jīng)濟(jì)發(fā)展需求的外在牽引,以及地方史志研究力量的成長,基于地域歷史研究的訴求顯著增長。內(nèi)在學(xué)術(shù)演進(jìn)取向及其尋求突破的需求,適逢海外相關(guān)學(xué)術(shù)理論方法的引入,迅速促成了區(qū)域史研究的興起。90年代中期以后,華北、華南、江南等地學(xué)者開始展開廣泛的田野(社會)調(diào)查,極大地促進(jìn)了區(qū)域史的研究。在“歷史學(xué)與其他社會科學(xué)的結(jié)合”的學(xué)術(shù)實踐中,日趨興盛的區(qū)域史研究成果和名目繁多的區(qū)域史研究取向,很大程度上改塑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其中華北、華南和江南三大區(qū)域史研究尤為顯著。在當(dāng)代史學(xué)研究的整體格局中,無論是基于經(jīng)濟(jì)史、社會史或文化史研究的深耕細(xì)作,還是聚焦于新革命史或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的新開拓,華北區(qū)域史研究都是成果頗豐且具有特色的一個重要領(lǐng)域。
發(fā)展脈絡(luò)與學(xué)術(shù)聚焦
關(guān)于新時期以來華北區(qū)域史研究整體態(tài)勢,我們可從三個主要史學(xué)雜志(《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學(xué)月刊》)的刊文及相關(guān)著作的統(tǒng)計情況見其演進(jìn)之概要。總體觀之,相關(guān)研究在80年代屬于起步階段,90年代后逐步走高,而高峰期則是在新世紀(jì)以后。
從學(xué)術(shù)演進(jìn)的基本軌跡來看,80年代所刊“華北區(qū)域史”論文,就內(nèi)容而言大都屬于既往政治史或革命史范式下的學(xué)術(shù)研究,論文選題幾乎都集中在抗戰(zhàn)時期具有特定指稱的“華北事變”“華北危機(jī)”“華北根據(jù)地”上,其學(xué)術(shù)旨趣和學(xué)術(shù)話語仍然守定于政治史、革命史范式,并不彰顯學(xué)理意義上的區(qū)域史特征。90年代以后,華北區(qū)域史研究才逐步形成一個史學(xué)發(fā)展趨勢或史學(xué)研究取向。關(guān)鍵在于,這一時期的研究選題也不再拘守于既有的革命史或政治史范式,學(xué)術(shù)研究的聚焦形成了屬于自己的時代性特征。
其一,鄉(xiāng)村史成為一個成果相對集中的研究方向。相關(guān)研究論題廣及晚清以來的鄉(xiāng)村規(guī)模、社會結(jié)構(gòu)、社會分層、人口構(gòu)成以及鄉(xiāng)村租佃關(guān)系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等,構(gòu)成了華北區(qū)域史研究一個頗有特色的重要領(lǐng)域。其二,城市史研究也構(gòu)成華北區(qū)域史研究的聚焦點(diǎn)。一方面逐步形成華北區(qū)域城市系統(tǒng)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且在社會史、文化史、經(jīng)濟(jì)史以及現(xiàn)代化史理論方法的吸納和融通中,擴(kuò)展了區(qū)域城市史研究的維度;另一方面在北京、天津、青島等區(qū)域中心城市研究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拓展了對石家莊、唐山、保定、張家口等中小城市史的研究。其三,在既往的政治史或革命史范式下,華北抗戰(zhàn)史或根據(jù)地史是研究力量相對集中的領(lǐng)域,構(gòu)成了華北區(qū)域史研究的重中之重。90年代后這一研究的視角和論題大為擴(kuò)展,同時又充分借鑒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理論與方法,形成了新的面相。
上述研究狀況的梳理實際立足于兩個方面,一是以鄉(xiāng)村史和城市史統(tǒng)合范圍性研究,二是以政治史和革命史呈現(xiàn)主題性研究。就研究問題的聚焦而言,社會史和經(jīng)濟(jì)史顯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關(guān)注點(diǎn)。從總體上看,大量的經(jīng)濟(jì)史、社會史或文化史論題,實際上都包含在鄉(xiāng)村史或城市史兩大體系之中,并不獨(dú)立性地呈現(xiàn)其主題性特征。至于政治史或革命史研究,因其并非“新興”領(lǐng)域而以論題的通貫性和新發(fā)展面相獨(dú)具特色,單獨(dú)列示則可清晰見其學(xué)術(shù)脈絡(luò)的傳承與轉(zhuǎn)向特征。
新時期以來華北區(qū)域史研究的歷史朝向,極大地拓展了近代史研究的視野和范圍,超越了以往“事件史”縱向拉開的單一取向,豐富和擴(kuò)展了研究的內(nèi)容;使既往的“少量地方史研究多是為了對朝代劃界的全國性狀況和規(guī)律的總結(jié)作一注腳,基本上沒有區(qū)域研究的意識”的學(xué)術(shù)境況發(fā)生根本性改觀。與此同時,在學(xué)術(shù)轉(zhuǎn)型過程中引入了新的理論和方法,在以社會、文化、經(jīng)濟(jì)為基本范疇的區(qū)域史架構(gòu)內(nèi)靈活地建構(gòu)起新的學(xué)術(shù)詮釋話語,試圖重建整個近代史研究體系。
研究取向與學(xué)理建構(gòu)
誠如前述,主題性研究和范圍性研究幾乎構(gòu)成華北區(qū)域史研究的主導(dǎo)取向。特別是90年代后,主題聚焦于“華北”的諸多研究,大多基于社會史或經(jīng)濟(jì)史的學(xué)科立場,以個案解析或樣本示例為切口,將學(xué)術(shù)問題引向更精深的層次。這些研究主題中均明確標(biāo)示“華北”界域,但研究內(nèi)容事實上是將社會史或經(jīng)濟(jì)史問題“在地化”。在這里,“華北”其實被認(rèn)定為不言而喻的當(dāng)然存在,卻很少有學(xué)理意義上“區(qū)域”立論的自覺意識。至于范圍性研究,則是基于行政區(qū)劃或地理分劃的“華北”地域之內(nèi)的各類問題的研究,難以構(gòu)成規(guī)范意義上的區(qū)域史,但在學(xué)術(shù)實踐中卻又通常劃歸在“華北區(qū)域史研究”之中,甚至在總量和趨勢始終占據(jù)主體地位。它們在聚焦研究論題、拓展研究視域、深究學(xué)術(shù)問題方面成果斐然,但與區(qū)域史學(xué)科或?qū)W理體系的建構(gòu)甚少關(guān)聯(lián)。
其間,具有自覺的學(xué)理或?qū)W科建構(gòu)追求的著作主要有:苑書義的《艱難的轉(zhuǎn)軌歷程:近代華北經(jīng)濟(jì)與社會發(fā)展研究》和喬志強(qiáng)的《近代華北農(nóng)村社會變遷》(以下簡稱苑著和喬著)等。然而,對于華北區(qū)域社會變遷而言,苑著側(cè)重于區(qū)域內(nèi)的“小區(qū)類型”,而非整體的華北區(qū)域;喬著“定義”中的華北區(qū)域也與實際研究的華北內(nèi)容并不完全契合。
研究內(nèi)容和論題主旨的疏離,使我們的華北區(qū)域史研究面臨一個名與實不相符的困境。“隨著‘華北’概念的產(chǎn)生,這個概念越來越多地被運(yùn)用到學(xué)術(shù)研究中。嚴(yán)格說來,‘華北’概念在學(xué)術(shù)研究中的運(yùn)用只是一種學(xué)術(shù)的想象,不僅因為古代并無‘華北’這個概念,更因為關(guān)于‘華北’概念的界定及所轄區(qū)域,學(xué)術(shù)界至今沒有達(dá)成一致意見。”
發(fā)展困境與學(xué)術(shù)反思
認(rèn)真檢視40多年的研究歷程,無論是主題性研究還是范圍性研究,一個共同的問題即是區(qū)域史學(xué)理或?qū)W科建構(gòu)上的困境。我們需要反思的問題是,區(qū)域史“并不等同于人為劃定區(qū)域內(nèi)的歷史變遷和風(fēng)土人情,也不是地方史;作為社會史的分支,區(qū)域社會史研究應(yīng)該具有社會史的整體視野”。如果只是從“時空范疇”上論列屬于“華北”地域內(nèi)的歷史研究的話,那么無論是城市史還是鄉(xiāng)村史,個案性研究或樣本性解析研究成果多年來在多視角多維度下已經(jīng)獲得了相當(dāng)精細(xì)或精深的解讀文本,但這些微觀或中觀的個案研究卻無法給出一個即使是概略性的“近代華北區(qū)域史”整體面相。相關(guān)研究總體上聚合為以華北為標(biāo)識的一種“區(qū)域化研究取向”,以至于“華北區(qū)域歷史”變遷研究的學(xué)術(shù)追求最終被淹沒在以華北命名的各類主題性研究或范圍性研究中。
首先,日趨泛化的“區(qū)域化取向”遮蔽了真正的區(qū)域史學(xué)術(shù)訴求。區(qū)域史研究的目標(biāo)“是為了更深入地了解某一個區(qū)域,進(jìn)而更好把握歷史整體”。問題恰恰在于,“時下所見大量的區(qū)域研究作品中,具有嚴(yán)格學(xué)術(shù)史意義的思想創(chuàng)造的還是鳳毛麟角,許多研究成果在學(xué)術(shù)的貢獻(xiàn),仍主要限于地方性資料的發(fā)現(xiàn)與整理,以及在此基礎(chǔ)上對某些過去較少為人注意的‘地方性知識’的描述”。其次,這一研究取向造成近代史研究走向“碎化”困境。在40年的大量個案研究和微觀研究取向中,日趨“碎化”的成果比比皆是,但卻未能構(gòu)織出一幅近代華北區(qū)域變遷的基本圖景。
這提醒我們,進(jìn)一步推動區(qū)域史研究需要把握好區(qū)域的同質(zhì)性和異質(zhì)性問題,不宜刻意強(qiáng)調(diào)區(qū)域的特殊性,更不能抱著尋找奇聞異事的心態(tài)來對待區(qū)域史研究。區(qū)域史研究的展開如果沒有學(xué)理意義上的規(guī)范維度,在作為研究對象的區(qū)位選擇方面就會呈現(xiàn)出嚴(yán)重的學(xué)術(shù)失范,所謂區(qū)域史研究就可以因個人所需而隨意標(biāo)示:有跨省區(qū)的大區(qū)域史研究,有省區(qū)史研究,有縣域史研究,還有村域史研究等。這種趨向不僅割裂了歷史演進(jìn)的整體性,也背離了“區(qū)域社會史把特定地域視為一個整體,全方位地把握它的總體發(fā)展”的訴求。
新時代的新期待
由于區(qū)域范圍的界定本身即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在研究實踐中區(qū)域史的定義和界域不易獲得一致認(rèn)同。歷史進(jìn)程中的華北區(qū)域概念極其復(fù)雜而呈現(xiàn)多態(tài)樣貌,其界域的多樣和多變確實難以一概而論。區(qū)域史是現(xiàn)代歷史學(xué)發(fā)展進(jìn)程中的學(xué)術(shù)建構(gòu),它不是歷史本體存在(如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典章制度等)。正因為如此,學(xué)術(shù)規(guī)范的建構(gòu)尤其關(guān)鍵,否則無法進(jìn)入真正的學(xué)術(shù)話語體系,以至于所有的研究內(nèi)容都可以標(biāo)示為區(qū)域史研究,而實際上又在消解真正的區(qū)域史。因此,在未來研究取向中如何規(guī)避區(qū)域選擇的隨意性和“無意識性”,超越既往的主題性研究和范圍性研究在區(qū)域史學(xué)理建構(gòu)上的困境,是華北區(qū)域史研究再出發(fā)的關(guān)鍵所在。
應(yīng)該強(qiáng)調(diào)的是,在學(xué)理意義上形成華北區(qū)域史的學(xué)術(shù)體系、學(xué)科體系和話語體系,關(guān)涉到這一重要學(xué)術(shù)研究取向的時代高度和歷史定位。面對40多年華北區(qū)域史研究的現(xiàn)狀,面對既有的成果和存在的問題,一個必須承認(rèn)的事實是,如果沒有研究取向上的省思和根本性調(diào)整,依然在“主題性研究”和“范圍性研究”取向中前行,盡管可以使“華北區(qū)域史”研究有增量上的變化,卻不能推進(jìn)華北區(qū)域史研究質(zhì)性的發(fā)展,尤其不能形成具有時代性的進(jìn)步。
區(qū)域史研究不同于微觀史研究中單要素或一組要素的深入解析。華北區(qū)域史的學(xué)理體系應(yīng)該是一個在整合各種要素基礎(chǔ)上的建構(gòu),其中包括自然環(huán)境、社會經(jīng)濟(jì)、制度文化乃至于政治軍事等;其間發(fā)生的歷史事變、歷史事件和人事興替等,在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中共同建構(gòu)了華北之所以為華北的區(qū)域歷史特征。影響或制約區(qū)域發(fā)展要素的相互結(jié)合的模式或結(jié)構(gòu),是區(qū)域史研究的一個學(xué)理性建構(gòu),正是這一學(xué)理性體系決定了華北區(qū)域史史學(xué)話語體系或?qū)W術(shù)體系的存在與否。
在鎖定的區(qū)域之內(nèi),人口、環(huán)境、制度、經(jīng)濟(jì)、人文諸多要素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及其發(fā)展趨向,這些要素在歷史演進(jìn)中的各自地位的變動等,即特定區(qū)域的綜合性、總體性歷史面相的呈現(xiàn)和揭示,構(gòu)成其之所以為區(qū)域史學(xué)術(shù)價值的要件;舍此而外的以個人喜好(或便利操作)的“華北地域范圍”的各類問題研究,只能是基于經(jīng)濟(jì)史、政治史、文化史諸學(xué)術(shù)體系或?qū)W科體系中的個案性學(xué)術(shù)探研,或不必(亦難以)歸屬于區(qū)域史研究。
基于區(qū)域史的理論元點(diǎn)和華北區(qū)域史的研究現(xiàn)狀,我認(rèn)為布羅代爾提出的歷史時段理論,有助于我們對華北區(qū)域史學(xué)理規(guī)范建構(gòu)的思考。布羅代爾在其名著《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將歷史時間分為三個層次,也即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個體時間,并分別賦之于歷史學(xué)特質(zhì)的概念: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這是一個蘊(yùn)含全面的時間空間和經(jīng)濟(jì)、文化、制度與人事的歷史學(xué)范疇,具有學(xué)科建構(gòu)的價值和意義。
三個時段概念在學(xué)理特質(zhì)上都與區(qū)域(空間)、歷史(時間)相關(guān),可以是區(qū)域史學(xué)科建構(gòu)的基本范疇,它們構(gòu)成了區(qū)域史學(xué)科建構(gòu)的三個向度。其一,長時段的研究對象指長期不變或變化遲緩并在歷史上長久發(fā)生作用的因素,諸如地理、氣候、生態(tài)環(huán)境、社會與文化傳統(tǒng)等。其二,中時段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社會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局勢、情勢,以及周期性趨勢等。其三,短時段的研究對象是事件和個人,包括突發(fā)性的歷史事件、重大歷史事變、革命運(yùn)動以及英雄和領(lǐng)袖人物的作用。
從近代史學(xué)科研究的具體情況來看,更值得關(guān)注和探討的是短時段維度下的區(qū)域史研究。一方面,近代以來伴隨著民族國家的重建進(jìn)程,也引發(fā)了區(qū)域社會、文化的重建。其中,既有基于經(jīng)濟(jì)建設(shè)內(nèi)容劃定的區(qū)域,也有基于社會建設(shè)設(shè)立的區(qū)域,還有基于不同政治—軍事力量形成的區(qū)域。這些短時段向度下的區(qū)域的形成及其演化歷史,以往通常在經(jīng)濟(jì)史、政治史、革命史的框架下展開,而其特定歷史條件下區(qū)域本身的演進(jìn)內(nèi)容、特質(zhì)以及歷史性影響,事實上未能進(jìn)入學(xué)術(shù)研究視域。亦即,如何從區(qū)域史學(xué)科高度上梳理近代以來各種區(qū)域的興衰起落?如何從區(qū)域的類型樣態(tài)上界定古與近的歷史區(qū)分?都是值得討論和研究的。
近代以來,基于人事與行政的短時段的影響出現(xiàn)了各種不同的區(qū)域劃分,這些區(qū)域的興廢變動,從特定角度揭示了歷史變遷中深刻而又復(fù)雜的面相,其中的經(jīng)驗和教訓(xùn)多多。歷史學(xué)本來就蘊(yùn)含“鑒訓(xùn)為戒”的學(xué)術(shù)訴求,因此,這一研究向度也應(yīng)該是區(qū)域史學(xué)術(shù)建構(gòu)中的重要方面。
在特定時空規(guī)范下的區(qū)域史研究視野,有著相對可以確定的內(nèi)涵與邊界,由此可以形成規(guī)范性的學(xué)術(shù)對話。華北區(qū)域史研究,尤其短時段向度下的近代華北區(qū)域史研究,在學(xué)科規(guī)范建構(gòu)的引領(lǐng)下一定會獲得時代性進(jìn)步。更重要的是,在這一向度下的區(qū)域史研究,人的主體性影響更為重要。因為個人之于歷史,即使英雄或領(lǐng)袖之于歷史的作用,也主要是限于短時段向度下的區(qū)域范圍之內(nèi)。這一向度下的區(qū)域史,應(yīng)更多地展現(xiàn)人的活動的主體性意義。近年來,有學(xué)者已提出:“區(qū)域史研究要真正活起來,關(guān)鍵是把人的因素更深入地納入研究中。區(qū)域固然是一個地理概念,但又不單純是地理概念……事實上,更多時候是人的活動而不是空間本身規(guī)定了某一區(qū)域的歷史和現(xiàn)實,規(guī)定了某一區(qū)域人和地、時間與空間的關(guān)系。”相信在學(xué)界的協(xié)力共進(jìn)下,華北區(qū)域史研究會更上一層樓,取得令人期盼的新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