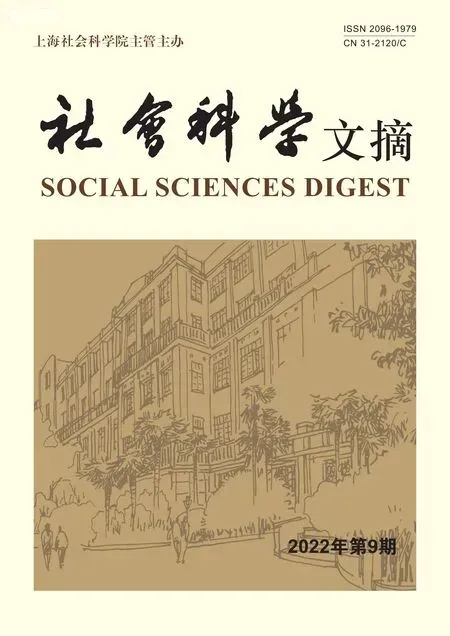觀念的“割席”
——當代中國互聯網空間的群內區隔
文/陳云松
背景、問題和基本概念
隨著互聯網逐漸成為各類信息的來源與傳播平臺,信息開始變得更有非連續性和自選擇性的特點,使得公眾對許多觀念議題,尤其是和“文化主體性”相關的議題出現集體認知和記憶的疊加、更新、斷裂與分化,最終演變為互聯網上的觀念之爭和個體觀念的固化,使得具有同質性特征的基礎性社會結構單位之內出現普遍的觀念的“割席”。之所以使用“割席”這個詞,是為了體現原本同一社會群體內的系統性共識和傾向被裂解分化了,如同東漢末年管寧與華歆這對友人因理念不合而割席斷交一樣。本文將這種同質性社會群體內部因觀念之爭而導致的異質性稱為“群內區隔”。在微觀層面,本文所討論的“群”,指的是個體在互聯網新媒體社交平臺上有聯系的基礎社會結構單位成員;在宏觀層面,我們討論的“群”實際上代表了家庭、單位、學校等具有同質性特征的社會基礎結構。
本文認為,全球化進程中多主體現代性的形成與“雙向脫嵌”所導致的“時空折疊”,為中國當代互聯網空間中的觀念的“群內區隔”提供了宏觀理論詮釋。接著,本文引入戈夫曼的劇場理論,強調了其催生的“強義務”特征,使得互聯網社交媒體形成分裂的“關系劇場”,以此為“群內區隔”提供微觀層面的理論框架。據此,本文初步構建了當代中國互聯網空間中的社會觀念與現實社會結構之間關系的總體圖景以及宏觀—微觀理論框架,有助于增進我們對當代中國互聯網社會心態的理解,提升治理能力。
“群內區隔”的宏觀背景:“時空折疊”與多中心現代性
當代中國互聯網空間圍繞文化本土性觀念所形成的“群內區隔”及其日益強化的趨勢,其宏觀背景恰恰來源于吉登斯所說的“綜合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基于社會系統時空變遷的總體秩序”。基于此,吉登斯提出了“遠距化”到“時空分離”路徑。制度結構所包含的規則和資源具有延續復制能力,形成了時空的“遠距化”,對應著現代性。而“遠距化”可以導致“時空分離”,使得具有現代性的社會系統“脫嵌”并在其他時空進行復制。“先發”社會的制度系統以“脫嵌”的時空分離方式延伸復制到“后發”社會,形成跨越地表的全球社會結構。顯然,吉登斯所討論的“脫嵌”暗喻了一種社會系統的體制勢能或以西方為中心的“中心—邊緣”假設。只是當作為社會結構的制度、規則和資源進行時空延伸之際,吉登斯和福山心目中的嚴整的全球秩序并不會保持某種超穩定的靜態結構。一方面,真正觸及深層制度的社會系統的脫嵌、復制往往是非常困難和不穩定的,甚至會出現原有社會系統的回流。另一方面,在一些看似成功的吉登斯心目中的現代性擴散案例中,其時空延伸過程中會出現經濟系統甚至政治和文化系統“反向脫嵌”的張力:完成了政治系統嵌入的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其經濟系統的崛起對西方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完成了市場經濟系統嵌入的當代中國,其基于文化傳統和政治系統的輸出性力量,形成了全球化進程中的“多中心現代性”。忽略了這種“多中心現代性”便是吉登斯“時空分離”理論的薄弱之處。
因此,我們在吉登斯的“時空遠距化”——“時空分離”概念路徑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提出對應著全球化多中心階段的“時空折疊”的概念。所謂“折疊”,指的是在現代化“后發”社會這一“地點”,不同的“制度時間”在同一個空間里形成了疊加。“時空折疊”的后果是,在宏觀上使得現代化“后發”社會,特別是成功汲取了全球化資源的“后發”社會通過對外來系統的片段移植,同樣具有了“時空分離”能力和反向進行“脫嵌”的傳播能力,進而形成現代性的“多中心特征”和“雙向脫嵌”的社會張力。在微觀上,“時空折疊”使得現代化“后發”社會的人群同時面對著歷史悠久的原生系統記憶和新生的外來系統記憶,催生了社會不同群體內的觀念分化,最終導致類似“北京折疊”那樣共同占據集體記憶,但在時間里此消彼長、分享空間的記憶割裂。投射到文化主體性層面,就形成了本文所說的社會觀念的“群內區隔”及其強化。
具體而言,在全球化的單中心階段,來自西方的社會系統片段,從西方“脫嵌”并植入到非西方的社會系統之中,完成了單向度的“時空分離”。在整合的過程中,其原生“制度時間”的結構層不會消失,而是被新“制度時間”的結構層遮蓋。一旦新的社會系統在規則與資源上成功地積蓄了足夠的勢能,原生“制度時間”及其載體深層“記憶痕跡”就總是會試圖上升,成為和當年外來社會系統一樣的主體不在場的新結構,具有同樣的“時空分離”和“雙向脫嵌”的集體意識。此時,被外來現代系統所定義和發現的原生的、傳統的社會系統,經過結構化重新定義了自身和整個世界,并把外來系統重新發現和定義為遠方的原生傳統。這個過程體現了原生性與現代性的相互定義和現代性的多中心、多主體流動特征,前文提到的中國的崛起和實質性系統輸出的能力就是典型案例。
此外,對不同世代的群體,時空折疊帶來的記憶組合呈現出不同的人群權重搭配。“60后”“70后”“80后”“90后”對于家、國、世界的認知以及對文化主體性的理解是高度差異化的。這種分化表現為同質性的社會群體卻會對同一件事物、同一個過程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不同世代的社會群體也會有類似的觀念鴻溝。以上因素相互摻雜互動,進一步形成社會觀念的分裂對峙。
“群內區隔”的微觀機制:媒體、關系和劇場
要構成對社會群體在文化主體性觀念方面較為普遍的割裂以及強化,則離不開互聯網新媒體的信息強化語境。
(一)互聯網新媒體的“信息負壓”
當代中國互聯網新媒體的兩大信息特征在個體層面催生并不斷強化著互聯網觀念的“群內區隔”。第一大特征是互聯網新媒體的信息高通量,指的是個體獲取的信息流量大、更新速度快。第二大特征是互聯網新媒體的信息自選擇。公眾可以選擇使自己愉悅的內容,但久而久之會將自身桎梏于像蠶繭一般的封閉信息空間之中,形成桑斯坦所說的“信息繭房”。這兩大特征最終形成了社會觀念體系中的“信息負壓”效應。“繭房”彼此間相互擠壓對峙,并向外輸出信息以試圖同化更多的人群,最后以“信息負壓”的形式構成社會群體的內部張力。而“繭房”內部的公眾逐步被自己所選擇的信息遮蔽,慢慢喪失反思能力與動機,最終導致“群體極化”,即團體成員一開始有某些觀念偏向,在群體討論后會進一步強化偏向甚至形成極端的觀點。
(二)互聯網新媒體的“關系劇場”
除此之外,互聯網新媒體和關系網絡的嵌合形成了具有特定時空和關系特征的虛擬空間——“關系劇場”,加劇了觀念分裂。
(1)劇場的時空特征——“強化表演”
具體表現為在場的時空分離性和延續性。前者指的是在社交平臺上,人們既可以進行實時互動,又可以通過調整信息傳遞的節奏來改變互動的時空分布。它使得各類行動者(例如“群主”“潛水者”)在劇場中既可以對自己的言行深思熟慮,又可以通過各類方法使社交空間變得更具有戈夫曼所說的“表演性”,進而加劇觀念對峙。而在場的時空延續性指的是網絡上的互動會隨著“群”的存在而持續不斷,它使得行動者在表演的過程中的觀念必須始終如一,否則或失去面子,或失去他人的信任,而信任是戈夫曼提出的表演行為的前提與核心。基于此,社交媒體中人們所表演出的觀念執著和對峙甚至比真實生活中更為激烈和持久。
(2)劇場的關系特征——“強義務”在場
大量的社會義務形成了新媒體的兩個關系特征,使得人們形成一種“強義務”在場。第一個特征是陌生人的快速強關系。即便是素未謀面的人,例如“博主”和“粉絲”,在公開場合的社會關聯一旦建立起來,就因信息互動的持續性和全天候而形成強關系,而不需要現實生活中長期的互動培育。第二個特征是熟人的退出壓力。在社交媒體上,在知曉彼此身份的情況下長期“潛水”,很快就會面臨同儕壓力。“拉黑”甚至退“群”更是一種艱難的決定。這些舉動會被解讀為對熟人特別是“群主”或邀約者的友誼和信任的背叛。
顯然,“強化表演”和“強義務”在場,會使得“關系劇場”中的主體不得不長期堅持自我觀念并加以鞏固維護,最終形成互聯網新媒體的平臺“規訓”。我們以微信為例,來描繪“規訓”的方式。首先,人們可通過微信相互設置對方的查閱權限和建“群”等方式來形成各類私密、半私密或公開的前臺,完成對虛擬空間的分配。在這種強制序列中,參與者不斷被分類并獲得了在網絡空間中的不同定位。其次,再來看話題節奏的控制。“微信”也完全可以實現福柯總結出的“規訓”三部曲:對活動節奏的安排,對日常事務的強制確定和周期調節,讓個體在生產(話語)過程中被形塑為“規訓”客體。再次,從創生活動的時間組織來看,“微信”平臺能夠如同監獄組織放風一樣,通過發“紅包”、統一“點贊”等近乎全員參與的形式,以連續活動的序列化讓個人的時間變成一種集體的、連續整合的線性時間,并指向一個穩定的活動終點。最后來看力量的編構。經過這樣的“規訓”,在“微信”群中,個體成為福柯所謂的經過精確命令系統的力量組合所能擺布、移動和構建的要素。例如,“微信”群中看似沒有公開發布的紀律,但實際上在冒犯性的語言后,“群主”或“骨干”會通過施加微妙的控制進行懲罰,從輕微的尷尬“表情包”、到語言勸誡、再到踢出群。這一過程使得社交平臺上的所有人實質上都處于一種永遠可見的福柯引述的“完美圓形監獄”狀態。
某種意義上,恰恰是對峙性觀念的此起彼伏,讓互聯網新媒體平臺上的時間和空間獲得了線性的方向和話語活動的意義,也讓參與者各自獲得了自己的社會空間位置,并為維持這種意義而樂此不疲。也因此,觀念的“割席”,“群內”的“區隔”,實際上已從人際交往中的觀念碰撞,內化和升華為一種經過慣習化后的個體“時空分離”的自我存在載體,是自我建構的定期與不定期組合的生活洗禮方式。每個人的異質性細節恰恰構成了“群”中的自我,并必須通過觀念“割席”而維持下去。這個時候,制造區隔和協調觀念分裂一樣,都成為互聯網新媒體平臺上人的存在的特征。人們在異見中爭論,但也在異見中達成社會結構的彼此判定。因此,社會結構形成觀念、行動的舞臺,同時又被觀念和行動所結構化與定義。“群內區隔”遂以這樣的方式獲得熵增式的均衡——每一個社會群體都在自我的牢籠中不可避免地朝觀念對峙的方向走去。
討論和結語
最后我們再來看看“時空折疊”理論跳出中國的價值和“群內區隔”這一互聯網現象在現實社會的擴散。
“時空折疊”現象并非僅局限于當代中國,2020年美國社會也因政治偏向而產生嚴重的觀念分裂。其中的案例包括圍繞時任總統特朗普、美國大選和“Black Lives Matter”(即“黑人命也是命運動”)等熱點人物、事件產生的爭論。實際上,當代美國的觀念分裂的宏觀背景可以理解為美式中產家庭的記憶折疊,這是二戰后的美國記憶對今日城市空心化、產業衰退、政治正確愈演愈烈的“時空疊加”。從這個角度,本文提出的“時空折疊”或可在抽離出中國特定的歷史背景后仍具有理論解釋力和一般性價值。
“群內區隔”是否已經擴散到網絡之外的現實社會生活之中?為此,本文使用非互聯網數據來進行統計檢驗,我們發現,“中西VS.西醫”之爭,不僅在互聯網中形成了“群內區隔”,而且在線下現實社會中也在發酵,打破了階層與觀念之間的對應。不過,互聯網空間中“洋節VS.土節”和“計劃VS.市場”的群內區隔并沒有規模性、實質性地彌散傳播到現實社會生活中并影響階層結構。因此,網絡上與此相關的看似撕裂的聲音,或許并未真正造成社會的撕裂。盡管“群內區隔”或許尚未全面、實質性地影響現實社會互動,但如果不加引導紓解,也可能會給社會治理帶來消極的后果,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個體心態的極端化。觀念對峙容易使得人們在社會交往群體中對持有不同觀念的人形成一種簡單化和極端化的失望甚至敵視、鄙視的態度。
第二,社會撕裂的彌散化。互聯網上的個體極端化心態不但會在虛擬空間中不斷蔓延,而且會向現實社會互動中延伸。這一方面會讓互聯網公共話語出現裂痕,另一方面也會導致現實社會中思潮的高度情緒化和對立公開化。
第三,交往結構的封閉化。觀念分裂,特別是線下的“群內區隔”會對中國傳統由家庭、親屬、朋友關系形成的“差序格局”造成一定的改變。新的“差序格局”將是混合關系網絡和觀念同質性的梯次結構。在關系的束縛下,“道不同不相為謀”式的自我隔離可能在一定時段內出現。這樣一來,觀念“割席”將會使社會交往結構進一步封閉化。
第四,意識形態的隱喻化。觀念之爭的背后潛藏著意識形態的傾向和潛移默化。互聯網空間中觀念的多元化和差異化是一個健康社會和健康互聯網空間文化繁榮與百花齊放的表現。但如果觀念形成強烈的難以兼容的對峙、分裂甚至纏斗,此時的“群內區隔”就會成為社會治理特別是互聯網治理的暗面,需要決策者和治理者發出堅定寬厚的主流聲音,讓網絡上無謂的爭論減弱,讓觸及治理根基的互聯網話語具有明確的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