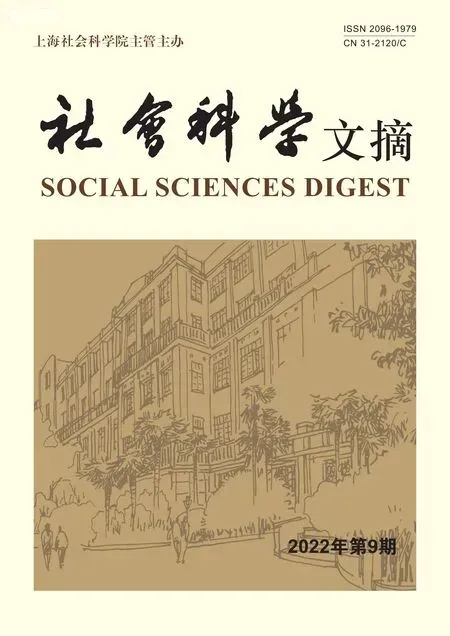問題域的轉換:公共新聞崛起與新聞理論創新
文/駱正林
隨著技術酵素對社會生活的催化,新聞傳播正在由職業活動演變成一種公共生活,新聞傳播的公共性被大大激發出來,新聞業和新聞學均遭遇巨大的“未來不確定性”。當社會大眾與職業媒體共同分享新聞傳播權時,新聞學的問題域走到了轉換的十字路口。
問題域的轉換:一種能夠激發新聞學想象力的方法論
俞吾金先生認為,“哲學的進展始終是以人們對基本問題的反省、超越或解決作為自己的前提的”。其實不光哲學需要反省“基本問題”,任何學科都需要對“基本問題”進行持續的反思和辯駁。為此,俞吾金提出了一組概念,如思想酵素、問題域、問題域的轉換等,這些概念可以有效詮釋“理論的進化和創新”。
思想酵素是從人類總體思想資源中采擷的,作為理論思考的起點和依據的思想資源。如果戴著俞氏眼鏡審視新聞事業和新聞理論,會發現新聞事業和新聞理論的演變也是由特定“酵素”引發的,技術酵素無疑是其中最令人矚目的催化劑。
問題域“是指某一理論體系可能提出的全部問題的總和”。問題域分第一問題、基本問題和具體問題三個層級。第一問題以單數的形式出現,在整個問題域中具有基礎性的、核心的地位和作用。新聞學的第一問題是“新聞是什么?”基本問題是從第一問題中派生出來的若干重要問題。新聞學問題域包含新聞屬性、新聞價值、新聞功能、新聞體制、新聞自由、新聞控制等基本問題,這些問題構成整個新聞學問題域的學科框架。具體問題是由基本問題孵化出來的數量更加龐大的現實問題,具體問題的演繹范圍是由第一問題和基本問題確定的。
當某種理論體系在發展過程中,原先所蘊含的“第一問題”的提問方式和解答方式已經被新的提問方式和解答方式所取代,而且前后兩種提問方式和解答方式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差別,那么此時就出現了“問題域的轉換”的現象。從俞吾金的理論邏輯出發,我們能夠找到新聞業界和學界變革的酵素,“問題域轉換”的思想則能幫助我們提高學術想象力,加快創新新聞理論體系的進程。
技術酵素的釋放:傳統媒體的困境與公共新聞的崛起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技術酵素引發了媒體生態的裂變。當職業媒體在互聯網技術的沖擊下茍延殘喘時,社交媒體、平臺媒體卻在資本的攪動下風生水起,互聯網技術公司成為信息產業鏈的終結蠶食者。
1.技術酵素催化懷舊潮,媒體人黃金敘事中的想象和記憶
社交媒體、平臺媒體的崛起沖擊了媒介權力場域,傳統媒體的制度性權利遭遇挑戰,職業媒體人的身份認同迅速下降。傳統媒體的職業困境引發了媒體人的記憶潮、懷舊潮,媒體人的黃金記憶是對“做新聞”“好日子”的一種懷舊。媒體人建構的黃金時代大約在1995—2010年間。那段時間,媒體既受到傳統體制的保護,壟斷新聞傳播的話語權;同時媒體也享受到市場經濟的紅利,體驗到新聞專業主義的實踐。20世紀90年代的媒體人,基本上是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媒體新人,他們的“青春期”趕上了媒體發展的機遇期,有幸成為媒體市場化的參與者、見證人。那時的新聞媒體具有權威性,從事新聞事業擁有崇高感,新聞人到各地采訪還頗為風光。當然,即使在當年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媒體人在批評報道、輿論監督等方面,依然經歷過諸多困難和考驗。因此,媒體人對黃金時代的記憶,不是對過去的客觀還原,而是他們對職業地位的重新評估。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記憶、輝煌歷史,當他們退場時都會把自己所經歷的時代浪漫化,這是一代人社會地位、歷史地位的“自我凸顯”的需要。當下傳媒人對黃金時代的建構,除了尋找身份認同、傳遞專業精神之外,更多的則是對“傳統媒體風光不再”的一種情緒反彈。媒體人通過對過去的懷念,表達的是對職業新聞發展的擔憂和對生存狀態的不滿,當然還有隱藏在文本深處的某種“抗議”。媒體人的懷舊是對職業媒體轉型的無奈和想象,也是新聞學新的問題域轉換的催化劑。
2.媒體人身份認同弱化,公共新聞卻在社交媒體中彰顯生機
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智能化等技術手段,徹底改變了新聞傳播的路徑、格局和模式,職業新聞機構無法壟斷新聞的采集權、發布權、詮釋權,職業新聞人因此陷入身份危機、職業危機之中。當感受到自己所信奉的新聞價值受到尊重時,媒體人會感到滿足、自豪和幸福;當信奉的價值受到漠視或威脅時,媒體人會感到迷茫、落寞或不安全。于是,很多媒體精英紛紛選擇離開自己的崗位。當他們選擇離開熟悉的崗位時,體制給予他們的“無形資產”立即耗散,他們在短期內很難找到新的身份認同。
與職業媒體的碌碌無為相對照,社交媒體卻顯示出更多的活力。新冠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的變化,公眾爆發出對“新聞信息”的巨大熱情。然而,在全球疫情、美國大選、俄烏戰爭、臺海危機等重大新聞事件中,傳統媒體刊播的新聞在數量上和及時性上均趕不上社交媒體。站在專業主義、理性主義的視角,職業媒體人可以嘲笑社交媒體的感性取向和非專業行為,但職業媒體的光環再也遮蔽不了社交媒體的信息浪潮。新聞原先是職業媒體人的職業活動,新聞報道尊奉的是客觀報道原則;現在新聞成了公眾的日常生活,公眾帶著情感體驗加入新聞實踐,傳統新聞價值觀在公共新聞時代遭受到無情的沖擊。
3.新聞傳播被迫向公眾開放,新聞活動的邏輯起點發生重大變化
媒介生態的變化是多元酵素催化的,如技術酵素、制度酵素、文化酵素等,但技術酵素無疑是媒體問題域轉換的起始點。技術酵素對新聞傳播領域的作用,拆散了新聞傳播的專業圍墻,使新聞傳播活動逐漸向社會公眾開放。公共新聞、算法新聞、機器新聞等傳播形式的出現,稀釋了傳統新聞傳播事業的神圣性,新聞生產的流程被改造,“什么是新聞”的提問和回答方式出現了重大的變化。當新聞傳播變成開放的公共生活時,媒體人可以通過“選擇離開”來應對“個人困擾”,而媒體機構、職業群體無法整體消失,他們必須要通過話語重構、流程再造,來化解傳統新聞價值受到的威脅,實現新聞傳播問題域的有效轉換。
新聞學問題域的轉換:技術酵素激發的新聞理論創新
隨著新聞活動公共化、新聞媒體政務化的出現,傳播學研究遮蔽了新聞學的光環,社會治理任務超越了信息傳遞功能。新聞學在這種背景下陷入兩難處境,它既無法承擔形而上的哲理和價值的思考,也難以承擔形而下的經驗指導,新聞學研究出現了相當程度的空心化傾向。當“新聞”越來越成為人類與世界接觸的方式時,新聞學必須要實現問題域的轉換,從而突破自己的兩難處境,提升自身的學科地位和生存的合法性。
1.解決理論懸置化問題,推動新聞學問題域的合理轉換
進入21世紀,傳播學的研究視域被無限放大,新聞學則滑到了新聞傳播學的邊緣:新聞學的定義被忽視,新聞學的內涵變得模糊,很多問題因為敏感而被懸置。新聞學理論建設的最緊迫任務是實現問題域的轉換,最高目標是實現對新聞傳播現象的邏輯解釋。傳統新聞學強調真實、客觀、公正、獨立,這些傳統的價值追求今天變得遙不可及,但它們仍然是新聞學學科高地上的精神旗幟。社交媒體的繁榮使新聞傳播成為一種公共生活,新聞傳播和意見表達的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如何平衡表達自由和社會治理的關系,仍然是新聞學理論建設的重要任務。面對新聞傳播生態的變化和新聞學的學科處境,我們需要發揮豐富的新聞學想象力,創造概念、更新話語、建構理論,實現新聞學問題域的有效轉換。
2.創新問題域的邏輯鏈,轉換“第一問題”的問答視角
近代西方哲學是圍繞“思維與存在何為第一性”而展開的,西方新聞學理論也基本遵循了這條“認識論”路線。因此,西方新聞學強調記者的專業主義精神,強調主觀對客觀的準確反映和報道。我國傳統新聞學理論也受到西方近代哲學的影響,即從認識論視角強調新聞是主觀對客觀的反映。只不過我國新聞理論更加傾向于唯物主義立場,非常強調社會主義新聞事業與資本主義新聞事業的區別。因此,我國傳統新聞理論的建構主要是沿著“認識論—客觀性—專業性—階級性”的線索而展開的,其中“認識論”是新聞學理論建設的邏輯起點。
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負有“解釋世界”的使命,而且負有“改變世界”的使命,因此馬克思的本體論應該準確地表述為“實踐本體論”。從“認識論”進化到“實踐論”,一種新的問題域被打開,原先很多“視而不見”的東西會立即顯示出來。在技術酵素的作用下,新聞不再局限于媒體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它已經演化成公眾參與生產、隨時體驗的公共生活。因此,新聞學問題域將沿著“實踐本體論—社會關系論—公共生活論—社會治理論”的路徑演化。當我們從傳統的認識論視角,從孤傲的專業主義精神中抽身出來,用全新的、開放的、沒有前見的眼光看待新聞學,會發現更多掩藏在新聞傳播活動中的生活體驗和社會意義。
“什么是新聞”是新聞學問題域的第一問題。傳統新聞學對新聞的經典定義是:新聞是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在新的問題域中,新聞學的第一問題仍然是“新聞是什么”,但提問和回答的方式均出現根本變化,新舊問題域的話語間出現明顯的話語界限。社交媒體時代新聞活動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成為社會組織、社會關系的聯系紐帶,成為公眾日常體驗的一種參與實踐和情感體驗。在此,新聞學第一問題被繼承了下來,但新聞的內涵和功能發生了轉向,“新聞”定義與媒體拉開了距離,與“客觀”“真實”的關系也出現了模糊。
3.正視新媒體的革命性,梳理“基本問題”的問答體系
傳統新聞學問題域遵循“認識論—客觀性—職業性—階級性”的邏輯線索,形成了新聞的客觀真實、新聞的職業精神、新聞事業的階級屬性等基本問題。在這樣的問題域中,“階級性”成為新聞學的核心問題,受眾經常被排斥到基本問題的范疇之外。當技術酵素拆解了職業媒體的新聞壟斷,原本被遮蔽的實踐主體被放大后凸顯出來,新聞成為現代人每天都體驗的生活狀態。
當新聞與機構的剛性聯系被切斷,傳媒技術賦權就成為公眾享受的普惠權利。當公眾可以直接參與新聞的生產和消費時,新聞傳播活動的“載體、主體、受體”等要素均發生了重大變化。客觀性是傳統新聞的本質屬性,媒體人信奉新聞專業主義,努力實現客觀、獨立、理性地報道新聞。當社會公眾成為新聞傳播的實踐主體時,新聞傳播便成為社會生產、社會關系的聯系紐帶,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布滿了新聞的印跡,新聞的主觀化、情感化、生活化趨勢不斷增強。隨著新聞學問題域從認識論轉向實踐論,新聞學的基本問題就出現了連鎖反應:有的基本問題被保留下來,但回答方式出現了根本變化;有的基本問題無法體現公共新聞活動,它們因落后于時代而被直接拋棄;有的基本問題是新媒體發展提出的新問題,它代表著新聞傳播發展的革命性方向。新聞要素、新聞屬性、新聞價值、專業主義、新聞自由等問題依然存在,但提問和回答的方式出現了明顯的變化;真相與后真相、職業新聞與公共新聞、客觀性報道與建設性新聞因此成為新聞學理論討論的新熱點。
近年學界對“真相”與“后真相”討論得比較多,其中就蘊含著新聞學基本問題的重要變化。傳統媒體強調新聞的客觀性、真實性,報道真相成為記者和媒體的首要職責。社交媒體讓人類深陷后真相時代,情感、觀點經常跑到了真相前面,真相和后真相開始糾纏不清。傳統媒體時代,真相是話語掌權人的“言說”,是媒體一次性的給予或認定,一般公眾常被排除在發現真相之外。媒體看似堅持專業主義精神,但因為缺少社會力量的參與和監督,真相可能成為媒體、權力、資本三方力量協同的產物,在特殊情況下權力和資本才是“真相”的真正定義者。“后真相”也許不能給我們更多的真相,但是它可以幫助我們反思真相,能夠創造一種可能逼近真相的機制。因為真相不是一種總結性的給予,而是一種眾人探索的真相尋找過程,所以當代新聞不再是一種認識論的結果式、終了式的報道,而是一種社會生活橫斷面的呈現,是一種眾人參與新聞、生產新聞、傳播新聞的公共生活。因此,“后真相”并非真相的黑暗時代,它為人類開辟了另一條通往真相之路,當然它也是重新回答新聞的基本問題之路。
4.洞悉新聞業務變革的技術化,再造“具體問題”的闡釋概念
技術酵素在改變新聞傳播生態的同時,也給新聞學理論建設提出了很多具體問題。面對技術酵素觸發的系統性的具體問題,需要根據時代背景創新和梳理新術語、新概念,從而給“具體問題”提供主導性的闡釋路線和話語工具。首先,技術酵素改寫了新聞表現形式、新聞生產流程,從而在整個生產線上制造了系列化的“具體問題”。因此,新聞學理論需要對公民新聞、數據新聞、算法新聞、智能新聞、數據挖掘、機器寫作等重新進行理論梳理。其次,在社交媒體時代機器和公眾的地位得到提升,職業媒體人卻出現了身份焦慮,傳統新聞價值面臨著巨大的考驗。新聞學只有生產出更多的概念和理論,才能詮釋好當下新聞傳播生態,才能重建職業媒體的價值理念。對種種具體問題的思考,可以幫助我們提煉出基本問題,進而反思和追問第一問題,如此才能形成新聞學完整的、邏輯的知識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