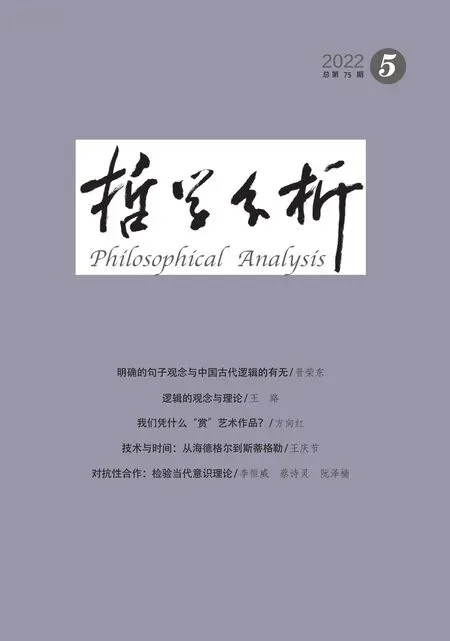批判傳統(tǒng)與分析傳統(tǒng)的匯通何以可能?
——從馬克思被維也納學派奉為“先哲”說起
安維復
哲學在于匯通,哲學社會科學的現(xiàn)實形態(tài),是古往今來各種知識、觀念、理論、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結(jié)果。在我國學界,批判傳統(tǒng)與分析傳統(tǒng)在一定程度上處于疏離狀態(tài),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與(邏輯)實證主義研究之間缺乏必要的思想溝通。這種疏離可能不利于學術(shù)的進展。筆者在對西方科學思想經(jīng)典文獻的編目進行整理的過程中,在維也納學派歷史檔案中發(fā)現(xiàn)一批有關(guān)馬克思思想的文獻資料(可能國內(nèi)并不多見),其中包括馬克思被奉為維也納學派的“先哲”(predecessors)的論述。這些文獻或可佐證批判傳統(tǒng)與分析傳統(tǒng)存在著匯通的可能性,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馬克思主義科學性及其影響力比我們想象的要大得多。為此,本文主要討論三個問題:馬克思何以被維也納學派稱之為“先哲”?馬克思的思想在西方科學哲學傳統(tǒng)中的流傳何以可能?如何厘定馬克思的批判傳統(tǒng)與實證主義的分析傳統(tǒng)的共識與界分?
一、緣起、發(fā)現(xiàn)新證及其評估
哲學在于“究天人之際”,但兩極相通。在馬克思主義與西方分析傳統(tǒng)之間,如何既堅守思想的界分,又能保持學術(shù)的關(guān)聯(lián)?以往的研究往往在批判傳統(tǒng)特別是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中尋找他們批判孔德主義的證據(jù),但往往忽略在分析傳統(tǒng)的著述中查找有關(guān)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的論理。這在論證上是不對稱的。筆者在從事“西方科學思想經(jīng)典文獻編目及研究”的過程中,整理維也納學派的《國際統(tǒng)一科學百科全書》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時候發(fā)現(xiàn),在約根·約根森(Joergen Joergensen)撰寫的《邏輯經(jīng)驗主義的形成》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Empiricism)一書中,歷數(shù)的維也納學派“先哲”,除了提到馬赫、羅素、維特根斯坦外,竟然列出了馬克思(還有費爾巴哈)的名字。筆者頗感意外——馬克思何以成為分析運動的“先哲”?
學術(shù)在于論證。事例枚舉并不是(有效的)證據(jù),證據(jù)必須嚴加考證!面對這份名單,筆者感到事關(guān)重大,因而沒有輕信其言,而是歷時經(jīng)年,旁征博引,反復比對文獻,盡力用馬克思特有的學術(shù)方法和西方的分析技術(shù)進行細密的學術(shù)考證。
第一,約根森及其“邏輯經(jīng)驗主義的形成”或許是人微言輕的“異見”之作?為此,筆者核查了約根森的學術(shù)簡歷及其公開發(fā)表的全部文獻和相關(guān)二手文獻,結(jié)論是:約根森雖非像石里克、卡爾納普那樣的維也納學派核心成員,但卻出任維也納學派《國際統(tǒng)一科學百科全書》的副主編,《邏輯經(jīng)驗主義的形成》就刊于該書1951年版第二卷。這就是說,約根森及其《邏輯經(jīng)驗主義的形成》是維也納學派重要成員撰寫的經(jīng)典著作。
第二,孤證不立。除約根森外,有無證據(jù)表明是否還有維也納學派成員認同這份“先哲錄”?有!我們在艾耶爾編輯的名著《邏輯實證主義》中,再次查到了幾乎同樣的名單,而且艾耶爾還給出了馬克思入選的理由:“馬克思成為維也納學派先哲的理由……在于他對歷史的科學研究”。馬克思作為維也納學派“先哲”不是孤證。
第三,馬克思的“先哲”地位是維也納學派部分學者的“異見”,還是維也納學派的共識?進一步查證發(fā)現(xiàn),這份“先哲錄”源自維也納學派官方宣言《維也納學派的科學世界觀》 (Wissenschaftliche Weltauffassung: Der Wiener Kreis)。這就是說,馬克思作為維也納學派“先哲”,是維也納學派官方認定的。
第四,“先哲”往往并不“在世”。馬克思的“先哲”地位是維也納學派供奉的“祖宗牌位”,還是依然“在場”的活著的“靈魂”?眾所周知,維也納學派內(nèi)部存在著邏輯原子主義與語義整體論、物理主義與“統(tǒng)一科學”之爭,筆者早在30年前就發(fā)現(xiàn),維也納學派的核心成員紐拉特(Otto Neurath)就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整體論立場,被后人稱為“紐拉特的馬克思主義”(Neurath’ Marxism),“對于紐拉特而言,整體性觀念是與人的理性活動密切相關(guān)的,其目的是通過馬克思主義倡導的教育和社會工程來實現(xiàn)社會的有計劃的重組。……尤其令紐拉特印象深刻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提出了一個全面發(fā)展的理想人格”。此外,紐拉特思想的研究者約貝爾(Thomas Uebel)參與撰寫的《在科學和政治之間的紐拉特哲學》 (Otto Neurath,Philosophy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tics)中多次提及“紐拉特的馬克思主義”(Neurath Marxism)。這些文本表明,馬克思的思想?yún)⑴c締造了維也納學派的“分析運動”和“統(tǒng)一科學”運動。在西方分析傳統(tǒng)中,流淌著馬克思的思想血脈,這值得引起中國的哲學學術(shù)界的高度重視,而馬克思思想和維也納學派,都需要被重新審視。
第五,馬克思作為維也納學派“先哲”是否對當代包括后現(xiàn)代科學哲學依然具有激活作用?有,而且很多。在科學哲學的后現(xiàn)代轉(zhuǎn)向過程中,我們隨處可見“馬克思的幽靈”徘徊在科學哲學的“歷史轉(zhuǎn)向”“社會(學)轉(zhuǎn)向”“STS轉(zhuǎn)向”“實踐轉(zhuǎn)向”等各種不同的探索路徑之中。例如,皮克林(A. Pickering)編輯的《作為實踐和文化的科學》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有四次提到“馬克思主義”;西斯蒙多(Sergio Sismondo)編輯的“科學技術(shù)研究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econd Edition)有多次提到“馬克思”及“唯物主義”。這說明,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科學哲學中依然是活的靈魂。令人遺憾的是,這些論題應(yīng)該得到中國學界的高度重視,畢竟“歷史”和“實踐”等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范疇,但是,我們的研究都將之歸結(jié)到“后現(xiàn)代主義”的西方話語,沒有讀出馬克思的“幽靈”在徘徊。
第六,馬克思(主義)作為維也納學派的“先哲”,是分析傳統(tǒng)的“門戶之見”,是否得到了國際學界的認可?在克雷格(Edward Craig)編輯的《勞特利奇哲學百科全書》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第6卷上,赫然刊載的馬克思主義科學哲學(Marx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詞條:“馬克思的科學觀既強調(diào)自然科學及其經(jīng)驗研究,又注重對觀察現(xiàn)象描述的超越,同時強調(diào)社會環(huán)境對科學的影響。”國際著名的《劍橋馬克思指南》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x)中也認為,馬克思與他同時代的孔德、W.惠威爾等人都深受維多利亞時期科學文化的影響,強調(diào)用科學方法研究社會規(guī)律。這些辭書典籍都在國際學界享有崇高學術(shù)地位,沒有明顯的流派意識。因此,這些有關(guān)馬克思主義科學哲學的界定,應(yīng)該代表西方學界的共識。
綜上所述,我們或可說:其一,馬克思(主義)用科學方法研究學術(shù)及社會問題,參與開創(chuàng)了西方分析傳統(tǒng)并得到了國際學界的認可;其二,馬克思主義科學性命題是基于唯物論和實踐觀立場,有別于西方分析傳統(tǒng);其三,西方分析傳統(tǒng)對我們細化和規(guī)范馬克思主義科學性的理解是有幫助的,借鑒和引領(lǐng)包括西方科學哲學在內(nèi)的社會思潮來建立健全馬克思主義學科體系、學術(shù)體系和話語體系,是值得的。
二、維也納學派中的馬克思何以可能:一種索引分析
將馬克思與孔德等并列為維也納學派的先賢是值得質(zhì)疑的。孔德作為實證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被列為維也納學派的先賢符合情理,但有理據(jù)說明,馬克思與孔德及其實證主義是思想上的對手甚或敵人。馬克思在1871年6月12日寫給愛德華·斯賓塞·比斯利的信中說:“我作為一個有黨派的人,是同孔德主義勢不兩立的,而作為一個學者,我對它的評價也很低。”這就需要我們給出理由:維也納學派將馬克思與孔德并稱為先賢,是一種學術(shù)上的“社交語言”,還是有其真實的思想關(guān)聯(lián)。盡管維也納學派“官宣”及其重要成員在不同場合都將馬克思尊為先哲,但依然需要證據(jù)!維也納學派眼中的馬克思究竟何為?馬克思的哪些思想究竟在何種意義上以及何種程度上影響了維也納學派?
無征不信。為了查實馬克思對維也納學派的真實思想關(guān)聯(lián),最穩(wěn)妥的方式就是在維也納學派的經(jīng)典文獻中考證馬克思學說的存在狀況。根據(jù)權(quán)威典籍,本文擬對費格爾(Herbert Feigl)等編撰的《科學哲學經(jīng)典選讀》 (Read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艾耶爾(A. J. Ayer)編撰的《邏輯實證主義》 (Logical Positivism)、施塔德勒(Friedrich Stadler)編撰的《維也納學派:邏輯經(jīng)驗主義的起源、發(fā)展和影響研究》 (The Vienna Circle: Studies in the Origins,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Logical Empiricism)以及約貝爾(Thomas Uebel)等編撰的《勞特利奇邏輯經(jīng)驗主義指南》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ogical Empiricism)等四部維也納學派代表性著述有關(guān)馬克思內(nèi)容進行索引分析。所謂索引分析就是利用權(quán)威著述所列的人名索引和主題索引來核對所提及的人物及其事件。
在費格爾等編撰的《科學哲學經(jīng)典選讀》 中,有“馬克思”詞條的地方在706頁;“辯證法”和“辯證唯物主義”詞條在第9,702,704,701—713等頁。經(jīng)核對,費格爾在其所著的《科學世界觀:自然主義與人文主義》 (The Scientific Outlook: Naturalism and Humanism)一文中,認為“作為蘇聯(lián)官方哲學的辯證唯物主義也在某些英國的科學團體中時興起來”,經(jīng)核對,這里的“英國的科學團體”主要指貝爾納領(lǐng)導的、包括李約瑟、霍爾丹等科學大家,這些科學家深受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黑森命題”的影響。有關(guān)馬克思和唯物辯證法等內(nèi)容主要在胡克(Sidney Hook)撰寫的《社會歷史領(lǐng)域中的辯證法》 (Dialectic in Society and History)之中。胡克在該文中主要討論了如下幾個議題:“辯證法作為周期變化的規(guī)律”(Dialectics as Pendular rhythm),“辯證法作為斗爭”(Dialectic as struggle),“辯證法作為歷史上的相互作用”(Dialectic as historical interaction),“辯證法作為聯(lián)系”(Dialectic as interrelatedness)等。胡克認為:“馬克思所理解的辯證法與科學方法在歷史文化科學中的應(yīng)用并無本質(zhì)區(qū)別。”對此,任何讀過馬克思《資本論》第二版跋的讀者都可以找到這樣的話:馬克思非常贊賞季別爾教授對他的評價:“馬克思的方法是整個英國學派的演繹法”;持這種評價的還有:“莫·布洛克先生……發(fā)現(xiàn)我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這就意味著,維也納學派將馬克思列為先哲,源自辯證法與分析綜合方法的一致性,這與國內(nèi)研究將辯證法與分析綜合方法對立起來的習見形成鮮明對照。
艾耶爾編撰的《邏輯實證主義》提及“馬克思”的有三處,提及“馬克思主義”(Marxism)的有6處,提及“唯物主義”(Materialism)的有兩處。艾耶爾第一次提及馬克思的名字是在他的編者導言第一部分“邏輯實證主義運動的歷史”(history of the logical positivist movement),他列出了近百個邏輯實證主義的先哲,其中包括馬克思,同時此處還提及約根森的實證主義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也指出了維也納學派內(nèi)部對馬克思主義是有爭議的,因為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jīng)驗批判主義”就將馬赫及其俄國的追隨者稱為資產(chǎn)階級的唯心主義。但紐拉特則是馬克思主義的堅定支持者。紐拉特的《社會學與物理主義》 (Sociology and Physicalism)盛贊馬克思主義是當今時代“最有用的社會學”,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確立了物理主義(physicalism)也即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在這里,紐拉特將作為維也納學派思想基石的物理主義等同于唯物主義,而且他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一種“經(jīng)驗社會學”(empirical sociology)。有證據(jù)表明,在艾耶爾編撰的邏輯實證主義中,就包容了一批像紐拉特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不僅將馬克思思想看作是維也納學派的思想來源,而且還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邏輯實證主義的思想基礎(chǔ):物理主義即唯物主義。
2015年,施塔德勒出版了《維也納學派:邏輯經(jīng)驗主義的起源、發(fā)展和影響研究》,這應(yīng)該是當代學者研究維也納學派的代表性著述,該書距維也納學派創(chuàng)立已經(jīng)有近百年的歷史。經(jīng)過一個世紀的沉淀,馬克思依然是常被提及的思想家。施塔德勒在開篇中就指出,維也納學派是世界性的跨學科、跨流派的學術(shù)性組織,其中包括英國經(jīng)驗論、美國實用主義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Austro-Marxist tradition)。施塔德勒還提及弗蘭克(Philipp Frank)曾經(jīng)撰文研究過維也納學派與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新實證主義和奧地利及其捷克的社會民主運動的關(guān)聯(lián)。而所謂奧地利馬克思主義不過是M·阿德勒(Max Aldler)將康德和馬克思進行綜合的結(jié)果。該著大致展示了維也納學派成員與馬克思主義的復雜關(guān)系:第一類如紐拉特,作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致力于將馬克思主義納入分析哲學之中;第二類如弗蘭克,站在馬赫主義的立場上反對列寧對馬赫的批判;第三類如卡爾·波普爾,經(jīng)歷了從馬克思主義到反馬克思主義的轉(zhuǎn)變。其實這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是1933年德國納粹掀起的“反對猶太文化的布爾什維克主義”(Jewish cultural Bolshevism),這場運動列出來一份超過4000多作者的“危險且討厭的著述”,包括馬克思、紐拉特、盧卡奇、霍克海默以及以A·阿德勒(Alfred Aldler)為代表的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但就思想譜系而論,維也納學派是一批深受馬赫主義影響的科學哲學家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共建的產(chǎn)物,如下圖所示。

圖一
約貝爾(Thomas Uebel)等編撰的《勞特利奇邏輯經(jīng)驗主義指南》不是從維也納學派的擁戴者的身份、而是以辭書典籍的編著者的身份來總括到2022年有關(guān)邏輯經(jīng)驗主義的研究狀況。該典索引所列出的“馬克思”詞條在第114、267、269、382頁,“馬克思主義”詞條在第114、266頁。但以關(guān)鍵詞查詢,有關(guān)“Marx”的出處有15次之多。在“維也納學派和馬赫學會”(Ernst Mach Society)的章節(jié)中,提及紐拉特對馬克思的“博士論文”的研究,紐拉特將馬克思與伊比鳩魯聯(lián)系起來,提出了“伊比鳩魯?shù)鸟R克思主義”(Epicurean Marxism)范疇。但該典最重要的思想來自奧尼爾(John O’Neill)撰寫的《紐拉特論政治經(jīng)濟》 (Neurath on political economy)一文,該文認為,法蘭克福學派可能誤解了維也納學派,將其等同于對社會科學的經(jīng)驗主義和科學主義(scientism)態(tài)度。奧尼爾認為,“二戰(zhàn)”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的真實歷史要比流行的觀點復雜得多。“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的核心人物與維也納學派的密切關(guān)聯(lián)超出我們的想象。科爾施與邏輯經(jīng)驗主義者的柏林學派保持密切關(guān)系,布萊希特日記表明其受到紐拉特社會行為主義的影響。”該文的作者奧尼爾還與約貝爾合作發(fā)表了一篇討論霍克海默和紐拉特思想關(guān)聯(lián)的論文。這就是說,維也納學派不僅與馬克思思想有淵源,而且還與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科爾施、霍克海默等具有理論上的承接關(guān)系。
根據(jù)上述文獻及其索引分析,本文或可勾勒一種日漸清晰的歷史軸線:到20世紀50年代,馬克思作為維也納學派的先哲主要是對個別思想家的影響,如紐拉特和弗蘭克等人;到了21世紀,學界漸次發(fā)現(xiàn)維也納學派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如果將這兩種思想傾向加以綜合,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維也納學派與馬克思主義是互相貫通的。
三、馬克思主義與維也納學派的兩點共識與三點界分
馬克思作為維也納學派的“先哲”是有理據(jù)的,但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究竟與維也納學派在學理上有何共識,又如何界分,這才是問題的關(guān)鍵。
馬克思主義與維也納學派主要有兩點共識。“拒斥形而上學”與“統(tǒng)一科學”,理據(jù)有二。
理據(jù)之一:“拒斥形而上學”以及轉(zhuǎn)向“唯物主義經(jīng)驗論”也包括馬克思主義對唯心主義及其烏托邦的批判。我們知道,除了“統(tǒng)一科學”外,“拒斥形而上學”并確立“科學的世界觀”也是維也納學派的重要理論旨趣。一般以為被維也納學派拒斥的形而上學只是傳統(tǒng)哲學中的本體論部分,其實,被維也納學派拒斥的還有“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紐拉特和卡爾納普編撰的《國際統(tǒng)一科學百科全書》特別提及了馬克思主義從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轉(zhuǎn)向科學的社會主義。卡爾納普曾提及,紐拉特認為作為維也納學派基本觀點之一的物理主義就是一種“改進了的、去除形而上學的、在邏輯上無可置疑的唯物主義”,這種唯物主義是“19世紀的機械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的綜合”。卡爾納普認為,紐拉特的觀點極富啟發(fā)意義,但堅持認為黑格爾的辯證法與當代數(shù)理邏輯還是有一定差別的。正如紐拉特所說,“歷史與政治經(jīng)濟學只有變成以唯物主義為基礎(chǔ)的社會學才能成為科學,因為唯物主義才能使一般的命題基于觀察并用于預見具體歷史事件,這些都來自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
理據(jù)之二:“統(tǒng)一科學”包括馬克思主義,也源自馬克思主義。我們知道,“統(tǒng)一科學”和“拒斥形而上學”是維也納學派兩大學術(shù)旨趣。所謂“統(tǒng)一科學”主要是將自然科學方法特別是維也納學派認定的數(shù)理分析方法應(yīng)用到社會學、心理學、倫理學、經(jīng)濟學等人文社會科學之中。在紐拉特和卡爾納普編撰的《國際統(tǒng)一科學百科全書》中,他們認為科學應(yīng)該是“多種要素的組合”,自然科學是如此,社會科學也是如此,“亞當·斯密和大衛(wèi)·李嘉圖揭示了市場體制的某些關(guān)系但并沒有關(guān)注西斯蒙第所說的某些人的財富不足問題;正是在商業(yè)循環(huán)理論方面馬克思主義較之斯密的觀點有更多的理論”。但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統(tǒng)一科學的一部分,“如果說馬赫功在自然科學的協(xié)調(diào)方面,那么馬克思則功在社會科學的統(tǒng)一方面”。R. S.科恩在《辯證唯物主義和卡爾納普的邏輯經(jīng)驗主義》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Carnap’s logical empiricism)一文中提及H.費格爾(Herbert Feigl)有關(guān)“自然主義和人本主義作為邏輯經(jīng)驗主義的準則”(naturalism and humanism should be our maxim)時指出,馬克思早在“巴黎手稿”中就提出了著名命題:“‘共產(chǎn)主義作為完整的自然主義就是人本主義,作為完整的人本主義就是自然主義。’雖然時代不同,但就知識和態(tài)度而言,馬克思和費格爾有兩個基本的共識:他們都希望拋棄社會發(fā)展可能性評估中的烏托邦幻想以及用智識觀點取代超自然主義。不論是馬克思還是費格爾,都是科學的人本主義。”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不僅是“統(tǒng)一科學”的重要思想構(gòu)成,也是它的思想來源。
綜上兩點,在維也納學派發(fā)起的“哲學變革”或分析運動中,就包括馬克思對舊哲學的批判和“自然科學與人的科學的統(tǒng)一”等思想。所謂馬克思被奉為維也納學派先哲以及維也納學派存在馬克思主義,可以得到馬克思著述和維也納學派文本的雙重理證。
雖然馬克思主義與維也納學派在“拒斥形而上學”與“統(tǒng)一科學”上有基本共識,但這并不意味馬克思的批判傳統(tǒng)與維也納學派的分析傳統(tǒng)就是趨同的。二者之間的思想差距也是都有文獻支撐的,都有思想史源流的。
第一個界分:在自然規(guī)律與社會/歷史規(guī)律的問題上,維也納學派成員乃至廣義的實證論者主要是一群具有哲學意向的自然科學家包括數(shù)學和邏輯學家,除了紐拉特等少數(shù)成員外,對人文社會科學并不熟悉,他們大多信奉物理主義,主張將社會科學還原為自然科學,用自然科學的方法或語言來理解人文社會科學,因而看不到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差別,他們對人文社會科學及其規(guī)律的解釋基本上是錯誤的,例如孔德的“三階段論”,羅素對社會主義的矛盾態(tài)度,維也納學派對迫在眉睫的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內(nèi)在矛盾缺乏基本的判斷。與此不同,馬克思在社會歷史領(lǐng)域發(fā)現(xiàn)了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規(guī)律,科學地解釋了資本主義社會產(chǎn)生、發(fā)展和最終將走向消亡的歷史規(guī)律。簡言之,維也納學派在社會科學方法上的貢獻不容低估,但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持有非歷史、非科學的態(tài)度。
第二個界分: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關(guān)系問題上,放眼人類幾千年的文化史特別是學術(shù)史,維也納學派在認識或解釋世界的問題上作出了重大貢獻,解決或改進了一系列重大哲學特別是認識論問題,如石里克認為,由于數(shù)理邏輯和語言分析方法的出現(xiàn),哲學出現(xiàn)了革命性的改變,卡爾納普也提出了“通過邏輯分析清除形而上學”等主張。但與此不同,正如馬克思所說,“以往的一切哲學都在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造世界。”從這個角度看,三代實證主義,從孔德、馬赫到維也納學派,盡管他們在哲學觀上都持有革命的態(tài)度,但沒有證據(jù)表明他們期望對社會現(xiàn)實有所改變,大多主張維系現(xiàn)存資本主義“秩序”;相比之下,馬克思主張,“社會的物質(zhì)生產(chǎn)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xiàn)存生產(chǎn)關(guān)系或財產(chǎn)關(guān)系(這只是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法律用語)發(fā)生矛盾。于是這些關(guān)系便由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形式變成生產(chǎn)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不僅在于科學地認識世界,而且還致力于改造世界。這與專注于解釋世界的維也納學派形成鮮明對照。
第三個界分:在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關(guān)系問題上,維也納學派在“拒斥形而上學”的同時,也將價值判斷置于“拒斥”之列。正如卡爾納普所說:“在形而上學領(lǐng)域里,包括全部價值哲學和規(guī)范理論,邏輯分析得出反面結(jié)論:這個領(lǐng)域里的全部斷言陳述都是無意義的。”由于否定價值判斷的價值,維也納學派陷入了“工具理性”的偏頗。與此不同,馬克思勇于承認并直指科學理論的價值負載,“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里涉及的人,只是經(jīng)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guān)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把經(jīng)濟的社會形態(tài)的發(fā)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guān)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guān)系的產(chǎn)物”。這就意味著,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有必要考察其價值觀或意識形態(tài)的背景或動機。西方馬克思主義如法蘭克福學派發(fā)現(xiàn)了“技術(shù)與科學作為意識形態(tài)”問題,并據(jù)此提出了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界分。
綜上所述,馬克思思想與維也納學派在“拒斥形而上學”和“統(tǒng)一科學”兩個基本點上是有共識的,馬克思被奉為維也納學派的先哲以及分析運動中存在者分析馬克思主義甚或“紅色的科學哲學”都是符合情理的。但是馬克思主義與維也納學派在自然規(guī)律與社會規(guī)律、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以及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問題上,存在差別甚至原則對立。這也是馬克思嚴厲地批判孔德主義、紐拉特與卡爾納普的隔閡、社會批判理論與批判理性主義對峙的思想根由。對于中國的科學哲學研究和馬克思主義研究而言,正確對待馬克思的思想與維也納學派的共識與界分,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四、結(jié)論:未盡的探索
根據(jù)分析及理證,本文或有三點結(jié)論,毋寧說是值得繼續(xù)深究的課題。
第一,馬克思主義與邏輯經(jīng)驗主義的批判、包容或匯通是可能的。由于種種原因,馬克思主義與邏輯經(jīng)驗主義長期處于隔閡狀態(tài),其原因可能有馬克思對孔德及其實證主義的負面評價,有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jīng)驗批判主義”對馬赫主義及其在俄國的追隨者的批判,有卡爾·波普爾對唯物史觀的無理責難,這些評價和批判都是有理據(jù)的。但這些理據(jù)不足以將馬克思主義與邏輯經(jīng)驗主義對立并割裂開來。有足夠的證據(jù)支持這樣的觀點:馬克思主義與分析主義,馬克思的批判理論與維也納學派的分析傳統(tǒng),存在著思想溝通。但這種溝通絕不是簡單的思想和解,而是需要作扎實的文獻及學術(shù)史的考證及其辨析,其中包括:全面地檢索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孔德思想及其實證哲學批判與吸收的第一手文獻及其學術(shù)史據(jù);重新查閱維也納學派歷史檔案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傳記;當代學界對馬克思主義與邏輯經(jīng)驗主義思想關(guān)聯(lián)的跟蹤研究等等。例如,1991年成立的“維也納學派研究會”(Institute Vienna Circle / Vienna Circle Society,簡稱IVC和VCS),其目的就在于整理并開發(fā)維也納學派的文獻和研究,整理出版了系列文集《維也納學派研究會年鑒》 (Vienna Circle Institute Yearbook),已多達30余種,國內(nèi)研究關(guān)注不多,其中南希·卡特賴特(Nancy Cartwright)等人編撰的《居于科學與政治之間的紐拉特哲學》 提及“馬克思”的索引出處就有22處之多;提及“馬克思主義”的就有18處之多。另有證據(jù)表明,維特根斯坦經(jīng)過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斯拉法(Piero Sraffa)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導致了他從邏輯原子主義立場(前期哲學)轉(zhuǎn)向以“生活方式”為核心的日常語言批判(后期哲學)。馬克思主義與邏輯經(jīng)驗主義的批判與交流,批判哲學與分析哲學的包容與匯通,是可能的。這種匯通及和解對這兩種世界級的思想體系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第二,對于馬克思主義研究而言,從馬克思被奉為維也納學派的先哲入手探究馬克思主義與維也納學派及其分析傳統(tǒng)的思想關(guān)聯(lián),至少可以給我們帶來三個理論可能:其一,從空間上將馬克思主義推進到過去不曾涉足的分析哲學領(lǐng)域,擴大馬克思主義運思和踐行的理論空間,將馬克思主義推進到過去由分析哲學把控的問題域和話語空間,同分析哲學一樣,馬克思主義具有同樣的甚至更為高超的分析技術(shù)。其二,重新詮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命題,以往我們在討論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時,都不得不面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性與分析哲學的科學性之間的取舍,似乎馬克思主義有一個不同于分析哲學的科學性,有證據(jù)表明,馬克思主義與邏輯經(jīng)驗主義在科學性本身并無二致,但馬克思主義還強調(diào)科學性與價值性的統(tǒng)一,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統(tǒng)一。其三,西方馬克思主義可能需要重新評估,國內(nèi)有些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往往把西方馬克思主義歸結(jié)為對蘇聯(lián)馬克思主義的反思,研究表明,西方馬克思主義更多地源自維也納學派所發(fā)動的哲學改造運動,有證據(jù)表明盧卡奇、科爾施、葛蘭西、霍克海默等第一批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或多或少都與維也納學派有這樣或那樣的思想關(guān)聯(lián);而且有證據(jù)表明,紐拉特可能是那個時代西方最具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他竟然以唯物辯證法為出發(fā)點撼動了邏輯經(jīng)驗主義的還原論等基本理論主張,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可能不能沒有紐拉特。就國內(nèi)馬克思主義研究而言,馬克思作為維也納學派先哲的史實值得深入研究;有證據(jù)表明西方馬克思主義奠基人盧卡奇、科爾施、葛蘭西等人均深受維特根斯坦和維也納學派的影響;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可能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起點;“紐拉特的馬克思主義”(Neurath’ Marxism)可能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流派。一言以蔽之,維也納學派可能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策源地。
第三,就中國的科學哲學研究研究而言,自20世紀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以來,自然辯證法研究的重點逐漸轉(zhuǎn)向西方科學技術(shù)哲學的流派及動態(tài),似乎馬克思主義與國際上的科學技術(shù)哲學是不可兼容的,這種對西方科技哲學的理解有失偏頗。我國的科技哲學研究者很少關(guān)注美國有一份名為《科學與社會》 (Science & Society)的雜志,這份雜志的主旨就是“一份有關(guān)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及其分析的刊物”。但國內(nèi)研究科學哲學(包括STS或SSK)的人,可能很少知道這份雜志是由美國的維也納學派成員創(chuàng)辦的,其首任主編就是布魯姆伯格(A. Blumberg),他與馬里瑟夫(W. Malisof)和薩莫維爾(J. Somerville)等人被稱之為“科學哲學左派”(lefts philosophy of science)或“紅色的科學哲學家”(red philosopher of science),其中布魯姆伯格又被稱為“哲學家和共產(chǎn)主義者”,他和莫里斯等人將維也納學派的科學哲學思想傳入美國,同時也是美國共產(chǎn)黨的早期領(lǐng)導人之一。這就意味著,維也納學派移入美國后,紐拉特等人的馬克思主義傾向也同時傳入美國,我們所熟知的庫恩、拉卡托斯以及各種后現(xiàn)代科學哲學流派如“實踐轉(zhuǎn)向”和“社會(學)轉(zhuǎn)向”等,都有馬克思主義的“幽靈”。對于中國的科學哲學研究而言,僅僅籠統(tǒng)地知道維也納學派有個邏輯經(jīng)驗主義是遠遠不夠的,邏輯經(jīng)驗主義不只是“對科學語言的邏輯分析”,它還包括將人文社會科學都包容在內(nèi)的“統(tǒng)一科學”甚至包括馬克思主義;將西方科學哲學局限在自然科學認識論是遠遠不夠的,科學哲學可能主要是從科學認識論的維度來探究整個世界。因此,科學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隔閡可能既不符合科學哲學的學科規(guī)制,更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品格。鑒此,中國的科學哲學研究完全有可能基于馬克思主義批判視角研究各種科學技術(shù)問題,以此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對話。
一言以蔽之,馬克思主義與邏輯經(jīng)驗主義,批判傳統(tǒng)與分析傳統(tǒng)之間的批判和包容、界分與匯通都是可能的,構(gòu)建馬克思主義科學哲學的學科體系、學術(shù)體系和話語體系是可能的,從而,用馬克思的話語書寫中國人自己的科學技術(shù)哲學是可 能的。